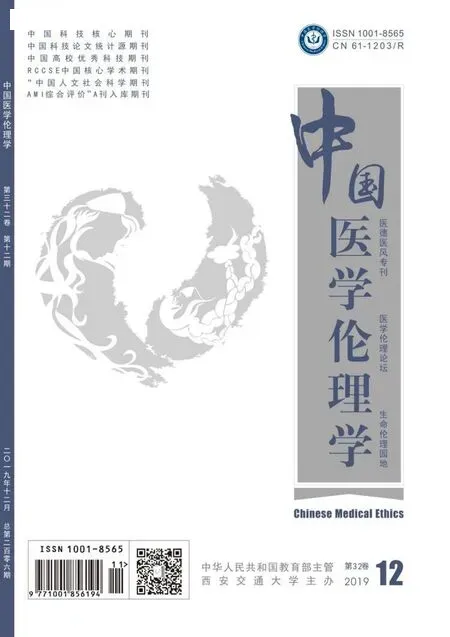脑科学伦理问题和治理探析
李萍萍,马 涛,张 鑫,孙燕荣*
(1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北京 100039,lipp@cncbd.org.cn;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 杭州 310003)
近年来,全球脑科学的重大科技突破不断涌现,随之产生的潜在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也引起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中国正在迎来脑科学领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学习和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积极应对脑科学创新的潜在伦理风险,对促进和保障我国脑科学领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抢抓新一轮全球神经科技竞争主动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脑科学领域前沿交叉技术的突破带来潜在的伦理和社会风险
近年来,认知增强、脑机接口、神经调控、人工智能等脑科学领域前沿交叉技术的不断突破,使得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干预性越来越强,但其在安全性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质疑。
1.1 安全性和公平性风险
在临床治疗领域,神经增强[1-2]等认知增强技术主要用于精神障碍的治疗和衰老症状的缓解。然而这类技术同样可以使得正常人体超出正常认知能力水平,其潜在的安全性和公平性风险引起了广泛关注及争议。一方面,作为一项新兴技术,认知增强对于人体产生的副作用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具有不可控性。例如现有可帮助人们短期内提高注意力的神经增强药物,已被发现可能引起药物依赖及神经紊乱[3];另一方面,认知增强技术有可能取代并超越个人努力,其商业化会使得一部分人群率先获得这项技术带来的技能增长,造成不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4]。
1.2 人格和身份识别
神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定义“人格”与“自我身份”。传统意义上,人类具有独立人格与独立自我。但随着脑成像、神经增强、脑机接口等新型神经技术产生,当人脑活动可被与之对接的外部设施控制并影响,或人脑可操控与之相连的外部设备时,人们不禁质疑,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是否还依然存在[5]。例如,人类能够通过脑机连接或脑机融合技术拓展到外部器械与设备上,而与人类大脑连接或融合的机器将有可能改变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其人格及身份将由人类大脑与和大脑连接或融合的器械共同决定[6]。
1.3 隐私和数据安全
神经活动等脑信息直接反映出个体的思想活动,这对脑成像技术、脑机融合等高新神经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对隐私的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研究常用的数据去隐私化处理方法不足以保证脑科学实验数据的隐私保护,因为脑科学研究数据本身已经自带受试者隐私,例如即时大脑扫描图谱很大程度上能够被用来鉴定主体并揭示主体详细信息[7],包括可能揭示主体的无意识偏见偏爱信息、有关人格特征、精神疾病、性偏好或者药物成瘾的易感性等基本信息。
1.4 双重用途
脑科学和神经技术具有双重效应,其成果将首要用于脑疾病治疗、智力提升等为人类社会造福的医疗及社会用途。但同时,这些成果也几乎必然伴随着其在军事、商业等非医疗领域的应用。英国皇家学会报告[8]指出,以失能为目的的神经药理学和其他相关技术的研究可能会违背人道主义,医学界参与失能武器的开发将严重影响医学伦理的基本前提,化学失能剂可能成为“进攻性、致命性失能”的伪装。目前基于神经调控技术、神经增强技术成果的大规模推广可能带来的风险难以估量,如若被非法利用,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危害[9]。此外,目前迅猛发展的脑成像技术可用于疾病诊断,但也可成为反映人类思想,预测人类行为的工具,被应用于监控、思想探查等方面[10],导致患者隐私泄露、受到伤害。
2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神经伦理研究框架和科技体系
2.1 总体情况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均在2013年前后启动了长周期、高投入强度的脑科学计划,全球总投入经费超过70亿美元[11]。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导致潜在的伦理和社会风险日益凸显,各国纷纷加强对脑科学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促进国家伦理委员会或学术组织参与政府决策,加强对神经伦理研究的支持,倡导建立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框架,促进公众交流和监督,以寻求解决方法。表1列举了全球主要脑科学计划在神经伦理方面的组织架构设置和经费投入,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神经伦理研究框架和科技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举措和经验。

表1 全球主要脑计划神经伦理组织架构设置

续表
2.2 美国
在2013年美国脑计划(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 Technologies, BRAIN)启动阶段,美国总统生命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U.S.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Bioethical Issues,PCSBI)即开始为期两年的与科学家、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团体的交流合作,产生了较好成果[12]。PCSBI于2014和2015年分别发布了两份研究报告:《大脑重要性:综合神经科学、伦理学和社会的方法》(Gray Matters: Integrative Approaches for Neuroscience, Ethics, and Society)和《大脑重要性:神经科学、伦理与社会的交叉话题》(Gray Matters: Topic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Neuroscience, Ethics, and Society),强烈建议将神经伦理学主动纳入所有神经科学研究工作中,用于指导和解决一些由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可能引起的伦理问题。
美国脑计划在其多部门工作组(NIH BRAIN Initiative Multi-Council Working Group)中专门设立了神经伦理学工作组 (Neuroethics Working Group,NEWG),由神经伦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共同组成,就如何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专家意见和建议,并协助确保神经伦理学能够完全融入美国脑计划。
针对美国脑计划的研究人员,NEWG于2018年发布了神经伦理学指导原则(Neuroethics Guiding Principles)[13],以指导脑计划资助的研究可能遇到的神经伦理问题。指导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将安全始终置于首位;能够预见涉及参与者的能力、自主性和代理授权相关的问题;保护神经数据的隐私性和保密性;关注神经科学工具和技术可能的恶意用途;在将神经科学工具和技术应用于医学或非医学用途时需谨慎;发现并解决公众对脑科学研究的特别关注点;鼓励公众普及和交流对话;行为公正,分享神经科学研究进展和成果。
NEWG还通过组织神经科学、神经伦理学、哲学、法律的相关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就脑计划研究的不同领域展开对话讨论。最近的研讨会主要关注人类神经组织研究以及利用新型侵入性和非侵入性神经装置的人体神经科学研究。
2017-2018年,脑计划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用于研究神经技术和脑科学进步的伦理影响,并解决关键的神经伦理学问题。截至2018年底,已有9个项目在脑计划得到资助。项目团队还通过脑计划支持的培训机制和行政手段加强神经伦理学培训,以便将神经伦理学更好地整合到现有脑计划的资助计划中。
2.3 欧盟
欧盟脑计划(The Human Brain Project,HBP)在设立之初就认识到脑科学研究可能引发各种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并将对这些潜在问题的识别、审视和管理作为HBP的首要任务[14]。
HBP由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内提供资金,在实施中执行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管理理念,这也是HBP开展相关伦理和社会问题讨论的基本框架。RRI旨在通过对创新实践进行管理,将科研创新与社会的价值观、需求和期望结合起来,以公共协商讨论等方式确定创新的目标和价值,并依此塑造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方向,提出符合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伦理规范,追求科技成果的绿色化和普惠化,力求使创新更好地造福社会。自2014年欧盟理事会发布《欧洲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罗马宣言》[15]以来,RRI已经在欧盟最高层面制度化,并在欧盟的各类科技创新项目中执行。
HBP具有完善的伦理学组织架构设置。一是设立“伦理与社会”子项目(SP12)(Ethics and Society Subproject),开展伦理、社会和哲学分析。该子项目并非HBP的外部项目,而是其12个核心子项目之一,投入资金约为4800万美元,占欧盟脑计划总预算的4%[11];二是在HBP董事会中邀请伦理专家参与管理和决策;三是在HBP外部设立伦理咨询委员会,确保由HBP各研究项目引起的问题得到公开透明的沟通和处理,并监督HBP研究人员遵守相关伦理准则和法律规范。
2.4 日本
神经伦理问题一直是日本脑科学研究中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MEXT)于2008年启动了脑科学战略研究计划(Strategic Research Program for Brain Sciences, SRPBS),并在其脑机接口项目中设立ELSI研究团队,支持人脑功能研究,并帮助公众参与和理解大脑研究。随后,日本于2011年在SRPBS中建立生物伦理研究组,执行负责任的研究框架(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在2014年启动的日本脑计划(Brain/MINDS)中,主要由SRPBS中的神经伦理学小组为其提供伦理学研究支持,涉及神经伦理研究的经费支持计划将达到3亿美元。
日本脑计划主要关注两类伦理问题[16],一是研究参与者的数据收集问题,在促进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需要特别关注能识别参与研究个体的特殊信息;二是神经科学疾病模型的社会和个人影响,包括神经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对患者的心理影响等问题。
3 我国神经伦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3.1 建设成效
神经伦理学研究自21世纪初由美国科学家提出并兴起[17],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也是当代神经科学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随着我国脑科学与神经技术领域研究的突飞猛进,国际交流不断深入,我国开始越来越重视神经伦理规范的制定和国家治理,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国家层面的规范和原则陆续出台。2019年6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18],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这是我国首次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对世界做出的倡议和承诺。二是科学家对神经伦理的关注越来越高。多位科学家大力呼吁“伦理与科学齐头并进”,并指出“随着中国学术国际地位的上升,为了达成国际共识,中国科学家应积极投入到国际上有关科学伦理的讨论之中”[19]。我国脑科学家近期发表研究论文,首次分析了中国脑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社会伦理问题,并从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特色角度出发提出了应对策略[20]。三是我国开始参与国际神经伦理问题的公众讨论。2018年,由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共同发起的国际神经科技创新研讨会在中国召开[21],汇集了百余位脑科学、伦理、社会学等领域的国内外专家,这是中国首次针对神经伦理及社会问题举办大规模国际专家研讨。
3.2 有待完善之处
目前中国在安全性保障与实验限度等主要问题上的伦理规定与国际规范基本保持一致,然而神经伦理学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科建设不足。中国主要高等院校及主要科研院所在开展脑科学以及相关研究时,几乎没有针对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在教学和培训中也几乎没有进行神经伦理规范的相关教学内容,中国现有的伦理审查机构中罕有专门针对脑科学与神经技术的伦理工作小组。二是专业人才匮乏。目前中国神经伦理学研究多局限于哲学和法学领域,少有神经科学家参与,限制了学科发展。三是科研与伦理研究脱节。中国科研人员对神经科学研究和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考虑尚未与科学技术的研究有效衔接,在早期技术开发和实验设计中缺少伦理方面的考虑。公众普遍缺乏对神经伦理的认识,科学界与公众交流途径匮乏。四是科研受传统文化影响仍较大。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社会公众对神经精神系统疾病患病人群的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重视不足。
4 对策建议
4.1 强化生命伦理研究对科技创新和政府决策的支撑作用
在国家层面,应大力强化生命伦理研究在科技创新和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咨询作用。一是建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对生命科学研究涉及的伦理与社会问题进行审慎的考察和分析,有前瞻性地规范创新工作,支撑政府决策。二是在中国脑科学计划及相关研究中,加强对神经伦理研究的投入。三是根据神经技术的创新进展,调整现行生命伦理准则,研究制定和规范中国脑科学与神经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4.2 加强生命伦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是加强生命伦理研究的学科建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展生命伦理学研究,尤其是神经伦理学相关的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应对生物技术引发的重大生命伦理问题与公众危机;二是注重生命伦理学人才培养,鼓励具有生物技术等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生命伦理学研究领域;三是加强对生物技术、临床医学等领域科学家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将伦理、法律和社会教育纳入神经科学课程、临床和工程的培训。
4.3 促进公众监督与交流
针对涉及重大生命伦理问题的神经科学技术,加强公众监督,促进公共机构、医疗部门、媒体、商业组织和公众之间的透明沟通,通过开展跨学科跨文化的公开对话,建立公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