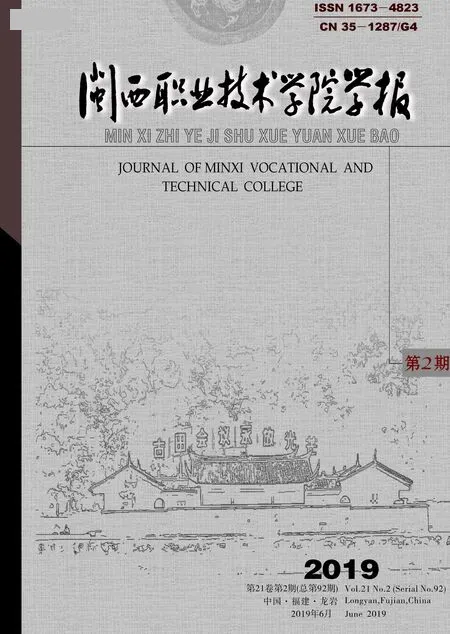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连环套》解读
陈 琪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女性主义批评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之一,它将女性作为研究视角,通过解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揭示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由于女性作家对女性经验有更多直接的体会,对女性所处生存状况有更为深刻的洞见,对性别偏见也更为敏感,所以,女性作家的作品比别的男性作家的作品更易带有女性主义倾向。”[1]张爱玲作为文坛上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在讲述沪港女性爱情与婚姻的同时,表现出对女性生活与命运的思索,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在小说《连环套》中,张爱玲讲述了霓喜三次与人姘居又三次被人抛弃的故事,不仅揭示了霓喜苍凉的命运,也表现出她对女性深层的关怀。
一、缺失的自我意识
“五四”时期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一些女性勇敢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2],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一呐喊显得苍白无力。张爱玲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残酷的揭示:女性缺乏自我意识,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庸。
《连环套》中的霓喜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她将依附于男性视为生存的唯一选择。在绸缎庄,霓喜和雅赫雅之间并无爱情,他们“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3],动不动就拳脚相向,但为了生活霓喜依旧选择和雅赫雅姘居。虽然霓喜知道雅赫雅对她并无真心,也知道雅赫雅和于寡妇厮混,但她依旧渴望雅赫雅发现她“把得家定”,将她扶正。在被雅赫雅赶出家门之后,霓喜甚至想通过带走孩子来展现自己是一个好母亲,以此让雅赫雅回心转意。吝啬的雅赫雅没有给霓喜想要的“一点零花钱与自尊心”[3],但是霓喜从未想过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金钱和自尊。被雅赫雅赶出绸缎庄后,霓喜又毫不犹豫地投向57岁的窦尧芳的怀抱,尽管年事已高的窦尧芳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窦尧芳死后,霓喜虽然已经年过30,但依旧通过勾引外国工程师汤姆生获得暂时的安宁。晚年的霓喜容颜老去,身材走样,无法再吸引男人,但她也没有想过凭借一己之力独自生活。失去了男人的依附,她将生活的筹码压在儿女的身上,坐着“养儿防老、积谷防灾”的美梦,而此时她的儿女还在集中营里等待着年迈母亲的救济。霓喜的一生流走于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将男人作为生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却不知依靠男人获得的只是片刻的宁静,待到她容颜不在,面对的就是被抛弃的命运。
霓喜自我意识的缺失还体现在她对自身价值的错误理解上。在霓喜看来女人唯一的价值就在于身体和美貌,她的身体是“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可以流通的女人的唯一资本”[4],因此她将身体与美貌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她通过与男人调情来维持她的自尊心,因为她知道“在色情的圈子里她是个强者,一出了那个范围,她便是人家脚底下的泥”[3]。在失去身材与美貌后霓喜做的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底气,面对汤姆生的抛弃,霓喜本可以光明正大地大闹一场,但是在汤姆生的办公室,她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身肥肉,“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她在他面前蓦然地萎缩下去”[3],失去了从前那种悍然的美。在这种错误价值观的指引下,霓喜失去自我,成为男性的附庸。
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一是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二是因为男权社会长期的教化。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对霓喜而言,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女佣、女店员等薪酬极低的工作,像雅赫雅那样的绸缎庄店主不会是女性,像窦尧芳那样的药店老板不会是女性,像汤姆生那样的工程师更不会是女性。经济上的不独立导致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法做到独立,因此她们将男性作为自己唯一的依附,希望通过婚姻来获得永久的保障。同时,男权社会的种种教化直接扼杀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着经济大权,由此他们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自古以来男性就以自己的理想来塑造女性,对女性提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要求,并提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将女性的生活空间限制于狭窄的家庭之中,又将“贤妻良母”作为女性的行为准则,一旦女性跳出这个圈子,出现某些叛逆的思想就会被冠以违背伦理道德的罪名。在男性长期的“循循善诱”之下,女性的自我意识消失殆尽,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在男权社会中,她们得不到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二、消失的女性话语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利,女性虽然可以言说,但她们言说的内容必须在男性所规定的言说范围之内,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女性的言说就是无意义的。在小说《连环套》中霓喜几次抗争性的言说都受到男性的忽视和冷遇。霓喜第一次试探雅赫雅时,霓喜的个人言说完全受到了雅赫雅的无视。
霓喜道:“她说我什么荤不荤,素不素的,往后日子长着呢,别说上天见怪,凡人也容不得我。”雅赫雅立在浴盆里,弯腰拧毛巾,笑道:“那便如何是好?”霓喜背着手,垂着头,轻轻将脚去踢他的浴盆,道:“她劝我结婚。”雅赫雅道:“结婚么?同谁结婚呢?”[3]
这段对话中,雅赫雅对霓喜的问题虽然有回答,但并未正面回答。此时的雅赫雅并不想正面得罪霓喜,但也无心与霓喜结婚,面对霓喜的试探,他故意装傻,刻意回避话题,因此霓喜的言说是无意义的言说。有意义的言说建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霓喜作为被雅赫雅买进家的一件“商品”,在经济上她必须依附于雅赫雅,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他们地位也不平等,因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雅赫雅有权让霓喜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霓喜作为从属者必须对雅赫雅言听计从。在雅赫雅面前,霓喜是没有话语权的,因此霓喜的抗争也必然走向失败。
如果说霓喜的言说在雅赫雅那里还获得了一些无意义的回应,那么在窦家人那里,霓喜的言说就更显得苍白无力。窦尧芳死后霓喜先是希望从内侄那里获得一些回应,她指着内侄哭道:“你也是个好良心的!你也不替我说句话!”[3]而此时内侄“如箭穿雁嘴,勾搭鱼鳃,作声不得”[3]。霓喜一番哭闹都没有得到一丝的回应,在她将花瓶砸向窦尧芳后,她高声叫喊道:“清平世界,是哪儿来的强人,平白里霸占我的东西,还打我,还捆我?我是你打得的,捆得的?”[3]然而此时众人七手八脚拆下白绫帐子,与窦尧芳周身洗擦,穿上寿衣,并不理会霓喜[3]。作为窦尧芳名不正言不顺的姨太太,霓喜在窦家人眼里就如同空气一般的存在,窦家人对霓喜直接采用无视的态度,让霓喜的所有言说都丧失意义。
在被雅赫雅和窦家人抛弃后,霓喜还有言说的权利,只是她的言说没有得到相对的回应,但是在汤姆生那里,霓喜甚至连言说的权利都被瓦解。汤姆生在英国娶了名媛,回港后他直接让发利斯告诉霓喜不能去码头迎接他,否则他再也不见霓喜。在办公室,他签下5 000元的支票给霓喜就不再多言,霓喜意欲哭闹,他竟然请秘书将霓喜赶走。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多次揭示女性“失声”的现状。《金锁记》中曹七巧在分家时觉得九老太爷的安排不公平便大吵大闹,但最终“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3]。《封锁》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翠远对家、对学校虽有诸多不满,但依旧选择沉默:她安静地听着宗桢的诸多抱怨,虽有想法,却未曾表露。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着经济权也就掌握着主流的话语权,女性也就不得不走向沉默。自我意识的缺失和话语权的剥夺使女性成为男性豢养在牢笼中沉默的金丝雀,“女人既在男性社会之内,又在其外。表面上她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同时又是被放逐的人”[5]。
三、悲剧化的女性命运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乏必要的自我意识,也没有获得话语权威,她们游离于男权社会之中,成为男性的附庸,这样女性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表现为无爱的婚姻,还表现为女性性格的变异。
《连环套》中霓喜的三段同居生活都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实现爱情的可能。霓喜被养母作为一件商品卖给了雅赫雅,雅赫雅买她“无非是因为家里需要这么个女人,干脆买一个,既省钱,又省麻烦”[3]。雅赫雅与霓喜之间是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在雅赫雅那里,霓喜是商品,是泄欲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被爱的女人。因此,尽管霓喜与雅赫雅共同生活了12年,是他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在霓喜将他惹怒后,他依旧可以狠心地将霓喜踢出家门。57岁的窦尧芳和霓喜之间更谈不上爱,在与窦尧芳姘居的日子里霓喜甚至与崔玉铭偷情。霓喜和汤姆生也只是相互索取的关系,汤姆生在与名媛结婚后便将霓喜抛在一边,连往日受他百般疼爱的女儿屏妮也不管不顾。女人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面对爱情与婚姻就显得被动与无奈,她们将自己的后半身系于一个男人的身上,她们拼尽全力,用尽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只为换取一个合法合理的太太的身份,尽管这个太太的身份并不像旁人眼里那么光彩艳丽。她们将婚姻作为唯一的保障,为了这份无爱的婚姻,她们甘愿忍气吞声,甘愿成为男人手中的金丝雀。
张爱玲在《连环套》中还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变异。霓喜本是一个正常的女性,但在男权社会中,在漫无天际的姘居生活中她变得虚荣、自私、疑忌而悭吝。在戏院听交响乐时,分明是霓喜要走,她却要虚伪对别人说:“我哪儿舍得走呀?偏我这朋友坐不住——也不怪她,不大懂,就难免有点憋得慌。本来,音乐这玩意儿,有几个人是真正懂得的?”[3]她穿了双新鞋,生怕别人不知道似地说:“下回做鞋,不镶这金辫子,怪剌剌的。”[3]她将窦尧芳家里的书信截了下来,“自己看不完全,央人解与她听,又信不过人家”[3]。她悭吝到连烧焦的毛竹筷子都不舍得换,还怀疑老妈子故意将筷子烧焦,这样的悭吝与疑忌令人讨厌。在与汤姆生姘居之后她为了报复,为了在尼姑面前摆阔而重新和她们周旋起来。为了报复雅赫雅,她故意到绸缎庄和店员争吵,“她把往事从头记起,桩桩件件,都要个恩怨分明”[3]。张爱玲说,姘居的女人“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6]。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无法做到独立,她们终日生活在男性的阴霾之下,抑郁的生存环境最终使她们灵魂扭曲。
除了表现女性性别的变异外,张爱玲在《连环套》中还表现女性之间人情冷淡、相互构陷。霓喜和梅腊妮师太表面上相处甚好,甚至还带着些远亲的关系,然而在暗地里二人却相互构陷。梅腊妮告诫雅赫雅不要让霓喜与米耳先生多有接触,怎料被霓喜反咬一口。梅腊妮衔恨于心,在药铺门口看见霓喜与崔玉铭闲聊便毫不犹豫地向雅赫雅告状,最终导致霓喜被扫地出门。霓喜和窦尧芳同居后,觉得旧时的小姐妹身份低,也就断了联系。窦尧芳病重之时,霓喜将金簪藏于小姐妹家,怎料被小姐妹一口否定。被窦家人赶出家门后,霓喜通过在汤姆生家作女佣的干姐姐认识了汤姆生,在与汤姆生交好后,又担心干姐姐会来请赏,竟狠心地让汤姆生辞退了干姐姐。《连环套》中的这群女人相互之间有的只是短暂的利益交往,她们之间的友谊也不过是一朵脆弱的花,看上去美丽,但一触即碎。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不仅讲述一段段女性的悲凉命运,也传达出作为一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隐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缺乏必要的自我意识,因此丧失了把握命运的权力,其结局必将是悲剧的。在小说《连环套》中她通过霓喜悲剧性的命运,揭示了女性命途的悲哀,为广大女性指明了一条出路:女性的命运“不应该取决于男性,无论是在两性世界里还是在女性自己的世界里,女性都应该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反思”[7],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想要占有一席之地,她的身份必然不能是男性的附庸,而要以平等的姿态和男性站立在一起。这份平等的获得既需要建立起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又需要女性树立起绝对的话语权威,为自己发声,让世界听到属于女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