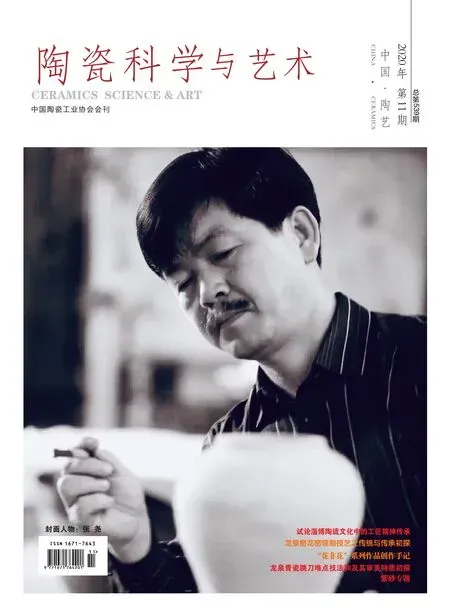画人物,要注重其背景故事
——兼谈我的釉下彩《四美图》
李小琴
中国的人物画,以描绘人物形象和人物活动为主要表现对象,不仅“反映了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风俗等社会意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
中国的人物画作者,由于生活境遇不同,使得他们在关注社会现象时的观察角度有所不同,选择创作的画题有所不同,因此,中国的人物画就形成了多个门类,如以历史故事为画题的“人物故实画”,以仙佛僧道为画题的“道释画”,以妇女生活为画题的“仕女画”,以儿童生活为画题的“婴戏画”,以社会风俗和市井生活为画题的“风俗画”等。然而,不管作者从哪个角度观察社会现象,不管作者选择哪类画题入画,最终都不会违背人物画最重要的两个宗旨——“教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和“写照现实生活”。
中国的人物画作者,常常有自己的艺术主张,常常会探索和选择最适合自己艺术风格的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来进行创作,因此,中国的人物画便有了纯以墨色线描表现的“白描人物画”,造型工整细致、色彩浓艳、略带装饰性的“工笔重彩人物画”,造型简炼、飘逸淡雅、纵意挥写的“减笔写意人物画”。然而,不管作者有怎样的艺术主张,采用怎样的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最终都是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
中国人物画的素材来源广博,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可以从历史资料中提取,可以从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中提取,可以从民间传说中提取……。然而,不管作者选择怎样的素材来源,都会尊重事实,都会确保其真实性;不管作者选择了怎样的描绘对象,都会深入挖掘其社会活动的背景故事,以求准确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神情仪态。
我从事瓷上人物画创作多年,既描绘历史背景中的人物画,也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画。最深刻的感悟是:画人物,其实就是在再现社会活动,就是在讲故事、讲事件。画人物,要悟透人物参与社会活动的背景资料,背景资料挖掘得越深刻,人物才能表现得越深刻,背景故事越生动,人物才能刻画得越生动。若是画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则要准确地反映历史背景,真实地反映历史故事。若是画现实题材的人物画,则要准确地反映当代背景,真实地反映当下故事。
我喜欢读史书,所以我创作了不少“人物故实画”。我曾经在瓷上以釉下彩彩绘工艺创作了以历史人物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为画题的《四美图》,故事情节选择了人们悉知的“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这组作品获得了2018年福建省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四美图》创作之初我是有点纠结的,因为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艺术珍品。然而,我自认为对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之美是有独道见解的,我心里有自己对人物精神的理解,有自己悟得的人物,我相信能创作出有别于他人的画作。
我认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之美,不能限于仪态容貌,而在于其精神:西施之美,在于助王者复国;王昭君之美,在于巩固了民族和睦、边塞安宁,在于为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貂蝉之美,在于助汉室除掉了祸国殃民的逆臣;杨玉环之美,虽无大气,却创造了绝世爱情。
我在进行人物塑造时,选择了最能体现我的个性风格的工(工笔)、写(减笔写意)兼用的表现技法,确立了尊重史料,工写人物神态,简化人物服饰的创作方向。我在构图布局时,设定了独有人物,不置场景,书画相融,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
独有人物,不置场景,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人物的神态。虽然没有根据故事情节设置人物的活动场景,但我从人物的背景故事里提炼出来的人物形象,能让读者一看即可分辩出哪一幅是“西施浣纱”,哪一幅是“昭君出塞”,哪一幅是“貂蝉拜月”,哪一幅是“贵妃醉酒”。
书画相融、图文并茂是中国画最传统的构图方式之一。以题跋醒画,既能丰富画面,平衡构图,也能让读者看懂画里画了什么人物,更能让读者了解人物背后的背景故事和人物精神。清代画家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由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为泛觞。”题跋,能代我向读者讲述画面背后的故事。图文并茂,能使画中人物精神显然。
我的《四美图》能获得金奖,应该是注重了人物精神的再现,应该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且有个性风格。
画人物是我的主创方向。画人物要知人论世,要注重人物活动的背景故事,这样的思想理念,是我从先辈的理论思想和画作中感悟出来的,是我从多年的创作经历中探索出来的。能有这样的思想理念的形成,要感谢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引导我、启迪我,让我深刻认识到人物与社会活动的密切关系,人物画中的人物与背景故事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