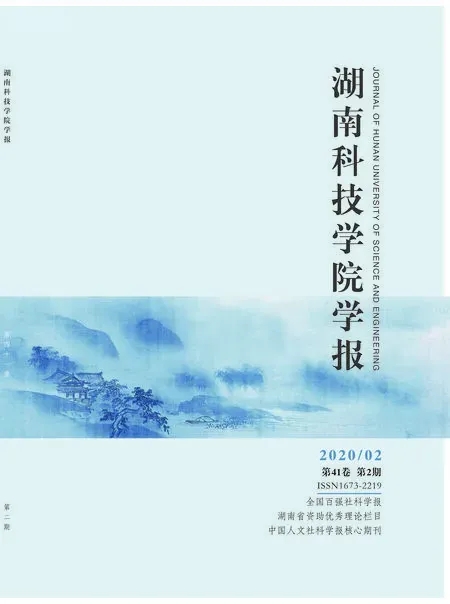以“文”为媒:朱熹评濂溪之学
吕 欣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引 言
周敦颐为后世尊为“道学宗主”,其称誉之传实自朱熹始。朱熹曾和好友吕祖谦共编《近思录》,直取周子与二程兄弟、张载一同并称“四子”,并曾言“《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关于“四子”是指《四书》还是周张二程,为学界有所争论处。依笔者所见,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近思录》首卷难看。……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只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可知,四子若是《四书》,《近思录》这个“阶梯”应比《四书》说的更平铺才对,而《近思录》又“难看”,故朱熹本意不可能是说《近思录》是读《四书》的阶梯。所以“四子”不是指《四书》。所以所引句的朱子弟子陈淳所云“所谓《近思录》者,又《四书》之阶梯也”(《北溪大全集》卷三十《答梁伯翔一》)是其个人理解有误,不能等同于朱子之意。再据明代吴与弼撰《康斋文集》卷四中“关闽濂洛是梯阶,朱子云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加之《近思录》的主体确实是周张二程加上朱熹、吕祖谦选取、设立分章主题次第而编定的,故朱熹所言“四子”当为周张二程四人。
实际上,朱子读书法呈现的读书次第,应先读《四书》,再读《六经》。唐宋变革中的《四书》升格运动,是朱熹的新经典系统提升了《四书》的地位,但不是说朱熹认为《四书》就比《六经》重要,而是比《六经》易读,易入门。然而周张二程之学并不易读,故而朱吕编《近思录》以作亲近四子学问的阶梯,由此才方便去读更不易读的《六经》。由此可见,四子之学在朱熹的学问体系中有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沟通串联着其经典系统,犹如其理学与经学之间的缠绕。然而,四子中,朱熹尤为重视、敬佩濂溪,除作《太极图说解》与《通书注》,还穷尽一生钻研品味及学习着濂溪学风,点点滴滴的文字记录流露着其倾慕与敬重之意。
以文字文本牵线,朱熹努力打造着理学的规模。而濂溪之文则影响着朱熹对“文”之论述的基调。沟通理学与经学,朱熹的“文”论可以从“学文”“为文”的进路去深入理解,朱熹的“学文”论沟通的是经典解释,依附于四书文本本身而发明出朱熹自己的经典系统来;至于朱熹的“为文”论,则直接受到濂溪及二程的影响,表现于朱熹自身的为文实践。故而,朱熹对濂溪之学的评价,也是其自身的“为文”行动,以“文”为媒,便可揭开二者间深沉厚重的跨时空之文脉相承及道统相续。
一 比年潜玩:朱子读濂溪之文的进路
濂溪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周敦颐集》也就薄薄一册。然而朱熹读濂溪之文,可谓终其一生而意犹未尽。在《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1187 年作)中,朱熹有言:
《通书》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独此一篇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既没,而传者鲜焉,其知之者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熹自蚤岁即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顾自始读以至于今,岁月几何,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为注释。虽知凡近,不足以发夫子之精 藴,然创通大义,以俟后之君子,则万一其庶几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后学朱熹谨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以下简称《文集》)
在这段后记中,朱熹表达了自己年少之时便有幸伏读过濂溪之文,但茫然不知其所谓。历来有学者以为朱熹接触濂溪之学是由于求学延平的渊源。虽然,延平有了使朱熹对濂溪“始得闻其说之一二”的作用,但年幼时初碰濂溪之文的切己体会,时年57 岁的朱熹并没有忘记。“学以为己”不假,朱熹比年钻研濂溪之章句文字,而岁月几何仍倾注心力,所幸是作为后学的朱熹体会到了濂溪学的意味妙旨,才能留下这样具有感染力的文字。
由于这是针对《通书》的后记,而又评论曰“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可以看出朱熹将《通书》作为读濂溪之文的法门和关键。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濂溪最具哲学性或理学特质的两篇代表作是《通书》和《太极图说》,朱熹还为这两篇作品作了《通书注》和《太极图说解》。而周敦颐《太极图说》是其对《太极图》的说明,其作的意蕴奠定了宋代易学的风格,图和图说以图和文本的方式均揭示了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易·系辞下》有“物相杂,故曰文”,故而卦爻象还是《太极图》,亦属于“物相杂”的未文字、文本之“文”。《太极图》在朱熹看来“精而约”,但从朱子易学自身出发,关于易图,朱熹亦非推举《太极图》一幅,而对《先天图》亦尤为肯定,伏羲高古早出,大概是朱熹肯定的要因。在《答黄直卿》中:
前书所论《先天》、《太极》二图,久无好况,不暇奉报。《先天》乃伏羲本图,非康节所自作,虽无言语,而所该甚广。凡今《易》中一字一义,无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极》却是濂溪自作,发明《易》中大概纲领意思而已。故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之精而约。盖合下规模不同,而《太极》终在《先天》范围之内,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虑安排也。(《文集》卷四十六)
至于康节濂溪之比较,在《语类》中有抑康节而赞濂溪之语:“康节之学,不似濂溪二程。康节爱说个循环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说得活。如‘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康节无此说。”(《朱子语类》卷七十一,以下简称《语类》)而对于方便理解“精而约”的《太极图》,朱熹曾明确说需要读《通书》才能开始明白:
周子留下《太极图》,若无《通书》,却教人如何晓得?故《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语类》卷九十四)
而《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言:
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文集》卷七十五)
根据朱熹对周敦颐著作编辑整理工作的过程,有学者考证得出朱熹仅根据了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所载而相信《通书》与《太极图》是分开的,故朱熹将二程本附在《通书》之末的《太极图》移置到全书之首,使之脱离《通书》独立成为一种著作,并明确标题为《太极通书》,且删去了附载部分宣称周敦颐思想不利的铭、碣、诗、文。最为重要的是将统一标作《通书》的单一名称改为《太极通书》的合刊名称。[1]然而移《太极图》于篇首的操作,体现了朱熹对《太极图》所凝练的智慧精华是尤为看重的,解释的文本是用来使人明晓的。朱熹亦曾直言《通书》皆是解太极说:
《通书》一部,皆是解太极说。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诚无为, 幾善恶,德”以下,便配着太极阴阳五行,须是子细看。(《语类》卷九十四)
续着“诚无为,幾善恶,德”而来的是太极阴阳五行。故而诚、幾、德是与天地之道是相连相配的。历来对濂溪学的批判和误会多集中于其图其文不接地气,神乎其神,过于“远人”等,然而朱熹用其亦“须有所传授”而说明其学问也不是全然自得于心、腾空出世的孤绝之物。在《语类》中有:
问:“周子之学,是自得于心?还有所传授否?”曰:“也须有所传授。渠是陆诜婿。温公涑水记闻载陆诜事,是个笃实长厚底人。”(《语类》卷九十四)
这也涉及到周敦颐对于“师”的解释。《通书》第七章中有“师为天下善”的论述:
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笃实长厚之师,影响着濂溪所持通达的“中”之体悟,天下大善。这亦是诚、幾、德的表象。人与人的交往之间贵在“感通”,方能发挥性中至善,而实现感通、化成天下,则还须有过濂溪这一番悟。整个过程的描述和宇宙的自然规律相通,这就是“诚无为,幾善恶、德”而来的太极阴阳五行,而文字的结晶便是《太极图说》。“濂溪作《太极图》,发明道化之原。”(《文集》卷四十一)朱熹对《太极图》的研读法,除了读《通书》,还要分次第:
濂溪著《太极图》,某若不分别出许多节次来,如何看得?未知后人果能如此子细去看否。(《语类》卷九十四)
而将次第说的清楚明白、“一一有理、毫发不差”的便是《太极图说》。在《语类》中:
林问:“太极:‘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南轩解与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轩说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极之书》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发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阴阳二端而已。始处是生生之初,终处是已定之理。始有处说生,已定处说死,死则不复变动矣。”(《语类》卷九十四)
朱熹与张栻是好友,但论及太极之说,朱熹则本着其对学问评价公私分明的态度直指“南轩说不然”,而高度肯定《太极图说》。又《文集》卷六十二中《答余国秀》:
始尝推测人之身所以与天地阴阳交际处,而不得其说。既读《太极图说》,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窃谓交际处于此可见。然形化既定,虽不复气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续,如川流之不息,凡饮食呼吸,皆是流通处。此身虽由父母生,而莫非天地阴阳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也欤?(《文集》卷六十二)
《太极图说》使朱熹得见“人之身”与“天地阴阳”的“交际处”。“形交气感,遂以形化”,正是人之于天地间,大化流行于天地阴阳的形象概括。这一番流动于世间万物的交际化育,也是天文地文人文的交汇。
二 非用意而为:濂溪之文的气象
朱熹对濂溪学问的钻研,由上章内容已略得一见。而朱熹更多精彩的评议,则体现在对濂溪“为文”及“文”论态度的认同与进一步延伸中。
(一)“岂用意而为之?”
朱熹对于其时人对濂溪的偏颇评价很在意。在《答汪尚书》中,朱熹表示:
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如《吕氏童蒙训》记其尝著《通书》,而曰用意 髙远。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又何髙下远近之可道哉?近林黄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记文》,极论“濂”字偏旁,以为害道,尤可骇叹。而《通书》之后,次序不伦,载蒲宗孟碣铭全文,为害又甚。(《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
“用意高远”来评濂溪之文,实是知濂溪甚浅。《通书》、《太极图说》之所以能明天理根源、究万物终始,是“用意”而为不了的。那么濂溪是怎样得道而为文呢?在《朱子语类》中,有弟子抓住周子窗前不除草的典故询问:
问:“周子窗前草不除去,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于生物中欲观天理流行处邪?”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会得。须看自家意思与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语类》卷九十六)
天理根源与万物终始,是宇宙的命题。濂溪窗前草不除去,无需强行解释。濂溪为文之气象亦是“自得会得”、自然而发的结果。这也源于濂溪对“幾”之妙的把握。在《答蔡季通》书信中,朱熹肯定了濂溪《通书》中“幾”字的意味:
“以礼为先”之说,又似“识造化”之云,不免倚于一物,未是亲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说得的当,《通书》中数数拈出“ 幾”字,要当如此,瞥地即自然有个省力处,无规矩中却有规矩,未造化时已有造化。然后本隐之显,推见至隐,无处不吻合也。(《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
“以礼为先”,就好比蓄意为文,都不是“亲切工夫”。濂溪的“幾”论看起来不易理解,朱熹在《语类》对此进一步回应:
曰:“ 幾固要得。且于日用处省察,善便存放这里,恶便去而不为,便是自家切己处。古人礼仪,都是自少理会了,只如今人低躬唱喏,自然习惯。……”又曰:“只有《大学》教人致知、格物底,便是就这处理会;到意诚、心正处展开去,自然大。若便要去理会甚造化,先将这心弄得大了,少间都没物事说得满。”(《语类》卷一百二十)
究竟,濂溪之为文的亲切工夫,从“幾”的视角来看,亦是在日用处省察的结果。而幾之工夫在朱熹看来实则与《大学》教人致知格物之工夫贯通,故而到意诚心正便是像张载《正蒙》所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对于自身将理解与《大学》为代表的经典相结合,朱熹自然而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对于伊川这样做,朱熹却留有不以为然的一面:
曰:“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又问:“伊川何因见道?”曰:“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对伊川易学颇有保留,而涉及到伊川学说“求之六经而得”,朱熹将其本溯源回濂溪处,也是侧面再肯定濂溪之灼见。那么关于何以为文,濂溪是怎样与道理“非用意”而配合的呢?
(二)“文辞”之辨与“文以载道”
在《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濂溪言: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对濂溪的文以载道说,朱熹回应:
“文所以载道”,一章之大意。“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言有载道之文而人弗用也。“况虚车乎?”此不载道之文也。自“笃其实”至“行而不远”,是轮辕饰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贤者”至“强之不从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务道德”至“艺而已”,虚车也。(《语类》卷九十四)
关于濂溪的文以载道说,有学者指出是北宋前期古文运动关于文道关系论的理论总结,认为周敦颐“将文学规限到传扬圣人之道的轨道。这种以儒家道德价值规限文学的做法如果走向极端,也会出现轻视、压制文学的弊端,后来的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有此倾向”[2]。观濂溪所言“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通书·陋第三十四》)这并非意味着周敦颐将“文学”限定在了传扬圣人之道上,而是觉得仅将圣人之道归于文辞是浅陋的,因圣人之道是听闻学习之后,存乎于心中,将德行蕴蓄而成,实践为事业。但这不能推出濂溪反对所有文辞。实际上,濂溪的文以载道说,压制的是远离道德,徒修于浮表的文辞,并不是“压制文学”。“文学”早出于《论语》。《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有“四科十哲”章:“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皇侃《论语义疏》引范甯解“文学,谓善先王典文”。而朱熹在《论语或问》中对“文学”的解释为:“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而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之“文”正是道德文章不二分之“文学”,是可以撑起道学体系的“文”。
故而濂溪之文字虽然不多,但种类丰富,且皆非用意而为文,却有着养德而通达之清和、灵韵。比如《爱莲说》、《拙赋》,这均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文章,而是“文学”之作。朱熹曾对此二篇言作过《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及《书濂溪先生拙赋后》。内容如下:
《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
右《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熹得窃闻而伏读之有年矣。属来守南康,郡实先生故治。然 㓂乱之余,访其遗迹,虽壁记文书,一无在者,熹窃惧焉。既与博士弟子立祠于学,又刻先生象、《太极图》于石,《通书》遗文于版。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为赠。乃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庶 幾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淳熙已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谨记。(《文集》卷八十一)
《书濂溪先生拙赋后》:
右濂溪先生所为赋篇,闻之其 曽孙直卿云,近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间,已断裂,然尚可读也。熹惟此邦虽陋,然往几先生尝辱临之,乃辟江东道院之东室,榜以“拙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后之君子,俾无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已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谨记。(《文集》卷八十一)
濂溪之文从有出以来便有刻文,以石刻资料最为具有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朱熹的记录亦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流露着自己极大的兴趣。以《拙赋》为例,除了朱熹所记江东道院之东室榜以“拙斋”刻置,后世清代张铭以榜以“拙榻”刻置于今道县月岩洞中小洞内(周敦颐悟道处)。而“榻”似乎又有着对濂溪来说“情有独钟”的场域作用,养成了其通达之气象与感染力。在《遗事》中有载,“或曰:‘江陵有侯师圣者,初从伊川,未悟,乃策杖访濂溪,濂溪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伊川亦讶其不凡,曰:‘非从濓溪来耶?’”(《伊洛渊源录》卷十二)伊川对其老师濂溪的敬佩之情实际上很深刻,只是因其学问走向与濂溪有所差异而历来被人忽略。比如《伊洛渊源录》收录了邵伯温《易学辨惑》中的一段记录:
伊川同朱光庭公 掞访先君,先君留之饮酒,因以论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处?”先君为极论天地万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叹曰:“平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伊洛渊源录》卷一)
饮酒而叹“平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的伊川,和惯例被认为刻板严格的小程子有一定反差,这样的师承关系注定为道统续命着,感染到了朱熹,被朱熹编到了《伊洛渊源录》里。这些有趣的记录,不由令人对相传“远人”的濂溪形象多了许些亲切感。而濂溪以来得其传的记录、石刻等内容亦属“载道之文”的范畴,承续着濂溪千年来的道者气象。
关于更多朱熹对濂溪之道者气象的引述及评价,先看《文集》卷九十七中,《延平李公先生行状》介绍了李侗对濂溪并不褒义的评价:
尝以黄太史之称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云者,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而朱熹和其师李侗对周敦颐评价并不相似,朱熹评濂溪之学也并非自师而来,相反独居卓见。对于濂溪的气象,朱熹直言:
濂溪清和。孔经甫祭其文曰:“公年壮盛,玉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皆倾。”墓碑亦谓其“精密严恕”,气象可想矣。(《语类》卷九十三)
“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惟程太中独知之。这老子所见如此,宜其生两程子也。只一时程氏,类多好人。”……窦问:“韩公一家气象如何?”曰:“韩公天资高,但学识浅,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纲皆正。”(《语类》卷九十三)
相较濂溪,朱熹对韩愈的评价就相当保留了,这也导向朱熹对“作文”的进一步看法。
三 塑造“道学宗主”:朱熹的别样“为文”
(一)“作文害道否”
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之所论影响链之大,在后世理学家身上表现了出来,并且精彩纷呈。如伊川有言: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佗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 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藴,自成文耳”,正是濂溪非用意而为文之路径。朱熹十分重视伊川这段话,将之类编于《近思录》中而影响到后世更多学人的讨论。自己也接续此意而有言:
大抵今之学者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使心不宁静,不暇深究义理,故于古今之学、义利之间,不复能察其界限分别之际,而无以知其轻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诵数虽博、文词虽工,而抵以重为此心之害。要须反此,然后可以议为学之方耳。(《文集》卷五十八)
在朱熹的语境中,为学之方也即读书法之切入,而学什么?正是“学文”。朱熹的“学文”论出于《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在自身学问养成中变换次序,进而中和“文行忠信”的次序将“学文”的对象无意识地过渡到学习经典,指向其经典系统的建构。“学文”是读经典之文,那么在《近思录》中体现“为学之道”的精彩选段是出自伊川的《颜子所好何学论》:
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
而《近思录》收录此条的上一条便是濂溪“圣人之道彼以文辞而已”句,这样顺承下来,正是朱熹给读者呈现的对“文”的正式方式及如何为学才能通往圣人之道。濂溪与伊川的文字则是榜样。濂溪有云“学者当寻孔、颜乐处”,此说影响着伊川。而江永集注则介绍:“《好学论》是程子十八岁时,已做得这文好,这个说话便是为学之本。”再一条《近思录》收伊川《答朱长文书》言:“后人之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张伯行集解云“后之人不知求道,当其始执卷读书,便以作文章为头一著事……不切于人心,不关乎世道……徒烦人耳目,愈多愈可厌”,如此作文,则贻害无穷。正如时下高校在读博士生被迫要求刊发核心期刊而敦促其在博士钻研期间另行作文以求发表,岂不祸患!进而朱熹对“文”的性质曾做过界定:“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治世之文,必与道具。
(二)文道并重
从“学文”到“为文”,是朱熹“文”论的主调与实践。“学文”到“为文”的理想状态是一种“发而皆中节”的过程。而“为文”最理想的状态是自然而成,也即濂溪式非用意而为。而“经典之文”在所“思”处之工夫论,便是圣人之道(或“先王之道”“孔子之道”),在今之为学者视角里,便是为学之道。此“道”与“文”之关系,才是朱熹的文道观之真正精髓。故朱熹曰: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 喫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再有《语类》中著名的一句,与濂溪“文所以载道也”论调一致: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本与末、根本与枝叶等比附,不代表朱熹轻视“文”。钱穆主张朱熹具备“文道并重”的思想,在《朱子新学案》“惟朱子文道并重”部分引述了朱熹《读唐志》的原文:
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着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 揜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
钱穆加以延伸这里的“文”,“此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3]。朱熹所论之“文”,并非现代观念中的文学的定义,也不是无所不包。而是分类之后,对“治世之文”有着呼吁,如此才能实现“文道并重”。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学者接受西洋“文艺复兴”、“文学自觉”,从而对“文以载道”提出质疑。但以我国传统而言,不仅文以载道,任何事物均须载道,不载道即无以成立。故道器不离,道与文不离。[4]亦是从这一角度而言开来。
(三)类编与塑造:另一种为文
在《孟子·告子上》“性无善无不善”章的讨论,朱熹也强调了濂溪的天资之高学养之深乃后世难以企及。《语类》有记:“自濂溪太极言阴阳、五行有不齐处,二程因其说推出气质之性来。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语类》卷五十九)
朱熹塑造四子及“道学宗主”周敦颐的最直接办法必然是“为文”。伽达默尔(H.-G.Gadamer)曾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5]这也同样生效于宋代道学谱系的传承,或者说“载道之文”的承续。没有为文再生的过程,也即再诠释再言说,从而留成凝固文字的努力,古人心灵的生命力就无法一直存活着。所以学者亦要“为文”,非刻意,但是在运用为学之道后,与圣贤之心产生交汇碰撞,进而用文字记录下来旨意与思索,这是可取的。而朱熹编定《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的行为,实则亦是“为文”,亦是将与先贤神交的心得体会,借助先贤原文,通过自行组合,而编纂成符合自己理解与心意的文本。而朱熹的这种类编的智慧,也为濂溪之文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着实地助了力。
余 论
淳熙八年(1181)闰三月二十七日,朱熹离去南康职,于四月六日抵江州拜谒濂溪先生像。其时,周敦颐曾孙周正卿、周彦卿设席于光风霁月亭,朱熹于此亲撰了《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以记其事:
淳熙八年,岁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后学朱熹、张 掦卿、王沅、周颐、林用中、陈祖永、许子春、王翰、余隅、陈士直、张彦先、黄干,敬再拜于濂溪先生书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所以建端垂绪,启佑于我后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叹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复出所诵说先生《太极图》,赞其义以晓众,咸曰休哉!《文集》卷八十四《书濂溪光风霁月亭》)
《语类》中有“杂记言行”专门收录了朱子门人对朱子日杂生活点滴的记录。其中有一条: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 褖,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它官相见,易窄衫而出。(《语类》卷一百七)
上举两条记录,体现了朱熹对濂溪其人其学的无比倾慕。颂其文可知其人,以“文”为媒,我们观察到了濂溪到朱熹这条文脉之线上,理学家的学问深情。“文明”二字出自《礼记·乐记》之言“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中国古人讲“文”,有“天文”、“地文”、“人文”。日月星辰是“天文”;高山流水是“地文”;人伦礼乐是“人文”。何谓“情深而文明”?钱穆说:“文是条理,是花样,是色彩。若使其条理很清晰,花样色彩很鲜明、很光亮,这就是‘明’了。一男一女配成夫妇,倘使这对夫妇相互间的情不深,马马虎虎,那对夫妇便像灰色的,甚至是黑暗的。所以说情不深便文不明。若使这对夫妇的爱情深了,夫显得更像夫,妻显得更像妻,那就是‘情深而文明’了。我觉得在中国古人观念里,这‘文明’二字,也是很有意义的。”[6]何止于夫妻,学脉相承,道统相续,正因“情深而文明”,而使得中华文明从古至今,并面向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