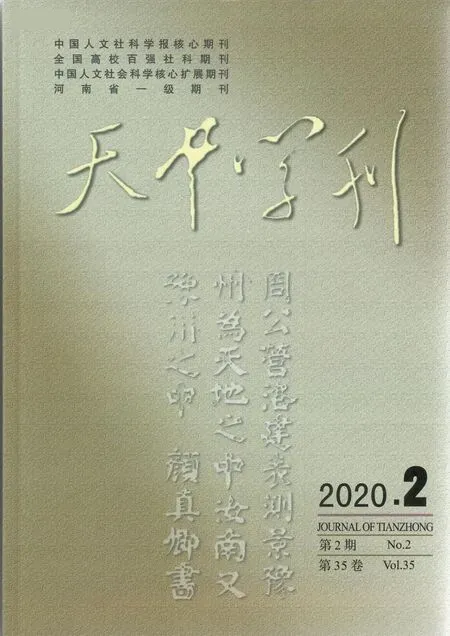从《搜神后记》看陶渊明的愤世思想
王前程,祁琳琳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搜神后记》又称《续搜神记》,亦称《搜神录》,梁朝僧人慧皎在《高僧传·序录》中最早认定其作者为陶渊明:“宋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阙。”[1]慧皎距离陶渊明的时代不过七八十年,是当时人说近事,其说法较为可信,故而唐人魏征《隋书·经籍志》便直接题写云:“《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2]但自明代以来多有学者否定陶渊明的著作权,其基本理由有二:一是陶渊明不信神仙鬼怪,也不崇信佛教,这样超脱放达的人怎么会拳拳于鬼神之事呢?二是陶渊明死于刘宋元嘉四年(427年),而《搜神后记》里居然出现了“元嘉十四年”等字样。第一个理由很难成立,因为思想信仰与文学创作内容没有绝对关联,不信神鬼佛教的人与不写神鬼佛徒故事是不能画等号的。何况陶渊明在其诗文里提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小说作品,足见他喜欢阅读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而陶渊明的挚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亦说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说明陶渊明有猎奇心理,因而其创作《搜神后记》的可能性极大。至于《搜神后记》中出现“元嘉十四年”等字样,那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原本已经不存,元明学者在搜集整理时以后人口吻增改字句叙述故事甚至杂入后世作品,出现“宋时有一人”“宋时有诸生”“宋元嘉初”“宋元嘉十四年”之类语句的作品共计8篇,均非陶渊明口吻。笔者认为,小说作品在中国古代地位不高,不像诗文那样受推重,后世随意增改前人文句的现象极为普遍,但不能因为杂有后世痕迹就轻易怀疑前人创作小说的真实性。
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逍遥派,老庄不是,陶渊明也不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离弃现世,始终没有忘却烦恼的世事。真正逍遥世外、对世事无动于衷的高士,后人不会知晓他们的姓名。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曾作《归去来兮辞》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下决心要同现世断绝交往,是因为现世与之“相违”,足见陶渊明是怀着强烈的愤世情绪而归隐田园的。这种强烈的愤恨现世的思想情绪在其志怪小说《搜神后记》里表现得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记述乱世凋敝惨象,同情百姓不幸命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年代,天下纷乱不堪,人民惨遭杀戮,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晋书·食货志》记述了西晋政局之动荡与经济之凋敝:“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3]513《晋书·刘琨传》载刘琨上表慨叹百姓流离失所:“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3]1112《晋书·帝纪第六》亦载东晋初年之丧乱:“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3]105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许多乱世惨象实为耳闻目睹之事,其心中的悲怆与愤慨不言而喻。干宝《搜神记序》云:“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4]干宝宣称自己写《搜神记》记载奇闻逸事的根本目的是娱乐人心,所谓“游心寓目”,就是赏心悦目、心中喜乐的意思。其实,魏晋文人写小说虽有游心寓目的一面,但更有刺人讽世的一面,干宝《搜神记》中许多故事乃是有感于现实而发,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同样如此。
《搜神后记》主要讲说近人近事,虽然其中以战争丧乱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多,但不少篇目客观记述了乱世烧杀劫掠的悲惨景象。卷二《吴舍人》写道:“蜀贼纵暴,焚烧邑屋。发掘坟垅,民人迸窜,猛(孝子吴猛——笔者注)在墓侧,号恸不去。”①卷三《蜜蜂螫贼》写道:“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卷五《木像弯弓》写道:“孙恩作逆时,吴兴纷乱,一男子忽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卷八《髑髅百头》写道:“晋永嘉五年,张荣为高平戍逻主。时曹嶷贼寇离乱,人民皆坞垒自保固。见山中火起,飞埃绝焰十余丈,树颠火焱,响动山谷。又闻人马铠甲声,谓嶷贼上,人皆惶恐。”《吴舍人》写西晋初年发生在蜀地(今四川一带)的乱象,《髑髅百头》写西晋末年发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市)一带的乱象,《木像弯弓》写东晋末年发生在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一带的乱象,《蜜蜂螫贼》写刘宋初年发生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市)一带的乱象,时间跨度一百余年,地域涵盖东西南北。百年乱世,贼寇纵暴,烧杀抢掠,无论官府、民舍、寺庙乃至死人坟墓均难逃劫难。虽然在作者笔下,这类横行无忌、作恶多端的贼寇大多遭到惩罚:或被神灵射杀,或被蜜蜂噬螫,或遭天火烧灭,但他们给广大无辜百姓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面对贼寇纵暴烧杀,百姓无不惊悚惶恐,被迫迸窜荒野,流离失所,性命朝不保夕。
中国古代社会尊崇先祖,重丧葬,祭祖坟,掘毁先人坟墓历来被视为大不敬的不轨行为。然而,掘坟毁墓却是乱世极为突出的乱象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掘坟毁墓高峰,正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丑恶现象在魏晋小说作品中有相当集中的反映,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亦不例外。除了《吴舍人》记述蜀贼“发掘坟垅”及吴猛号恸守护父母坟墓,《鲁子敬墓》《承俭》《上虞人》等篇目则是专写掘坟毁墓故事的小说。《史记·货殖列传》曰:“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5]司马迁将“掘冢”视为作奸犯科的不法行径之一,认为其基本目的是图谋钱财。但《搜神后记》所写掘冢故事较为复杂。《吴舍人》记蜀贼“发掘坟垅”,是为了“财用”。《承俭》写东莞人承俭死后十年,托梦本县县令,告诉他有盗墓贼挖掘其坟墓,县令即刻带领百人“驰马往冢上”,果然“闻冢中讻讻破棺声”,最终捉得盗墓贼五人。此盗墓贼亦为钱财而来。但《鲁子敬墓》写京口王伯阳将宅东“大冢”即鲁肃墓掘毁以葬亡妻(其妻为东晋重臣郗鉴侄女),结果鲁肃阴魂带领数百侍从直奔王伯阳的厅堂上,怒云:“我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故毁坏吾冢?”说罢令左右“以刀环击之数百而去”,王伯阳“登时绝死,良久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寻便死”。这个掘冢毁坟故事很难说是为了钱财,它更多地反映了乱世之人毫无敬畏心理,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或一时之需而胡作妄为的乱象。《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四《葬送二》曾引《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6]郝昭是魏国名将,为了解决战争器械问题而多次发冢取木,被他发掘的墓主多半是有地位者或富贵者。王伯阳是东晋重臣亲族,为了夺占风水墓地而不惜掘毁吴国名臣鲁肃之冢。二者性质有类似之处,即掘墓者都不是贫穷者,他们掘墓不是为了盗取钱财,这充分说明了掘墓平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不分贫富、不分官民、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
像鲁肃这类名臣显宦的坟墓都不能幸免,普通百姓人家的坟墓被毁便更是平常。小说《上虞人》形象地反映了普通人墓葬被毁坏和尸骨被遗弃的不幸遭遇:
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时在丹徒,忽梦见一人,自说己是上虞人,死亡,浮丧漂流江中,明日当至。“君有济物之仁,岂能见移?著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殷明日与诸人共江上看,果见一棺,逐水流下,飘飘至殷坐处。令人牵取,题如所梦。即移著冈上,酹以酒饭。是夕,又梦此人来谢恩。
作品以虚幻的形式写了一个尸骨漂流、灵魂不安的悲剧,虽未直接点明掘坟毁墓所为,但作者将此篇置于《鲁子敬墓》《承俭》之下,使读者不难推想:死者为普通百姓,坟墓被发掘,棺木被移出,除了累累白骨而一无所有,于是棺木尸骨被掘墓者丢弃,最终被风雨冲至江中漂流而下,以致亡灵不安而托梦殷仲堪,求其安葬尸骨。这其实是一个尸骨露野、游魂不归的沉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乱世人民的不幸遭遇。
古人很早就产生了鬼魂观念,认为人死之后化成鬼依旧游走人间。《搜神后记》共计117篇小说中,写鬼故事的作品有近50篇。尽管这类鬼故事主题比较复杂,作者的态度也存在差异,但其鬼形象绝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特征:不可怕,不复杂,通人情,近人性。卷六《异物如鸟》写鬼与人相视而笑,《上虞人》写鬼夜来谢恩人,《腹中鬼》写腹中鬼被草药毒杀,《韩冢人》写鬼被人吓跑,《四人捉马》写四个鬼被聪明人利用,《白布裤鬼》写鬼对人搞恶作剧,《鬼设网》写笨鬼设网捉人反被小儿捉住,等等。这些鬼形象与人间普通人十分相似,小说中的人见了鬼也绝少感到他们狰狞可怖。还有许多鬼形象令人感到可爱、可亲,其不幸死亡令人同情和哀伤。《懊恼歌》写诸暨县西山下一鬼常穿赭布裤褶,在草丛中漫步,唱着《懊恼歌》。《懊恼歌》是流行于晋宋时期的民间歌曲,抒写男女爱情受到挫折的苦恼之情。这个鬼多半是在人间因失恋而死亡,其遭遇令人感伤。《陈阿登》写会稽句章人暮至东野投宿路旁小屋,小屋少女夜弹箜篌,句章人问其姓名,少女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绥复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显得高雅而有诗才,作品结尾才点明少女“近亡,葬于郭外”,原来是个女鬼,这一女鬼形象其实与人间的美丽才女似乎并无区别。《张姑子》写诸暨人吴详日暮投宿山中,遇一少女热情接待,“二情相恋,女以紫手巾赠详,详以布手巾报之”。但第二天再寻少女家时,“但有一冢尔”。卷五中《临贺太守》写义兴人周氏日暮赶路,见一位“姿容端正”的少女从道边小屋出来主动邀他寄宿,并得知其名叫“阿香”。但第二天上马前行时,“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鬼,无异于人间情意绵绵、可亲可爱的青年男女形象,只是以坟冢鬼魂作结,流露出了十分浓烈的哀婉情调。
鬼魂故事的产生,与人类死亡密不可分。《搜神后记》大量描写坟冢鬼魂故事,实为乱世人民悲剧的曲折反映。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经济凋敝,人口锐减,荒冢新坟林立,骷髅白骨遍地。正如曹操《蒿里行》所悲叹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7]陶渊明笔下坟冢累累、尸骨漂流、鬼魂歌泣的场景,正是乱世凋敝毁败、人民大量死亡悲剧的真实写照,充分表现了陶渊明对于黑暗现实的愤恨以及对于人民不幸遭遇的悲悯之情。
二、讥刺见利忘义之徒,痛恨图谋不轨奸雄
毋庸置疑,仁、义、忠、信、俭等传统美德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道德体系遭到了严重冲击,以致世道人心险恶,社会私欲膨胀,见利忘义的不法之徒比比皆是。陶渊明《搜神后记》生动地展现了道德沦亡、利欲熏心的乱世风貌。如卷四《陈良》写北地人陈良与同郡李焉合伙做生意,因“大得利”而李焉“杀良取物”。卷九《乌龙》写会稽句章张然之妻不守妇道,在家与奴仆私通,更不念夫妻恩情,在张然回家后主动与奴仆合谋设局,“欲得杀然”。卷九《杨生狗》写一路人碰见掉落深井的杨生,杨生呼救,路人因为杨生不愿以爱犬相送而拒绝救援。世俗民风如此,官场更是黑暗,许多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贪钱敛财,如卷四《李除》写襄阳李除死后不断气,至三更时分,“崛然起坐,搏妇臂上金钏甚遽”。原来阴司官吏作弊枉法,向死者索取财物,李除答应送金钏与吏以求放还阳间。这无疑是对现世官吏敛财索贿行为的讥刺。卷六《朱弼》则直接描写现世官员假借死人之名谋取私利:“会稽朱弼为王国郎中令,营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谢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书多张功费,长百余万,以其赃诬弼,而实自入。子木夜寝,忽闻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顷而到子木堂前,谓之曰:‘卿以枯骨腐肉专可得诬,当以某日夜更典对证!’言终,忽然不见。”由此不难想象,现世多少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套取国家钱财而中饱私囊。
与人间见利忘义之徒、贪腐索贿之败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野蛮无知的卑贱动物,它们往往显得心地淳厚、仁爱善良、有情有义。张然家犬乌龙和杨生狗都是在主人性命危在旦夕之时,不惧危险而舍身救主,不仅表现了犬类的灵性,更显现了犬类的忠诚、勇敢与情义。卷五《白水素女》写少年谢端少丧父母,孤苦伶仃度日,谢端至十七八岁时,“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来捡得一大螺,带回家中贮藏瓮中。大螺化一少女,每天为谢端烧火做饭,解决其后顾之忧。卷十《放龟》写邾城一军士在市场上买回一只白色小龟,长大后将其放归江中。过了几年邾城遭兵难,军士仓皇投江逃亡,许多人被淹死,而军士“既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水裁至腰。须臾,游出,中流视之,乃是先所放白龟”。作者以动物助人为乐、知恩图报的行为来反衬人间势利之徒的冷血无情。
在描写动物故事的小说中,卷七《毛人》和卷九《熊穴》是颇具深意的两篇作品。《毛人》写一丈有余、浑身长毛的毛人(类似后世传说中的野人)遇见入山采茶的秦精,不但不危害他,反而将他带到野茶丛生之处,又从怀中拿出二十枚“甘美异常”的野橘送给秦精,使秦精既诧异而又喜悦。《熊穴》写一位猎人在山中堕入极深的洞穴,见里面有几头幼熊,猎人自知大熊来“必以害己”。然而采果喂食幼熊的熊母回来,“分与诸子”之后,又分出一份野果给猎人吃。不知过去了多少天,猎人因熊母分食而存活下来,一直到幼熊长大后,“其母一一负之而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于是跃出”。毛人帮人想得周全,而熊母救人救得彻底,它们跋涉在深山荒野之中,过着简陋、艰辛而自然的生活,却表现了荒蛮世界的温情脉脉,使读者读之深感人不如动物、美德不在人间而荒蛮世界有仁义。很显然,这类小说蕴含了陶渊明深刻的愤世思想,流露了陶渊明对于风俗不纯、人心不古、少仁寡义的现世社会的强烈反感。
天下残破不堪,国运艰难,生灵涂炭,乃至世风浇薄,道德沦丧,这一切根源何在呢?这当然与争战不息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正如刘宋文臣孔琳之所说:“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8]1029孔琳之述及的晋宋之交战乱不息、饥荒连年的悲惨现状,正是陶渊明所熟知和亲历的历史。陶渊明讨厌现世频发战争,更痛恨那些图谋不轨、轻启战端的野心家和当权者。《搜神后记》中许多小说的讽刺性和批判性是很鲜明的,如卷七《平阳陨肉》写刘聪宫廷中发生怪异现象:宫廷崇明观在地震中凹陷为池,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尝有哭声,昼夜不止。数日,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各害人而走”。不久,刘氏死亡,哭声消失。卷八《二人著乌衣》写广州刺史王机入厕时遇见两个乌衣人,与王机搏斗,王机擒获他们,结果他们却化为“乌鸭”样的鸟类。不久,王机被朝廷诛杀。卷八《诸葛长民》写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在梦中同长有蛇头、黑身、黑毛、巨手、大臂的怪物相斗,“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不久伏法被诛。卷八《人头堕》写王绥家中屋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沱”,不久后“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卷九《张平家狗》写并州刺史张平养有一狗,忽然有一天狗爬到厅事屋上行走,张平“未经年,果为鲜卑所逐,败走,降苻坚,未几便死”。
这类小说在写作上有两大特征:第一,所写主要人物都是近世和当代私欲膨胀、品格卑劣的野心家或野心家之子孙。刘聪为西晋末年后赵君主,发起灭亡西晋之战,俘、杀西晋怀帝、愍帝,屠戮无数百姓,是个罪恶累累的战争罪犯。王机在东晋初期曾任广州刺史,后与杜弘等人起兵叛晋,兵败被诛。诸葛长民在东晋末年曾任青州刺史、豫州刺史等,后图谋不轨,事泄被杀。王绥是东晋末年前将军王愉之子,王愉曾图谋作乱,祸及子孙。张平为东晋时人,曾为“贼帅”,独霸一方,自封并州刺史,后归晋又降前秦苻坚,是个无忠无孝的反复小人。第二,恶人及其家族不得善终,死前常有凶兆。地震、赤龙、异蛇、怪兽是刘聪家族败落前的凶兆,怪物相斗、夜眠跳踉是诸葛长民伏诛前的凶兆,人头落地是王愉家族灭族前的凶兆,“乌鸭”扑人是王机败亡的凶兆,狗的异常行为亦预兆了张平的横死。很显然,陶渊明以此警告那些不忠不孝之人,狼子野心不可有,图谋不轨、轻启战端者绝不会有好结果,这分明寄寓了陶渊明警示后人、垂戒来世的思想。
陶渊明这种警戒野心家的创作用意,在描写东晋权臣桓温父子故事的几篇小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如卷三《流星堕瓮》写桓玄出生异象:“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其中妓女阿马在铜瓮中取水饮之,一个流星正入瓢中,“俄而怀桓玄”。桓宣武,即大司马桓温,桓玄之父。小说对晋末犯上作乱者桓玄进行了嘲讽,说他其实是妓女生的儿子。小说结尾云:“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这里用正话反说的方式告诫那些图谋篡位者:桓玄虽然享受了数年荣华富贵,但因篡位而不得善终。卷五《灵见》写桓温拜简文皇帝陵,简文帝灵魂对桓温说了什么话,众人“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过后不久,“遂遇疾,未几而薨”。作者意在告诫后世当权者:功高才异如桓温者有几人?桓温产生野心异志,尚且受到先帝英灵的严厉警告,终致忧闷而死,何况碌碌平庸者呢!卷二《比邱尼》警戒意图更加明显: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讽刺、戒惧狼子野心家之所以成为陶渊明《搜神后记》的重要内容,乃是魏晋严峻的政治现实所致。自从魏文帝曹丕逼汉献帝开启禅让制之后,试图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大有人在,先是司马懿擅权,继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位,西晋建立。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死,晋惠帝继位之初,王室开始争权夺利,内部发生“八王之乱”,进行了长达十六年的大混战。诸王的军队到处烧杀劫掠,屠戮人民。之后,刘渊、刘聪、石勒等“胡人”将佐亦叛晋,西晋很快灭亡。东晋初元帝永昌年间(322―324年),大将军王敦起兵叛乱。成帝咸和二年至四年(327―329年),又发生历阳内史苏峻叛乱。晋穆帝至简文帝时(345―372年),大司马桓温专擅朝政,野心勃勃。晋安帝隆安二年至兴元三年(398―404年),荆、江二州刺史桓温之子桓玄起兵叛晋,建立桓楚政权。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宋公刘裕受禅登基,取东晋而代之,刘宋王朝建立。总之,两晋一百五十余年间,内乱外患不断,战争频繁,狼子野心之徒此起彼伏,作威作福之权臣走马灯似的变换,至于不守臣节拥兵自重、不顾民生疾苦危害一方的不良军阀更是多如牛毛。陶渊明用神秘、虚幻的小说故事对当世那些不守臣节的狼子野心家们提出警告,以期戒惧后来者,充分表现了陶渊明对黑暗政治的厌恶。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9]陶渊明曾做过刘裕的参军,对刘裕中兴晋朝抱有希望,但刘裕篡晋建立刘宋政权之后,陶对政治更加反感,作《述酒》一诗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刘裕篡晋事件的不满。陶渊明确实没有忘却现实政治,《搜神后记》讲述了当时许多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的故事,虽然没有针对具体政治事件做出评价,但无疑委婉地表达了对于动荡不安政局的焦虑与愤懑。
三、反对官府横征暴敛,描绘人民理想王国
天下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萧条,人口大量死亡,统治阶级为了应对战争和满足自身奢华生活之需而横征暴敛,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晋书·范宁传》载东晋名臣范宁上疏云:“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3]1320–1321《宋书·徐豁传》载始兴太守徐豁在宋元嘉初年上表指出农民课税过重云:“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8]1508极其频繁的劳役、兵役使得民众苦不堪言,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导致百姓无法养家糊口,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被迫逃逸躲税,生儿不养,鳏寡不娶,甚至多有被逼为盗贼者。与此同时,在朝廷横征暴敛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还要饱受各地豪强地主们的压榨。《宋书·武帝中》曰:“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8]19–20每一片土地皆为豪强所有,每一根柴薪和每一条鱼虾都含税收,权者兼并,强徒凌弱,百姓倾家荡产。
陶渊明的家乡在江州,陶离开官场后亦隐居于此。那么,陶所熟知的江州百姓的遭遇又如何呢?《宋书·庾悦传》载刘裕大将刘毅上表陈述江州人民生活现状曰:“自顷戎车屡驾,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力弱民慢,而器运所继。自桓玄以来,驱蹙残毁,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对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单力竭,无以至此。”[8]982男不被养,女无家室,驱蹙残毁,真可谓惨不忍睹,江州无数百姓唯一出路便是“逃亡去就,不避幽深”。人民的苦难尤其是江州百姓的纷纷逃亡正是陶渊明《搜神后记》构建理想“洞穴世界”的现实基础。
《搜神后记》中直接描写繁重役调和苛捐杂税导致百姓走投无路的作品并不多,但有所触及。卷六《张姑子》开头写道:“诸暨县吏吴详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点明了繁重役调使百姓委顿不堪而被迫逃往深山的事实。卷十《斫雷公》是一篇专写农民穷困的小说:吴兴人章苟辛劳耕作,却食不果腹,每天只吃一顿晚饭,而蛇又将其饭食偷吃干净。章苟一怒之下以鈠(锄头之类农具——笔者注)斫蛇,追赶负伤之蛇至洞穴。蛇招来雷公劈章苟,章苟乃大骂曰:“天公!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若来,吾自当以鈠斫汝腹。”虽然雷公最后劈死了偷食之蛇,但并没有使章苟的生活有任何改善。
陶渊明对于横征暴敛、强取豪夺的黑暗现实的不满之情,突出体现在《搜神后记》卷一的故事设计上。卷一计11则故事,有8则故事集中虚构了独特美妙的洞穴世界,即《仙馆玉浆》《剡县赤城》《韶舞》《桃花源》《刘驎之》《穴中人世》《石室乐声》《姑舒泉》。陶渊明笔下的洞穴世界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洞穴远离现世,处在深山幽水之中。《仙馆玉浆》写“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剡县赤城》写剡县赤城在“深山重岭”中,“山穴如门,豁然而过”。《韶舞》写“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桃花源》写“缘溪行,忘路远近”,“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穴中人世》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穴才容人”。《刘驎之》写刘驎之“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所写洞穴无不超尘绝俗,处在人迹罕至的荒僻之地,充满神秘之感。
二是洞中别有世界,或食物丰盛,或土地平旷肥沃,人们生活无忧。《仙馆玉浆》写一人误堕穴中,寻路前行,十余天后见到两位对坐围棋的仙人,仙人拿出玉浆解除此人饥渴,使其“气力十倍”,又为此人指明回家之路,并提供了丰美神奇的“井中物食”以充饥解渴。《剡县赤城》写剡县猎民袁相、根硕进入了绝崖壁立的赤城,那里土地平敞,“草木皆香”,物果丰茂。“容色甚美”的二位仙女与袁相、根硕结为夫妇,生活美妙。当袁相、根硕思归故乡之时,二仙女各自送给他们一个装有小青鸟的腕囊。《韶舞》写何氏跟着一个跳韶舞的人进入一个山洞,里面“有良田数十顷”,何氏便在此垦作为业,“子孙至今赖之”。《桃花源》写武陵人进入“土地旷空、屋舍俨然”的洞穴世界,村人用丰盛食物热情招待他。《刘驎之》写石囷(石头做的圆形仓库,乃特殊的洞穴世界)一开一闭,里面“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穴中人世》写进入狭窄的土穴后,便“开明朗然”,土地平旷。
三是洞穴世界没有朝廷,没有官府,没有劳役,没有苛捐杂税,更看不到烧杀抢掠的战争,社会一片祥和安静,人们生活美满,精神快乐。这是陶渊明构建的理想天地。《仙馆玉浆》《剡县赤城》等小说固然描写了仙人,但这些仙人宽厚多情,和蔼可亲,毫无现世中君王、权臣的威严和暴戾,他们生活优雅娴静,自由自在,且对人宽厚友善。《石室乐声》《姑舒泉》等小说篇幅短小,虽未述及仙人,但写到了弦歌声声、金石悦耳的美妙音乐,昭示了洞穴世界的祥和欢乐。
在陶渊明描写洞穴世界的小说中,《桃花源》和《韶舞》两篇集中表现了陶渊明心中的梦想。《韶舞》写荥阳人何氏,不愿做荆州别驾,“隐遁养志”,耕作田舍。有一天他在一个翩翩起舞、自称跳“韶舞”的奇人的引导下,进入了独特的洞穴世界,那里“有良田数十顷”,何氏便在此安心定居,以耕作为业,生活圆满幸福。何氏有陶渊明自己的身影,而“韶舞”传说是大舜时代的乐舞名,象征着太平盛世。显然,陶渊明借此表达了对于太平时世的向往和追求,洞穴世界为乱世百姓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苦难的人民可以在这里找到依归,可以安身活命。而最能够体现陶渊明理想的小说是众所公认的《桃花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深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乃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
学术界早已指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其虚构的理想王国,既像道家推崇的“小国寡民”的自然世界,又像儒家推崇的“大同世界”,还像东晋初年鲍敬言主张的“无君”社会。诚然,没有君王统治,没有战乱,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民丰衣足食,老幼怡然自乐,这种太平安宁的“桃花源”是陶渊明构建的独特“洞穴世界”的最高境界,它受何种思想启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为乱世人民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想,尽管它并不实际存在,但却是千百年来饱受战争摧残、饱受欺凌剥削的乱世百姓心灵深处的一束亮光、一丝慰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社会愈是动荡,人们愈是企盼安定和平;生活愈是艰难,人们愈是憧憬丰衣足食;阶级压迫愈是惨烈,人们愈是渴望平等自由。正是人民的这种强烈的追求、迫切的愿望,引发了进步思想家的思考,促使陶渊明创构了他的理想社会——桃花源。”[10]
总之,一部《搜神后记》看似猎奇搜异,却饱含了陶渊明强烈的愤世思想,饱含了作家对统治阶级的极度不满和对乱世百姓的深刻悲悯之情,也为中国劳苦大众构建了一个极其美丽的理想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就会赢得光明。这正是陶渊明《搜神后记》的文化价值所在。
注释:
① 本文所引《搜神后记》原文,均见干宝、陶潜撰《搜神记·搜神后记》(曹光甫、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