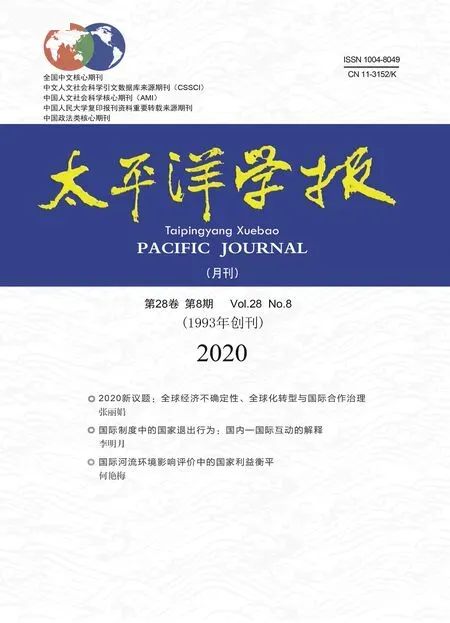“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赵迎结 吕耀东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7)
近年来,日本将积极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作为新的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扩大战略影响力,日本通过价值观外交,拉拢所谓价值观相同的“民主国家”“海洋国家”,不断扩大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合作范围,构建全球性“海洋安全合作机制”。(1)吕耀东:“日本安全政策取向及对东北亚的影响”,《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9期,第46页。与此同时,英国通过派遣军舰,有意在亚太地区显示力量存在。日英军事合作发展迅速,并以构建“准同盟”关系趋向在外交上相互支持,介入亚太政治、安全事务,推动两国军事合作。(2)“日本扩充军备野心引忧虑”,《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9日,第21版。通过加强相关合作,日英日益成为影响印太地区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
针对日英“准同盟”关系,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准同盟”相关理论,力求解释日英为何选择构建“准同盟”关系而非同盟关系,并总结日英“准同盟”关系的特征,探讨日英“准同盟”关系构建的促进因素与制约因素。
一、研究综述、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有关日英安全防务合作与“(准)同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和英国,且研究倾向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国内侧重于动因和影响分析,而日英侧重于路径构建考察。
1.1 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日英安全防务合作与“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动因,有学者认为,英国旨在提升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力,而日本则为争取更多西方支持;(3)参见胡杰:“英日防务与安全合作——路径、动因与影响”,《国际观察》,2017年第6期,第82-89页;胡杰:“英国干涉中国在南海维权:前瞻与预防”,《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3期,第64页。也有学者认为,日英两国加强安全合作是因为在应对俄罗斯威胁、中国崛起、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开发新型武器和维护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存在共同的安全关切,也是日本防务政策调整的结果;(4)嵩旭:“日本的防务外交”,《坦克装甲车辆》,2017年第24期,第23-24、26页。还有学者认为,构建日英“准同盟”关系是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外向性表现、在美国之外寻求可能的结果。(5)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0页。
关于日英安全合作的影响,国内有学者认为,日英加强安全合作增加了解决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复杂性,力求长期联合制衡中国、促进美日英三边合作,但双方战略利益契合点并不完全一致,对华政策存在差异,加之各自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日英同盟近期不会出现;(6)解晓东:“日英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复活?”《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6-121页。也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认为,日英的结合有可能形成20世纪初同盟解体以来最重要的伙伴关系,甚至可能与美国建立三边同盟,重塑全球贸易和政治格局。(7)Michael Auslin, “Britain and Japan Have a Unique Chance to Reshape the World-They Should Seize It”, The Telegraph, April 28, 2017,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4/28/britain-japan-have-unique-chance-reshape-world-should-seize/.
关于新日英同盟的功能,日本研究报告指出,新日英同盟可以补充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低下,扩大自由贸易体制的全球规模,抑制大陆新兴国家,获取战略情报,避免日美关系疏远,确保日美安保体制的永久存在,增加武器与技术开发的商业机会;(8)「新日英“同盟”の時代 ―グローバルな海洋同盟の構築に向けて―」,平和政策研究所,2018年9月20日,第16-20頁,https://ippjapan.org/pdf/policy14.pdf。日本学者鹤冈路人(Michito Tsuruoka)认为,日英防务合作有助于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9)Michito Tsuruoka, “Japan and the UK as Strategic Partners after Brexit”, East-West Center, January 9, 2018,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410.pdf?file=1&type=node&id=36466.秋元千明认为,新日英同盟关系是综合性安全保障合作同盟,是构建“网络型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国家牵制大陆国家的地缘政治及构建和平稳定的美日英正三边形的需要。(10)秋元千明:「多層な安全保障協力の構築と「新日英同盟」―今後の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戦略―」,『政策オピニオン』,2018年第99号,第3-6頁。
关于新日英同盟的构建路径,日本学者平间洋一认为,日本选择同盟国的标准应是国家利益、力量平衡和情报能力,新日英同盟将会影响美国的政策,扩大与英联邦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合作,巩固日美同盟;(11)平間洋一:「日英同盟再考―近現代史からの遺訓―」,『政策オピニオン』,2018年第88号,第6-8頁。英国学者认为,未来日英关系可能会趋向同盟关系,双方应从地缘战略与全球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12)John Hemmings and James Rogers, “Global Britain and Global Japan: A New Alliance in the Indo-Pacific?” East-West Center,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452_3.pdf?file=1&type=node&id=36979.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研究员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认为,日英合作应优先支持一种强大并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解决日本在亚洲的不安全问题,维持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合作。(13)Robin Niblett, “Prospects for the UK and Japan as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Partners”, The UK and Japan Forging a Global and Proactive Partnership, Chatham House Report, pp.10-13.
但也有学者指出,新日英同盟的形成存在局限。英国学者菲利普·谢特勒·琼斯(Philip Shetler·Jones)认为,日英防务合作的主要障碍是维持防务资金的压力、中国经济对英国繁荣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以及对美国的长期战略依赖;(14)Philip Shetler-Jones, “Britain’s Quasi-alliance with Japan”, Natural Partners? Europe, Japan and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al Instituto Elcano Report, pp.15,18-19.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亚洲中心主任约翰·海明斯(John Hemmings)认为,两国在安全目标和地理挑战上存在差异,且每个国家缺乏能投入对方地区的资源,日本将英国引入亚洲,却并未关注英国的地区安全利益;(15)John Hemmings, “UK-Japan Cooperation in Preserving the Liberal Order”, East-West Center, January 11, 2018,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411.pdf?file=1&type=node&id=36470.而美国有观点认为,英国或其他北约国家若想获得日本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配合就应该在东亚对中国施加外交影响。(16)Zack Cooper, “East China Sea Observations, Predictions, and Prescriptions”, JIIA-RUSI-CSIS Joint Open Seminar on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port,pp.40-41.
以上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对日英安全防务合作与交流进行了研究,但日英美学者致力于两国同盟关系构建,更倾向于使用“同盟(alliance)”这一概念和“新日英同盟”这一表述。国内学者侧重于对日英安全关系的动因和影响分析,对日英“(准)同盟”的关注较少。同时,国内外学者对日英“准同盟”、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对日英安全防务合作与交流的催化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会影响两国的对华政策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因此,有必要对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特征表现进行梳理,并借助“准同盟”相关理论对其促进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1.2 “准同盟”概念界定
“Alliance”对应的中文语境是“同盟”或“联盟”,于铁军在《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一文中解释,“同盟”与“联盟”是同义词。(17)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第14页。同盟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研究成果丰富,对同盟的定义却不尽相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18)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2-13.但一般而言,只有将安全合作的内容以正式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才是真正的同盟关系。而对于非正式同盟的安全合作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准同盟”。(19)参见孙德刚:“联盟、准联盟与合作关系——国际安全理论的重要命题”,《亚洲论坛》,2003年第2期,第75页;凌胜利:“南海争端准联盟化评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9页。
“准同盟”既具有同盟的部分特征,又不等同于同盟。同盟与“准同盟”都属于安全合作的狭义范畴,都是对外的合作指向。但同盟的基本逻辑是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护军事安全,同盟间通过核心主权让渡形成紧密依赖,受法律约束强,成员间关系不平等但具有稳定性。而“准同盟”的基本逻辑是以签订次级安全合作协定维护综合安全,同盟间以非核心主权让渡形成较松散的依赖,受法律约束弱,成员间关系或平等或不平等且更具动态性。(20)孙德刚:“国际安全合作中联盟概念的理论辨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第57页。
本文认为,“准同盟”与签订正式军事条约的同盟不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在没有正式签订军事安全协定的情况下保持积极安全防务交流的一种次级安全合作机制。虽然日英安全防务交流愈加频繁,但两国尚未签订正式的军事安全协定。因此,现阶段的日英安全防务关系更符合“准同盟”这一概念。由于英国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考察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状况及其走向,成为中国进行日本外交研究的新课题。
1.3 基于“准同盟”理论的分析框架
当决策者认为只有结盟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时,就会不顾同盟安全困境和成员之间分歧的影响,而倾向于选择结盟政策;当决策者认为只有避免纷争才能保全自己,就会倾向于奉行中立政策;当决策者认为只有兼顾结盟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时,就会倾向于选择“准同盟”政策。在“准同盟”状态下,促进“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变量与制约“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变量便形成一组“多元平衡”(Multi-facet Balance)。(21)促进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变量:安全威胁、发展利益、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制约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变量:分歧、牵连、抛弃和挑衅。孙德刚著:《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26页。
至于日英“准同盟”关系,日本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有意构建日英基于政治、安全及经济合作的同盟关系。日本与英国虽然在发展利益、意识形态和安全威胁等方面存在相互交叉,但对国家利益的描述、在彼此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以及对华政策等方面存在分歧,造成了日英选择“准同盟”关系而非同盟关系的战略合作意向。尤其是2017年8月日英关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可视为双方“准同盟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化意向。
二、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
历史上日英曾三次结盟,两国在冷战期间是美国东西两端最重要的盟国,但战后日英之间的安全防卫合作却很少。2012年6月,日英签署了《防卫合作备忘录》;2013年7月签署了《日英情报保护协定》与《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2014年5月,日英举行了首脑会谈,为强化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双方有意开启外长和防长磋商(“2+2”磋商)和签订《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并强化自卫队与英军共同训练;(22)『平成27年版防衛白皮書』,日本防衛省,2015年版,第288頁。2017年8月,两国签订了《安全保障合作日英共同宣言》,视彼此为亚欧地区最密切的安全伙伴。(23)「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英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85661.pdf。日英在安全合作上的这种定位,事实上确立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形成。
日英“准同盟”合作聚焦于印太地区。经过2015年和2016年的外长和防长磋商,日英安全防卫合作覆盖了亚太、中东、非洲等地区,但还需要一个框架将其统筹起来。(24)「日英外務·防衛閣僚会合共同声明(概要)」,日本外務省,2015年1月2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66163.pdf;「第2回日英外務·防衛閣僚会合(2+2)共同声明(骨子)」,日本外務省,2016年1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23078.pdf。2016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S),为日英安全防卫合作体系提供了合作框架。2017年1月,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正式提出“全球英国”外交构想,将英国定义为欧洲伙伴最好的朋友和邻居,但同时也是一个超越欧洲边界的国家;一个走出去与老朋友和新伙伴建立关系的国家。(25)Theresa May, “Davos 2017: Prime Minister’s Speech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UK Prime Minister’s Office, January 19,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davos-2017-prime-ministers-speech-to-the-world-economic-forum.2017年8月,特蕾莎·梅访问日本,并与日本就印太地区合作达成了共识。(26)「日英共同ビジョン声明」,日本外務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85774.pdf;「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英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85661.pdf。
日英“准同盟”关系构建较晚,但起点较高。日英不仅是“亚欧地区最紧密的安全保障伙伴关系”,更强调“安全保障与防卫是两国关系的基石。”(27)「日英共同ビジョン声明」,日本外務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85774.pdf。为落实日本“积极和平主义”与“全球英国”理念衔接,并进一步提升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表示将继续努力,加强在世界范围,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合作。(28)「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英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85661.pdf。其中,“2+2”磋商成为日英“准同盟”合作的重要机制。始于2015年的日英“2+2”磋商是探讨日英安全防务与外交合作的平台,日英于2017年8月就加强印太地区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29)同⑧。2017年12月,日英举行了第3次“2+2”磋商,并开始探讨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双方强调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尤其是“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并表示为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开展的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日本欢迎英国通过包含派遣航母在内的军事力量和海陆空部队访问的方式,加强对印太地区安全保障的关注,并欢迎英国通过《五国联防协议》(FPDA)(30)《五国联防协议》涉及的五国为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于1971年。机制介入该地区事务。(31)「第3回日英外務·防衛閣僚会合(2+2)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17年12月1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17793.pdf。《日本经济新闻》称,“在东北亚情势紧迫的背景下,日英作为‘准同盟国’身份加强安全保障合作的战略更加明确”。(32)「日英、共同訓練を拡大 「準同盟」全面に」,『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2月15日。
日英“准同盟”合作内容偏重海洋安全。近年来,日本拉拢英国介入南海事务,并举行联合军演,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趋势加强。2019年1月10日,日英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日英共同声明》,详细规划了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内容,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强化双边海洋安全保障合作、促进日英与东南亚等地区第三方的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双方确认彼此为最亲密伙伴,推动日英关系向下一阶段提升。双方认为,相互合作并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符合彼此的利益。(33)「日英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19年1月1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36826.pdf。
日英“准同盟”侧重政策协调并推动双边合作。2019年2月20日,日英两国相关部门举办了“为实现自由开放印太与欧洲合作”会议。在本次会议中,日方指出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在印太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加强日英在该地区的合作,推进政府一体化措施。为加强与英国的合作,双方认为应进一步采取更为具体和更大范围的措施,并讨论了海洋安全保障、高质量基础设施、5G网络安全等议题。(34)「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向けた欧州との協力のための関係省庁会議の開催」,日本外務省,2019年2月2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gb/page4_004761.html。值得注意的是,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于2019年2月1日生效,而日本在2019年2月中旬就开始谋划“自由开放的印太”与欧洲合作的对接,其目的是扩大日本在印太地区、欧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而英国正是该对接的重要“节点”。
可见,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促进了日英的安全防务交流,从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并被作为日英“准同盟”关系的试验场与检验场。因此,日英将日益成为影响“印太地区秩序”的双边关系之一,值得进一步关注其动态发展与未来走向。
三、日英“准同盟”关系走向“泛化”
冷战后,随着国际社会对安全的定义不断扩大,同盟所关注的议题和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单一军事同盟转向政治、军事等综合性同盟,同盟概念随之扩大。由于“准同盟”是从同盟理论发展而来的,其概念也随之泛化。近几年,除了安全合作,日英还在推进经贸合作、海洋权益等领域政策的一致性。日英在安全、经济、政治上不仅达成了更多共识,更朝着“准同盟”机制化方向发展。日英不仅加强了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还全面拓展了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和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加强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的合作,推动了双边“准同盟”关系的泛化发展。
3.1 以防务安全交流为重点
近年来,日英关系得到了迅速而全面地提升,但其中发展最为显著的则是防务安全关系,这与两国谋求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提升安全防卫保障能力与构建区域安全网络密切相关。其中,日英防务交流主要基于民主、法治等共有价值观和交流机制,其合作领域主要有部队共同训练与交流、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其合作的重点区域逐渐从“亚太地区”转向“印太地区”。日英不仅在安全理念上达成了更多共识,还积极推动两国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发展。
首先,为促进日英之间开展人员与物资交流合作,日英签订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2017年1月,日英两国在伦敦签署该协定,英国随之成为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缔结该协议的国家,也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订该协议的欧洲国家。(35)「中国を牽制日英両政府がACSAに署名米豪に次ぎ3カ国目」,『産経ニュース』,2017年1月26日。
其次,日英开始加强航空部队间的合作。2016年10月,英国派遣了4架“台风”战斗机访问日本,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了代号“北方卫士2016”(GUARDIAN NORTH 16)的联合训练。(36)“Announcement: RAF Typhoon Aircraft to Visit Japan”,The UK Government, September 16, 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announcement-raf-typhoon-aircraft-to-visit-japan.英国成为美国以外第一个在日本本土与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的国家,为两国航空部队后续开展更多合作提供了可能。
最后,日英加强了军舰之间的互访与海军之间的共同训练。2017年8月,时任日本防卫大臣陪同英国首相视察了停靠在横须贺港的“出云”号。英方指出,“日英防卫合作正在取得显著进展,两国共同训练不仅能提高两国能力,而且能够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希望今后进一步推进此类合作”。(37)「平成29年8月31日 テレーザ·メイ英国首相による護衛艦「いずも」視察について」,日本防衛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docs/2017/08/31.html。同年12月,日方参观了停靠在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此外,英国还越发频繁地派遣军舰到日本,如2018年4月的“萨瑟兰”号、8月的“阿尔比昂”号、12月的“阿盖尔”号、2019年3月的“蒙特罗斯”号。英国此举的目的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支持国际和区域安全保障,进一步深化日英安全保障伙伴关系,维持和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38)“HMS Montrose Joined Trilateral Exercises with Japan and US”, The UK Government, March 18,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ms-montrose-joined-trilateral-exercises-with-japan-and-us.
此外,日英开始加强陆上自卫队与英国陆军的合作。2018年10月,英国陆军部队与日本自卫队举行了“机警岛演习”(Exercise Vigilant Isles)。(39)“British Troops Exercise in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Army.Mod.UK, October 4, 2018, https://www.army.mod.uk/news-and-events/news/2018/10/british-troops-exercise-in-japan-for-the-first-time/.可见,日英海空陆部队合作与交流逐渐增多,逐渐向机制化方向发展。近来,日本与英美为首的“五眼联盟”表达了战略合作意愿,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而日英之间日趋形成的各种机制,一方面将巩固与扩大日英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但另一方面也将给该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2 全面拓展战略伙伴关系
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构建,不仅影响着整个印太地区,而且引起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浓厚参与意愿。在此背景下,日英全面拓展了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拓宽了双边合作领域,而且深化了双边交流的层次。
广度上,日英的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交流合作得到了全面发展。2017年8月,双方签署了《日英共同展望声明》《安全保障合作日英共同宣言》《繁荣合作日英共同宣言》及《对朝共同声明》四份文件,涵盖了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40)「日英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2017年8月3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gb/page4_003242.html。2019年1月,安倍晋三访问英国,与时任首相进一步协调了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此外,日英还注重网络安全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相继举行了5次网络会议和4次反恐会议。由此看来,日英在拓宽双边合作领域的过程中,延伸并扩大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内涵。
深度上,日英两国不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5月,安倍晋三首相访问英国。英国将日本视为“亚洲地区最亲近的安全伙伴”,并再次确认了英日“动态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日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就安全合作达成了“亚欧地区彼此最紧密的伙伴”关系。在经济层面,两国为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希望建立新日英同盟关系。基于这样的共识,至今,两国仍在不断推动“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向下一阶段迈进。
对于在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构建新日英同盟关系,双方均有战略诉求。正如川村雄介所言,“日英两国若无自由海洋贸易,繁荣不可实现。在欧美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的今天,日英应携手合作,共建新日英同盟关系”。(41)川村雄介:「EU離脱後の新「日英関係」」,Forbes JAPAN,2017年3月6日,https://forbesjapan.com/articles/detail/15411/2/1/1。对于构建新日英同盟的相关议题,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杰拉米·亨特(Jeremy Hunt)曾表示,“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英日联盟——我相信这种友谊会在未来几年得到加强”。(42)Jeremy Hunt, “Jeremy Hunt Takes Forward ‘New Era of Friendship’ with Japan”,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eremy-hunt-takes-forward-new-era-of-friendship-with-japan.由上看来,日英出于安全、经济等考量,正在为构建新日英同盟关系创造相关的条件。但是,从目前来看,日英的战略伙伴关系还处于为未来构建日英同盟关系创造条件的阶段,“准同盟”关系将是其过渡阶段的表现形式。
3.3 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和加强海洋安全合作
除了日益频繁的防务安全交流外,日英两国还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这既是两国对美国地区规划的支持,也体现了共同利益所在,即两国皆为岛屿国家、海洋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贸易,都强调海洋“航行自由”。
一方面,日英重视自由贸易。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安倍晋三与特蕾莎·梅举行了首脑会谈。安倍称,“支持梅首相在G20峰会上关于自由贸易的发言,自由开放的贸易是两国繁荣的基础”。(43)「日英首脳立ち話」,日本外務省,2016年9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gb/page1_000244.html。这是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及日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后,日英两国首脑第一次在国际场合的会面与交流,可见维护自由贸易符合两国利益,这也成为双方加强合作的经济动力。
日英均重视维护自由贸易体系。日本自诩为维护自由贸易的“旗手”,为获得地区合作的主导地位,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构建,如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由贸易区(FTA)、经济合作协定(EPA)等。于英国而言,其经济和金融因“脱欧”受到冲击,自由贸易体系对于维持国内经济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这也促使日英加强经济合作。此外,日英两国均受到“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与影响。2017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开始提倡“美国优先”原则,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日英认为自身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只有维护该体系,“安倍经济学”和英国的经济稳定才能实现,两国的经济大国地位才能维持。同时,日英对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也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巩固日英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进而构建“准同盟”关系的经济基础。从2020年6月9日开始,日英就开始启动《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程序,并于近日对其涉及的大部分领域达成了共识,且力求在8月月底之前达成一致意见,争取在2021年初生效。(44)「日英間の経済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茂木外務大臣とトラス英国国際貿易大臣との協議)」,日本外務省,2020年8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cm/ie/page4_005173.html。因此,日本在与英国的交流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另一方面,日英两国均强调维护“海洋秩序”的安全合作。日英在历次“2+2”磋商和《安全保障合作日英共同宣言》与《日英共同展望声明》中都强调“海洋秩序”的重要性。日本和英国作为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地区的重要盟国,采取了追随美国“航行自由”政策,扰乱中国南海局势,侵犯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正当海洋权益。早在2016年,美、英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将领举行了会谈,三方在强化海事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2019年3月,日英美三国海军首次举行了共同训练。其中,英国有意转向亚太地区,在提出“全球英国”理念后,开始更加关注印太地区事务,并频繁派遣军舰到该地区。而日本多次表示,欢迎英国加强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关注,引导英国关注甚至介入东海、南海事务,并以安全合作为名加强日英防务安全交流,拓展双边合作领域。
3.4 加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日英不仅注重双边关系的提升,而且重视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与交流。在全球问题上,随着“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于2019年2月1日生效,标志着日本开始同欧洲国家围绕军控、恐怖活动、气候变化、教育、司法等全球课题展开合作。(45)「日EU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SPA)」,日本外務省,2018年7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1943.pdf。在地区层面,日英在非洲、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安全事务上都在加强合作,并保持声音一致。
其中,非洲是日本“印太构想”的重要支点之一,也是英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关注地区。非洲社会存在的问题复杂多样,为两国开展多种共同合作提供了机遇。根据日英第一次“2+2”磋商结果,2016年8月在日本举办的非洲开发会议上,日英两国共同举办了“性别平等与女性权利创造和平社会”讨论会,旨在保护非洲女性安全与平等。(46)「TICAD VI公式サイドイベント「ジェンダー平等と女性のエンパワメントが平和な社会を創る」の開催」,日本外務省,2016年9月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gb/page4_002307.html。根据日英第二次“2+2”磋商的结果,日本与英国于2017年在安哥拉共同实施了扫雷活动,共清理了191 692平方米土地,使2 490余人受益。(47)「アンゴラにおける地雷除去に関する日英連携の実施」,日本外務省,2017年6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4723.html。通过上述日英在非洲事务合作的案例可以看出,双方针对非洲的合作恰恰是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形式,也为构建两国“准同盟”关系创造条件和拓展合作区域。
此外,日本与英国还在世界其他重要地区展开了合作。在东北亚地区,日本与英国于2017年8月签订了《对朝共同声明》,其目的是在“朝核问题”上保持共同立场。(48)「日英共同記者会見」,日本首相官邸,2017 年 8 月 31日,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831uk.html。在东南亚, 日本与英国于2018年2月举行了面向东盟各国的网络研讨会,向东南亚各国参加者介绍了日英两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的适用、责任国家的行动规范、网络犯罪条约、网络安全机构现状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49)「日英共催ASEAN諸国向けサイバーワークショップ」,日本外務省,2018年2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5709.html。可见,日本与英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不断增加,其实质是日英战略伙伴关系深化的“外溢”表现,推动了日英“准同盟”的泛化。
四、日英“准同盟”关系构建的促进因素
根据“准同盟”理论,促进“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四个主要变量是:安全威胁、发展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且每个变量都是构建“准同盟”关系的充要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日英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支持存在互补(发展利益),强调价值观相同(意识形态),而且都受到美国同盟机制的牵连(安全威胁),这些因素综合促进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
4.1 谋求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
日本在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定义了国家利益,即“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裕,强化我国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为此,作为海洋国家,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强化自由贸易体制,创造高度稳定、高度透明、未来可预测的国际环境。此外,维持和拥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普遍价值观或原则的国际秩序,同样是我国的国家利益。”(50)「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外務省,2013年12月17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7/20131217-11.pdf。为实现国家利益,日本不断增强自身的战略自主,其具体举措包括:维护国际体系和秩序——全球多边自贸体制;自主构想、推进并引导美国接受其对于印太地区的构想;积极塑造大国关系格局,调整与俄罗斯、印度、欧盟主要国家等的关系。(51)吴怀中:“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页。
而英国试图在“脱欧”后,重塑大国形象。英国在回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追随美国“航行自由”政策,愈加频繁染指中国南海,并将战略目光从“亚太地区”转向“印太地区”。有学者认为,在“脱欧”背景下,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方面:履行现有条约承诺和义务;支持地区盟友,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维持现有海上秩序,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52)Alessio Patalano, “Forward Deployed and Committed: Britain’s Post-Brexit Indo-Pacific Strategy”, Global Asia, Vol.14, No.2, 2019, p.110.有学者指出,英国是为了在中美博弈中间保持平衡、体现大国地位、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还可以争取对华主动权、巩固英美同盟以减少“脱欧”震荡,提升英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53)胡杰:“英国干涉中国在南海维权:前瞻与预防”,《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3期,第65-68页。
可以说,日英双方的合作与交流既是双方对美国战略的呼应,更是彼此谋求或体现大国地位的现实需要。但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日英两国都在谋求美国之外的可能,并追求战略上的自主。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与英国的“全球英国”理念正是日英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体现,扩大本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影响范围,提升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树立大国形象,这种战略利益的交叉为两国展开合作提供了可能。
4.2 互为彼此国家对外战略的新支点
英国被日本视为其构建海洋国家联盟的重要“支点”之一。为谋求“国家正常化”,实现日本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目标,安倍晋三上台后积极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战略性外交,努力增强本国的战略自主性与国家军事力量,在稳定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组成日美澳印“民主安全菱形”,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组建海洋安全联合体,企图遏制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活动。日本在2017年就有这种意图,即联手美、澳、印等国创建“四边机制”,落实美国对印太地区构想中的安全合作内容,并在未来拉入英法等国,构建广域的安保合作机制。(54)吕耀东:“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第31页。“自由开放的印太”强调共同价值观和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成为日本诱导和拉拢英法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过程中,英国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此外,由于英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签订了五国联防协议(FPDA),日本希望通过提升日英关系并加强日英安全防务交流加入英国主导的五国联防体制中,从而扩大海洋国家联盟。(55)永田伸吾:「5カ国防衛取極(FPDA)とアジア太平洋の海洋安全保障―防衛装備·技術面での日英協力の視点から―」,海洋安全情報特報,2017年10月1日,第2頁。
日本被英国视为转向亚太的最佳伙伴。在“全球英国”理念的指导下,英国政府指出未来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地区是:北美(特别是美国)、欧洲及其邻国、印太地区,因为它们是全球经济与政治的中心。(56)“Written Evidence-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PW0027) ”, UK Parliament, Octorber 28,2018, http://data.parliament.uk/writtenevidence/committeeevidence.svc/evidencedocument/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mittee/foreign-policy-in-changed-world-conditions/written/79900.html,转引自李靖堃:“‘全球英国’理念下英国非洲政策的调整”,《西亚非洲》,2019年第2期,第117页。这是由于虽然英国“脱欧”了,但不得不继续以美国为依托,加强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开拓新的外交活动区域。但如果英国真正想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并发挥影响力,寻找战略伙伴就成为其现实选择。日本被称为“亚洲的英国”,与英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且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自然成为最佳选择。(57)解晓东:“日英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复活?”《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5页。日本学者提出,日英两国作为世界两大强国,如果能更紧密地结盟,就可以重新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58)John Hemmings and James Rogers, “Global Britain and Global Japan: A New Alliance in the Indo-Pacific?” East-West Center,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apb452_3.pdf?file=1&type=node&id=36979.这恰恰反映出日英两国都存在寻求盟友的意愿,其中在亚太地区,英国更依赖日本,这也促使英国选择日本成为其转向亚太地区的支点。
4.3 强调价值观相同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除战争时期外,一直提倡“脱亚入欧”,政治体制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经济利益与西方国家协调,寻求与西方的共同利益。日英两国拥有相近的政治体制和共同的法治、民主等基本价值观,使得两国在对话与交流中更易达成共识。
2006年至2007年,安倍晋三第一次任日本首相时,其内阁成员麻生太郎就提出了“自由繁荣之弧”,并被发展成为“价值观外交”。所谓“价值观外交”,是指在推进外交时,高度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59)刘江永:“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07年第6期,第47页。安倍再次执政以来,不断推动持相同价值观国家之间的联盟。2018年9月,出席第73次联合国大会的安倍表示,“自由开放的印太”需要联合太平洋岛国、美国、澳大利亚与印度等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60)「第73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日本外務省,2017年9月2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unp_a/page3_002562.html。而2017年4月,特蕾莎·梅会见安倍时称,“我们共同努力,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促进自由贸易和维护民主价值观”。(61)Theresa May, “PM Statement Following Talks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28 April 2017”, UK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pril 28,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tatement-following-talks-with-japanese-prime-minister-abe-28-april-2017.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在2019年1月安倍访英时称,“英国和日本拥有相同的人权和法治价值观,以及在世界各地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决心。与我们观点一致的国家间的友谊,才是‘脱欧’后英国充满信心的重要基石”。(62)Jeremy Hu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Visit Is a Chance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with Like-minded Nations”,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January 10,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japanese-prime-ministers-visit-is-a-chance-to-celebrate-our-friendship-with-like-minded-nations-article-by-jeremy-hunt.
显然,日英两国在不断强调相同的价值观,这为两国开展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也促进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因此,强调相同价值观仍将是日英构建“准同盟”关系的重要手段。
4.4 配合美国战略且应对亚太秩序转换
“准同盟”理论认为,外来威胁越大,国际实体与相关国家建立“准同盟”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日英两国正处于构建共同威胁共识之中,同时两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家,受同盟机制的“牵连”,必然会适时配合美国的安全利益诉求。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原有的亚太地区秩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为保持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并防止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被取代,先后推出“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以加强与同盟国家和伙伴国家的关系。(63)沈铭辉、李天国:“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第11-12页。美国有意改造亚太地区旧有的“辐轴体系”联盟框架来遏制中国,并鼓励各盟国之间进行双边、三边及“少边”合作,从而推动“辐轴体系”的网络化发展。(64)王竞超:“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探析:历史演进、动因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40-41页。日英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将是其改造同盟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和英国的合作具有非常强的战略性,可以完善美国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功能。(65)永田伸吾:「5カ国防衛取極(FPDA)とアジア太平洋の海洋安全保障~防衛装備·技術面での日英協力の視点から~」,海洋安全情報特報,2017年10月1日,第11頁,https://www.spf.org/oceans/b171001.pdf。这种观点表明日本学者在为日英海洋安全合作和构建“准同盟”关系寻找现实理由。同时,由于英国曾是印太地区许多国家的宗主国,而日本又与这些国家关系友好,故位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日本与英国可成为该地区“网络型同盟”的“中轴”。(66)秋元千明:「多層な安全保障協力の構築と「新日英同盟」―今後の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戦略―」,『政策オピニオン』,2018年第99号,第5頁。
由上可知,配合美国战略的需要、弥补美国在该地区安全结构上的不足,是推动日英“准同盟”关系构建的结构因素。而美国也乐见盟友国家之间的合作,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也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现实利益,符合日英印太地区合作的长远利益。
五、日英“准同盟”关系构建的制约因素
根据“准同盟”理论,国际实体构建“准同盟”关系时的制约因素主要涉及四个变量:分歧、牵连、抛弃和挑衅。日英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促进了“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但双方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等方面存在分歧,并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些因素将制约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
5.1 遏制中国不完全符合英国国家利益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国家之间利益趋同则合,利益趋异则分。而日英分歧表现为对国家利益的不同描述,相比日本更加注重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并以此为国家利益,英国则出于自身安全与繁荣的国家利益考虑,更注重该地区的经济活力与政治影响力。
从经济与政治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后需要新的经济和政治依托,而作为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印太地区自然是英国的重点选择区域之一,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中国和印度可成为英国的合作对象。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推动了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开启和升级。(67)张颖:“首脑外交与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49页。英国“脱欧”后,中国可以成为英国维护经济稳定与发展、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对象。从国际组织参与情况来看,英国重视多边主义的地区机构,并积极参与其中。例如,英国于2015年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而作为亚洲地区重要力量的日本至今未加入其中。从日英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内容来看,虽然日本对印太地区的构想一直将中国视为对手,但这对于加入“亚投行”的英国来说,不符合其国家利益。
5.2 双方外交战略存在错位
日本的外交战略是根据日本国家利益制定的。日本认为,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提高英国在日本外交中的比重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中国有学者认为,日本外交应根据自己对地区乃至全世界力量格局变化的现实判断,来决定是继续依赖美国同盟关系,还是适应中国的崛起,或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决策,抑或是兼而有之。(68)张勇:“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82页。日本学者则认为,为实现国家利益,日本的外交选项是“日美同盟+α”,其具体实施路径就是“印太构想”。(69)[日]小原雅博著,王广涛、丛琬晶译:《日本的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5、191-192页。近年来,日本积极提升日英双边关系,拓展安全与防务交流,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并邀请英国加入“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或构建日英“经济合作协定”(EPA)等新型经济关系。由此看来,英国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正在快速提高。
反观英国,其外交布局则是:在依托英美同盟的前提下,与欧洲地区伙伴在“脱欧”后仍保持最紧密的合作和务实的关系,威慑俄罗斯,从战略层面重构与印度的关系,重视与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大国建立联系,参与多边组织与地区集团。对于中国,英国认为完全把中国当作对手不符合英国利益;相反,英国的目标是为了与中国互利共赢,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重大全球挑战,并确保这种合作符合“国际人道主义”。对于日本,英国认为日本是重要的“地区力量”,与英国拥有共同价值观,应努力巩固与日本的关系,在对华合作上应平衡与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亲密友谊。(70)“UK Foreign Policy in a Shifting World Order”, Parliament UK, December 18, 2018, p.3,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1719/ldselect/ldintrel/250/250.pdf.
总之,相比日本对英国外交的热忱,英国的对日外交定位更为理性。在英国的外交战略中,中日都占有重要位置,对中国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而对日本则侧重于“地区力量”、价值观和亲密友谊,这使得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与日本存在不小的差异。
5.3 两国战略指向尚在对接
虽然日本和英国在战略上寻求共同的利益,但各自的战略指向并不完全一致。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虽然英国官方正式表态支持日本对印太地区的构想,但并不想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与中国对抗,鉴于英国“脱欧”后未来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必须与日本和中国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71)[俄]B.O.基斯塔诺夫、杨俊东:“日本‘印太战略’:构建、核心与延伸”,《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4期,第28页。英国上议院应对中国长期开放表示欢迎,不能完全将中国当作对手,但必须确保中英关系不会损害英国与美国或日本的关系。(72)“UK Foreign Policy in a Shifting World Order”, Parliament UK, December 18, 2018, pp.3, 20, 24, 98,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1719/ldselect/ldintrel/250/250.pdf.
有日本学者积极倡导构建新日英同盟,譬如日本的英国问题学者秋元千明认为,日本所警戒的是中国的海洋发展,英国则是遏制俄罗斯的霸权,日英两国皆以欧亚大陆力量为对手,面对的是同样的威胁。(73)秋元千明:「今なぜ日英同盟「復活」なのか 膨張する中国とロシアに「平和と安定の正三角形」で対峙」,Wedge,2018年2月1日,http://wedge.ismedia.jp/articles/-/11778?page=4。他的观点恰恰表明日英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指向性以及利益所在。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俄罗斯威胁论”并加以共同遏制,也成为日英两国的战略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深化日英战略伙伴关系进而构建“准同盟”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战略目标。
在战略指向上,英国转向亚太,尽管仍然关注俄罗斯的东亚政策,但不可避免认同日美等国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并加以遏制。譬如,英国在涉港问题上的言行,便是明证。2020年6月30日,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就香港局势发表谈话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的通过表示担心和遗憾,并将联手相关国家对华施压。(74)「香港情勢について(外務大臣談話)」,日本外務省,2020年6月3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6_000400.html。8月5日,茂木敏充访英期间,与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交换了意见,将携手应对《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局势。(75)「日英外相会談」,日本外務省,2020年8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page4_005172.html。但对于日英双方在东亚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因双方的利益诉求及战略目标尚存落差,使得两国在寻求共同利益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磨合、协调与对接。
5.4 国内事务影响“准同盟”关系的构建进程
“准同盟”理论认为,国内政治会影响国际实体“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但现有研究并未系统说明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准同盟”的构建。本文认为,国际实体忙于内部事务或者政治议题的重要次序的转换会影响“准同盟”关系的构建进程。以日英关系为例,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使英国和日本各自忙于应对国内事务,从而影响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
英国“脱欧”造成国内政坛分裂和外交重心偏向欧美,进而影响日英“准同盟”的构建。2019年,特蕾莎·梅领导的英国内阁无法调和国内党派的不同意见,于6月7日提出辞职。而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则继续推进“脱欧”,并于2020年1月31日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英国“脱欧”使其外交重心偏向于欧洲和美国而无暇东顾,日英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被暂时搁置。最明显的是,原定于2019年4月举行的第4次日英“2+2”磋商一直被推迟。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两国的重要关切,传统安全合作议题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近期,日英在第8次外长战略对话时表示,将尽快确定日英“2+2”磋商的举办时间。(76)「第8回日英外相戦略対話」,日本外務省,2020年2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8323.html。但由于当今全球受到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都在积极应对,日本与英国也在采取措施应对国内疫情,传统安全合作议题的重要性相对下降。2020年3月,日英举行了首脑电话会谈,相互介绍本国的应对政策。(77)「日英首脳電話会談」,日本外務省,2020年3月1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gb/page6_000380.html。新冠疫情已成为日英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并影响到两国传统安全合作新内容的制定,从而延缓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
六、结 语
日英曾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三次结成同盟,而现在的日英“准同盟”关系是在新情况下日英同盟关系的历史轮回。日英两国在发展利益、意识形态和安全威胁等方面的一致性促进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等方面存在差异并受各自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将制约日英同盟的构建。日英两国将继续以构建“准同盟”关系的方式扩大和深化在印太地区的安全防卫合作。
日英两国的安全防务交流发展迅速,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这是两国战略自主的表现,同时也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同盟体系调整的结果,这为研究转型中的同盟体系,尤其是海洋国家同盟体系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参考。
日英两国皆自视为典型的海洋国家,维护印太地区海上“航行自由”及法治是双方构建“准同盟”关系的价值取向。同时,两国是美国在欧亚地区的主要同盟国家。因此,无论研究当代大国海洋政策,还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转换,日英两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关注对象。除了日英双边关系研究外,将其置于历史纵向发展、全球秩序转换以及三边和多边等框架内加以探讨,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