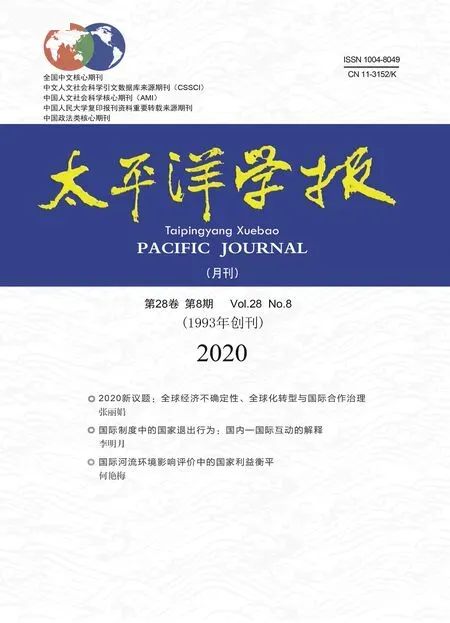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许善品
(1.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411105)
冷战结束之初,在苏联解体、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局势下,地缘经济压倒地缘政治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亚太地区大国合作呈现良好态势。但进入21世纪,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日渐崛起和中美权力转移加速,美国对华战略疑惧日甚,美国在中澳关系中由积极因素转变为消极因素,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面临进一步动态调整。严重依赖美国安全庇护的澳大利亚,其外交政策逐渐偏离“平衡外交”而向美国倾斜,追随美国在亚太前沿的战略部署;同时,不断崛起的中国逐渐被澳大利亚视为不确定因素。澳大利亚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追随美国仍然是最稳妥的外交选择。由此,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偏离平衡外交,走向外交失衡。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对“平衡外交”进行了颇多富有启发性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专注于研究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过程中采取“平衡外交”,以此维护国家利益和外交独立,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1)参见孙西辉、金灿荣:“地区大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为例”,《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54-72页;王少普:“韩国的平衡外交及其面临的挑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5期,第6-11页;William Guéraiche, “The UAE-Tunisia Diplomatic Relations: A Subtle Balance between Economy and Secur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Economy, Vol.3, No.4, 2017, pp.316-329等。国内学术界研究普遍认为澳大利亚的平衡战略取得了积极成效,既实现了与亚洲国家互动并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不断提升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维护地区秩序。其中,赵昌认为,霍华德在文化传统与地缘现实、经济发展与政治联盟、国际公义与国家利益等方面维持平衡战略。(2)参见赵昌:《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也有学者对澳大利亚“平衡外交”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探析,并通过澳大利亚利用达尔文港的军用和商用价值分别与美国、中国签署协议这一事例,充分展示了澳大利亚在中美间如何奉行“平衡外交”。(3)赵昌、许善品:“从租借达尔文港看澳大利亚的中美平衡外交策略”,《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2期,第57-73页。李泽认为,鉴于中美对澳大利亚也存在较高程度的依赖,所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澳大利亚不需要与其中一方形成捆绑,它完全可以确定在具体问题上相对支持某一方的标准,从而在中美之间维持动态的战略平衡。(4)李泽:“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7页。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外交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2007年之后的澳大利亚历届政府继承了霍华德的外交遗产,继续遵循平衡战略,但随着中国崛起,澳大利亚也面临日益严峻的战略困境——如何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美国盟友和中国伙伴之间保持平衡。(5)参见[澳]马克·比森、李福建:“中澳关系:地缘政治抑或地缘经济?”《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38-49页;王联合:“战略两难与利益均沾: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澳大利亚亚太战略解析”,《国际观察》,2016年第4期,第98-112页; Takashi Terada, “Australia and China’s Rise: Ambivalent and Inevitable Balanc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2, No.2, 2013, pp.129-145; Chengxin Pan, “Neoconservatism, US-China Conflict, and Australia’s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 Dilemm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4, 2006, pp.429-448.也有学者围绕亚太、印太、南太地区及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研究澳大利亚对中国不断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担忧,(6)参见许少民:“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115-156页;张亮:“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认知与反应”,《国际论坛》,2018年第5期,第69-75页;Nathan Paul Smith, The Role of Individuals in Foreign Policy Outcomes: A Case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Murdoch University, 2014; Marc Lanteigne, “Water Dragon? China, Power Shifts and Soft Balancing in the South Pacific”, Political Science, Vol.64, No.1, 2012, pp.21-38.但并未分析澳大利亚平衡外交的新动向——转向失衡。部分学者则从澳美同盟的视角分析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澳大利亚选择不断强化并升级澳美同盟。(7)参见程鹏翔:“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美澳同盟”,《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3期,第29-42页;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70-86页;Mohan Malik, “The Australia-U.S.-Chin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18, No.4, 2006, pp.151-170.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和对华政策进行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但既有研究中,大多数文献认为2016年之后,澳大利亚依然在中美间奉行平衡战略,也有部分学者意识到澳大利亚逐渐开始偏离“平衡外交”轨道,但既有研究对澳大利亚为何逐渐偏离平衡外交的研究并不充分,也相对缺乏从国际体系、双边关系、国内政治等层次分析滑向失衡的原因。事实上,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反华声音不断,对华外交逐渐走向失衡,导致中澳关系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因此,研究澳大利亚逐渐偏离“平衡外交”立场、日益由平衡滑向失衡的新动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澳关系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深层次变化。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对澳大利亚之所以奉行平衡外交的原因与希望实现的战略目标进行分析,再探讨澳大利亚逐渐偏离平衡外交的表现,然后从国际体系、双边互动和国内政治等层次探究外交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并展望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未来趋向。
一、澳大利亚推行平衡外交的基础与目标
“‘平衡外交’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种外交方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理论的角度看,任何国家都可能实施某种形式的‘平衡外交’,平衡的对象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8)孙西辉、金灿荣:“地区大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为例”,《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54页。平衡策略就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外交策略,反映了实用主义的外交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霍华德政府的外交独立性,对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9)丁念亮、王明新:“霍华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2期,第54页。而本文将澳大利亚的“平衡外交”定义为:在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澳大利亚在地缘安全方面与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在地缘经济方面与经济快速增长且市场广阔的中国保持友好伙伴关系,通过在中美间保持战略平衡、谨慎避免“选边站队”,以期同时获得安全保障与经济繁荣。
1.1 澳大利亚推行平衡外交的现实基础
澳大利亚之所以长期将平衡外交作为其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是综合考量国家身份、地理位置、国家利益的结果。
(1)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背离
长期以来,在亚太地区一直存在着所谓的“东亚悖论”或是二元格局,也就是几乎所有亚太国家都在地缘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地缘安全上依赖美国,澳大利亚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背离程度、割裂程度几乎是亚太国家中最严重的。澳大利亚外交与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2018年对外贸易出口货物中有36.1%面向中国市场,(10)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2018-19”, January 2020, p.58,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cot-2018-19.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18日。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日本、韩国等。同时,受制于人口规模,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相对有限,抵御周边安全威胁的能力相对不足,而所处的亚太地区冲突频发、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所以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严重背离,既难以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故推行平衡外交既能够实现经济利益,也可以同时保证其安全利益。
(2)西方国家身份与地处亚太地区的错位
在国家身份上,澳大利亚属于西方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从英国承袭了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法律制度等。1901年独立后,澳大利亚继续支持英国,并先后卷入两次世界大战。而二战末期,澳大利亚希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与美国签订了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并几乎追随美国参加了历次海外军事行动。可见,澳大利亚仍然坚持西方国家身份,认同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始终坚持与西方大国结盟。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面对地处亚太的地理现实,地理的逻辑、经济的利益逐渐超越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成为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经济和安全利益考虑,澳大利亚思考了地处亚太对其战略环境、地区合作、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冲击与机遇。早在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就决定正式开启融入亚洲的进程。如今,随着亚洲国家的群体性崛起,21世纪将成为“亚洲的世纪”,澳大利亚逐渐意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亚洲,而非欧洲。(11)许善品:“国家身份视角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选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3期,第80页。
时至今日,作为位于亚太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仍然试图在地理与文化之间、亚洲与西方之间、经济与安全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维持大致的战略平衡,以此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2 澳大利亚平衡外交的政策目标
由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美国保护,澳大利亚实行了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平衡战略,主要表现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兼顾、中澳伙伴关系与澳美同盟并重、强硬保守与务实理性兼备。
(1)保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平衡
澳大利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且人口有限、国内市场狭小,因而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与对外贸易。而亚洲巨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对能源和资源的大量需求,尤其是正在迅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国,对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繁荣来说至关重要。在地缘经济方面,澳大利亚不仅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而且注重提升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2009年2月,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在2012年10月发布的《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阐释了要在经济和战略层次上融入亚洲这一新立场。(12)Barthelemy Courmont and Colin Geraghty, “India and Australian: An Emerging Partnership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5, No.2, 2013, p.289.2015年底,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澳大利亚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基于地缘经济考虑,澳大利亚不断拓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并逐渐将战略重心由欧洲转移到了亚太地区。
在发展地缘经济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注重维护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处远离世界舞台中心的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诸多地缘政治关切,为了维护地缘政治安全,澳大利亚1996年与美国签署了《关于21世纪澳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悉尼联合安全声明》,2007年与日本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6年以来,近期外交政策趋势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澳大利亚继续与美国密切对话,进一步采取措施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寻求与日本合作的新途径,包括与美国开展新的三方对话,并与印度尼西亚达成新的安全协议。(13)Frank Frost, “Perspective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2006”,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 No.3, 2007, p.403.通过不断强化与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政治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的地缘环境、地缘政治安全得到有效改善。
(2)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
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大国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伙伴,三边关系保持总体融洽。“9·11” 事件后,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中美澳三国紧密合作,澳大利亚实施平衡外交的空间不断扩大。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就曾多次表示,“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并非不可避免,因而澳大利亚无需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14)Chengxin Pan, “Neoconservatism, US-China Conflict, and Australia’s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 Dilemm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4, 2006, p.440.通过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确保中澳伙伴关系与澳美同盟并重,澳大利亚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迅速融入国际社会、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澳大利亚希望抓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实现经济繁荣。澳大利亚政府不断促进中澳伙伴关系健康发展:时任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部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在2003年的《中国工业腾飞——东亚面临挑战》报告中指出,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最大受益国。(15)“China’s Industrial Rise: East Asia’s Challeng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October 29, 2003, 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download/media/pressrel/87RA6/upload_binary/87ra64.pdf;fileType=application%2Fpdf#search=%22media/pressrel/87RA6%22.2013年10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晤时强调,澳大利亚的繁荣得益于同中国的合作,澳将继续强化两国互信、经贸、人文、安全四个纽带,发展更强劲的澳中关系,做中国的好朋友,并欢迎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16)“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3年10月6日,http://www.gov.cn/ldhd/2013-10/06/content_2501315.htm。2014年11月17日,中澳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6月17日,中澳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CAFTA)。
在发展中澳伙伴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强化澳美同盟。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坚持澳美同盟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并追随美国先后参加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等;在澳美同盟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同样支持美国的全球政策,并效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做法。(17)William T. Tow, “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u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n Ambiguous World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17, No.2, 2004, p.272.在2011年9月15日发布的澳美同盟部长级会议(AUSMIN)联合声明里,澳美宣布将双边同盟合作领域扩大到网络空间领域,共同致力于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开放性。(18)“Australia-United State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2011 Joint Communiqué”,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 and Trade, September 15, 2011, https://www.dfat.gov.au/geo/united-states-of-america/ausmin/Pages/ausmin-joint-communique-2011.正如保罗·迪布(Paul Dibb)所言,“澳大利亚不是在美国盟友和亚洲伙伴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平衡两者的关系”。(19)Paul Dibb, “Australia’s Alliance with America”, Melbourne Asia Policy Papers, Vol.1, No.1, 2003, p.9.可见,澳大利亚曾希望在保持与中国友好伙伴关系的同时,并行不悖地长期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然而,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地缘政治、大国竞争在亚太地区强势回归,澳大利亚在中美间推行平衡外交的空间正在慢慢缩小。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澳大利亚在中美间“选边”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逐渐趋于强硬。“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导致澳大利亚决策者被迫做出‘选择’,澳很可能会支持美国。”(20)Michael J. Norris, “The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ustralia, and the U.S.”, Inquiries, 2010, Vol.2, No.12, p.1.地缘政治优先于地缘经济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主导因素。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后,中美地缘政治对抗态势日渐凸显,地缘政治再次超越地缘经济,中澳关系开始偏离正常轨道。当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轮驱动时,中澳关系则会驶入“快车道”;当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冲突时,地缘政治会制约地缘经济发挥作用,地缘经济难以摆脱地缘政治的制约,而对应的中澳关系则会出现偏离正常轨道或“急刹车”的可能。(21)许善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澳关系发展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0月8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1910/t20191008_4980313.shtml?from=timeline。
二、澳大利亚偏离平衡外交的表现
正如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指出,澳大利亚与中国不断加深的经贸联系在原先由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关系中扮演了“僭越者”的角色,这迫使澳大利亚采取一种分离的外交政策——经济和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断裂。(22)Nicholas Thomas, “The Economics of Power Transitions: Australia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4, No.95, 2015, p.846.然而,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却成为澳大利亚沉重的心理负担,给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造成了空前的困境。(23)Jian Zhang, “Australian and China, The Challenges to Forging a ‘True Friendship’”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 Hill, eds., Middle Power Dreaming: Australian in World Affairs 2006-20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1.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平衡外交已经缓慢但稳定地走向失衡。
2.1 中澳关系不断遭遇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澳伙伴关系不断遭遇挑战。澳大利亚在南海、“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等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造成了目前两国关系困难的局面。
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最初持超然姿态,但之后的立场有失偏颇。2014年以来,随着美国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澳大利亚随之高调介入,支持并追随美国巡航南海,并派出军机和军舰闯入南海,以捍卫所谓的“航行自由”、响应美国的外交呼吁,发挥所谓“中等强国”作用。2016年7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出台后,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表示菲律宾和中国都应该遵守判决。(24)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Supports Peaceful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12, 2016, https://www.dfat.gov.au/news/news/Pages/australia-supports-peaceful-dispute-resolution-in-the-south-china-sea.由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紧随美国,对中国维护主权的行动横加指责,致使中澳关系面临严重挑战。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放弃以往相对客观的中立立场,逐渐滑向深度介入,试图与美国一道在南海制衡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澳方有关南海问题的错误言论与做法不仅于己不利,也无益于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过度介入与己无关的地区冲突只会增加“战略牵连”的风险,同时导致南海地区的政治合作氛围趋于恶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问题上,澳大利亚的态度由积极参与转为消极抵触。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澳时曾发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中澳在国家最高层面就发展战略对接问题的互动已在推进,中澳两国总理2017年3月在第五轮年度会晤中就澳国家发展战略与该倡议对接问题进行了磋商,(25)孙君健:“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6期,第49页。但此后澳大利亚政府态度日渐消极。2018年2月18日,澳方媒体发布消息透露,特恩布尔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商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选择。(26)Philip Coorey, “Australia Mulls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with US, Japan, India”,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 18, 2017,转引自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88页。澳虽然在实际行动中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收益,但在战略层面却避免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积极回应,并表现出对中国发展成就及未来规划的恐惧,而后据此做出政策应对,体现为国家政策、行动中的对华防范和牵制。(27)同①,第55页。
受对华心态日益失衡影响,澳大利亚开始无端指责中国“干涉澳洲内政”,包括炒作所谓“中国干涉论”“中国渗透论”和“中国威胁论”,将中澳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政治化、污名化,甚至是安全化。澳大利亚始终狐疑地看待中国在澳方的政治、经济与人文影响,质疑中方正常的投资并购、人员交往、资金往来背后具有“政治目的”。澳方不断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商业投资、正常往来污名化,却始终拿不出任何坚实的、有说服力的关键证据,只能以“莫须有”的罪名和无中生有的方式给中方冠以恶名。澳大利亚以强硬的反华立场来向美国表示战略忠诚、避免被美国“战略抛弃”,在国际社会中传播“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干涉论”,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指责和非难呈不断上升趋势。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全球、澳洲经济前景堪忧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却试图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展开所谓的“独立国际调查”,本质上仍然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防范心理而对中国的污名化行径。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澳美同盟不断升级、地缘政治回归等因素影响,中澳关系正遭遇诸多挑战,未来将面临不小的下行风险。
2.2 澳美同盟不断强化升级
在中澳伙伴关系与澳美安全同盟之间,澳大利亚日益重视澳美同盟的升级而忽视了对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维护。21世纪以前,澳美同盟的实质是维护地区秩序,并未考虑将中国纳入行使同盟义务的范围之内,而随着中国崛起逐渐对澳产生所谓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积极追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动,借助澳美同盟防范中国。澳美同盟的命运与国际格局演变和美国的亚太战略密切相关。由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澳美同盟关系又一次进行重新定位,即从21世纪初的联合反恐,变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28)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77页、第82页。
从近年来澳方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不难看出:澳大利亚日益将中国崛起视为国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在200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担忧;(29)See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May 2, 2009.2016年2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源于“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安”,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亚太秩序的挑战者。(30)See “2016 Defence White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February 25, 2016.虽然在和平时期,澳大利亚可能不愿触怒中国,但澳最终会在任何冲突中站在美国一边,因为在地区事务中保持中立从来不是澳大利亚的选择,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战略利益确保了澳对同盟的坚定支持。(31)Mohan Malik, “The Australia-U.S.-Chin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18, No.4, 2006, p.151.出于对中国崛起和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担忧,澳大利亚希望不断强化澳美同盟以保障自身安全及地区秩序。2018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参加美国州长协会会议期间表示,希望美国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存在,相信美国可以继续保证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并强调美国主导的原则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32)Zhang Jiegen and Li Hongmei, “Australia’s Cognition of the ‘India-Pacific Strategy’,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June 12, 2019, p.121.为了强化澳美同盟,澳大利亚宣布2019年底将派遣一架海上侦察机、2020年初将派出一艘护卫舰,加入美国倡议并领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护航联盟”。澳方军事人员也将就职于位于巴林的“护航联盟”总部。(33)Sam Bateman,“Australia in the Gulf: Will We Make a Difference?”, Lowy Institute, August 27,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australia-gulf-will-we-make-difference.在2020年7月1日发布的《2020国防战略升级》(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和《2020部队武装力量结构计划》(2020 Force Structure Plan)中,澳大利亚认为地区战略环境正在快速恶化,计划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以“塑造地区环境、回击侵略行动”。(34)“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and 2020 Force Structure Plan”,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July 1, 2020.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认为,必须对美国表现出忠诚,因为澳大利亚的不忠诚只会导致美国未来的不忠诚。(35)Iain D. Henry, “Adapt or Atrophy?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in an Age of Power Transi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June 19, 2020, pp.5-6.澳大利亚主动或被动地强化澳美同盟,最根本的考虑是依靠澳美同盟,防范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
2.3 地缘政治逐渐优先于地缘经济
在平衡外交时期,澳大利亚基本维持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平衡,甚至一度对地缘经济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地缘政治的重视。但2016年以来,地缘政治逐渐超越地缘经济成为澳大利亚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而澳大利亚不断倡导、推广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的“印太”概念,甚至准备以牺牲地缘经济利益为代价,尽快将“印太”由概念落实为战略,则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
出于应对中国崛起、避免美国战略收缩等考虑,澳大利亚提出了“印太”构想,并积极与美国进行战略协调,以期实现战略同步。因为澳大利亚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靠对外贸易,非常关注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稳定。澳大利亚认为,一旦中国“控制”了南海地区,将对其国际贸易航线产生严重威胁,甚至可能威胁到关乎澳大利亚战略生存的东南亚、南太地区。随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心理日益加重,澳大利亚精英层越来越认为只有在印太地区与美国实现战略同步,才能彰显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36)高程:“澳大利亚的‘印太’政策:表象、动机与前景”,载李向阳主编:《亚太蓝皮书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东亚之行正式宣示了美国政府对印太地区的新规划与新布局;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用“印太”取代“亚太”,提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37)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46.对此,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甚至不排除联合其他国家将“四方安全对话”扩展为“印太”版“北约”(Quad+)。(38)许少民:“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142页。澳大利亚追随美国,一是为了彰显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和忠诚度,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二是联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三是借助美国实现澳大利亚的“印太构想”——提升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
在2017年的《外交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将“维持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视为其安全与繁荣的首要目标,此白皮书是时隔14年澳大利亚对外交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其中以较大篇幅阐述了澳大利亚的“印太”构想,在136页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提到“印太”地区概念多达60余次。(39)“Australia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ovember 23, 2017, 转引自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第24页。但澳大利亚的“印太”构想受制于自身实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附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构想,借助美国强大的实力实现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2018年以来,地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北邻西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期望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引起美国的重视。澳大利亚试图将地理优势转化为战略价值,为美国提供印太地区构想的“大后方”、延展美国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纵深。
2016年之前,澳大利亚曾努力在中澳伙伴关系与澳美同盟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但是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逐渐视中国崛起为“不确定因素”,不断恶化双边关系,造成中澳伙伴关系日趋紧张。而与之相对的是,澳大利亚日益强调将本国的国家安全与“伟大而强大的盟友”美国进行战略协调,以实现战略同步。综上所述,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通过不断强化澳美同盟、对华强硬保守来防范和制衡中国崛起,说明澳大利亚开始偏离平衡外交立场,对华外交持续滑向失衡。
三、澳大利亚偏离“平衡外交”的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益滑向失衡,反映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国际体系层次的中美权力转移、双边层次的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拉大、国内层次的民粹主义抬头等原因共同助推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滑向失衡。
3.1 中美权力转移加速
中美权力转移的加速对澳大利亚构成了直接、强烈的冲击。澳大利亚认为,随着中美权力转移的加速与中美关系的恶化,推行平衡外交的基础已经受到削弱。二战后,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力量对比日益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亚太地区的权力重心正逐步由美国转向中国。受中美战略竞争冲击,澳大利亚实施平衡外交的空间不断缩小,对华外交逐渐走向失衡。
二战后,澳大利亚一直依赖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国和海外市场。(40)Nick Bisley, “Australia and Asia’s Trilateral Dilemma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Asian Survey, Vol.54, No.2, March/April 2014, pp.297-298.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国逐渐崛起为可与美国一道对澳大利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并很快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市场。(41)“澳大利亚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242/1206x0_681244/,访问时间:2020年7月5日。“显而易见,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亚地区格局,尽管中国似乎远不能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但它的崛起对美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最终在于对军事优势的争夺,中美竞争的关键必须以各自的军事实力来衡量。”(42)Yves-Heng Lim, “Locating Transition: The Prospect for a US-China Transition in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7, 2010, p.934.而2009年以来,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军事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澳美看来,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外交利益,推动军事能力现代化,美国及其太平洋伙伴已经表达了担忧,认为中国过去十年的“和平崛起”可能会让位于更加务实和坚定的立场。(43)Marc Lanteigne, “Water Dragon? China, Power Shifts and Soft Balancing in the South Pacific”, Political Science, Vol.64, No.1, 2012, p.38.
面对中美权力转移加速,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治领导能力严重下降、中国积极有效的抗疫行动成果显著,澳大利亚的焦虑感日甚,视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为一种需要加以防范的“不确定因素”,在强化澳美同盟的同时,也增强自身的战略行动能力,以应对战略环境的变化。
3.2 中澳相对实力变化导致澳对华心态失衡
中澳实力对比的急剧转变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心态复杂。二战后,澳大利亚长期以“中等强国”自居,一直试图在亚太地区发挥特殊影响力。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澳两国联系密切,一度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典范”。(44)侯敏跃著:《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曾积极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各种支持和援助,并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当时,中国向澳大利亚学习澳方发展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两国关系发展总体态势良好,并未出现外交波澜或政治冲突。
然而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依然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发挥中等强国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在亚太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澳相对身份和角色逐渐发生了转变,(45)1978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约是中国的2.2倍;2019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为1.42万亿美元,中国为14.22万亿美元,中国约是澳大利亚的10倍。“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2/weodata/index.aspx,访问时间:2020年6月20日。澳大利亚一时难以调整心态适应新的实力对比。这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舒感”转嫁和投射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致使整个社会都充斥和弥漫着一股急躁感日深、焦虑度日重的倾向。(46)丁工:“澳大利亚对华态度转变的原因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国际论坛》,2018年第5期,第63页。面对中国快速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澳大利亚未能适时紧随时代步伐,其心态调整滞后于中澳实力转变,战略调整滞后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对华心态日渐失衡。
3.3 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而日渐焦虑
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战略收缩、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澳大利亚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为了争取美国保留甚至扩大在亚太、印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澳大利亚力图提升澳美同盟,以避免被美国战略抛弃后独自面对亚太强国——中国。
对于中美权力转移加速,澳大利亚有两点担忧:一是中国军事现代化不断加速与外交影响力不断增长对澳构成的战略“不确定性”,二是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一旦被美国抛弃,则意味着在国际格局加速转型的今天,澳大利亚的安全将无法继续得到有效保障。澳大利亚认为,为了缓解联盟困境、避免被战略抛弃,必须向美国表明自身战略价值和外交立场,以提升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关注和重视程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美国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的中心地位,源于长期以来的一种信念,即澳大利亚的安全依赖于与海上强国保持伙伴关系。此类海上强国早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47)Derek McDougall,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5, No.2, 2010, p.286.但是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优先”、去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严重损害了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澳大利亚,澳美关系开始面临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有意无意疏远澳大利亚的行为让澳方日渐焦虑,澳大利亚担心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会步1969年尼克松主义的后尘——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以利于美国实行战略收缩。
特朗普上任后,更是把政策关注点投向国内,这意味着美国会进一步把相应的资源投入国内,而对美澳同盟的关注和投入势必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对美澳同盟产生不利影响。(48)杨毅:“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澳大利亚安全认知与实践的两难抉择”,《当代亚太》,2017年第3期,第92页。另外,美国有加大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合作的意愿,对澳大利亚来说,此举可能会削弱澳美同盟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避免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大利亚积极追随美国,为美国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提供所需的部队、基地和资源,以此换取美国保护其安全的承诺。(49)George Friedman, “Australia’s Strategy”, Geopolitical Weekly, May 22, 2012, p.2.澳大利亚希望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保持对澳的安全承诺。
3.4 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
受西方民粹主义逆流影响,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也不断抬头,在外交层面即表现为对中国的排斥、疑惧心理不断上升。从2014年欧洲各国议会选举到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2017年特朗普的上台,西方民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澳大利亚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废除了“白澳政策”,但种族主义并未被彻底清除。澳大利亚人可能只是不怎么爱用“种族主义”这个词而已,但当他们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会不自觉地放弃对种族主义的警觉,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支持者。(50)赵昌、张秋生:“论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兼论华人的文化融入问题”,《世界民族》,2017年4期,第38页。不容忽视的是,在西方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国内种族主义渐有抬头之势。
受民粹主义思潮冲击,澳大利亚两大党的对华政策严重受制于澳国内少数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团体。由于自由党和工党两大政党执政基础薄弱,组建联合政府离不开右翼政党的支持,如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等在大选拉锯战中成为两大党竞相拉拢的对象。受此影响,澳大利亚的小党近几年呈异军突起之势,发挥着超过其自身实力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潮的裹挟下,澳民众对华友好程度急剧下降。根据罗伊研究所2019年民调显示,中国在2018年罗伊研究所的“情感温度计”(Feelings thermometer)中的得分为58度,与过去五年的数据相当;然而在2019年,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信任大幅下降至32%,比2018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这是罗伊研究所15年来民意调查中最大的一次下降。(51)“Lowy Institute Poll 2019”, Lowy Institute, June 26, 2019,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lowy-institute-poll-2019.为了迎合国内部分保守团体,澳大部分政客有意激化对华关系,煽动对华敌意,来达到捞取政治资本、巩固执政地位的目的,而这反过来又助推澳民众反华情绪的进一步上升。
四、中国的因应之策
面对澳大利亚对华心态失衡、外交失衡的新动向,中国需冷静观察、理性应对。虽然在中美权力转移未完成之前,澳大利亚对华外交由“平衡”滑向“失衡”恐仍将持续,但不论从提升周边外交环境,还是从预防中澳冲突升级的角度,提升中澳双边关系都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目前,澳大利亚主要针对南海、南太地区等对中国发难。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
4.1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南海问题是澳大利亚关注中国战略动向的焦点,但并不是中澳两国的争端,因为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推行“美国优先”,试图摆脱海外防务负担,加大了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战略收缩的担忧,促使南海争端国产生了改善对华关系的良好愿望,客观上缓解了中国在南海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中国需抓住宝贵机遇,加快与南海争端国签署“南海行为准则”的进度,联合南海沿岸国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减少域外国家澳大利亚过问南海地区事务的动机和可能。中国—东盟共同接受并认同的“南海行为准则”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它的签署将成为展现中国政治领导力和战略信誉的重要机遇,也将有助于打消澳方不必要的担忧和顾虑,使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中国与澳大利亚应就共同关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而非南海争端举行沟通和磋商,以共同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取代在南海竞争地区影响力。
4.2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
面对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加强与南太岛国合作的疑虑,中国可以积极促进与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和南太地区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2017年9月16日,在第三次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与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签署了《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和食品、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52)“中澳签署部门间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年9月18日,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wzs/sjjdt/201709/t20170918_1037675.html。中澳应抓住时机,大力开拓在东南亚、南太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减缓澳对华疑虑、深化中澳战略互信。在澳大利亚质疑中国在南太地区制造“债务陷阱”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邀请澳大利亚采取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同参与的方式来推进南太地区的合作项目,两国应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互补性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能够为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做出贡献,而且确实已经做出了贡献。(53)Jing-Dong Yuan, “Beijing’s Institutional-Balancing Strategies: Rationales, Implementation and Effic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2, No.2, 2018, p.110.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以为南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澳大利亚在金融服务、教育、医疗、能源资源、社会治理等方面拥有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南太岛国应对全球变暖和自然灾害提供帮助。随着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区域主义开放属性越来越显著,且中澳都反对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54)汪诗明:“开放的区域主义与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第54-56页。中澳可以借助南太地区已有平台,共同为南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化相互猜忌为良性互补。如果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参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带动澳相关基础建设行业的发展。(55)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89页。
4.3 以“非安全化”应对“安全化”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南太地缘价值的上升,中国积极参与南太地区合作和地区治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引起了澳大利亚、美国的猜疑和排挤。澳大利亚、美国将中国进入南太“安全化”“污名化”,其对中国参与南太进行“安全化”的本质是运用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来炮制“中国威胁论”,以巩固西方政治霸权。对此,中国应通过积极提供南太地区公共产品,加大话语体系能力建设,与美澳开展开放性合作,打造南太命运共同体,推进南太地区治理来开启“去安全化”进程。南太岛国大多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全球变暖、气候变化、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迫切需要国际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大国竞争。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南太岛国应借助南太地区已有合作平台,注重对于南太地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创新地区合作发展模式,为南太地区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以地缘经济替代地缘政治。
4.4 加大话语体系建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把持着国际社会的话语霸权,澳大利亚一些媒体滥用自身的话语优势来歪曲事实,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南太地区的不安。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尚未建立有效的话语体系,因此更有必要加强在话语能力方面的“软实力”建设,变被动应对为主动作为。中国学者和外事部门可主动发声、敢于发声、善于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和平、负责任的中国国家形象,缓解澳大利亚民众对华疑惧、焦虑心理;与澳大利亚严肃、客观的媒体和学者一道共建多元、自由的舆论环境,避免右翼澳媒和政客把持其国内政策辩论话语权,让其民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当前,中国正处于重塑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话语能力是未来中国提升周边外交的重要课题。
五、结 语
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澳美同盟不断升级、地缘政治回归、民粹主义势头不减等因素影响,中澳关系将面临不小的下行风险,因而未来双边关系可能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甚至存在“急转直下”的危险。新冠疫情虽对中澳关系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上冲击有限,难以彻底扭转澳大利亚对华外交由平衡走向失衡的趋势。未来,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能否重回平衡、中澳关系能否重回正轨,取决于澳方能否放弃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的错误做法。
在平衡外交时代,澳大利亚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连续增长,也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证,外交成绩不可谓不显著。而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偏离平衡外交,澳大利亚的地缘安全、经济繁荣可能不仅难以得到保障,反而面临许多挑战,如失去在中美间转圜的外交空间、被牵连到与己无关的地区冲突、地区影响力继续下滑、深陷联盟困境难以自拔。通过对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分析不难发现,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并不面临“选边站”的战略困境,对澳大利亚而言仍然存在在中美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56)李泽:“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7页。因此,在世界格局日益平衡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回归“平衡外交”、对华外交“再平衡”才是明智之举。如今,中澳关系进入多事之秋,经贸依赖并没有有效发挥中澳关系“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中澳关系以往的合作基础受到冲击,亟需在稳定既有合作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形成新的战略共识,双边关系有望在此基础上校准方向、重新定位、再度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