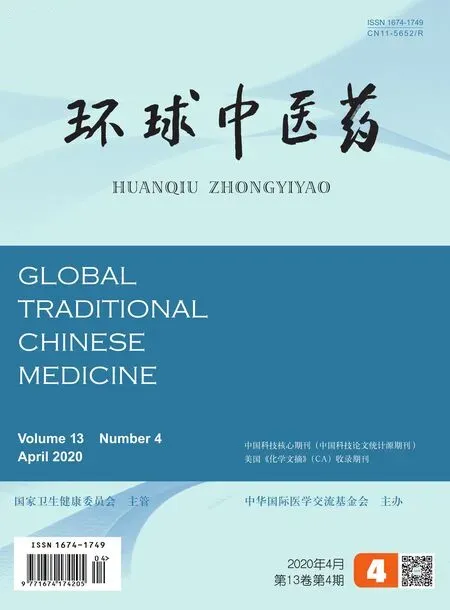从医案看赵辑庵“意法”治病的思路、方法及启示
范曼琪 范嘉伟 方元芝 许能贵
赵辑庵(1877~1938),名赵熙,自号遁仙,为清末民初医家,尤善针灸,因疗效显著而闻名山西,被誉为“三晋名医”。1912年北洋政府欲取消中医,中医事业备受摧残。为使中医不致湮灭,赵老编撰《针灸传真》八卷,并在骑兵团长孙秉彝支持下,于1923年由山西代县石印局出版。后续还完成了作品《夏屋山房笔记》,其中包括中医经典著作阅读笔记、祖传秘方、外科单方、膏药方等,但因民国期间战乱频发,未及出版便毁于战乱。其中关于针灸的《针灸要诀》《按摩十法》《针灸验案》及《针灸经穴图表》四卷内容经其家人转移得以保存,后由其长女赵玉青于1997年将四卷集为一册命名为《针灸要诀与按摩十法》[1]并出版。笔者在研读书中的按摩验案时,对于其用意法治疗疾病深受启发,现将其治疗思路、治疗方法及所受启发详述如下。
1 赵辑庵之意法
“意法”是赵老所撰《按摩十法》中的一法,是根据《针灸大成·卷之五》中“以意通经广按摩”一语,结合自身多年临床经验领悟而得。即医者在治病之时,若审视病因为神志误用而得,则在未行针刺、指针及循切法之前,先细察病人的喜怒哀乐,按照脏气相胜之理,通过言语诱导等方式调理病人之神志,从而使得气血流动通畅,即“以意通经”之义也。其认为“意法”为治神之法,其感至灵至捷,而神气通行如电力之速,故又曰“电行”。
赵辑庵老先生在治病过程中十分看重情志疏导,其将“治神篇”列为《针灸传真治症》的开篇,并强调治病首要是治神,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所说“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凡刺之真,必先治神”。而对于《内经》中“治神”二字,赵老将其理解为:“治”就医者言,“神”就病者言,即是以医者之治法,调病人之神志。赵老认为疾病可由饮食所伤、外感六邪侵袭、房劳不当所得,亦有从神明误用、五志失调而得,而人之神志误用,最足以使得气血流通失常,从而导致机体发病。
1.1 神志误用直接伤及脏腑
《素问·宣明五气篇》将人的精神活动分属五脏而有“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之说[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亦有“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之谓,可见情志活动由五脏精气化生,即情志活动的产生以脏腑精气为物质基础,倘若脏腑精气受损,则情志活动也将受影响;反之,情志失调亦能损伤所主之脏。《灵枢·百病始生》言“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也”[3]。情志不调可致病从内生、五脏六腑受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所言“肝……在志为怒,怒伤肝”“心……在志为喜,喜伤心”“脾……在志为思,思伤脾”“肺……在志为忧,忧伤肺”“肾……在志为恐,恐伤肾”。后世医家对情志不调伤及脏腑亦有阐述,如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气叙论》言“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朱丹溪也在《脉因证治·七情证》中论述了情志不摄而脏腑受损的各种症状表现。
1.2 神志误用扰乱气机
气的运动称为气机,主要有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以其运行不息而激发和调控机体的新陈代谢,推动人体的生命进程。脏腑之气的运动变化,在情志活动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情志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脏腑之气的运动,故情志致病所导致的基本变化亦能体现在气的变化中,如《素问·举痛论篇》云:“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后代医家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中也论述了九气导致心理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赵老在历观《内经》中关于情志方面内容论述后,认为人之神志误用,最易使气血运行失畅,因而喜怒哀乐不节,情志失调,则生百病,故治疗情志病当以“意法”。
2 赵辑庵运用意法治病的方式
通过阅读赵老运用意法治病的验案,笔者认为赵老所用意法即为情志治疗法,并将其总结为情志相胜法、顺情从意法、劝慰开导法3种。
2.1 情志相胜法
情志相胜法是根据情志的五行属性以及五脏的分属关系,通过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来调整不良情绪所致的脏腑阴阳气血失调的方法。心主神志,各种外界信号刺激人体后,心神会将内脏精气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体内脏腑精气的分布状态会随着不同性质的外界刺激而改变,并由此产生相应的情感活动[4]。而五志分属五脏,五志之间存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此即为情志相胜法的运用基础。此法为医者根据人的情志变化相互制约的理论,人为诱导出其“所不胜”的情志变化,用来控制、调节致病的情志,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医方考·情志门》云“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5]。后世医家张从正在其著作中也阐述了以情胜情之法:“悲可以治怒,以怆侧苦楚之言感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赵老认为五脏有五志,则喜怒忧思恐,而五脏各有所胜,各有所制,深刻理解其意义,在辨证论治过程中,若审察病因为情志因素,合理运用情志相胜法来调整不良情绪所导致的脏腑气血阴阳失调,便属于“治神”的内涵。赵老通常是在患者不知情情况下使用情志相胜法,其具体方法多样,通过对患者病情辨证后灵活选择使用。例如赵老治疗人处于暴怒之下,气上而血升、胆为之益张者,便会利用病人最伤心、最可悲的往事使其精气并于肺,由怒生悲,悲极而泪下,而怒气自消,即悲胜怒之义。而对于经历大伤心、大悲哀之事后,泪流不止而气消神惨之人,便会让其家属向患者诉说一件大喜庆、大荣幸事,使得彼精气并于心,由悲转喜,气宣而泪止,即喜胜悲之义。人体神志安然,精神内守,则人不易患病;患病者精神状态好否也将影响病势的发展、转归,情志相胜法治疗核心就在于调神治神,使得气血正常运行、脏腑功能正常发挥,机体生理回归平和状态。
2.2 顺情从意法
顺情从意法是利用欲求对情志的作用规律,顺从患者意念,了解患者的身心需求并予以满足,以化解其心理症结的一种心理疗法[6]。此法在《内经》及其他许多古代文献均有论述,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云“各从其欲,皆行所愿……任其服,乐其俗”。《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云“治之极于一……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灵枢·师传》也指出“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圣济总录·治神》亦有“凡以形体之乖和,神先受之,则凡治病之术,不先致其所欲,正其所念,去其所恶,损其所恐,未有能愈者也”[7]。顺情从欲法通过认真了解患者诉求,找到患者致病的根本原因,进而满足其愿望,从而治愈其原有情志障碍,使其躯体化症状在精神因素影响下慢慢缓解。例如赵老治疗一西关妇人王氏,因其丈夫到外地经商,恰逢战乱发生,该妇女思夫过度,脾气郁结而得软黄病,症见面色发黄、身体困倦、纳差三月余。赵老脉诊时发现其脉沉而缓,两关脉急,便用针泻章门穴两次,而未起效,突然领悟此即为世人所说的“相思病”,利用针灸、中药治疗只能暂开脾气,病因不除不能有好效果,便想到一“治神”之法。让其家属以她丈夫的名义写一封信告知此妇人他过几天就会回家,该妇人接到信后,喜笑颜开,精神好转,此时赵老再为其用针泻两章门穴、两内关穴,没过几日身体黄色渐渐消退,胃口大开。此医案中病人因过于思念丈夫而得病,故赵老在审察病因后,采用顺从病人意念、满足病人要求的方法来化解病人的心理病因,此时再予以针刺,在神的调控下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以抵御疾病,激发自我修复能力,疾病遂得治愈。但运用此法,并非毫无原则的顺从患者欲念,而是倾听患者诉求后,综合评估满足患者诉求对其病情恢复的利弊、方法的可行性及安全性后,针对具体病情实施。
2.3 劝慰开导法
劝慰开导疗法是在了解患者的具体病情,评估其心理状态后,针对性采用语言交流方式进行心理疏导,从致病心因层面纠正其不良情绪的一种心理疗法[7]。这需要医者在治病过程中,用真诚关爱的情怀,耐心地与病人进行充分、到位的沟通与交流,向患者分析疾病的原因和战胜疾病的办法,用言语慢慢诱导启发,消除其沉重的思想顾虑,使患者树立和提高其战胜疾病、争取康复的信心。对此,《灵枢·师传》作出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告”即为严肃地告诉患者疾病产生的原因、性质和预后情况;“语”则为告诉患者,通过及时采取正确得当的医疗措施,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有望战胜疾病并恢复健康;“导”则为指导患者加强生活调摄,帮助其制定协同治疗并促进身体康复的日常生活调养保健方法;“开”则为开导患者保持良好心态,帮助患者消除思想顾虑及心理上的创伤、痛苦和压力。赵老在《按摩十法·按摩验案》中记载了一个利用劝慰开导法治病的案例:赵老的家族侄子天福因腹邪误用补法后,疾病越治越重,卧床不起而大生忧虑,进而成疑怯症,症见面黄肌瘦、身疲厌食,闻见较大声响便骤然惊吓;邀请赵老为他治病时,一直询问治疗能否有效,忧虑不已;赵老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后,认为该患者病因胆气虚而忧思不定,思则脾气结,脾生化气血功能不足而见面黄肌瘦,脾运化水谷功能不足而见身疲、厌食,进而胆气更虚,疾病陷入恶性循环。故此病因神志误用,当治以壮胆气,便告诉患者其脉络气色无一坏象,许诺他最多两至三次针灸治疗便可治愈,告诉患者不必害怕、忧虑。经过这样的言语开导,使得患者胆气壮而忧思消,进而脾气得开而恢复正常的生化及运化功能,仅用此法,患者治愈后未再发。由此可见,审察病因病机后,医者适当的劝慰开导,可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调动了患者机体强大的自我调控能力,有时不用一针一药便治愈患者。赵老数十载临床经验的积累,认为在诊疗过程中,除了针灸、推拿等外治法及药物内服之外,疏解患者致病心结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因而赵老在临证治疗时,十分重视患者情志疏导调节,使其心结得解,所用治法才可效若桴鼓,这与丹溪诊治时重视患者的心理疏导有异曲同工之妙。朱丹溪的朋友载良在《丹溪心法·丹溪翁传》中载丹溪临证时,“以医来见者,未尝不以葆精毓神开其心……凡关于伦理者,尤谆谆教诲,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8]。
3 赵辑庵运用意法治病的启示
意法是赵老根据《针灸大成·卷之五》中“以意通经广按摩”一语,结合日常生活实践及多年临床经验而领悟得来的治神之法。其认为意者,以意通经,调和五志是也。情志太过致病,或直接伤及脏腑,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或扰乱气机,气机不畅进而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故以意法治疗神志误用为病时,便是通过调和精神情志,使得气机得畅,平衡脏腑气血而治愈疾病。赵老在《针灸传真·治神篇》便指出:“盖人之精神气血,互相为用,气为神之使,神为气之帅,神之所注,气即至也”。并列举了习拳艺之人的例子,当他想用手打人时,便握拳而气注于手,想用脚来踢人时,便抬起脚而气注于足,可见意念,即是人的精神活动对于机体气血运行的影响十分明显。古人认为,气不能自行,需有神来引领,故有“神气”之说。《素问·针解篇》也指出:“必正其神,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此亦是赵老所说以意通经之义。赵老在一生诊治过程中,十分重视调和患者情志,运用意法治病的验案不胜其数。其认为患者情志已定,再予以针刺、推拿或药物治疗,便能取得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的治疗效果。通过总结赵老重视“意法治神”的临床经验,笔者得出以下启示。
3.1 医者意也,医者应知晓患者心中所言,从意治病
意在《说文解字》中为“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9]。《灵枢·本神》曰“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可见,意从心,人的精神、情志、思考、智慧都在意的功能范围内,而医者意也,医学行为的实际内涵中始终包括精神、情绪、思虑等心理活动。《后汉书·方技列传》中言“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10]。故欲为上医,需耐心聆听患者症状倾诉,适当引导,病情相关不可错过;仔细观察患者病候表现,皮毛腠理均不可忽略。察言观色,从病人的表情、言语、动作中知晓患者心中意图,从“意”出发而治病。赵老先生临证时,必周察患者症状根本,周全考虑各种致病因素,若为精神不摄、情志不畅致病,则在用药之前先用意,以“意法”去除根本病因,然后用药而见速效。笔者认为,医之为言意也,所以医者临证时,既要倾听病人有声之言了解表面躯体症状,也要细听患者心中无声之言晓得内在精神、心理障碍;治疗时,以医者严谨之言告知患者疾病的原因、发展趋势及转归情况,使得患者了解疾病,有心理情绪因素者,需用针对性言语解开患者心结,并用激励之言鼓舞患者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故医者先知晓患者致病之意,再以意运量,临机应变,辨证论治,辨因论治,治病时意、针、药结合,才可以更快速、更彻底地治愈病人,此亦为赵老先生“意法”治病的根本内涵。
3.2 医学模式转变,辨证论治应强调社会心理因素
伴随现代化社会出现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及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的心理负荷不断加大,身心处于高应激状态,因而,这种以躯体症状为主,且在疾病发生、发展、预后和预防方面与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心身疾病”日益增多。当前医疗模式正由单纯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同时心身医学越来越得以重视及发展,推动医者诊疗思维的改变:从综合、整体观点寻找疾病的原因,而非单纯依赖生物学证据,突出了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现如今大部分临床医师,一方面固守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由于病人数量较多,问诊时间有限,导致其在诊疗过程中只注意生物致病因素,将理化仪器的分析结果作为首位诊断依据,而忽略患者躯体症状背后所掩盖的情绪心理障碍,治疗时仅针对躯体症状,将治愈定义为实验室检查指标的正常,这往往使患者错失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的机会。故《素问·著至教论篇》对医者有以下要求:“……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所谓“中知人事”,《素问·疏五过论篇》便有具体内容指出:“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暴乐暴苦,始乐后苦……封君败伤,及欲候王……离绝菀结,忧恐喜怒……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同时还强调了诊断过程中忽略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治病过失,认为“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故临床医生在诊治过程中,要认识到人的生命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了解病人的喜怒哀乐、地位变迁、生活条件等人事情况后,结合疾病本身制定更完善的治疗方案,才是新医学模式下的辨证论治内涵。
3.3 治病当形神共治,且以“治神”为先
神为形之主,统领人体一切生命活动,人体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气血的正常运行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平衡,均离不开神的统帅和主宰。此即《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所谓“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十二官危”,一项关于女大学生的实验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可使得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下降而减弱机体免疫功能[11],可见负性精神心理意识不仅可以导致疾病,也是导致衰老虚弱的终极原因[12]。形为神之舍,人的思维敏捷、心情安和、心理健康均离不开形的支持和充养。《灵枢·平人绝谷》:“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人体内气血调畅,脏腑之气平和,功能得以正常发挥,才能使人之神明不受扰动。故神形相互为用,正常人体神安而形养,两者协调平衡,患病时则神扰而形伤,故临床治病时需形神共治。《灵枢·九针十二原》曰“粗守形,上守神”,“粗”与“上”不仅反映了治疗技术的高低,更反映了治疗疾病时不同的诊疗思路及治疗层面。粗工只着眼于皮肉筋骨脏腑等形体出现的不适症状而“对症下药”,局限于治疗“人的病”;上工则透过形体的各种不适窥察神机的异常,注重形体与神的统一,整体地调和“病的人”。《内经》十分注重调神、治神,书中条文论述处处可见,并同时论述到某些疾病治疗效果不佳与不良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如《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曰“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谓神不使?岐伯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可见“神不使、神去”是疾病疗效欠佳、预后差的根本原因。这告诫后世学者,治病之时,仅看到有形的脏腑组织损伤所出现的各种现象是不足的,患者形体的局部病变与全身的精、气、神密切相关,故医者更应着眼于整个机体神的得失,通过调整患者的精、气、神,将患者的心神力量转化为其生理效应,从而调动患者的主动祛病能力及自我修护能力,为治愈形体病变提供良好的基础,这才是超越守形之粗,达到形神同治的精神内涵。而医者想要审察患者机体神的得失,就必须如《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所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即需要拥有一颗“感同身受的心”,宁心静气,专心致志,认真仔细倾听患者的诉求,在知晓患者形体病痛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进而全面把握疾病的发展及转归,最后达到神治和顺而形治安泰的治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