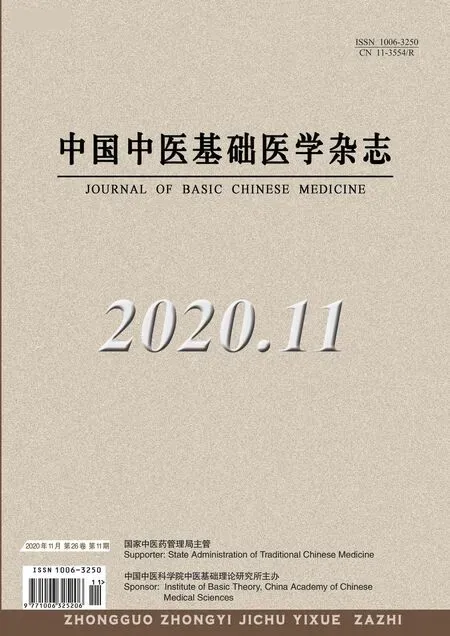《本草述钩元》学术特色探析
韩海伟,柳成刚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150040)
《本草述钩元》为明末儒医刘若金对上起《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中及金元四家、下迄明代诸贤中医药理论的梳理总结之作,其分析异同、去伪存真,耗时30年十易其稿而成。清代名医杨时泰“翻阅数过,爱不能释”,认为“刘潜江文笔萎尔……略其繁芜,则精博自见”[1],故删其繁芜,达其辞理,辑成《本草述钩元》(以下简称《钩元》)三十二卷。该书为明清两位名医对传统中医辨理用药思维的精华凝练,但卷帙浩繁、义理精微,初读易让人望洋兴叹,故梳其脉络、析其大义,以为读者入门之助。
1 《钩元》的学术承启与体例分析
1.1 《钩元》的学术承启
从本草学的演变来看,宋以前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均以药物的性味和主治功效的收集与补充为主。受到宋代理学格物求理思潮的影响,中医学家尝试对药物功效的“理”进行探究,并将对医理的理解扩展为对药理的解释(在此时期医理之外更无药理),于是各家对药理的阐释便烙下了中医学各家学说争鸣的印记。宋徽宗的《圣济经》开此风气,金元诸家则扬其波澜。如张元素论医理重藏象之位与气机升降,他的《医学启源·用药备旨》重视药物的“升、浮、降、沉”。朱丹溪本儒而习医,把周子“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火土木金水”的宇宙演化说引入医理,其《本草衍义补遗》亦重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此时期药物的性味功用在不同著作中存在差异,便是诸家医理争鸣在药学方面的一个体现。
金元时期的诸家争论繁荣了中医学术,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临床用药的混乱,有门派之见者又墨守成规,反而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钩元》针对这一局面,希望“贯串四家,联络一线”,完成中药学说的统一。作者首先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广泛收集各家本草著作中药物的性味主治。其次,作者认为造成中药学混乱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于各家对医理认识的差异和立论角度不同,二是在于诸家论药理缺乏一个统一的模式。于是,书中论理部分既重视对各家医理的沟通融合,又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医理见解,还初步建立了一个中药药理分析模式,形成一个理论自洽且合于临床的中药学体系。刘若金所开创的论理形式和析药模式直接对诸多清代医家产生了启发作用,他们把中药学的研究对象回归到《神农本草经》,产生了《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神农本草经读》《本经疏证》《本草思辨录》等中药学专著,而这些著作又对经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2 《钩元》的体例分析
该书分诸药为水、火、土、金、石(包括卤石)、草(分为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谷、菜、果(分五果、山果、夷果、果之味、果之蓏、水果)、木(分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虫、鳞、介、禽、兽、人总十六部三十二细部。每味药先出某药之名,再言该药花实之时、采收之时、药物颜色性状、出产之地,次言药物性味、《神农本草经》及后世诸书(以金元时期为主)对药物功效的记载,再列体现该药物独特功用的精简效方,又以“论”的形式分析药理和用药禁忌,最后以药物的炮制收尾。
对药效的阐释以及主治功能的扩展应用不是凭空想象的,而应该根据每味药物的气、味、形、色、性推知药物之“理”,进而知其功用以及临证应机变化活用。邹澍总结该分析模式为以“药物生成之时”和“五气、五味、五色”“以明阴阳之升降”[2],书中的体例安排也是为这种模式而设置的。简言之,除了人们熟知的气味属性之外,还须辨析药物的其他属性,如由药物的分部可粗知其清浊(血肉者浊,草木者清)、轻重(草木轻,金石介类重),再由生、成、花、实之时测其禀赋天气之情(如夏枯草夏枯、禀一阴之降,款冬花冬花、禀一阳之生),由所产之地测其禀赋地气之况(如茯苓生于地中能化湿,泽泻生于水中可泄水),由采收之时以测人为对药性的取舍(如采霜后之桑叶禀秋金气厚通于肺,收二月之茵陈禀春生气旺通于肝),由药物的五色可推所入之脏腑气血,由药物形象可测其功力趋向,对药理的“论”在对药物性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展开。这种体例的安排秉承了中医学“司外揣内”思想和由浅入深的论述方法,故《钩元》一书虽庞大而不散乱、深奥而有门径可入。
上文提到金元时期的药理理论实际上是医理的扩展,《钩元》一书继承了此种思想,故书中多以医理释药性,又以药理合医理,熔二者为一炉,提出了一些实用的药物分析方法和医理的独到见解。
2 药理分析举隅
2.1 酸涩二味的分析与运用
《钩元》对药理的分析除了四气五味基本属性外(四气:温、木、生,热、火、长,凉、金、敛,寒、水、藏;五味:酸肝、苦心、甘脾、辛肺、咸肾),又涉及涩酸2味,认为涩为津液收敛气行坚阻之象,应归于肺金。与之相对的为酸味,酸入肝为阳气升而未浮之象(能浮则属心),涩为肺气收而未能藏之象(能藏则属肾),故“酸者阳气之不尽宣,而涩乃阴气之不尽畅也”[2]503。
如书中释矾石其气寒,味酸涩多而咸少。寒为水之气,咸为水之味,涩又属金之敛,能取金之敛“以成其(水)润下之用”,故总结矾石的作用为敛藏阴气、收摄津液。后人又言矾石性燥,实际上并非自身有祛湿的作用,而是因为津液下归,“则在上阳中之阴少,故曰燥”。进而推知矾石对应于人体的病机为阳亢而为风,则阳不行阴反而蚀阴,使寒水所化的津液凝聚为痰;痰湿阻气生热更伤阴气;阴伤不能效其“守阳”之职则风阳更盛。在这种情况下,阴被蚀而不化,阳上腾而不归,如果“欲抑阳而益阴,犹水沃石耳”。用矾石之酸以收阳之亢而为厉,寒涩以敛护津液以消阳蚀,“俾阴气有主,令寒水所凝之痰自消,而亢阳失恃。是由祛痰而风静,由静风而阳化也”[2]81。
临床应用矾石时,既要参考其“主胸中痰癖,除风去热,消风痰热痰,风热喉痛……中风痰厥,风痰痫病,治阴蚀恶疮”等功效,更要辨析患者的病机与所论矾石的药理是否相合。相合虽患者的证候不在药物主治范围之内也可运用,就是临证活用;如果不合,虽证候为药物主治也不可用,是为用药禁忌。
2.2 气、味分析的变通
参合分析药物的气、味常变与“权重”才能更好地分析药理。五味所入并非一成不变,如苦应入心,但因肾为心火对化,心肾互为体用,苦寒类药物味(苦)归气(寒)化,故“凡苦寒之属,类(多)入于肾”。一般来说,气温则能升能补,气寒则能降能泄,若药物气温但味苦甚,则能“从升补中以散之”;若药物气寒但味苦甚,则能“从降泄中以导之”。如厚朴与枳实皆能理气滞,但一苦温一苦寒,且寒邪宜温、湿邪当散,热邪当降、燥邪须破,故“厚朴之治,宜于寒或宜于湿,而枳壳之治,宜于热或宜于燥,当各从其所对以投之”[2]488。
3 医理创见
3.1 重视阴气,发明阴伤的病机
“阳主阴从”的观念深入人心,易使人过度推崇阳的重要性而一味“扶阳抑阴”。《钩元》发扬《黄帝内经》“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的观点进行析辨。盖藏于五脏,血脉之内能制阳气之亢,为营血之源者谓之阴气。阴气盛能使阳和,此合和之气为人身升降收藏的动力,故生理状态下的阴气可称为元气。六腑以阳气之传导变化为用,五脏以阴气之潜藏默运为用,故刘若金总结为:“脏气者,即经所云五脏皆有阴气也”“五脏阴气为人身中元气”。阴气伤损的程度不同,古人又分轻重以立名,“病于阴气不足,即谓之劳,至阴气大伤,谓之劳损,甚则遂云劳绝矣”[2]646-647,古人治劳损之法多从 “阴气”上求便是这个道理。
阴气又为血中之气,能化营入脉,为营血之母,且能行血、摄血使血入脉中循脉道之度而不外溢。故阴气之伤多累及于血,而“诸血证之治,悉以救阴气为主”[2]647。分析血证的病机,其初多由于六淫七情伤人五脏之阴气,阴伤则阳亢化火更迫劫阴气,入经循脉之血遂奔亡于外。火因阴伤而起,故清火只为治标,且苦寒能伤阳以绝阴之化原,故“必图完其阴气,以为营血之母,而善守之”[2]647。如果阴气不行而使痰瘀内生渐成形而为癥瘕,则涤痰活血、消癥破结为治标,益阴气使之行乃为治本。故鳖甲益阴破结之品,朱丹溪发明其功能“补阴气”,以释《神农本草经》主“癥瘕坚积”的深层机理。“方书治肝积肥气、心积伏梁、脾积痞气统以鳖甲为之君,则积之本于阴虚而生者,固不能舍专于阴气之味以奏效也。[2]600”
3.2 融通“阴火”学说,发挥“阴火”治法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以阴火学说解释脾胃病的病理现象:“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3]”李敏等认为,李东垣所论阴火的概念较为广泛,约其病机,“实为脾胃元气亏损,阴阳升降失常,阳陷阴中之证”[4]。
《钩元》提出“夫阴火即水中之火,乃人身元气之根蒂,宜温养,不宜寒泻者也”[2]485“真火在水中,阴火是也”[2]295,人身心火虽然位于上焦,但其根藏于下焦水中,也可以认为下焦水中之火为火之本、真,而上焦心中之火为标、为假,所以古人也称下焦水中之火为真火;因位下为卑位上为尊,亦称之为相火;火藏水中又处阴位,也名阴火。李俊在《圣余医案诠解》中解释道:“水中之火在位则生土而生万物,出位则克金而戕生命。[5]”所谓“当其位则正,非其位则邪”,可知“阴火”之名,既为病理性概念又是生理性概念。
书中进一步阐释阴火下起的机理。由于七情劳逸或六淫邪气伤人后天气血,累及下焦元阴则水不配火,阴不宅阳,亢阳无制。本来温煦生物的三焦元气化为灼土焚金之烈火,即《黄帝内经》所说的“阴虚则无气”。此时阴虚受灼当用寒水所化苦寒之味(如黄柏)以坚阴伏阳,亦即助阴以育阳,则转“壮火食气”为“气食少火”,元气回肾阳自壮。此论阴火起于后天阴气不足者。再者,人身无形之气寓于有形之精血,只有后天之精血充盛才能厚育阴气以制阳亢,若精血不足也能使阴气弱阴火动,或阴火更伤精血使阴气化生无由,此时当或补精髓(天冬、枸杞、女贞之类)或益阴血(熟地、首乌、当归之类)以培阴气之基。又有虚阳上浮无以下归,或阴盛不化拒阳于外,此时虽有阴火热象,内则阳衰,且无阳以化,阴亦不固而见下利、亡血、脱汗等证,此时须或破阴,或温阳,或镇摄,如附子、肉桂、石硫磺之属。当然未发之火为正当养当敛,已发之火为邪当清当散,若阴火烁、肺阴枯燥、天气不清,或肝胆风木随阴火而焚,木挟火势,火助风威,则当清金制木又在言外。
3.3 阐释并扩展“化”的涵义和运用
中医学者多从“气化”角度分析“化”的含义,“气的运动变化过程,称为气化。实际上是指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从生长发育到衰老死亡的整个过程”[6]。气化的动态过程为升降出入[7],但能使气“化”的机理多未曾涉及。
“化是变之渐,变是化之成”。究“变化”的原因,“对待者相摩相荡,相反相求,于是引起变化”[8]。也就是说,事物受到与其自身性质或功能相反的作用,因相反相争最终相化相成,而使事物有变化的产生。《钩元》把阐释宇宙演化规律“化”的概念引入其药理体系,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的常变和药物治病的机理。
阳性本升、出,阴性本降、入,必阳气受到与其相反的阴的反制,因阴的相反相成能使阳“化”,故阳升、出之后又能降、入,从而使阳的作用不“穷”。相对的阴能升、出也是此理。否则,阳不以阴为体则为孤阳,阴不以阳为体则为孤阴,“孤阳不生、孤阴不长”,便不能维持气化正常的升降出入而呈现出病理状态。如书中分析体内风、湿的机理,阳本升散,因阴使阳化,所以阳升而不乱、宣而不散,若阴弱无制则阳不能化,故内生散乱肆虐之风邪。若更进一步分析,阳既变生风邪便不能完成其化阴的作用,阴内郁则生湿邪。阴既生湿,更不能使阳化,互为因果、循环不已,则人之正气暗为消耗。即“阴气不足则阳无以化而为风,阳气不足则阴无以化而为湿,然湿又能化风,即阳之化风者,亦能化湿也”[2]540。
各家所论的气“化”多指阴阳,《钩元》更论及脏腑。某一脏腑必须有与其功能相反脏腑的克制作用使其“化”,方能完成自身的生理功能。如肝木、肺金的功能相对,则肝脏疏通宣散作用只有在肺脏收肃的制约作用下才能发挥出来,“以金化木,木从金化,乃于经气之行最为切要”。临床中有经络气结、痰热壅滞,虽用疏肝理气、清热化痰而不效者,当考虑到肺气不清不能使肝“化”的病机。此时当清肺金而化肝气,肝气化而舒达,则因经络气结而产生的继发病理状态也能迎刃而解,故“结散而经气畅,则热自清,血自化,痰自消”[2]565。再者,既然肝之温升以肺的凉降为体,那么因凉降不足而致肝气不化而为风淫的情况,其治疗绝不可用辛温升散之剂,当“于凉降以成其温升,不使阳之戾气化为风眚”[2]537。一脏腑的病证有可能是相对脏腑“无制”不能使其“化”导致的,故辨病用药可以“正”求,也可以“反”求,《钩元》所论“化”理,对临床辨病用药思路有极大的扩展作用。
《钩元》一书虽为刘杨二家的菁华之作,但杨时泰好友邹澍认为其中仍有缺憾之处。一方面论理尚须驳正,“于金元诸家,无论是非,必欲令成一贯”。另一方面体例略显枝蔓,“篇中每缘论药,竟直论方,并成论病,越畔之思,固难免矣”,这也是造成该书卷帙浩繁、义理艰深的一部分原因。但瑕不掩瑜,在中医药学“基于中医思维,能体现中医药特点,同时也能与中医临床实际相吻合”的研究尚少的今天[9],《本草述钩元》集明以前中药理论之大成,启清代本草学之风气,仍不失为传统中医药临床思维培养的上乘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