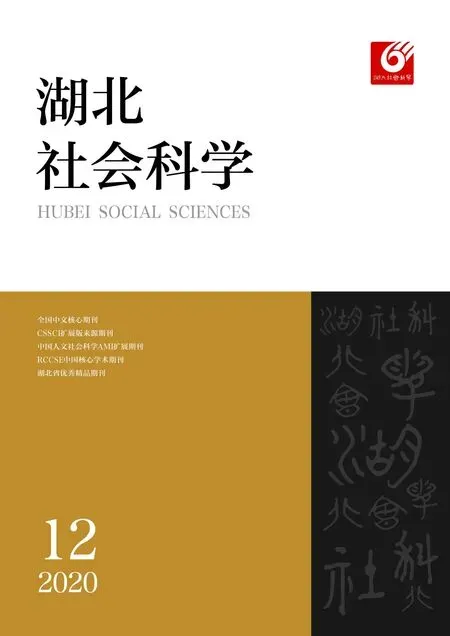网络直播环境下的女性媒介形象异化研究
隗 辉
(武汉东湖学院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212)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2019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在线直播用户有望达到5.01 亿人次,女性主播占49.2%,其中43.3%为娱乐主播,27.3%为游戏主播,23.5%为秀场主播。[1]大量女性参与网络直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群体,她们在大众化的公共表演情境中,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形象,表现自己的才艺,追逐名气和收益,看似实现了“草根”的逆袭,昭示了女性思想、话语权与独立意识的解放。遗憾的是,女性在直播平台获得了形象展示与话语表达权,但却在获利动机作用下集体无意识地放弃自我形象建构与权力表现,潜移默化地异化为“物化”角色乃至于“消费”对象。
一、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媒介形象的外在表现
(一)自我包装下的美女形象。
形象审美属于男女双向化的认知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中,会形成差异化标准。然而其塑造自我形象始终受到社会规制、伦理道德的约束,保持主体认知的平衡,构成了社会形象审美认知与表现情境。网络直播平台所营造的“传”与“受”的虚拟情境,打破了现实生活中形象认知与表现的平衡,女性主播成为内容提供主体,而广大男性网民则成为内容接受主体,依据男性审美标准来建构自我形象成为女性主播提供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美女形象成为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主播所表现出的一个普遍化的形象风格。
其形象包装手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自我装扮,她们大眼睛,白皮肤,纤细身材,长发飘飘,而且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光鲜的衣服;二是技术赋能,借助直播平台自带的“美颜技术”,进行磨皮、祛痘、调整肤色,甚至可以将眼睛变大,将圆脸变成瓜子脸。女主播尊崇现代社会形象审美标准,将自己打造成为男性追求乃至于女性艳羡的理想对象,将世俗化、生活化的审美在虚拟情境中推向极致,强化了人们对于网络直播环境下美女形象的认识。女性主播自我包装成为千篇一律的“秀色可餐”,是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表现出的最直观的媒介形象,追求的是成为广受欢迎的网红。
(二)情境表演下的才女形象。
网络直播属于一个内容建构与传播平台。YYLITV、美拍、斗鱼属于娱乐类直播平台,虎牙、战旗、火猫属于游戏类直播平台,京东、淘宝、唯品会则提供有购物类直播平台。各个平台均拥有大量女主播,形象鲜明、印象深刻的则是部分主播在规定表演情境下所塑造出的才女形象。其在光线明亮、色彩柔和、装饰唯美的室内场景中,或者是表演舞蹈,或者是演唱歌曲,抑或是介绍商品,塑造出一个个具有良好艺术修养、表演能力的才女形象。网络直播在形式上,俨然成为现代女性展示自我、自由发声、张扬个性的重要平台,改变了人们对于普通女性才艺能力的漠视,如同“明星”般地欣赏、审视女性主播,从普通的形象审美上升到才貌崇拜,而这恰恰是催生网红的核心因子。
虎牙直播是最早一批做网络直播的平台之一,其“娱乐天地·星秀”板块设置有好声音、新秀、脱口秀、舞蹈、全偶美女、女团、乐器、颜值八个子栏目,均是以女性主播为主,通过才艺表演建构直播内容,包括“好声音”栏目中的歌唱表演,“脱口秀”栏目中的主题讨论,“舞蹈”栏目中的舞蹈表演,“女团”栏目中的组合歌唱与舞蹈表演,“乐器”栏目中的吹拉弹唱表演。女性群体将个人专业化或者是业余性的才艺集中呈现在直播平台之中,塑造出一个才貌俱佳的现代才女形象,使人们对新时期女性产生艳羡与追求。
(三)温柔可人的淑女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女权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从传统社会“夫为妻纲”迅速进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情境,无论是社会所标榜的优秀女性,还是大众媒体、影音节目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均表现出“女强人”的特点。时至今日,我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思想极大开放,人们在弱化发展诉求而追求美好生活的观念主导下,逐步形成了温柔、体贴、开朗的女性审美标准。“傻白甜”无疑是对此类女性的一种极端刻画。
网络直播具有突出的“互动”优势,女性主播除了呈现优美形象和特殊才艺的直播内容之外,也会展开与观众的沟通、交流活动。其遵循当代女性审美标准,迎合男性审美诉求,形成了呆萌、单纯、娇弱、无心机的语言行为,塑造出一个个温柔可人的淑女形象。系统梳理虎牙直播“娱乐天地·星秀”板块中的各个女主播发现,其普遍表现出温柔、单纯的语言特征,声音温柔娇弱,言辞亲和单纯,表情淡雅呆萌,自然地与观众进行沟通,表现出一种涉世未深、清新脱俗的特征,即便是遇到负面语言,也会轻松地加以化解。网络直播环境下的女主播遵从现实生活中男性对温柔可人的理想女性的审美诉求,将自己打造成“淑女”形象,从而超脱现实女性的形象特征,在虚拟平台中呈现出一个拟真实的媒介形象。
(四)风姿绰约的性感形象。
现实社会中女性塑造审美形象是没有直接利益动机的,而且受限制于社会规制、伦理道德、亲缘氛围的约束,潜移默化中遵循着“无形”的规制、伦理、道德底线,形成了普众接受的女性形象。
网络主播具有匿名特征,抱有强烈的获利动机,而且在竞争激烈的虚拟情境中,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打造风姿绰约的欲女形象,来吸引男性观众,实现大流量、高获利的直播目标。部分女性主播穿着暴露,吊带衣、包臀裙、开叉胸衣十分普遍,甚至出现穿着内衣进行直播的现象。部分女性主播不断地撩拨头发,摆弄身姿,展示胸、臀等部位,而且还通过语言挑逗男性,或者是附和男性观众的色情语言。轻佻的动作与暧昧的语言游走在“道德”与“法律”底线的边缘,风姿绰约,无处不彰显“性”的韵味与暗示,塑造出鲜明的“欲女”形象。这极端化地展现了现时代女性“开放”与“自由”的观念,突破了现实社会中常规认知与普众接受的女性形象,使人们通过虚拟直播平台对当代女性形象产生错位的认识。此种认识在乐观层面表现为开放与自由,是女权进步与升级的直观表现,而在悲观层面则表现为满足与迎合,乃至于色与性的泛滥,暗示女权退化甚至是异化。网络直播环境下的女权主义不再是简单地诉求语言、行为、职业的自由,而是解构女性“无意识”行为背后的规制与自由,形象异化无疑是对其最准确的描述。
二、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媒介形象的内在异化
(一)女性媒介形象被消费倾向突出。
波德里亚在描述当代身体消费现象时强调:“在当代消费的整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珍贵、更美丽、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就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在营销与消费情境中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已经变成了救赎物品。”[2](p216)消费时代的女性身体俨然成为刻意设计与精心包装的商品,理所当然地走进各个营销与消费情境,成为最美的消费品。网络直播兼具营销与消费双重属性,广大女性主播身处身体消费的社会环境与具体情境之中,潜移默化中沦为身体消费的对象,由此所形成的媒介形象也表现出明显的被消费倾向。
“打赏”是网络直播平台评估女性主播价值的核心依据,依附于身体之上的装扮、语言、才艺都沦为赤裸裸的交易。女性主播根据男性观众的审美诉求来制作和包装“身体商品”,直观层面所形成的美女形象、才女形象、淑女形象、欲女形象则均是身体商品化制作与包装的直接结果,背后则是男性观众运用点击、观看、点赞、打赏来“购买”女性主播的身体商品。身体变成女性赚钱的工具,尤其是暴露、轻佻、挑逗、暧昧成为身体商品的“亮点”甚至是“核心价值”。女性媒介形象被消费问题造成女权的退化、女性形象的异化、女性角色的贬抑,而女性不但没有察觉,还乐于其中,不得不说是当代女性的悲哀。
(二)女性媒介形象被规训意识强烈。
福柯认为:“规训反映的是近代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权力技术,既表现为权力干预、监视、训练肉体的技术,同时也是一种制造知识的重要手段。”[3](p351)在传统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构建起社会基本人伦关系,规制、伦理、道德构成了对传统女性行为与形象的权力规训,中间充满暴力、血腥的惩戒手段,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时至今日,女权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女性边缘化地位、受歧视现象仍然存在,权力规训在大众传播与商品社会相结合所构成的男性凝视、女性景观环境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女性身体,促使其按照男性标准与男性幻想来进行装扮和表演。福柯将此描述为“全景敞视主义监狱的规训模式”,也即是“不需要身体暴力和物质禁止,只需要通过‘凝视’,所有的人都在凝视中变得卑微,沦为暴力监视者,看似普泛化的外在监视,实则是个人所施加的。”[3](p216)
女性主播在形式上是内容设计与建构“主体”,实则在权力规训社会环境下以及男性观众全景敞视主义监狱的规训情境中,沦为被凝视的客体,男性的兴趣、审美、诉求与幻想构成其身份认同的“他者”。尤其是网络直播内容的“交易”属性,促使女主播身体在常规“女人身体、男人目光”的凝视与规训机制中融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价值”,强化女性的依附性、从属性、边缘性。网络直播环境下的女性主播看似获得了思想、话语权与独立意识的解放,实则在男性凝视和规训中淹没了个人独立思想与精神,为男性而装扮和表演,甚至不惜改造自己肉体,最终将初步萌发的女性主义意识带入“绝境”。
(三)女性媒介形象符号化导向明显。
女性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指”的身体外表与语言行为背后,暗含着特殊的“能指”内涵,从而构成了丰富、多样、个性、特殊的形象特征。这促成了人们对于女性群体多样性社会角色、生活价值的认识,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女性思想解放、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生活平等的认识。然而在大众传播与商品社会相结合所构成的男性凝视、女性景观环境中,女性群体渐渐沦为符号化的存在。波德里亚提道:“人们离消费商品的本来目的越来越远,附着在商品之上的一个又一个‘泡影’反而成了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这种追求永无止境,一旦赶不上趟便会黯然神伤,伤心欲绝。”[4](p184)这是对消费者心态的直观写照,而作为被消费的商品也在此种消费情境中演化成了一个个“泡影”符号。
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主播的身体以及附在其上的语言、表演行为具有商品属性,此种情境中形成的女性媒介形象也具有了符号化导向特征。首先从表面上来说,女性主播的身体遵循着统一的审美标准,大眼睛、瓜子脸、长头发、白皮肤、苗条身材,乃至于相同的呆萌、单纯、娇弱、无心机的语言行为。这构成了直播环境下女性美的代表符号,成为人们认知、凝视、评价女性美的固化标准,并潜移默化中将此种标准从虚拟情境移植到现实生活,通过男人的凝视形成对广大女性的权力规训。这将直播平台中的女性身体符号引申、固化为社会审美系统,造成社会审美的符号化。其次从内涵上来说,网络直播强化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女性主播隐藏了个人真实的背景,而在镜头前、平台中塑造一个拟真实的虚构形象。这造成男性观众忽略了凝视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将女性主播视为一种美的、可以选择、能够购买的影像符号。此种拟真实的、虚构的影像符号虽然表现为简单化的消费和娱乐,但也造成人们对于女性片面化、简单化认识,“女主播”被视为色情代表符号,便是其重要表现。
(四)女性媒介形象低俗化问题突出。
网络直播平台构成了以主播个人策划、生产、交易内容为主体的娱乐与消费场域。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草根”女主播面向庞大的男性观众,在庞大的竞争压力、强烈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构建的“一脱成名、迅速暴富、不劳而获”的舆论情境中,而通过低俗化的手段来博眼球、求打赏。伦理、道德遇到成名、利益变得不堪一击。
部分女性主播在穿着、语言、动作方面打色情“擦边球”,通过暴露的穿着、轻佻的语言、魅惑的动作来激发、迎合男性观众的性幻想。YYLITV 平台“娱乐”板块中的音乐、舞蹈、脱口秀、美食栏目以女性主播为主,其中“舞蹈”栏目中的主播所设置的直播标题有“S 型性感大静静”“性感170 美腿舞姬小肉肉”“江苏性感尤物美女”“有你的夜晚高潮迭起”“单身少女等你解救”等,内容更是充满挑逗与魅惑。这塑造出“欲女”媒介形象,不仅造成女主播被视为色情代表符号,破坏女性主播的形象,而且会被代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群体,造成人们对年轻女性形成不良认识。部分女性主播为了满足人们猎奇甚至是变态的心理诉求,而呈现出低俗性的直播内容。例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造人事件、偷拍事件、玩黄鳝事件、直播喝酒等,进一步催生人们对于网络女主播低俗形象的认识,甚至形成对当代女性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放纵、道德低下的负面认识。除此之外,部分女性主播还充分利用“宅文化”社会中懒惰、逃避、享受、孤独、不劳而获、自我中心等人性弱点,来打造语言上的“糖衣炮弹”,看似可以为观众带来语言快感,实则催生严重的负面思想。
三、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媒介形象异化的根源
(一)女权退化的现实氛围。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其指出:“父权制下的女性是有别于男性的第二性,网络环境下所塑造的女性表象,也即是在虚拟情境下对作为‘第二性’的女性的媒介再现。”[5](p182)我国数千年来始终保持稳固的父权制思想,对于女性的占有、窥视与欢愉成为权力规训下的符码。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蓬勃进行,国内女性意识觉醒,精神自由、身体独立成为主流,促使女性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父权制关系。时至今日,整个社会浸润于消费环境之中,长期以来作为占有、窥视与欢愉的女性身体也在消费主义情境“交易”与“获利”中沦为“商品”,传统父权制下立足伦理规制而依靠暴力、血腥惩戒手段所形成的女性“第二性”,则在自由表达、自由选择、自由消费的表象下,积极主动、欢快愉悦地沦为父权制下的权力规训对象。当代女性遵从男性诉求的审美标准来包装自我,主动迎合男性凝视来构建自我景观,在男性认知系统中寻求身份认同,甚至主动将身体化为性别隐喻符号,依靠魅惑男性来创造存在价值。消费社会女权的潜在退化构成了现实两性关系情境,而网络直播中女性媒介形象则是此种关系的极致表现。
(二)直播逐利动机的驱使。
快速发展的消费社会,“逐利”成为社群行为的核心动机,女性身体的商品化“生产”与“消费”同样是逐利动机驱使的结果,体现在各种生产、生活、营销、消费情境之中。波德里亚指出:“哪里有对女性对象化、视觉化的消费,哪里就会有满足此种消费的生产。”[2](p126)网络直播环境中女性主播的出现,由此塑造出的美女形象、才女形象、淑女形象、欲女形象,堪称是满足消费的表现。网络直播环境的消费属性,必然催生女性主播逐利动机,包括提高观看人数、扩大直播流量、增加点赞数量、获取丰厚打赏等。大量女性主播来自“草根”阶层,文化修养不高,公共道德意识与法律观念薄弱,而且长期受到大众媒体中一夜暴富、不劳而获、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等负面信息的影响,便在逐利动机驱使下而放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价值判断,甚至是放弃道德底线,践踏法律规制,无原则、无底线地打造“暧昧”内容,迎合男性观众窥视、幻想需求。逐利动机所带来的无底线直播行为必然造成女性主播媒介形象的异化,催生诸多负面观感。
(三)直播平台自身的放任。
各个直播平台为广大女性主播提供了直播空间,并安排有大量的营销宣传、服务引流、技术辅助的支持,通过平台广告、主播带货、打赏分成来获取收益。直播平台无论是作为平台提供者,还是作为利益关联者,乃至于作为普通商业主体,均应承担起“把关人”的角色,加强对女性主播的监督,避免消极行为的出现。然而,直播平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面临着庞大的竞争压力,在法律规制模糊甚至是缺位的情况下,而降低对女性主播的监控力度,放任女性主播无原则、无底线的迎合男性观众的行为。网络直播领域所出现的造人事件、偷拍事件、玩黄鳝事件、直播喝酒等,平台方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等一系列制度,直播平台加强了对直播人员的管理,但打法律“擦边球”、挑战道德“底线”、呈现低俗“内容”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暴露身体、轻佻语言、暧昧动作、不雅行为充斥在直播平台之中,导致女性主播媒介形象异化问题十分明显。
(四)大众集体无意识驱动。
网络媒体与智能终端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促使以反中心、反权威、强调折中主义和个人经验为核心价值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大行其道。人们沉醉于戏仿、拼贴、杂糅的“符号现实”“娱乐现实”乃至于“梦幻现实”之中,模糊了精英与草根、高雅与低俗、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分野,对于所有行为都习以为常,乐见其成,不关注虚构现实背后的真相,更不重视其存在危机。“感官娱乐”与“符码游戏”成为人们接触、评价事物的核心依据。尼尔·波兹曼指出:“大众传媒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提供娱乐性内容,而是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形式表现出来,促使人们超脱生活的压力、烦恼而从娱乐‘鸦片’中寻求精神寄托。”[6](p214)网络直播处于大众娱乐的时代环境之中,提供具有鲜明娱乐性特征的直播内容,面对大众对于过度娱乐、低俗内容、女权退化的集体无意识行为,甚至是强烈的猎奇、窥视、围观动机,导致网络直播环境下的女性主播在利益驱动、监管缺位、观众诉求下,而理所当然地放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价值判断,甚至是呈现低俗内容。女性主播成为一幅全息图上被非现实化了的由各种认知形态因子构成的幻想符号。
四、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媒介形象异化的处理
(一)各级教育部门加强女性意识觉醒和话语权教育。
女性主播是策划、制作和传播直播内容的主体,其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话语权的争取,是解决网络直播环境下女性媒介形象异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推动女权主义发展、营造两性平等社会环境的核心力量。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网络直播中娱乐类、游戏类、秀场类直播以女性为主,67.24%的主播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1]
针对女性主播年轻化的特征,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女性意识觉醒和争取话语权的教育活动,一是培养女生思想解放、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生活平等意识,辩证性地看待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家庭关系所赋予的性别特质和责任,努力从依附、顺从、迎合男性审美与欲望诉求的情境中解脱出来,完成慎独、规制,塑造积极女性形象、角色与权力。二是要培养女生自我意识,深刻认识到消费社会、商品经济对于女性“物化”与“商品化”的异化,拒绝通过迎合、取悦男性而寻求自我价值,更要拒绝通过低俗化、负面性手段来实现经济目的。学校要培养女生通过人格魅力、良好修养、脚踏实地的努力来获得别人的接受与尊重,实现个人经济与社会价值。
(二)大众媒体努力构建两性平等社会环境。
大众传媒时代,每一个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媒体显性信息内容与隐性思想观念的熏陶,潜移默化中形成固化思想与行为。当前,女性群体“第二性”的媒介再现,营销、娱乐、消费领域“物化”与“商品化”的异化传播,沉溺“感官娱乐”与“符码游戏”的媒介体验,乃至于逐步形成的一脱成名、一夜暴富、一蹴而就、不劳而获、金钱至上、物质消费等思想,大众媒体均承担着直接责任。女性主播生活于此种环境之中,长期接受这些思想与精神“食粮”,必然催生不良观念,最终带入到直播活动,表现为女性媒介形象异化问题。
大众媒体需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思想教育、行为引导方面的社会教化功能,有意识地筛选、过滤、选择信息内容,尤其是要关注信息背后所暗含的女性角色、男女关系之类的内涵,重点关注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积极的表现与正确的思想,传播女性身体背后健康的意义与价值,而不是将其视为窥视对象、欲望符号、获利工具、交易商品。大众媒体要宣传符合女权思想、契合时代特征的性别观,抵制、消除女性偏见与歧视,营造平等、和谐、宽容的两性社会环境。为女性主播提供健康精神“食粮”,培养其思想解放、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生活平等意识,从而更好地参与网络直播活动,塑造正面媒介形象。
(三)政府部门构建基于公德性的监管机制。
直播平台是监管女性主播的主体,承担着“把关人”的角色,然而经济利益的刺激和行业竞争压力的驱动促使其很难做到严格把关。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督促、指导、监控直播平台的把关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主播低俗问题,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负面事件,但打法律“擦边球”和挑战道德“底线”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前一阶段的政策规制主要以治理严重低俗事件为核心目标,缺乏对违背社会公德、破坏社会风气等相关行为的细化说明与具体治理。
政府部门应积极构建以社会公德为基础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强调主播人员将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所具有的自尊心、自爱心、自重心和个人对于社会和谐、社会风气、社会文明的责任引入到网络直播工作之中,以社会公德标准来要求直播行为,避免衣着暴露、语言轻佻、行为暧昧、动作魅惑的问题,规避传播极端言论与负面思想。各个直播平台要努力“消化”和“执行”监管制度,结合平台内容、主播身份、观众对象特征,制定更加细化、更具针对性的执行方式,促使女性主播进一步提高个人素养,形成线上与线下一致的道德观,避免出现低俗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