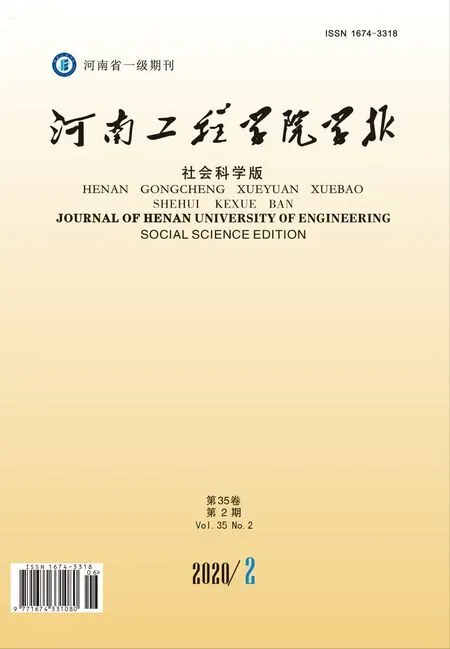《庄子》内篇养“命”哲学论析
兰辉耀
(井冈山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所谓养“命”,就是育养生命之“命”。养“命”和安“命”不无联系。安“命”泛指安顿遭遇不幸和困惑的生命以消解世人生命的困顿,而养“命”则指育养生命以使生命本性达至谐和的境界,二者共同的目的皆是为了提升生命存在的质量和价值。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里的养“命”和安“命”都属于《庄子》所谓“养生”(1)“养生”是《庄子》(本研究引文采用郭庆藩版本: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本有的概念,见于“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M]//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4)、“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庄子·达生[M]//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645)、“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庄子·让王[M]//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971)。实际上,《庄子》的“养生”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其中涵括了安“命”和养“命”的内容,即《庄子》并未对安“命”和养“命”严格分开进行讨论,只要是依据“道”而进行的有益于“命”的实践均在其“养生”的视域之内。实践的范畴。当然,在严格意义上,养“命”无疑有异于安“命”。安“命”侧重安顿生命以免自己的生命遭受损伤,是养生实践的基础课题;而养“命”侧重育养生命以使自己的生命达至谐和状态,是养生实践的高级阶段。二者显然不尽相同。本研究主要探讨生命谐和状态的育养路径。依《庄子》内篇之见,养“命”主要通过“养心”来实现,而“养心”的枢机在于“游心”,即游心于恬淡,游心于道德,游心于生命的真性。
一、“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养“命”原则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通常认为庄子所提的“缘督以为经”是养生的基本原则。从广义上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狭义上说,倒不如直接认为这是庄子保全生命之“命”的基本原则,这从其后的原文便知:“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115这里明显说的是,只要“缘督以为经”就能达到“保身”“全生”的目的,也就是能够达到保全生命的目的。无疑,保全生命是养生实践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也是安顿“命”的主要实现路径。当然,按庄子之见,完整的养生显然不只是保全“命”而已,因为从庄子主张秉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1]160的基本原则来看,它必然也要求提升内在心灵的涵养,也就是要育养一种内心空灵
寂静、谐和的境界。其中“乘物以游心”的意思是心神任随外物的变化而悠游自适,它的直接目的就是“养中”。陈鼓应认为,所谓“养中”就是“主体通过修养的工夫除排名位的拘锁而使心灵达到于空明灵觉之境界”[2]。可见,这里的“中”也就是表达心灵虚空状态的意思。许建良则指出,这里的“中”就是中虚的意思,也就是内心空灵寂静的意思(2)许建良认为,庄子所谓“养中”的“中”与《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中”具有相同的意思,“守中”的“中”就是中虚的意思,也就是内心空灵寂静的意思(参阅:许建良.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43)。。当然,这里的“中”也内含着中和的意蕴,因为既然内心是一种空灵寂静的中虚状态,那么它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中和的状态,所以成玄英把“养中”解释成“养中心”[1]160,疏15也不无道理。合而论之,庄子所侧重育养的是具有空灵寂静的中和之心的“命”,而不是重在强调保养形体意义上的“命”。就狭义而言,肉体的保全不是庄子强调养“命”的主要内容,而是庄子强调如何安“命”的实现路径,只有内心空灵寂静的性命才是庄子所要养成的目标。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养心而不是通过养身来实现内心空灵寂静的生命境界。
当然,庄子认为,通过养心而不是养身或养形来育成具有空灵寂静的中和之心的“命”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既然要育养这样一种心灵和谐的状态,那么通过养心这样的最直接的途径去努力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二是因为庄子认为,对“命”而言,心远比形重要:“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1]275这就是说,人之生命应当有形体的变化而无心神的损伤,有躯体的转化而无精神的死亡。如果说形体发生变化,那么心神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对生命而言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庄子说:“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1]56可见,心的养育对保持生命的存在状态是至关重要的,而形体却显得不那么重要。正如庄子所说的,小猪发觉死去的母猪之后皆“弃之而走”,是因为小猪“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1]209。这是说,小猪发觉死去的母猪虽然形体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母猪的生命状态不一样了,所以小猪皆“弃之而走”,即小猪对母猪的爱,不是爱其形体,而是爱“使其形者”。根据郭象的注解,“使其形者”指的是“才德”的意思,成玄英解释说“才德者,精神也”[1]160,疏3,所以“使其形者”也就是主宰形体的精神。然而,精神的修炼显然必须通过养心来实现。庄子认为,心的育养决定生命的存在状态,所以他强调必须加强对内心的修养,以使个人育成内心空灵寂静的状态和境界,即强调必须坚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1]160的育养原则。
二、“游心乎德之和”的养“命”目标
“养中”的“中”既有中虚(内心空灵寂静)的意思,也暗含中和(中和之心)的意蕴,合而言之,空灵寂静的内心应当是一种中和的状态和境界。对此,庄子有专门的思考和论述。依他之见,心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心莫若和”,这样生命个体就能达到心灵空明的和谐状态。这是庄子对养“命”目标的设定,犹如有学者所言:“庄子所真正关注的是人的自我心灵之和。在他看来,‘和’是生命的应然,它应成为我们终极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3]庄子说: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1]164-165
庄子认为,对于“命”而言,必须做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而且“形就”必须是“不欲入”,如果“形就而入”,就会导致“为颠为灭,为崩为蹶”的后果,也就是会使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根据郭象的注释“就者形顺,入者遂与同”[1]160,注4可知,“形就”而“不欲入”就是顺而不同的意思,“形就而入”就是顺而同之的意思;而“心和”必须是“不欲出”,也就是不过分凸显自己的能耐,因为过分显现自己的话,往往是“为声为名,为妖为孽”,这也同样会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如前文所述,相比于形来说,庄子当然更加看重心的育养,因为心更能决定生命的存在状态,所以“心和”就是庄子内在生命修养的目标,而庄子所说的“心和”之“和”也就是“德之和”,是道德之和,所以庄子又着重强调应当“游心乎德之和”。庄子说: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谓也?”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1]189
其要义是在“命物之化”的基础上实现“游心乎德之和”,即心灵游放于道德和谐的境地,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心灵应当游行在生命本性的和谐轨道中。其中“命物之化”意指顺从万物的变化(3)“命物之化”是指顺从万物的变化。参照郭象注:“以化为命,而无乖迕。”(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190),也就是“顺物自然”[1]294的意思,其本质就是要求“守其宗”,即遵守“道”,而“游心”的枢机也在于循于“道”(4)参照孙以楷、甄长松所说:“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讲,‘顺物’‘游心’的主体就是道,人‘顺物’‘游心’即是法天道。只不过人是有意志的,而天道是自然而然的并没有意志罢了。”(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30)。如果人们依据“道”而使心灵徜徉在“德”的和谐境地里,就自然能从相同的一面去看待万物、涵容万物,即“物视其所一”。不但如此,而且可以做到无视形体的存在和保全,即“不知耳目之所宜”“视丧其足犹遗土也”。依庄子之见,这种“游心乎德之和”的生命样式是心灵和谐的最佳状态,也是生命育养的最高境界。实际上,这种状态或境界就是人们对生命真性的回归和呈现。
三、“心斋”“坐忘”“撄宁”“自得”的养“命”方法
“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养“命”原则及“游心乎德之和”而使生命回归本真状态的育养目标,这两者是具体理论上的运思。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如何养“命”?易言之,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具体演绎生命的育养原则,从而实现“德之和”的育养目标和境界?这是具体方法论上的思考。对此,《庄子》内篇主张以“心斋”“坐忘”“撄宁”“自得”的育养方法,作为育成“德之和”的生命境界的实现路径。
(一)“心斋”
庄子主要是通过持守“游心”以“养中”的原则来养“命”的,也就是主要通过“养心”来实现生命的育成,所以,“心斋”自然就是“养心”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一。易言之,庄子提出“心斋”的育养方法就是自然而然的抉择,因为庄子所说的“养中”是育养中虚之心的意思,而“心斋”也正是达到心灵虚空的途径。庄子说:
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1]146-148
显然,庄子认为,如果“有心”(即有了成心)去做事的话,自然不会是“易”,否则,就与自然之理不合(即“皞天不宜”)了。于是,庄子提出必须先通过“心斋”才行。当然,“心斋”不是“祭祀之斋”,因为“祭祀之斋”只要“不饮酒不茹荤”就可以了。“心斋”是指心灵方面的斋戒,也就是修炼一种清虚的心境,这是借助“气”来达到的心境,因为“气”具有“虚而待物”即空明而能涵容外物的功能,而且只有“道”才能“集”这种清虚之气。这种清虚之气实际上就是指心灵通过修养而达到的空明灵觉的状态或境界,即养成一种清虚的心境(5)陈鼓应认为,“虚而待物”之气是指心境而言的,心灵通过修养活动而达到空明灵觉的境地就称作气(参阅: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34)。,这就是“心斋”。易言之,如许建良所说的,“心斋”是“依靠心灵的气化来推进的,其特点就是虚静,这是‘道’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即‘唯道集虚’”[4]246。客观地说,“心斋”的育养方法并不能直接解决人们在人世间所遇到的种种矛盾或纠纷,其功能主要在于可以修炼一种清虚的心境,即让心灵达至空明灵觉的境地,这样就可以使心灵的一切活动都因循自然之理去进行,即能自然做到外于心知、无心而为地去进行一切心灵层面的活动。于此可见,借助“心斋”的实践方法,有助于完成“游心乎德之和”,即心灵和谐的育养目标和境界。
(二)“坐忘”
应当说,“坐忘”的育养方法和“心斋”具有类似的一面,二者都是强调通过对心灵层面的修养达到育养生命的共同目的,但它们在实际的操作方法上有所不同。“心斋”之法意指心灵斋戒的方法,其功能在于可以修炼一种清虚的心境,即具有让心灵通过修养而达到空明灵觉的作用;而“坐忘”之法意指形神皆忘的方法,其功能在于可以忘掉对自己的一切束缚,达到一种心灵“大通”的境界。庄子说:
颜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282-285
于此可知,庄子所谓的“坐忘”不只是“忘仁义”及“忘礼乐”,而是“形”和“知”必须皆忘,也就是要形神两忘。“堕肢体”就是“离形”,实际上就是忘形,即忘掉形体的限制,意在消解人们源于生理所产生的贪欲,这属于忘形的领域;而“黜聪明”就是“去知”,实际上就是忘智,即忘掉心智的运用,意在摒弃人们源于智巧所产生的伪诈,这属于忘神的范畴。毫无疑问,形体上的贪欲和心智上的伪诈都足以扰乱本当虚静和谐的心灵,所以必须坚决加以扬弃,从而解除对心灵的桎梏。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达到“同于大通”的境界,其中“大通”就是大道(6)成玄英诠释说:“大通,犹大道也。”(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285)的意思,“大通”的境界实际上指的就是大道的境界。既然达到了同于大道的境界,人们自然就不会有是非好恶了,能够冥于大化的流变而不偏执,此即“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这样,心灵和谐的育养目标也就可以实现了。
其实,通过“忘”的方法来育养生命是庄子一贯非常注重的方法。《庄子》内篇反复强调“忘”就是明证说:“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1]108“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1]155“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1]216“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1]242“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1]268“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1]272。这里所列举的这些“忘”作为一种修养方法直接关乎生命本身。
(三)“撄宁”
当世人身处万物生死成毁的纷繁嘈杂、烦扰混乱的环境中时,若能根本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而仍然保持内心的安宁平静,就是庄子所言的“撄宁”。显然,“撄宁”既可以视作生命育养的一种境界,又可以看成生命育养的一种方法。当然,这里仅将其当作育养的一种方法来进行分析。庄子说:
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1]251-253
于此可知,女偊虽然年事已高,但仍“色若孺子”,究其原因就在于其“闻道”了,因为“闻道”后守道三天就能“外天下”(遗忘世故),如此接着再守道七天就能“外物”(不为物役),继而再守道九天就能“外生”(把“命”置之度外)(7)“外天下”“外物”“外生”,顺序由易到难。参照陆长庚、宣颖的诠释。陆长庚:“外天下与外物异,天下远而物近,天下疏而物亲,故外天下易,外物难;外物易,外生难。”(崔大华.庄子歧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295)宣颖:“自天下而物、而生,愈近则愈难外也。”(宣颖.南华经解[M].曹础基,校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53);只要“外生”就能“朝彻”(心境仿佛朝阳初升一般清明洞彻)(8)参照成玄英疏:“死生一观,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启,故谓之朝彻也。”(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254),只要“朝彻”就能“见独”(见到至道的胜境)(9)成玄英疏:“夫至道凝然,妙绝言象,非物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绝待绝对。睹斯胜境,谓之见独。”(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254)识见至道的胜境,实际上,也就是识得和回归自己的本性,故而阮毓崧认为“见独”就相当于“见性”:“独立无对即本性也,见独犹见性也。”(崔大华.庄子歧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238),只要“见独”就能“无古今”(突破时间的限制),只要“无古今”就能“不死不生”(“命”不受生死的束缚)(10)修道者破除妄念之后,自然就进入“无古今”“不死不生”的状态,即不受古今、生死的束缚。杨文会说:“妄念迁流,方有古今之异;既能见独,则妄念全消,过(去)未(来)现在,不出当念……岂有古往今来之定相耶。古今迁流,方有死生去来之相,今证一刹那际三昧,时量全消。迷着妄见生死,实无生死。”(杨文会.杨仁山全集[M].周继旨,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0:307)。而作为“杀生者”和“生生者”的“道”本身就是“不死不生”的。道之为物,一面有所“将”也一面有所“迎”,一面有所“毁”也一面有所“成”。意思是说,就整体宇宙而言,万物无时不处于生死往来的变化运动中。庄子认为,这就叫作“撄宁”。所谓“撄宁”,简言之,就是通过守道修炼而由“撄”入“宁”,即在扰乱中保持安宁。其中,万物的“将”“迎”“毁”“成”就属于“撄”的方面,其演绎的节律是自然产生、自化自成的;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等则属于“宁”的方面,这需要通过人们的修炼而得。因此,“撄宁”的育养方法要求人们面对万物“将”“迎”“毁”“成”的运动变化而不动其心,即通过守道修炼从“外天下”到“不死不生”,逐步实现内心的宁定安然。
可见,庄子认为,倘若通过守道修炼即由“撄”入“宁”,尽管年事已高也能保持“色若孺子”的样态,其关键就在于不动其心,即保持内心的安宁。这就是说,“撄宁”犹如“心斋”和“坐忘”一样能让心灵世界达到寂静和谐的状态和境界,而借以实现生命的育养目标。显然,这种“撄宁” 的养“命”方法无疑启示当今世人,为了提升“命”的内涵和质量而回归生命的本真,就应当安然面对尘劳杂乱、利欲熏心的社会环境而不动其心,始终持守一个安宁淡然的内心世界。
(四)“自得”
如上所述,万物的“将”“迎”“毁”“成”是自然产生的,因为万物无时不处于生成往来的变化运动中,其生命演绎的节律是自化自成的。实际上,这里就暗示世人也需要锤炼和运用“自得”的方法来达到养“命”目标的实现,而不只是通过上述方法的内心修炼而得。庄子说:
古之真人……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1]226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1]296
真人“当而不自得”,真人虽行事得当,但他也“不自得”,即不自己占有行为所获得的成果;历史上的“明王之治”,即使是“功盖天下”也“不自己”,即不显示自己的功劳,而且也不去占有现实的成果,即“游于无有者”。可见,他们对自己行为而获得的成果,皆不以为是自己而得的,即“不自得”,而反倒认为是自然而得的,即“自得”。显然,“自得”就是自然而得的意思,正如许建良所说:“自得是依据‘道’而自然而得的意思,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得,而且这种获得的追求是以他物的价值实现为依归的。”[4]250不难理解,这种“自得”的育养方法主要是强调生命育养的自然无为之特性。从人际关系中来审视,自然无为的“自得”对行为者自己而言,可以自然而然达到育养的目标,而对行为关系里的他人而言自然也是最大的获得,因为自得“充分给予他人自然行为的条件和机会,这些都为最大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最好的条件”[3]250。易言之,“自得”的育养方法不仅可以自然而然提升自己的生命涵养,而且不妨碍甚至有益于行为关系里的他人达到养“命”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在具体的育养方法上,一方面,庄子选择了“心斋”“坐忘”“撄宁”重在内心修炼的操作方法,使人们的心灵世界充满空明与和谐的景象,借以提升自己的生命涵养;另一方面,庄子采取了“自得”即自然而得的行为方法,以此育养自己的生命,这同时也给行为关系里的他者提供了养“命”的条件和机会,最终让自己和他者完满实现养“命”的目标。总之,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四种操作方法,就是庄子所强调的抵达“德之和”之养“命”境界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