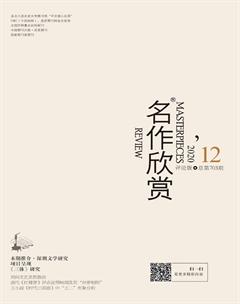《陈太丘与友期行》的叙事艺术
摘 要: 《陈太丘与友期行》是一则志人小说。对于小说的阅读,如果只是关注人物形象,而完全忽视小说的叙事与虚构,未免有失偏颇。笔者从“铺垫与递进”“虚与实”“小与大”三个角度分析了这则志人小说的艺术特色,发现了文本更加丰富的内容与趣味。
关键词:志人小说 叙事 艺术特色
我们知道,《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集,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故明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a 《陈太丘与友期行》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世说新语》在写人上的特色,它通过一则短小的故事,就塑造了一位既聪慧又正直的小孩——陈元方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作为小说的阅读,如果只是关注人物形象,而完全忽视小说的叙述与虚构,未免有失偏颇。因此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就尝试从叙事的角度来谈谈这篇短文的艺术特色。
一、铺垫与递进
《陈太丘与友期行》中的主角是陈元方,然而文章开篇的文字说的却是他父亲以及父亲友人的事情。文章开篇说,“陈太丘与友期行”,约定的时间是“日中”,但是友人过了中午还没有来,于是“太丘舍去”,陈太丘走了以后,友人才赶来。这一段文字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是必不可少的铺垫与交代。
文章后面写到,陈元方当时只有七岁,正在门外嬉戏,友人问元方:“尊君在不?”乍一看,这友人挺懂礼貌的,因为在他的问话中使用了敬称“尊君”。而如果不联系前文的交代,我们则会认为陈元方的回答恰恰是不礼貌的——“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作为长辈,很客气地向陈元方询问他的父亲在不在家,按照一般的逻辑,元方只需要回答在或者不在即可。然而,元方却不这样回答,他告诉友人自己的父亲等待了友人很久,而友人却一直没有来,所以父亲已经离开。这样,陈元方一上来非但没有直接回答友人的问题,还含蓄地指责了友人的迟到,并把父亲离开的责任全部都推到友人的身上。这样,陈元方就显得“尖牙利嘴”,形象多少有点走向负面了!而如果我们联系开篇的交代,原来陈太丘与友人有约在前,约定的时间是“日中”,而友人“过中不至”,太丘这才离开。看样子,友人的确是失信在前,那么陈元方不直接回答友人的问题,反而在言语中暗示友人有错在前所以父亲才离开,就不是蛮不讲理,而是聪慧伶俐了——含蓄指出友人的错误,维护自己父亲的行为。可见,有没有开篇的铺垫与交代,直接关系到陈元方的形象是“尖牙利嘴”还是“聪慧伶俐”,是负面还是正面,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正是因为有开篇的铺垫与交代,我们才觉得友人的愤怒是毫无道理的。既然是有约在先,友人过了约定的时间才到,那么陈太丘不再等待友人独自离开就是合理的,而友人却发脾气说“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就不在理了。正是因为友人失信在前,这会又犯了失礼的错误,所以后面陈元方抓住这两点,直接指出友人“无信”“无礼”的错误,我们才会完全赞同陈元方的所言,并且觉得他真是反应敏捷、思维缜密。友人自知理亏,想要下车来拉元方,而元方“入门不顾”,我们联系前文,就会觉得元方这样做,实在是特别正派的、符合道义的。虽然友人感到了惭愧,还下车来拉元方表示亲近拉拢,但是陈元方一点也没有因为友人的惭愧拉拢而改变对友人的态度,或者收回对友人言行的批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做错了事情,他知错而改,我们大都也是就此作罢(原则性问题除外),不会紧扭着他的错误不放,也不会一直严肃冰冷地对待他(毕竟宽容是我们提倡的美德)。只有七岁的陈元方与大多数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他认为错误就是错误,不能因为人们认错、知错、悔错或者向受害者表现亲近,那个错误就可以揭过不顾,仿佛没有发生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陈元方小小的、倔强的背影,是会升腾出一种敬意的。陈元方身上还没有圆融的世故,还保持着一种“绝对的正直”,而这种“绝对的正直”很多人在成长中把它丢掉了。透过这个七岁的小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魏晋时代名士们的风骨和神韵!
总而言之,《陈太丘与友期行》开篇的铺垫交代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一番交代,后面的故事才能表现出陈元方的聪慧正直,读者才会对陈元方持欣赏赞美的态度。分析完了文章开篇的铺垫交代后,我们再来赏析文章情节结构张力的递进式展开。
文章开篇交代陈太丘与友人相约一起出门,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时分,结果友人过了正午还没有来,陈太丘就先行离去了。这里面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较轻微的,他们尚未见面,连正面冲突都算不上。陈太丘看约定的时间已过,也就独自离开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心理的波澜。这时候的情节的张力可以说很小。随后友人终于来到,他很客气地问元方,“尊君在不”,也许友人带着一种出行的期待,认为陈太丘还在家等着自己,所以此时的他心情是很放松很愉快的。但是陈元方说的是“待君久不至,已去”。这句话没有直接回答友人的问题,但是却暗示友人,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家,而他之所以離开的原因是友人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前来。因此,这句话是在含蓄地指责友人失信。这时候,友人和元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升级,而挑动冲突升级的就是元方。元方其实可以说“家父不在家”,这样的口吻与词语既回答了友人的提问,也不会激起友人的愤怒。然而元方选择了“待君久不至,已去”的回答,一方面元方聪慧,能够采用暗示的方式含蓄地指责友人,一方面元方正直,看到做得不对的事,忍不住就要批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将故事急速地往高潮推进,情节的结构张力越来越强。友人还是听懂了元方绵里藏针的话,暴躁如雷,开始骂人。日常生活中,一个大人对着一个七岁孩子发怒,一般是孩子会被吓到,要么哭着跑开,要么发傻呆住。而陈元方仿佛是就等着友人发怒,然后镇静从容地反驳:“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是怒目以对、高声吼叫,元方则冷静客观、针锋相对。他们二人站在对立的两极,没有调和的可能。此时情节结构张力达到极高程度。友人也不是蛮不讲理之辈,他觉得元方说的话有道理,觉得惭愧,想下车来拉拢元方表示亲近。结果元方头都不回地径直走进家门。这表明元方与友人的对立冲突并没有和解,元方表现出一种“绝对的正直”,友人哪怕“惭愧”“下车引之”,也终究显得无地自容。一个认错想改想得到原谅,一个却紧扭住错误不放,绝不改变态度,这两者的冲突终于达到极致,文章的张力趋于最大。
由此可见,故事的发展其实都是由小小的元方主导的,矛盾的升级及矛盾的不可调和缓解,都是元方性格使然。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篇短小文章的矛盾冲突、结构张力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与意义。
二、虚与实
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法就是虚实结合。
小说主体部分从正面直接表现出了陈元方的聪慧正直。那么,一个七岁的孩子就表现出这样的聪慧与正直,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其实,这个问题文本已经有所暗示,陈元方之所以这样的聪慧正直,特别是他的正直,是受到他父亲陈太丘的影响。陈太丘与友人约定的时间是“日中”,过了“日中”友人没有来,陈太丘就直接走了,他可并没有继续等待。可见,在陈太丘心中,也是把“守时”看得很重要的。他的离开,表现出的就是对“友人”不守时的一种否定。将这个情景置换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如果朋友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有来,我们有多少人会不再等待直接离开的?现代通讯发达,我们可能还会主动联系,问朋友现在在哪里了,打完电话后就继续等待,除非他今天确实来不了了,否则我们很多人不会独自离开。古代通讯不发达,如果友人没到,我们不能立刻与他取得联系,那么是不是我们也会多等等,而不会径直离开?陈太丘的所为与我们很多人都不一样,他是直接离开了的。看来,陈太丘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我们把陈太丘的所作所为与陈元方的联系起来,很容易发现一种因果关系:正是因为陈太丘的性格、气质对陈元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陈元方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与他父亲相似的精神气质。所以,这篇小说实写的是陈元方,但是也间接塑造了陈太丘的形象,这就是叙述中的虚写。
我们所谓的虚实结合,还指小说在叙述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空白”,给了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友人过了正午未到,陈太丘径直离开了,他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他的脸部表情会是怎样的,文章没有写明,但是却不难想象。陈元方在与友人对话过程中,有怎样的心理波澜,有怎样的表情变化,也是很值得咀嚼的。友人一上来是很客气地问元方,“尊君在不?”元方知道父亲已经走了,但如果只是回答“家父已去”,那么就会显得自己父亲失信失礼——明明是与人约定一同出门,怎么自己先离开了呢?为了维护自己父亲的尊严,也是因為元方看不惯友人的迟到、不讲信用,于是元方说“待君久不至,已去”,把父亲离开的原因全推到友人身上,并含蓄指出了友人失信于人。这就是元方的心理活动,而在他回答的时候脸上可能还带着一丝不满呢!有了这些想象与添加,是不是元方的聪慧、正直的形象更加鲜明了呢?友人看来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明明自己失信在前,而且已经被人给指出来了,还好意思说“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面对友人毫无道理地对父亲的侮辱,陈元方肯定要维护自己的父亲。不过与友人的气急败坏、口不择言相比,陈元方的回复有理有据,紧紧抓住友人“失信”“失礼”进行反驳。此时,陈元方内心也许充满了对友人的鄙视与不屑,但是说话的口吻与面部神情可是冷静、镇定而从容的,一股凛然正气弥漫在元方身上。友人感觉惭愧,想下车来拉元方,这是实写。而元方入门不顾,又含有虚写。元方心里可并不接受友人的拉拢亲近,甚至连这个人都不想再见,话都不想与他再说,所以头也不回地走进家门。带着这样的情绪,他的脸上定然是写满了讨厌与鄙弃的。总之,我们将文本中的“空白”之处补充出来,一方面元方正直、聪慧的形象就会更加丰满立体,另一方面小说的内容也大大得到丰富,小说阅读的趣味也就越来越浓郁。
三、小与大
“小与大”也是这篇小说叙述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陈元方只有七岁,是个小孩,属于晚辈,友人是大人,则是长辈。然而在这一场矛盾冲突、言语较量之中,不是大人教训小孩,而是大人情绪失控、口不择言、蛮横无理,小孩却是冷静理智、有理有据、从容不迫。不是长辈把晚辈训得老老实实,而是晚辈将长辈批得羞愧难当。这样的“小大”对立的安排,就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和趣味性。同时这样对立的安排,又用友人衬托出了陈元方的聪慧、正直,将元方的聪慧、正直抬升到更高的水平与境界。
这篇文章的“小大”还指用一件生活小事来表现人物独特性格和精神风貌,让人领略到魏晋时代名士的风骨与神韵,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笔者想要补充的是,这篇小说还用一件生活小事表现出了一个宏大主题。陈太丘与友人相约出行,友人迟到了,陈太丘就独自离开。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生活中的小事,但是整篇小说却把“迟到”上升到“诚信”的高度来加以看待与评价。友人脾气暴躁,情绪冲动的时候随口一句“非人哉”(其实,这骂人可算是文明的了),却被上升到“礼貌”这个高度来看待和评价的。这样,这则短短的故事,就暗含了批评“失信”“失礼”、倡导“守信”“讲礼”的主题,真可谓“以小见大”了!
总之,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从“小说是如何叙事的”,“这样叙事有何意义”这个角度来解读,就会发现小说文本丰富的内容,获得阅读小说的巨大趣味。渐渐地,我们鉴赏小说的能力就会训练起来。
a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8页 。
作 者: 杨宇鹏,文学学士,重庆市巴蜀中学校高级教师、语文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