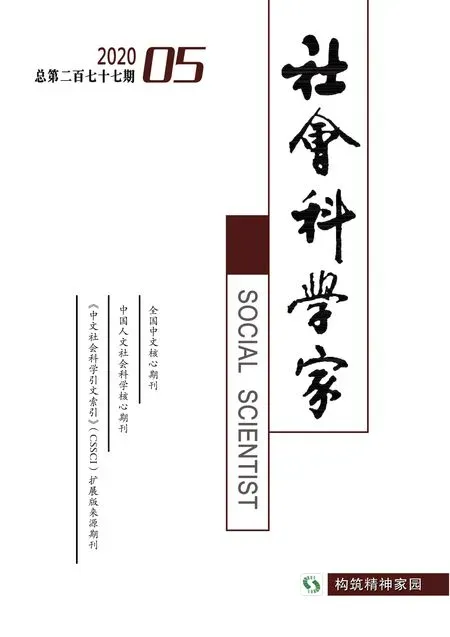西医东渐新路径:晚清时期国际医学会议初探
江 涛,田 涛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后,国际会议获得长足发展,成为国家之间交往和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单就医药卫生领域而言,随着西方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国际性医学会议成为重要的学术与知识交流平台。这些会议既有政府创办,也有民间发起,形式多样,主题丰富,对现代医学的交流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世纪8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与此类国际会议发生联系,先后多次受邀参加在各国举行的国际医学会议,并于1911年在奉天(今沈阳)主办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国内举办医学国际会议的开端。有关晚清时期中国以国际性医学会议为平台开展的活动,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万国鼠疫研究会,而整体性考察较为有限。①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3期;王银:《1911年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略论》,《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焦润明、焦婕:《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马学博:《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建立》,《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7期等。本文主要依据晚清相关史料,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求进一步丰富对晚清西医东渐进程的了解和认识。
一、清政府参与国际医学会议概况
晚清时期,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医学会议涉及诸多领域,如卫生保健、军事医学、医学技术、药学、精神疾病、传染病、残疾人教育、牙科等等。根据可见资料,清政府参加国际医疗卫生会议活动,最早起于光绪七年(1881年)的华盛顿万国医病会,经多方考虑,清政府于最后时刻派时任驻美大臣陈兰彬出席了这次会议。[1]据笔者查阅晚清档案、报刊、驻外使臣著述等资料初步统计,从华盛顿万国医病会举办到清廷覆亡的30余年间,清政府收到的医药卫生类国际会议的邀请至少有58次②数字系笔者根据《晚清国际会议档案》、台北近史所档案馆馆藏史料等初步统计而来,由于划分标准等因素的不同,该数字或有增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卫生博览会之类展会、赛会性质的国际集会与“会议”在性质以及运作方式上有明显区别,本文所论不涉及此类国际集会。之多。从时间分布上来看,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为分水岭,清政府与国际医学会议又可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的约二十年时间里,有10余次会议与中国产生关联,而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及随之而来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也就是1902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受邀的国际医药卫生会议达47次,频率明显高于前一个阶段。这种情况,除国际会议本身的发展之外,还与《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更进一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被列强牢牢掌控有关。这一时期,不但发来邀请的国际会议更多,清政府参加的会议比例也有明显提高,有据可查派员参加了的会议超过半数,其中还不包括清政府相关衙门指示驻外使馆派人参会,但由于缺少相关史料而难以确定是否参加的会议,而在第一个阶段,能够确定派人参加了的会议仅有两次。
经历过如此众多的国际医学会议后,通过考察整个参会过程,从中可以管窥清政府在参加会议过程中的变化或者说进步,这种进步在参会人员的选派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关于人员选派,大体上经历了从象征性出席到专业人员参与的变化过程。已知清政府参加的历次会议中,依据中国方面与会人员的身份,大体可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由清朝驻会议举办国使领馆就近派出外交官出席;一类是由专门派赴会议的医疗专业人员参加,或由医学专业人士及外交官共同参加。在清政府参与的医学国际会议活动中,初期与会者常以外交官为代表,后期则多见医学专业人员出席。
由外交官员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情形多出现于早期,这些人或为驻外大臣,或为使馆参赞、随员、翻译等,考其专业背景,均与医疗卫生并不相关,以他们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原因,或是时间紧迫国内不及派人,或是所派之人“熟悉交涉,强干精明,堪以派往赴会”,[2]专业性并不在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政府对此类国际会议认知有限,并且具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从晚清档案中可见,至晚在同治时期,西方国家举办的国际会议即有邀请中国与会的记录。但出于对列强“协以谋我”的疑虑和担心,清政府对此类活动往往怀有很强的戒备心态,多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即便是派出外交官参与,也要求“但采听众论,不必插议,期于联络之中寓持重之意”[3]。二是缺乏专门的西医人才。尽管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已开始将西方医学输入中国,但清朝官方的西医教育和西医实践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才逐渐展开。缺乏精通西医的专业人才,使中国方面难以选派专业人士与会。晚清时期,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专业性国际会议,清政府常常派出外交官员出席,实则缺乏实际的意义,清朝官方对此也不无认识。1889年美国拟举办万国保护行海船只会议,邀请中国与会,醇亲王奕 就曾建议派专业人员与会,“官阶大小尽可不拘”,即使是在外学习的水师学生,“亦足以资考究,比之以使署人员滥竽充数,徒博会议之名较有实际”。[2]但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形短期内难以改变。直到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对国际会议活动态度趋向于积极,同时也随着国内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医学专业人士才成为这类国际会议主要的参加者。
医学专业人士出现在参会人员名单中,始于1905年的第十四次美国军医会,关于这次会议的派人情况,相关信息散见于多份史料中。1906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邀请清政府派员参加第十五次军医会时提到:“上年第十四次会系于米西干省第得罗得地方举行,美政府及该会甚喜款接中国所派往医生三名。”[2]这份档案从侧面证实了清政府派人参会的事实,至于所派三名医生各为何人,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6年7月致外务部的咨呈中曾有提及,“上年派赴美国第十四次军医会之海军医院总医官何根源,参考新法,学业颇有心得,此次拟请仍派该员前往与会。”[2]至此,另外两份缺乏关键信息的史料才能够获得完整解读。1905年8月,袁世凯行文外务部,“查海军西法医官何根源由北洋军医学堂学生出身,前年派充海天船西医,现在海军供差,年力富强,品学兼优,堪以派赴。兹当即饬该员赴天津医学堂,听候起程前往。”[4]几天后,袁世凯又增派军医徐英扬参加会议,“昨据军医总局徐道具禀,拟调卫生局医官徐英扬与海军医官何根源一同赴会,业经批准,于本月十五日咨呈贵部查照。”[4]袁世凯先后致外务部的这两份咨文虽然没有提及将两人派往哪次会议,但结合一年后的两份档案能够知道,这是在为参加第十四次美国军医会做准备。1905年9月,南洋大臣周馥同样咨文外务部,表示南洋也已派定赴会人选。“查有候选知县钟文邦,于中西医术颇称精善,现充山东中西医院及高等学堂正医官,已奉宪台电调来宁,拟以派赴美军医会,尚堪胜任。”[4]至此,柔克义所说三名医生的确切身份都已得到了证实。从此之后,清政府参加的国际医学会议,专业人士基本上再未缺席。
二、以会议为载体的中外医学交流和互动
通过不断参与国际医学会议,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展开了较为频繁的医学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的形式多样,并不局限于参加会议一途。而且从会议的主题来看,交流和互动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西医,少有关于中医方面的内容。
参会人员在会交流及会后呈递会议相关材料,是中外以国际会议为载体开展医学交流的第一种重要方式。据笔者目力所及,早期的参会人员在会上以听议和记录为主,这既与他们不是医学专业人士,难以展开深入讨论有关,也因为这本身就是清廷派人参会之初对参会人员的要求,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留下在会讨论和交流的记载,到后期医学专业人士逐渐登上会议舞台,中国的参会人员才有了与各国专业人士的在会交流。
1909年8月在挪威白尔根城举行的万国消除麻风病会上,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郑豪发表了一次英文演讲,向世界医学界介绍中国麻风病防治状况及中国医学的发展水平。郑豪在演讲中坦率承认中国在治疗麻风病上处于落后的局面,“在与该病的抗争中,我们落后了很多年。换言之,我们还处于童年时代,中国的医学科学将全力以赴对抗此病”,但他同时表示,“今晚,我高兴能够向你们汇报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过去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都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卓有成效……中国渴望西方的科学,但没有哪一个科学领域比医学来得更为迫切。因此,中国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在此,我们感谢此行带给我们的学习机会和收获,也感谢此行对未来的成果将产生的影响。”[5]通过参加会议,郑豪不仅了解到中国在治疗麻风病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学习到了新的医学知识,同时通过他的演讲,西方国家得以了解中国对抗麻风病的现状以及对抗麻风病的决心,就郑豪参会本身而言,发挥了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作用。
郑豪是留美医学博士,归国后又被授予医科举人,任广州军医学堂总教习等职,他还参与创办了光华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之一),并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除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外,他还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写成《赴那威国白尔根城万国消除麻疯会纪略》一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他挪威之行的收获和感悟。[6]从中外医学交流的角度来看,郑豪的挪威白尔根城之行足以成为一个范例。
并不只是参会人员有所作为,有时驻扎在会议主办国的清廷使臣也会主动向国内提供会议相关信息,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外医学交流的作用。钱恂任驻意大利大臣之时,该国在1909年5月主办了百工人等有危险之事医生研究会,他派员出席会议之余,还考察会议主题,“查此会一部分属于医学之专研,一部分属于慈善之措置……而会议于医校者计七次,议目凡七。”于是会后,他将会议送来的原刊议目一册呈递给外务部以备查照。[2]与钱恂的做法类似,驻法大臣刘式训在巴黎万国卫生公会召开之前,即于1911年4月将该会的卫生专约译呈国内。不过,刘式训此举除了医学因素,还有较多的政治考量,“此次法政府重开卫生公会,适在哈疫恐慌之后,或将修改公约以期推行尽利,将来劝我列约自意中事,在我不得不先行研究以资因应。”[2]此处“哈疫”应是指主要发生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虽然其时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仍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式训预见到不久后召开的万国卫生公会可能对中国产生的政治影响,“兹觅得一九零三年卫生公约及一九零七年专约法文约本,照译汉文刷印成册,除咨送民政部及章厅丞外,特将汉洋文各全份寄呈察阅并备查考”,提醒国内对这种状况早做准备。
除上述交流方式之外,清末被派往国际医学会议的专业人士,通常还被赋予了顺道考察沿途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任务,这也成为中外之间医学交流的重要方式。1905年赴美参加美国军医会的何根源、徐英扬、钟文邦三人,会议结束后并未直接回国,而是借道欧洲考察医学。驻奥大臣杨晟向外务部汇报说:“本年秋间,北洋派赴美国军医会之医员徐英扬、钟文邦、何根源三员在美赴会毕,便道游历欧洲,考查各国医学,日前到奥。经晟函会奥京医会,约期亲自偕同该医员等,到各科医院以及施医所、救济会等处逐一考求。”他称赞三人“言论应对亦颇得当,深为各医士所称许”。[4]此后第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四次美国军医会情形与此类似,与会中国代表会后均展开了考察各国医学的活动。1906年第十五次会议由何根源、陈世华、周贵生三人参加,“兹准会办练兵大臣、直隶总督袁咨称,拟饬该员等留美三月,分赴各制药厂悉心考究,俟回国后集资仿办。”[2]1907年,北洋医务股提调何守仁赴美参加第十六次会议后转赴欧洲,历时半年,考察了英、法、德、奥、意等国的医学,尤其是军事医学。[7]参加第十九次会议的游敬森、粱景昌则在考察欧美医学之外,增加了赴日本的考察。[2]考虑到游、梁二人的语言背景,禁卫军训练处还特意给外务部发函请求帮助,“惟该员只通英文,于日本等国语文素不谙悉,若无通译人员偕同办理,殊多窒碍,特函达贵部,敬祈分电出使各国大臣,于该员到后准在使馆借用译员襄助一切。”[4]被派赴第二十次美国军医会的黄毅、陆昌恩会后则赴德国参观了卫生博览会。[4]
在以个体为单位的中外医学交流之外,晚清时期的部分国际医学会议作为一个整体与清政府相关衙门之间信息、资料的往还也不鲜见。1908年,俄国卫生总会欲创办强迫种痘会,“亟须采取各国之法以为参考之资”[2],特委托俄驻华使臣向清廷民政部索取中国种痘章程,“查种痘事宜,贵国业已办有成效,用特函恳将现行章程及颁行此章程时措置方法一并详示”,表明了希望与中国交流种痘相关事宜的意愿。对于俄国的请求,作为当时医疗事务主管衙门的民政部在指出中国的现实困难后,还是尽力予以满足。“查中国种痘事宜向系各处善堂于每年春间举办,或由地方绅民集资办理,并无一定章程。自光绪三十二年本部创设官医院,规定种痘章程,所有京师内外城关厢种痘事宜统归该医院照章办理。其各省卫生事务、各项章程,前经行文咨取,现尚未据咨报,兹特将本部官医院现行章程抄送咨复贵部。”[2]
除了主动向清政府索取医学资料,还有国际医学会议在会前或者会后主动向清政府送来与会议主题相关的材料。1907年9月举行的柏林第十四次万国卫生民学会,即在会后委托德国外部向清政府寄来了这次会议所订各项条规。[2]稍有遗憾的是,从已知的晚清时期国际医学会议的资料来看,这一崭新的中外医学交流的平台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除了部分会议在派人之初赋予了参会人员考察沿途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任务,其他时候的中国与国际会议的关系中,清政府基本处于单方面满足会议要求的境地,很少主动向会议提出要求或索取资料,对会议成果的落实也少有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三、中外医学交流的高峰:万国鼠疫研究会
在清政府参与的国际医疗卫生会议中,1911年在奉天(今沈阳)举办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是最特殊的一次。它的特殊之处既在于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医学会议,也是晚清时期由中国政府主办的唯一一次国际医学会议,还在于该会举办于中国东北大鼠疫刚刚得到控制之时,因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肆虐东北的大鼠疫,从1910年9月初报告出现咳血患者,到1911年4月疫情得到控制,前后蔓延八个月,疫情从满洲里沿着铁路传播到满洲其他地方,感染范围包括东北三省,然后再跨过山海关,一路经北京、天津,最远到达山东,南北跨度达数千公里。整个疫区统计在册的死亡人数为52462人,如果计入漏报的死者,死亡总人数至少达到6万人。[8]这样一场瘟疫,牵动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神经,世界上与中国有人员、货物往来的国家也不得不绷紧了防疫这根神经。[9]“且以交通被隔而营业受其损,防疫需费而财政受其损,甚至因防疫而邻有责言,更影响于国际,有不独生命损失已者。”因此,“朝廷悯焉,既叠谕民政部及该省疆臣赶速扑灭,复允东三省总督锡良之请,设会于奉天,知照各国政府,遴派医员与会,研究传疫之由,并筹拟防疗扑灭之方法。”[10]为办好这次会议,宣统皇帝还下旨:“所有会中筹备接待事宜,甚关紧要,着东三省总督会同外务部妥速布置,并派施肇基届期赴奉莅会。”[11]
清政府任命正在东北主持抗疫事务的伍连德组织筹备这次会议,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赴东北主持抗疫前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对于首次举办此类国际会议的中国来说,并没有成例可循,衣食住行各方面均需伍连德亲自过问,而此时距开会还有三周时间,伍连德自己也认为,“中国作为一次当代会议的东道主,确实正在经受首次考验”。[8]
1911年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开幕,来自中、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墨等12国的34位正式代表出席会议。东三省总督锡良、钦差施肇基以及中国卫生顾问、各国医士和从事防疫的中国相关部门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等,也列席了会议,参会人员共计130人。[12]由于当时中国抗击鼠疫取得成功的消息经过《泰晤士报》等大量欧美报刊的报道已经传遍世界,伍连德“鼠疫斗士”的名声蜚声中外,这使他能够冲破日本代表团的阻挠,最终被11国专家公推为大会主席。[13]关于日本代表团的阻挠,伍连德在自传中有简略述及,“客人之中,为会议带来最强不和谐音者,当属日本人……他们通过策划南满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已经表明,他们已将包括整个奉天省在内的这片土地视为禁脔。经数日之谋划与调配,派出以著名的北里教授(如今已经年迈,他是世界公认的鼠疫杆菌的发现者)为首的庞大代表团赴会作为第一步,企图压服中国医生接受日本人作为领导者。”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领导者,伍连德认为,“中国科学毋庸置疑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代表必须当仁不让,不落人后。”[8]不过,考虑到北里教授在世界细菌学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在随后的会议过程中,伍连德还是邀请北里教授代替他主持了三次会议,“这一谦恭之举对漫长的会议得以顺利进行贡献良多。”[8]
会议共收到各国代表学术论文24篇,报刊撰稿12篇,大会演说、发言达95人次,会间各国代表发言踊跃,各抒己见,从鼠疫的病名、种类、流行病史、致病菌传染途径、生存能力、治疗、防疫措施及预防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并在当时即有单行本印发,会后又由东三省督都府承办,奉天图书印刷所印刷,1911年11月出版发行。日本、美国、俄国的医学专家还将各自在细菌学、微生物学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会上予以公布,为进一步控制疫情传播提供了依据。[10]4月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举行闭幕式,参会代表随后赶赴北京,于5月1日在紫禁城勤政殿受到了摄政王载沣的接见。至此,万国鼠疫研究会圆满落幕。
伍连德在哈尔滨主持扑灭疫情时,采取了多种手段阻止疫情的蔓延,包括征用货场、作坊、仓库等作为消毒站和临时隔离营;从铁路局借来120个货车车厢用于隔离大量鼠疫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用约两天时间集中火化堆积的约2000具病人尸体;推广佩戴简易口罩等。[8]此外,清廷自上而下也采取了很多防疫措施,以阻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例如加强防疫宣传、停驶火车、限制旅行等。此后疫情的变化证明,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行之有效,从伍连德1910年12月下旬抵达哈尔滨开始对抗疫情,到1911年3月1日记录最后一例病人,当地用时3个月控制住了鼠疫的传播,其他的染疫区域也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使疫情陆续得到了控制。因此,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之时,正是中国基本取得对抗鼠疫取得胜利之时,在此过程中中国医务人员积累了大量有实战意义的对抗疫情的经验,为会议上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万国鼠疫研究会从学术交流成果、宣传、参与人数等方面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万国衣冠联袂一堂,世界硕学东西相会,互倾智囊,罄尽底蕴,将为人群消除祸患,增进福祉,甚足庆幸”[13]。这次会议前后历时26天,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决议45项,确定了多项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事业的发展。[11]会议不仅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还直接促成了东北及京师防疫机构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晚清中国数十年引进西方医学特别是参加国际会议所获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体而言,晚清现代医学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中,参与国际会议活动是学习、引进现代医学一个特定的渠道和方式。国际会议为中外医学界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新平台,包括万国鼠疫会在内的各种国际性医学会议,为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断提供了契机。这些国际性的医学交流活动,也使西方医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晚清西医东渐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