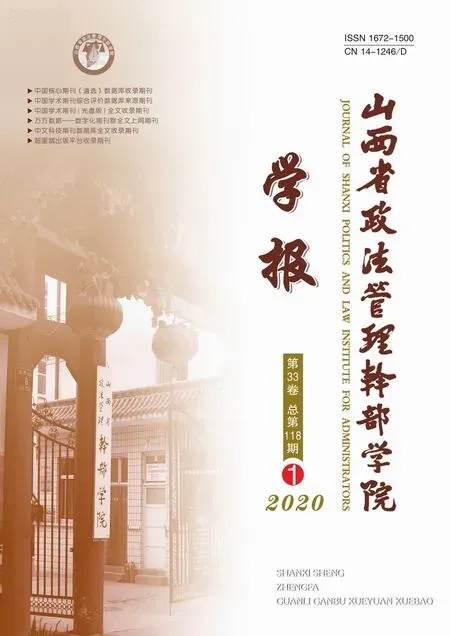通谋虚伪行为浅析
童哲俊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通谋虚伪概述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条,对通谋虚伪的规定描述为:须以他人为相对人而做出的意思表示,系与相对人通谋而只是虚伪地做出的,无效。另一法律行为被虚伪行为隐藏的,适用关于被隐藏的法律行为的规定。而根据最新的《民法总则》文本来看,文本中第一百四十六条对之作出的规定,与德国的描述基本一致。
通谋虚伪,在学理上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根据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的描述,其认为的虚伪行为(即通谋虚伪)指的就是行为的表意人和相对的受领人达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来追求事项不能够生效,也就是说根据卡尔拉伦茨的理论,通谋虚伪需要有表示人的虚伪表示,还需要有首领人接受表示的行为,另外两者需要存在共同行为的合意。而在我国理论界,王利明老师在其表述中认为:虚伪表示行为(即通谋虚伪)是指民事行为的行为人与行为相对人共同通谋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当事人在实际上并不期待该民事行为发生效力。相对于卡尔拉伦茨的理论,笔者认为王利明老师所说的这种概念所展现的构成一方面需要存在共同的不期待民事行为生效的主观心态,另一方面则需要双方当事人共同决定的虚构意思表示行为,显然这种理解更注重双方当事人事先的共同追求虚假表示的一种状态。
而从《民法总则》的文本表述中,笔者认为其更偏向于上述的认定方式,即只需要认定双方行为的依据是一种共同意思表示,而这种共同意思表示是一种共同而为的虚伪的意思表示,只要是如此构成的法律行为,均可以认为是一种通谋虚伪表示下的行为。这种认定方式可以把通谋虚伪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会将个人虚伪表示所作出的单方行为涵括在内,造成过大的周延。
二、通谋虚伪的适用领域
在《民法总则》正式生效之前,我国对于通谋虚伪的规范缺少标准明确的规范,而仅仅是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规定了对于恶意串通而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规定可以认为是解决司法实践中通谋虚伪行为的效力问题的简单规范,但是可以看到国际实践中如德国、法国都已经在其民事法律规范中明确作出了相关的法律规范,故在《民法总则》中也参考德国与法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作出相应的描述。
而在《民法总则》之前也明显可以看到,在旧的法律制度规范之下能够解决的仅仅是合同领域内的民事行为效力或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的民事行为效力问题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那么对于如何处理除合同领域以外法律问题的相关情形以及双方虚假,而非基于恶意串通,或者并没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的问题就陷入了法律的困境。如双方虚假表示协议离婚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等情形,显然从法律条文上来说是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规范的,故在《民法总则》的规范之中我国吸纳了《德国民法典》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
而对于通谋虚伪制度的法律适用范围的问题,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通谋虚伪表示的相关制度不应当仅仅限于有行为相对方的意思表示行为(契约行为),为了应对现实社会实践中更为复杂的民事行为构成,应当将通谋虚伪的相关制度同样适用于没有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行为(单独行为)。
而对于国内的学者,王泽鉴老师在论述通谋虚伪表示的定义时,对其适用范围同时也作出说明,认为“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契约行为、合同行为,以及有行为相对人的单独行为等民事行为,而这些行为无论其是财产上行为(如通过通谋虚伪来达成的不动产买卖,并转移其所有权的行为),或者是身份上行为(如通谋虚伪的虚假离婚行为),均应当被认为有适用余地,但是对于那些无相对人的单独行为(如遗嘱、动产所有权抛弃行为),则不应当适用该制度。”对于以上两位学者的理论,其主要的观点差异在于通谋虚伪表示对于无相对人的单独行为的适用可能性,对于此,笔者首先是对双方表意行为的适用性表示认同,但是对于单方行为,持有保留意见。
从通谋虚伪的名字可见,通谋虚伪的重要构成之一就是通谋行为,这也就意味着为此类法律行为的各方均需要有行为虚伪的意思表示,此为通谋。而对于通谋虚伪的假离婚行为,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均可以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那么显然可以构成所谓的通谋,但是放弃对于某人所享有的债权,显然只需要债权人个人的意思表示,而对于债务人并不需要其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那么如果债权人是因为虚假意思表示做出的放弃债权行为,而债务人并不知道债权人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处理呢?显然不应当适用通谋虚伪的表示,因为此放弃债权的行为只存在一个意思表示,也就没有通谋的空间,故在只有一方做出意思表示所致之行为中,显然不可能构成通谋,也就不应当将之纳入通谋虚伪的规制范围。
综上,在单独行为中对于有相对人的单独行为,还应当根据具体意思表示的数量来进行区分,应当从法律行为的构成中去探究意思表示的具体数量,对于单方虚伪意思表示而成立的行为,显然不应当纳入到通谋虚伪制度所规范的情形之中,而对于双方或多方共同虚伪意思表示而成立的行为,应当认为其具有适用余地。
三、通谋虚伪行为的法律效力
(一)通谋虚伪行为对于当事方的效力
对于当事双方的效力,从通谋虚伪的整个构成来看,当事人的通谋就是通过虚伪的表示来达成一种法律行为,但是其本质上并不希望其所为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行为本身应当带来的法律效果,那么显然,这种法律行为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空有形式的法律行为,那么其必然不应当发生所对应的法律效果。从法理上来说,这也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
在实践中各国也普遍采用了这种理解,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条文表述如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在德国,《德国民法典》在其文本第一百一十七条中规定:“对于相对人所为之意思表示,若与相对人通谋而故为虚伪之表示者,无效。”而作为同属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所订立的法律中采用了与德国及我国相似的一种规定模式。
当然这种意思自治必然需要有一个界限来进行限定,并不可以理所应当地认为所有的通谋虚伪行为均无效,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形是应当排除该条款适用,而认定该通谋虚假表示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
第一,为保障公众信用及交易安全。例如票据行为排除本条之适用。第二,身份行为不应一概认定为无效。例如在日本,日本民法就在条文中作出规定,认为虚伪表示之婚姻是无效婚姻,即使是善意的第三人也不得主张以上婚姻是一种有效婚姻,而在德国则规定为如依法律规范的方式订立的婚姻,也应当认为此婚姻为有效。那么我国在第二种情形下应当采取哪种态度呢,特别是针对虚假表示的离婚行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虚假离婚行为大多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了买房,二是为了逃避债务、藏匿财产。故对于此类通谋虚假表示下的身份行为应当区别对待,对于第一种,因为不涉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应当认定为这就是基于通谋虚伪表示而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从而认定其适用通谋虚伪的制度规范,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对于第二种,因为该行为可能会导致债权人难以实现其完整债权,对于这种影响第三人合法权益法律行为的效力就要再进行分析。
(二)通谋虚伪行为对于第三人的效力
从逃避债务型的假离婚中可以看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往往不仅仅及于当事方,一个法律行为经常会给第三人带来相应的影响,那么这种通谋虚伪表示下的法律行为在对当事人无效的基础上,对于第三方而言其应当具有怎么样的效力呢?
对法律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对于不影响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认为其就是简单的通谋虚伪行为,故而直接认为其应当适用通谋虚伪规范的规制,认定该行为无效。当该法律行为可能带来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变动时就应当对其再进行区分。作为第三人,它是一个排除在法律行为当事人之外的,但是与法律行为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一方。那么就可以从第三方是否参与通谋,将第三人分为恶意第三人和善意第三人,而对于善意第三人和恶意第三人,显然应当做出不同的处理。对于恶意第三人,也就是第三方明知当事人是通谋虚伪而放任之,或者指示或者协同当事人通过通谋虚伪表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一类人,应当认为该通谋虚伪行为对其权利造成的损失是其自愿放弃其原有权力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放弃权利的意思自治的行为,在其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承认其自由意志的自主性,认定通谋虚伪行为并不对其利益造成损害,故该法律行为应当受到通谋虚伪制度的规制,认定其行为对第三人同样无效。而善意第三人就是对此不知情也不应当知道情况的第三方。因为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事方共同虚构的意思表示而影响了自身的权利,基于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其并未做出任何影响自身权益的事情而受到了影响,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此,应当认定这种不直接适用虚假通谋的规定,在认定对当事人无效的基础上,可以以形式生效要件为基础,而赋予善意第三人提出认定行为无效的权利,而这样的方式更可以将第三人权利的决定权交由第三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这样也能够实现对于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以维护整体的民事秩序。
当然,以上通谋虚伪行为针对第三人的效力分析,仅仅针对由于通谋虚伪而直接采取的法律行为本身,而对于通谋虚伪所为的法律行为下所隐藏的隐藏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如法条所明确规定的,依据具体法律规定来判断其效力如何。
(三)通谋虚伪下隐藏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
对于隐藏法律行为,理论界对于该行为的定义表述为:“隐藏行为,是指隐藏于虚伪表示中依其真意所欲订立的法律行为”。而隐藏法律行为的常见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由当事人双方通过虚构买卖关系而达成实际上的赠与行为,或者为了实现避税而故意签订低于实际成交价格的买卖合同等行为,赠与行为和避税行为就是隐藏行为。
对于此类隐藏法律行为,德国在其《德国民法典》文本的第一百一十七条中规定为:“因虚伪行为,致另一法律行为隐藏的,适用关于该隐藏的法律行为的规定。”而在此之外,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其《民法》中,第八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为:“虚伪意思表示,隐藏他项法律行为,适用关于该项法律行为之规定。”通过两个法域对于隐藏法律行为的司法实践,体现出现代法律对于隐藏法律行为的思考。
从法律行为的构成来看,显然这种隐藏行为才是通谋虚伪行为当事方意求达到的法律结果,也就意味着这种隐藏法律行为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行为,故应当认为其是独立于通谋虚伪行为的独立法律行为,故其效力不应当受到通谋虚伪行为效力的影响,而应当依据规范隐藏法律行为所涉及法律关系的相关法律来进行考量。
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条文描述,是在充分考虑了理论基础和国内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移植了《德国民法典》中对于通谋虚伪行为的相关规范模式,进而表述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但是具体而言,这种隐藏法律行为对于第三方的行为效力是否应当同样进行分析呢?笔者认为,对于第三人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主张恶意第三人的表面法律行为效力是失效的,那么是否可以将隐藏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规定应用于通谋虚伪行为下的恶意第三人呢?笔者认为还应当进行区分,即对恶意第三人的恶意范围进行区分,即对于该第三人是否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存在,如果该恶意第三人的恶意范围及于该隐藏法律行为,那么笔者认为,该隐藏法律行为的真实法律效果应当同样及于该恶意第三人,只有这样的处理模式才能使各方真正追求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各方之间形成效力,并能对真正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与规范。
四、总结
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条文描述,实际上就是我国对“通谋虚伪行为”作出的相应民事法律规范,从该制度的根源来看,也是我国对于德国相应的“虚伪行为”制度的法律移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相应的学理和实践创新。目前,仅在《民法总则》中做了相关规定,具体的解释和适用还需要相应的完善。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条文的适用范围,以及对于行为外不同性质第三人的效力问题,还有就是隐藏法律行为的效力这三大方面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以及优化,以适应我国的社会现实,主要就是将无对象的单独行为排除在通谋虚伪的制度之外,并对第三人进行区分对待,对于恶意的第三人,即明知当事人是通谋虚伪而放任之,或者指示或者协同当事人通过通谋虚伪表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该通谋虚伪而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对其应当无效,而对于善意的第三人,因其行为是基于善意的信任,故应当认为在其善意范围内的通谋虚伪行为有效,以保障其合法的利益。而对于隐藏法律行为关系,笔者同样认为应当以第三人的恶意范围作为判断标准,来确定各方之间真正的法律关系,从而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