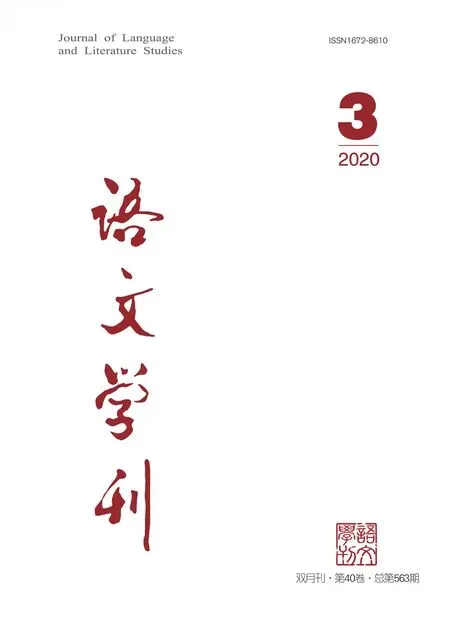丛林法则与帝国情怀:《丛林之书》概念隐喻分析
○ 高艳丽 刘晓庆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一、引 言
约瑟夫· 鲁德亚德· 吉卜林(1865-1936)是英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英国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布拉德布里在其著作《现代英国小说》中这样评价他:“吉卜林被许多人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作家。”[1]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以《丛林之书》最为出名。它不仅仅讲述的是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之间的故事,更是借助动物之间的童话故事来表达吉卜林的帝国思想及殖民主张。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和主张使得《丛林之书》超越了一般的童话故事,变得更有深度,受到成人和评论家的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部作品进行了解读,主要是从丛林法则与帝国关系、身份认同危机以及东西方文化融合三个角度分析《丛林之书》[2],以及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丛林之书》中“丛林法律”的具体所指[3],以此揭示人类的虚伪、肤浅与堕落。
二、丛林法则与帝国法则
美国语言学家拉考夫(Lakoff)和杰森(Johnson)撰写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对隐喻加以新的阐释:“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其本质从根本上说是隐喻性的。”[4]即隐喻的本质是目标域和源域的映射。在此书中,拉考夫把概念隐喻分为三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丛林之书》中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其实就是帝国世界的法则,这是一种本体隐喻。本体“丛林法则”和喻体“帝国法则”的映射,在动物世界的生存和人类社会资产阶级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将两个概念连接起来,将动物的生存法则映射到人类社会。
《丛林之书》中的《莫格里的兄弟们》《卡奥捕猎》和《老虎!老虎!》都是关于莫格里的故事,讲述的是莫格里的父亲,在一次上山的途中遭到老虎希尔汗的袭击,致使尚在襁褓中的莫格里流落森林,被狼群收养,从此与狼为伴。在森林里,棕熊巴鲁教会他丛林法则,在动物朋友黑豹巴希拉等的帮助下,最终杀死了邪恶的老虎希尔汗。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不同于封建专制权力的强制制度,资产阶级将现代社会控制方式转化为一种隐性的奴役,其本质就是规训,形成以一种自觉被遵守的纪律为生存原则的自拘性。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 既发现了自由权利,也发明了纪律[5]249。传统专制奴役制度下肉体可见的暴力,如皮鞭和屠刀下的顺从未必是最好的实现形式,资产阶级通过“纪律”支配肉体达到的顺从是一种控制的艺术,被支配者则认为是自主性的民主和自由的实现[6]。在资产阶级隐性奴役下,被支配者无意识、无条件地被“纪律”“法则”控制了自己的语言、思想和行动。
每个故事的开始都有一首诗歌,《丛林夜之歌》 是《莫格里的兄弟们》的开始,也是“丛林法则”的序幕。“蝙蝠蒙释放了黑夜——现在鸢鹰兰恩把它带回了家,牛羊关在牛棚和小屋……噢,听那号子!——都捕猎顺利,遵守丛林法则的兽民们!”[7]2书中开始就强调“丛林法则”,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们都必须要遵从,丛林中的动物世界其实就是我们人类世界,“丛林法则”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法律法规,人们都要遵从“规则”,在“规则”的范围内生活。书中写道,根据丛林法则的规定,狼群中的幼崽必须带到族群议会,接受其他狼的检视,族群里任何成年狼不得杀死幼崽,否则受到的惩罚就是处死[7]8。从这里不难看出,“丛林法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弱肉强食的杀戮法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秩序和规范,是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们必须遵守的纪律规范。狼族就是在帝国法则的约束下的帝国公民,法则的实质是维护帝国的利益。这是吉卜林所期望的帝国世界,人们要遵守法则,有秩序地生活。
《卡奥捕猎》中更加强调规则的重要性。狼孩莫格里在老棕熊巴鲁的教导下学习着丛林里的捕猎规则。只要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地范围之内捕猎都要大声吼叫直到得到呼应之后才可以捕猎,意思是告诉它们正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请求在此捕猎,而收到的回复就是只可以捕猎不能取闹[7]25。捕猎前的吼叫及回应就是在殖民侵略前要得到英帝国的允许,帝国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帝国权力之上。除此之外,巴鲁还教会莫格里树林和水的法则,这样才能在丛林中更好地生存。与之相反,丛林中的猴民是一个禁忌,因为它们没有规则可言,做事没有任何计划,被认为是下流货。猴民出于玩闹把莫格里强行带到一座废弃的印度城市,因为它们毫无规则和章法。最终在棕熊巴鲁、黑豹巴希拉和蟒蛇卡奥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营救出了莫格里。遵守法则必然会取得胜利,而与法则相违背的必然走向失败。吉卜林隐晦地表达出大英帝国的强大是建立在规则之上,正是因为人们遵从这些法则才使得英国变得强大,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法则保障人们的权益和利益。
《老虎!老虎!》中的帝国意识更加清晰。自从岩石会议和狼族大战后,狼王阿凯拉被废黜,丛林世界对莫格里关闭了大门,他不得不离开狼群到人类世界。他在他出生的地方重新学习人类的习俗,学习人类的生存技能。在一次放牛的途中,莫格里成功利用牛群杀死了老虎希尔汗,但也因此被人类认为他会巫术遭到驱逐。他又回到了狼族,并拥立老狼王阿凯拉。莫格里作为人类生活在狼群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杀死威胁者,他充满智慧、冷静、勇敢、无私,无疑是吉卜林心中帝国的管理者。拥立老狼王则充分体现出吉卜林的忠诚意识,忠诚于女王、忠诚于英国,即使他一直工作、生活在印度,但是骨子里的每一滴血液都在宣誓他只属于英国。
福柯认为资产阶级政治运作是隐性的机制,不起眼的“小过程”往往至关重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支持,最终组成政治蓝图。在他看来,“政治解剖学”“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的”[5]156。不是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最大的政治,“丛林法则”实则是帝国法则的隐喻,被“法则”支配的人,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都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公正的法则可规范人们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但帝国法则是加入帝国主义元素后的法则,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剥削和压榨殖民地的武器。
三、帝国法则与殖民主义
1588年,英国在女王伊丽莎白的领导下,击败了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成功崛起。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进一步强大起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范围扩大。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殖民地已经遍布各大洲。通过殖民控制,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英国的联系变得紧密,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帝国主义国家。
动物世界领地的扩张就是现实世界殖民扩张的缩影。“隐喻均有蕴涵,隐喻通过其蕴涵来突显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并使之连贯。特定的隐喻可能是突显和准确连贯组织经验的这些方面的唯一方法。隐喻可以创造现实,尤其是社会现实。因此隐喻可以成为未来行动的指南。”[8]143隐喻突显某些现实,是连接文本与现实的桥梁,借助隐喻手段,可以分析文本中的殖民主义在现实中的本质内涵。殖民扩张常常是帝国文明与武力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已经屈服的殖民地人民逐渐形成“殖民地心态”,否认自己的尊严,接受卑贱的地位,依附殖民者的统治[9]。《白海豹》中,海豹群面对同伴被“长着黑头发和扁红脸”的捕海豹首领克里克·布特林屠杀,家人及同伴的冷漠态度让白海豹柯提卡很是不解。
“我很孤单,非常孤单!”柯提卡说道,“他们正在所有的海滩上屠杀所有的单身汉!”
那只海豹转头朝向内陆,“胡说!”他说道,“你的朋友们还和以前一样在大声吵闹。你一定是看到老克里克把一群海豹剥光了。他都那样干了三十年了。”[7]77-78
就连他温柔的妈妈玛特卡也说:“你永远也不可能阻止屠杀。到海边去玩吧,柯提卡。”[7]79
人类已经在此屠杀海豹30年,除了柯提卡,所有的海豹早已形成“殖民地心态”,面对同伴的死亡漠不关心,理所当然地认为屠杀是合理的。柯提卡无法接受人类的残忍和同伴的冷漠,决心寻求新岛屿。经过不懈的努力,柯提卡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清静和安全的场所。寻找新的岛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场新的殖民扩张,海豹们没有经过海牛的允许擅自在它们的领地定居。带领海豹们前往新的岛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海豹们的“殖民心态” 一时很难改变。它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人类的统治之下,它们其实是被人类“奴化”,对于同伴遭受到的迫害习以为常,不再想着如何反抗,而是默默承受着一切。结构隐喻是拉考夫提出的概念隐喻中的一类,指通过一个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域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结构保持不变,即各自的构成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4]6。通过概念隐喻将动物的“奴化”现象与殖民主义的“奴化”相映射。这种被殖民主义“奴化”的心态在当时的印度体现得淋漓尽致。东印度公司为了避免印度人民大规模反抗,仍然保留纳瓦布等印度官职,按公司旨意行事,强化他们的奴化心理,使他们听命于公司,唯英帝国之命是从。殖民主义是奴化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手段,通过武力使人们屈服,通过利益引诱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成为帝国的奴隶。
四、帝国法则与“白人至上”原则
欧洲封建社会的天主教宣称社会阶级是由上帝决定,从而将人划分不同的等级。到15世纪中叶,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发展,为摆脱封建社会的束缚,新教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武器。加尔文宣扬“宿命论”和“上帝的旨意”,认为不断增长的财富是上帝给予人类最高的恩惠[10]。恩格斯称之为 “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11]。种族主义始终是为阶级服务的,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查尔斯·卢卡斯认为大不列颠人民有着共同的文化和信仰,殖民地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人的优秀品质,有色人种之所以在殖民地享受不到充分的权利,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无力肩负管理他人的重任[12]。“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件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事物。”[8 ]3借助隐喻可以分析作者潜在的种族意识,以此更好地解读文本。受宗教影响,种族的优越性深深地烙印在每个殖民者的心里,吉卜林也不例外。
《白海豹》中的主人公柯提卡是一只罕见的白海豹,它机智、果敢,带领族群找到了传说中的“伊甸园”,避免了被无止境的屠杀。借助本体隐喻,可以发现“白海豹”实则暗指“白人”,柯提卡在族群中能脱颖而出,实则表明白人的种族优越性,白海豹展现出的优越性实际映射出的是白人的优越性。英国殖民者认为印度土著居民在其统治下摆脱过去的愚昧,给他们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科技,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成就。但获得这些好处的前提是帝国控制殖民地资源,进行大规模掠夺,他们忽视了印度土著居民所受到的迫害。
《女王陛下的侍从们》更是用“野蛮”来形容埃米尔国王:“总督正在接待阿富汗埃米尔的来访——那是一位来自一个非常野蛮国家的野蛮国王。这位埃米尔随身带了一个有八百人的护卫队,他们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营地或是火车头——这些野蛮人和野蛮人的马来自中东后面的某地。”[7]127这些来自埃米尔的访客们从来没有见过正统军队,没有见过火车。先进的文明和技术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种族优越感,把落后的国家称之为野蛮的国家,就连国王都要用野蛮来修饰。
他们也遵守命令,就和人一样。骡子、马、大象还有公牛,他们遵从自己主人的命令,他们的主人听令于他们的中士,中士听令中尉,中尉听令上尉,上尉听令少校,少校听令上将,上将听令统领三个团的旅长,旅长听令将军,将军又遵从总督,总督就是女王的侍从。就是这么完成的[7]142。
“要是在阿富汗也是这样就好了!”酋长说道,“因为在阿富汗,我们只听从自己的意愿”。
“也正是因为那原因,”那位本地的官员捋着胡子说道,“你们不服从的埃米尔必须来这里听从我们总督的指令啊”[7]142-143。
官员用傲慢的语气和来自阿富汗的酋长交流,言语间透露着不屑,因为他对自己国家的统治感到自豪,从动物到人所有的一切都在女王的控制下有序地运转。而那位远道而来的国王也只不过是依附于帝国。官员对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透露出优越感。他坚信只有白人才有能力控制一切,也只有白人才能肩负起重任。一如当时被殖民的印度,白人统治着印度的一切,种族色彩在当时体现得更加突出,从经济命脉、政治导向到文化传播都是依靠白人。土著居民没有丝毫话语权,他们被边缘化,是不被重视的群体,他们的渴望和诉求一直被忽视。
五、结 语
吉卜林在《丛林之书》中借助动物的视角来书写他的政治理念。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什么样的扩张手段,其实质都是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产和镇压人民的反抗,进而实行原始积累和暴力掠夺[13]。早期的殖民主义是以殖民扩张、财富掠夺的暴力手段来实现的,后期殖民主义是通过隐性的文化侵略,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霸权。“将欧洲之东的地域空间命名为‘东方的’这一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做法部分地是政治性的,部分地是宗教性的,部分地是想象性的;它并不表明在东方的实际经验与有关东方的知识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14]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15]。殖民者利用文化载体将自己描绘成救赎东方的拯救者,将东方刻画成落后、愚昧的被拯救者。“当代认知科学普遍认为,隐喻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对我们认知世界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16]运用隐喻修辞手法,揭露吉卜林笔下的丛林世界并不是优越于人类社会的伊甸园,而是人类现实社会的缩影。丛林居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殖民地人民与殖民者的关系,隐含着帝国主义的残暴与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