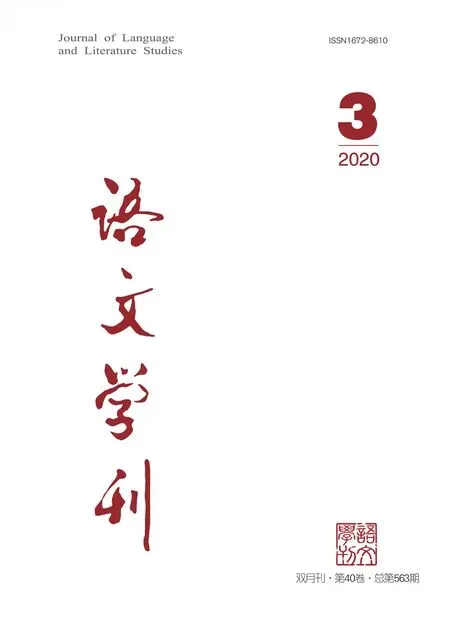附辞会义,首尾相援:《文心雕龙·附会》篇探析
○ 王凤英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一、刘勰专作《附会》篇的意义和重要性
《附会》篇专论文章写作的附辞会义问题,属于“剖情析采”的重要篇章,也可谓创作论部分的收官之作,在《文心雕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刘勰开篇强调,“附会”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一样重要。建筑房屋必须打好基础,裁制衣服要细针密缝才能结实。文章写作的附会即是探讨写作中命意谋篇、附辞会义问题,解决的是基础、是根本,也是关键,因此对于文章写作非常有益。
其次,众多研究者均认为,《附会》与《镕裁》《章句》三篇都是讲文章作法的,三篇的侧重点不同,且《附会》讲文章作法,讲得更加全面。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说:“循玩斯文,与《镕裁》《章句》二篇所说相备。二篇各有首尾圆合、首尾一体之言,又有纲领昭畅、内义脉注之论,而总文理定首尾之术,必宜更有专篇以备言之,此附会篇所以作也。”[1]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则说,附会篇即补成彼篇之义,讨论如何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以上学者的观点都说明了《附会》与《镕裁》《章句》等共同组成了刘勰所构建的一整套相当完备的文章谋篇布局理论体系。《附会》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缺一不可的篇章,且因其所论“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等四个方面的理论观点,在这一体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第三,刘勰通过《附会》篇,有为创作论收官之意,其意义在于指向了全部创作论的最终归宿——“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因前所论,“附会”意味着命意谋篇与附辞会义兼而有之,内容涵盖了文章创作缺一不可的诸方面,刘勰通过《附会》强调了文章要实现“附辞会义,首尾相援”“弥纶一篇,杂而不越”的最高境界,这是《附会》篇的旨归,也是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
二、《附会》所涵盖的内容
《附会》开篇指出:“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此句意为:什么是附会呢?意思是总括文章的内容条理,贯通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决定材料与章句的取舍,衔接上下文意,组合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使其内容丰富、章节交织而又不离于中心。刘勰意在说明,文章的构成需要精心组织,统筹兼顾,多元统一,最终实现“弥纶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刘勰已经注意到了文章写作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无疑,刘勰的视野相比之前甚至同时代的作者更加多面、更加广阔。那么,《附会》的内容包括哪些?
一是“总文理”。即总括文章的内容条理。这里刘勰主要强调的是总揽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即主旨,使之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文章的总纲领,实现“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文章要以思想感情作为灵魂,首先创作者要有思想感情。刘勰一向认为,文章写作是饱含感情的精神创造活动,故而指出“情者,文之经”(《情采》),强调感情、情理是文章的主线、灵魂,文章写作的本源就在于情。情不但决定文章质量的高低、价值的大小、作用的强弱,而且对文章谋篇布局、章法运用、文辞章句的运用等都有重要作用。对此刘勰曾在许多篇章多加论述,可以说贯穿《文心雕龙》始终。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物色》)。刘勰深刻认识到情感之于文章的重要性,认识到情感是主导文章写作的总指挥这一重要规律,所以提出了“总文理”的观点,反复强调主旨的重要性。只要作者心中对文章主旨有一个整体性把握,就为整篇文章的创作奠定了基调,奠定了基础。
二是“统首尾”。即贯通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刘勰一贯重视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而且认为一篇好的文章,就应该是首尾贯通而成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目中也有论述,如《镕裁》篇:“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章句》篇:“跗萼相衔,首尾一体。”《附会》一篇,又提出“首尾圆合,条贯统序”;“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惟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
首尾一贯、收尾相援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刘勰附会理论的重要方面。在重视首尾作用的同时,刘勰还在《附会》篇就如何处理首尾关系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要重视结尾。“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如果文章开头写得漂亮,而结尾枯瘦无力,就会使文章余势受阻而湮没,余留的韵味也不会畅通。以上这句话从语法结构和句意看,重点在后部分,强调媵句即结尾的重要性。为此,他又进一步从正反两面提出对结尾的处理。首先,正面要做到“克终厎绩,寄深写远”。刘勰通过形象的比喻指出“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厎绩,寄深写远”,意即一篇文章的收尾和一个章节的结句,就好比乘船要用力摇桨;连缀文辞切实事理,则像是骑马要拉缰挥鞭。文章的结尾要寄寓遥深,耐人寻味,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次,从反面指出,结尾犹如最后冲刺,是画龙描凤的点睛之笔,草率马虎,仓促收兵,就会文尽而意尽,没有思索回味的余地。其次要首尾相援。重视首尾,最理想的效果就是要从整体出发,实现开头与结尾彼此“相援”,协调呼应。既重视开头,也注重结尾,而且首尾要相应。古代创作者历来都很重视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如“凤头”之说,就是指要把文章开头写得漂亮,引人入胜,吸引读者注意力;又有“豹尾论”,即文章结尾要响亮有力。刘勰在前人基础之上,辩证地指出了“统首尾”,进而又提出“首尾周密”“首尾圆合”“首尾相应”“首尾联络”“首尾勾连”等,甚至认为:“惟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只要首尾呼应,密切相连,那么附辞会义的作用,也就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可以说,“首尾相援”是“附辞会义”理论观点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其包含着对文章内在思理脉络和形式表达方面应意脉通畅、首尾浑融、表里相契的综合要求。而要达到这种要求,作者在谋篇创作之时,就需要具有整体观念,总体驭文统筹,以期达到“弥纶一篇,杂而不越”。
三是“定与夺”。即按照主旨的需要决定材料与章句的取舍。刘勰在“总文理”之后接着提出“定与夺”,就文章材料的筛选、取舍和统筹进行论述。那么,定什么,如何定,刘勰就此展开层层递进论述。首先,他指出,定整体与部分。《附会》:“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意思是画匠把人的头发画得再逼真,也画不出人的容貌神态;射手只注意小地方,反而失了大目标。旨在告诉我们,文章只关注细碎的、细节的无关大旨的材料,其命意布局就会零乱。因此,文章写作不能太多选取琐碎细小而与主旨关系不大的材料,要有主次、轻重之分。要从整体出发,根据主旨的需要,与主旨关系密切的材料多用,相对细节琐碎的材料、不能够强化主旨的材料少用。要重整体,轻部分,与主旨关系不大的材料作为陪衬使用。接着,他提出定繁和简。《附会》:“夫文变多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率故多尤,需为事贼。”意即,文章写得过于简略,道理会说不清楚;写得过于琐碎,则又文辞沉闷乏味。写文章一定要把握好详略得当的技巧,合理安排材料,取舍章句。该详则详,不要吝啬笔墨;该略则略,应惜墨如金,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样文章方能重点突出,中心明确。
四是“合涯际”。即文章层次、过渡及照应的处理。文章写作必须确立思想脉络和表现层次,处理好上下文之间的合理转换、衔接,以及前后内容的呼应,文章才能整篇合一、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刘勰的“合涯际”论述的正是文章写作的层次过渡照应。文似看山不喜平。好的文章应该是有层次、多维度、有照应。
首先,他提出:“夫能悬识腠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刘勰借用比喻指出,文章写作如同人体肌肉有自然纹理一样,也要有合理的层次结构,就像胶和木粘合为器具,石和玉天然构成璞玉。
其次,刘勰还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层次结构的处理。从正面,他再次用身体做比喻,提出“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意思是写文章能够把不同的层次用意结合得肝和胆那样亲近;又如驾车,“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四匹马的力气不同,各有大小,但只要如操琴弦般掌握好缰绳,并驾齐驱,也能一气呵成。从反面看,不会安排层次结构,就会把文章写得支离破碎,南腔北调,不伦不类,“拙会者同音如胡越”。刘勰还列举了两个事例:“昔张汤拟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理事之不明,而词旨之失调也。”汉朝廷尉张汤写的奏章,一再被武帝退回;三国时中书令虞松起草的章表,屡次受到司马师指责,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文章写得事理不明,层次不清,造成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大打折扣。以上反例说明,写文章一定要“合涯际”,做到“道味相附,悬绪自接”。由上文可知,文章想要实现整体合一,作者必须要善于安排层次、文辞,才能达到和谐的最高境界——“首尾一贯”。
三、《附会》提出的命意谋篇之法
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说:“大体说来,所谓附会也就是指作文的谋篇命意、布局结构之法。”[2]《附会》的命意谋篇之法,是指文章写作中所遵循的一些法则规律,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缀思之恒数”。刘勰认为,要遵循“缀思之恒数”,法则是“宜正体制”,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一)宜正体制
对于“体制”一词,在《文心雕龙》中有多种含义,对于《附会》篇中体制的含义也一直存在着分歧。詹锳注为“包括体裁及其在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也包括风格”[3];周振甫译为“文体”;郭晋稀、陆侃如、牟世金等则译为“文章的体制”;赵仲邑译为“文章本身的制作”;张长青、张会恩释为“‘正体制’的布局方法”;缪俊杰在释文中仍沿用“体制”;而林杉则认为是“文章的整体规范,亦即刘勰在‘文体论’各篇中所强调的‘大体’‘大要’”;而徐浩以为:“‘体’是文体,‘制’是与其相适应的规格和要求”“‘体制’所涉及的当是不同的文体及相应的规格和要求”,这种看法与詹锳相同。
“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一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才量学文,宜正体制”,这是前提;其次是以“体制”为前提的“情志、事义、辞采、宫商”,这四者共同形成了宏观大体。把握了大体,然后才有对“辞藻、声律”微观的雕琢。“情志”与“事义”结合起来,构成了文章的思想内容;“辞采”与“宫商”结合起来,构成了文章的表现形式。“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考虑到了,然后就可以‘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阙中’,使文章的格调保持一致,这些为作文之定律。”[4]因而,刘勰强调的“宜正体制”,即是确立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统一的“大体”。“此‘大体’,既包括文章的‘体裁’‘体式’,也包括文章的‘格调’,还有其‘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为文定律。”[5]
(二)附会之法则
刘勰认为构成作品应有四个部分:即情志、事义、辞采和宫商。刘勰以人体为喻,说明各部分对于文章组成的作用以及不可或缺性。情志为主体,好比人的神经中枢;其次是体现其思想感情的素材,好比人体的骨骼;再次是辞藻和文采,好比人的肌肉皮肤;最后是文章的声调音节,好比人的声音。
其一,情志为神明。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是文章的灵魂,或者说是中枢神经,它在文章中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文成之后,它随即转而成为文章的主题思想。情志是作家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作品的核心和创作的推动力。刘勰认为文章的情志就像精神、智慧和性灵对于人一样,具有统领一切的地位和主导作用。“神明”大抵指人的精神、智慧、性灵。文章应该是灵动的活物,文学创作即是要创造具有智慧和生命性的作品,而生命运动是作品有序性的集中表现。
其二,事义为骨鲠。把各种事料、理据加以整理,选义按部,使之成为文章中的主干,这对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事义”主要涉及具体事例或材料,它是用来传达作家思想,撑起文章内容的骨鲠。事义概念的出现,说明刘勰既强调内容的首要地位,又重视选材在表达思想过程中的必要作用。
其三,辞采为肌肤。把语言辞藻加以修饰,使之在文章中具有充分显示主旨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是文章得以述情说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刘勰这部深得文理的著作用很大的篇幅论及文学语言的一系列问题,形成颇有特色的文学语言观。《声律》《练字》《指瑕》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文学语言的音韵美、精练美、准确无误的纯洁美,突出了辞采之于文的价值。
刘勰指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此处借用比喻,虎豹之皮极其珍贵,若去掉外面的毛色花纹却如同犬羊之皮,进而说明质待文的道理。此外还引用具体的例证加以阐发:如用“丧言不文”反证君子平时的言辞不可以不注意修饰,其文章更应注重言辞修饰。他评价庄子与韩非子的文章,认为其文采的丰富多变已经达到了极致。总之,依刘勰之见,文章必定要具有文采,没有华美的文采,文章就不存在了。
其四,宫商为声气。以声律作为文章的韵调和气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和韵味。诸如句式的长短,用韵的方法,以及后来所谓的平仄,都包括在宫商范围之内。齐梁时期是我国声律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刘勰设专篇《声律》讨论诗文的声调和韵律问题,足见其对声律理论的重视。他把诗文的声律喻为人体中的声气,与神明、骨髓、肌肤共同成为人体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自然之道的理论出发,指出声律乃是人的自然现象,借助唇吻吐纳,有着疾徐、抑扬、强弱之别。刘勰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合理地提出了声律运用的原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世借鉴。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曾对舍人此篇大为赞赏曰:
舍人“内听”之说最精。盖言为心声,言之疾徐高下,一准乎心。文以代言,文之抑扬顿挫,一依乎情。然而心纷者言失其条,情浮者文乖其节。此中枢机至微,消息至密,而理未易明。
此语深得刘勰论声律要旨,又很有见地,揭示了诗文创作中的声律运用与音乐不同。前者属内听,故“难为聪”,后者属于外者,故“易为察”。即内听“声与心纷”,诗文创作听不到内心的音响,因此很难判断声律效果。音乐就不同了,其响在彼弦,由于能听到琴音,所以容易识别声律是否正确。《校释》往往能看到刘勰论文的本质所在,其“内听之说”旨在强调声律与文情的关系。声律不仅是文章韵律美的表现,更是为文情发肺腑的自然流露。依情用律,则声与情符,情以声显,文章的感人之力亦深矣。
诸如此种论述、举例,被刘勰在《声律》篇中屡屡所用。他溯源声律的发展过程,总结前人用韵的经验,得出自己的观点:运用声律要以情思为准;做到无法而不离法,有定而仍善变。诗文写作中声律的运用是很重要也具有难度的,然研究声律问题也是“驭篇”的重要之“术”。虽今天的声律运用较之刘勰时代已大大减少了,但是声律仍然值得研究。现代的小说、散文语言缺乏优美的音律,读之不能朗朗上口,而一些诗歌亦平仄无序,不具备应有的声律美感。作为诗文独具特色的语言特征,声律应该得到运用和发扬,而探讨、研究声律理论就尤为必要了。
以上情志、事义、辞采和宫商是文章组成必不可少的四个部分,明确这个原则,才能轻重适宜地处理好全篇作品,从而实现文章结构的完整周密,构成一个整体。文章想要安排得当,就必须在创作之初,在心里对文章的整体结构有个全面的勾画,从头到尾的每一个部分都布置妥当。只有当思绪自然连贯时,内容才能真正完整和谐。要想内容布置妥帖,作者的内心必须配合协调。诸如此类的言说,无一不是在体现着《附会》篇中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即“杂而不越”观点。
《镕裁》《章句》再加《附会》篇,刘勰全面论述了文章谋篇布局的理论体系。刘勰提出的总文理、统首位、定与夺、合涯际四个方面理论,反映了谋篇布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是文章结构安排的四个重要法则。这些谋篇布局理论,是刘勰对历代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揭示了写作实践活动发展的规律,也为现代文章创作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