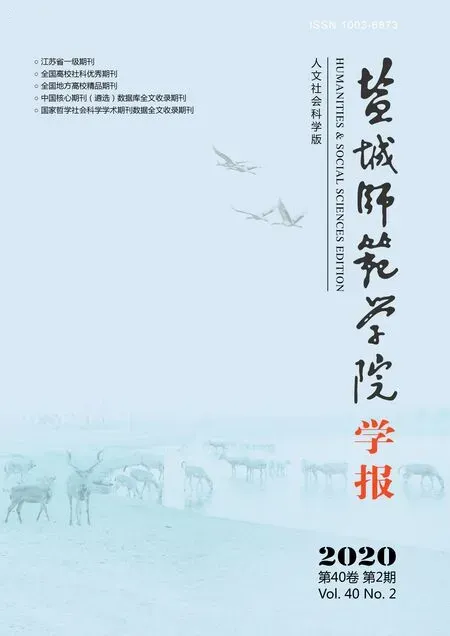清代扬州女性文学社团“曲江亭诗社”考论
赵 阳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明清时期,文人雅集唱和或者结为文学社团的行为非常普遍。不仅在男性文人中蔚然成风,不少地区的女性也大胆地迈出了由个体吟咏到群体唱和的重要一步,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吴江叶氏群体”“仪征阮氏群体”“太仓毕氏群体”“闽南郑氏群体”“贵州许氏群体”等都是满门风雅,才女辈出。更有“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等成熟的女性文学诗社,赫赫有名。在乾嘉时期的扬州也曾出现过一个女性诗社----“曲江亭诗社”,它是在扬州地区学术、文学最为繁荣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个群体社员互相之间大多具有姻亲关系,所以该诗社一般被视为男性推动之下的家族文化的副产品。通过搜罗文献,钩稽历史,发现这个女性群体的文学活动已经超越了家族文学群体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公众性和社会性,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曲江亭诗社”的形成
曲江亭诗社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第一,社会风气的感染和影响有催发之功。明清时期女子结社虽未风行,却也有春潮怒上之势。蕉园诗社、随园诗社等诗社的出现,都是女性文人为自己开创的另外一个生存空间,她们的智慧和身心在这个空间里得以施展和释放,这种实践无疑对其他知识女性有巨大影响。对扬州女诗人影响最大的地区莫过于相邻的金陵、吴中、京口。袁枚在乾隆十七年绝意仕进后,迁居金陵,经营随园,广收弟子,包括20多名女弟子。因三妹素文与长女成姑的遭遇,他对红颜薄命的女性予以更多的关心。扬州女诗人与随园女弟子多有联系。袁枚有堂妹秋卿,也是他的诗弟子,嫁扬州汪氏。袁枚过往扬州,必经停其家指导诗文。乾隆五十五年、五十七年,袁枚借回杭扫墓之机,大会女弟子,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嘉庆初,袁枚辑成《随园女弟子诗选》,广为流布。这样的事件必然对扬州女性诗人产生触动。在吴中,任大椿族弟震泽诸生任兆麟,“承家学,博闻敦行,又从长洲褚寅亮、彭绍升游。自经传子史、音韵古籀,及诗古文,皆颖悟解脱,心契其妙,为王鸣盛、钱大昕所重”[1]。他无意科场,隐居著书授徒。尝辟林屋吟榭,广收女弟子,雅集唱和。夫人张允滋为太史张大受曾孙女,喜吟咏,夫妻琴瑟和谐,诗学益进。乾隆五十三年,编成《吴中女士诗钞》,又名《吴中十子合集》,收张青溪允溪、张紫蘩芬、陆素窗瑛、李婉兮薇、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荪纕、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十人诗。是书附录扬州女诗人王琼《爱兰诗钞二集》,卷首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王鸣盛、任兆麟、马素贞序。这是两地女诗人交往的实证。两地诗坛女诗人相互都有一定的了解和联系。
第二,扬州一带有着孕育女诗人的良好氛围和土壤。扬州多诗礼传家的望族。家族经常举行的各种宴集酬唱,或者家族男性频繁的文人交游,对女性成员的影响都是积极且深远的。阮元的夫人孔璐华曾在《唐宋旧经楼诗稿题识》中写道:“于归后,夫子喜言诗,始复时时为之。又因宦游浙江,景物佳美,同里张净因夫人馆于署中,复多唱和,此后往来曲阜、扬州、京师、踪迹无定,得诗转多。”[2]阮元为汪嫈《雅安书屋诗集》作序云:“今子镇北,余癸巳礼闱所取士也。曩曾奉节母《秋灯课子图徵》请余为记,得知节母为余友汪君埙之长女,工诗能文。……扬州当乾隆、嘉庆间,言诗学者有春谷、秋平两黄君;闺秀则张净因孺人。……今观诗中,知节母为春谷表侄女,早受学于秋平,又从游于净因,此其渊源固有矣。”[3]这是阮元晚年对往事的回忆。钱大昕《畹香楼诗序》更是较为客观深刻地反映了扬州女诗人产生的背景和根源。《序》云:“维扬汪孝廉剑潭,力学嗜古,而尤工于诗,比来京师不数月,而诗名隐然出诸老宿之右。询其师承所自,则曰:‘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经书,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咏,间示以诗法,因得粗窥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畹香楼诗稿》相示,神韵渊澈,无绮靡卑弱之调。剑潭天才固超逸,然非得诸内教,安能成之早而诣之深若此!窃观古今巾帼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偻指数,要其归有两端。或以才艺擅名,或以节义见重,春华秋实兼之者盖鲜。虽然,松柏介如其独立,其黛色苍皮,自秀于凡木也;圭璋皭然而不滓,其浮筠旁达,自异于它石也。三家村叟目不识一丁,食味别声而外,了无所长,虽无缨绂之累,岂得遽以隐逸许之哉!夫人幼习诗礼,及丧所天,抚孤全节,备历人间坎坷,终能教其子为名下士。贞蕤雅操,已足贻我管彤,而诗格之工,又能驾若兰、令娴而上之,岂非兼古人之所难者乎!”[4]在这样的城市文化背景下,曲江亭诗社的出现绝不会是偶然现象。
第三,阮元翠屏洲访王豫,商讨编辑《江苏诗征》,为曲江亭诗社的成立提供了直接机遇。嘉庆十年七月至十二年夏,阮元守制在籍,与诗人王豫相识相交,复访之于翠屏洲,确定了一件江苏文化史上的大事,编辑《江苏诗征》。阮元不但惊异于王豫之诗才,也艳羡翠屏洲之风景,遂嘱其弟阮亨筑曲江亭于洲上。他在《题曲江亭图》中说:“扬州城东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之北,有康熙间新涨之佛感洲或名翠屏洲,诗人王柳村(豫)居之。丁卯秋,余与贵仲符吏部徵、梅叔弟亨屡过此地。梅叔买其溪上数亩地,竹木荫翳,乃构屋三楹、亭一笠于其中。柳村又从江上郭景纯墓载一佳石来置屋中。予名之曰‘尔雅山房’,又名其亭曰‘曲江亭’,以此地乃汉广陵曲江,枚乘观涛处也。”[5]885从“屡过其地”四字可知,阮元丁忧期间,翠屏洲是常来的,并嘱阮亨买地、构屋、立亭于其中。屋中因有佳石,名之曰尔雅山居,因其地乃汉广陵曲江观涛处,故名之曰曲江亭。实际上,到嘉庆十二年冬,亭方落成,阮元已除服晋京,无暇来此了。阮元之所以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可看出他为人处世之道。他请王豫辑《江苏诗征》,“抄胥费,梨枣之资”一概无需王豫考虑,自己常来,今后也会常来,不能过多地烦扰主人。还有一层意思:“名曲江者,尊高庙之说,思有以敬明此义而志此古迹也。”[5]624
他到翠屏洲来,与王柳村商量辑诗之事,一众家眷当是随行的。王豫的妹妹女诗人王琼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懂诗爱诗的夫人、女史,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她肯定希望能像张清溪编《吴中女士诗钞》一样,编一本维扬女子诗钞。按礼法,阮元重孝在身,不当吟咏,众家眷也应随之,但谈诗总是可以的。待服除,唱和便正常了。故诗社之立,唱和集之成也就水到渠成了。其时,曲江亭虽未落成,而从阮元起,大家已如此称呼,故名之为“曲江亭诗社”是再恰当不过了。
简言之,曲江亭诗社之形成,由阮元访王豫于翠屏洲共商辑《江苏诗征》引起,阮元爱其景幽,买地建曲江亭,王琼与阮元家眷等交往相知相契,互相唱和,遂成诗友,并有唱和集问世。虽然比较成熟的文人结社应当具有一定的组织要素,比如“社名、社长、社员、社所、社约”等等。但是在明清社会,更多的诗社形式没有这么严格,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诗文唱和,集会有一定的次数,诗文有一定的数量,即使没有什么明确的社启和章程,甚至有些结社在当时都没有明确的社名,这也不妨碍同时代的人,或者后世将其作为文学性组织看待。对曲江亭诗社当如是看。
二、诗社成员的内部构成
曲江亭诗社有诗集传世,名为《曲江亭唱和集》。集中一共收录了张因、孔璐华、刘文如、唐庆云、王琼、王廼德、王廼容、季芳、鲍之蕙、王燕生、张少蕴、朱兰、江秀琼等十二位女诗人的作品,其中收录了王琼、王廼德、王廼容六首,季芳、鲍之蕙五首,张少蕴四首,孔璐华、刘文如两首,张因、唐庆云、江秀琼、王燕生、朱兰各一首。
王琼在《曲江亭唱和集》的序中说:“琼僻处江洲粗解声韵之学,年未笄即有《爱兰初集》之刻,吴中张清溪夫人见而爱之,附刻《林屋吟榭》。十子之后,江浙诸名媛咸以琼为能,诗筒往还不下数十人,其间如张月楼、陆素心、江碧岑、沈蕙荪、毕智珠、金仙仙诸子,皆相继赴玉楼之召,甚可慨己。如侯香叶、骆秋亭、张霞城诸子又远隔千里百里之外,不得合并。心非木石,曷能恝然于怀耶?丙寅春大中丞阮云台先生来访。家兄柳村子爱种竹轩林木幽邃,建曲江亭于轩西,为逭夏著书之地。夫人孔经楼贤而才,不鄙弃琼,遂偕张净因、刘书之、唐古霞、家凝香诸子,与琼互相赓和以为乐,而江瑶峰、鲍茞香二子亦先后寄诗订交,暨侄女辈共得十有一人,洵为一时闺阁盛事。去年冬净因忽为古人,今年春三月,经楼、书之、古霞随中丞入浙,而琼索居江村,睹溪边飞絮,闻郊外流莺,辄悼旧怀人不能已已,爰捡唱和之什,付之梓氏,以志予怀。”[6]
根据诗集和诗序,诗社核心人物两个:一是阮元夫人孔经楼,这个是由她的身份地位决定的,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诗社撑不起来;一是王琼,她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操作者,诗社与外部的联系交往基本上是依靠她维系的。
孔璐华(1777--1832),字经楼,山东曲阜人,衍圣公孔宪增长女,阮元继妻。幼娴诗礼,出嫁后受封一品,所撰诗数卷,内有恭迎宫辇七律一首及《题石室藏书图》《饲蚕纪事》,《冬日雷塘暮芦有感》,皆一时之名作。有《唐宋旧经楼诗稿》7卷(一作6卷),嘉庆二十年刻本[7]507。
王琼,字碧云,晚号爱兰老人。江都人,王豫的妹妹,周维延妻室。擅长作诗,如她自己所言,年未笄,即有《爱兰初集》之刻。得到张允滋的赏识,张所著《清溪诗稿》一卷,录诗42首,题“匠门女史张氏滋兰著,同学诸子参阅。”卷首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其夫任兆麟《清溪诗稿序》,吴江县令龙铎题诗,江珠题词及和诗等,卷末有乾隆五十三年宋林跋、王琼题诗。这证明王琼的诗是有一定地位和分量的。所以《吴中女士诗钞》附收了王琼的《爱兰诗钞》二集。由此也拉开了她与江南闺阁诗人唱和的序幕,与之诗筒往还者不下数十人。她著有《爱兰书屋正续集》五卷、《爱兰名媛诗话》四卷,可惜今都不传。王琼广泛的文学交游,推动了诗社境界的开拓。
以孔氏和王琼为核心形成了两大家族的女性诗歌创作群体。
以孔璐华为核心的阮氏家族有刘文如、谢雪、唐庆云,皆为阮元的侍妾。刘文如(1777--1847),字书之,号静春居士,天长人,旧隶扬州。工绘事,惜不多作。擅诗文,撰有《四史疑年录》七卷。又有《古列女传诗》。谢雪(1782--1836),字月庄,号蓉庄,长洲人。娴于诗,善绘事,有《咏絮亭诗草》。唐庆云(1788--1832),字古霞,吴县人,工花卉虫鱼,工于诗画,著有《女罗亭稿》六卷[7]521。
以王琼为核心的王氏家族有王燕生、王廼德、王廼荣、季芳。王燕生,她的生平几不可考,但是按照王豫的说法,“《曲江亭唱和集》,女史王燕生选刻”。她为《曲江亭唱和集》作序云:“夏五,爱兰夫人又以所刻《曲江亭闺秀唱和诗》索序。予忝葭莩之谊,兼棣萼之盟,不敢固辞。因即曩所企慕之私心,为书数语于颠末。”落款为“嘉庆十三年五月午日,华亭宗妹燕生凝香撰于珠湖草堂”[6]。为后人提供了不少信息。“又以所刻……索序”,此前当有事求之,与王豫之说可合。“葭莩”“棣萼”表明有亲戚关系,属于平辈,“宗妹”至少说明同宗。华亭,松江古称,或为松江人。“珠湖草堂”则为北湖一带,为今之住所。无疑,燕生为王氏家族中人。《寄翠屏洲诸女史即和江瑶峰夫人原韵》,燕生和诗的第三首“燕语呢喃遣醉魔,竹林深处发高歌。春云淡白春波绿,一路沾衣柳汁多”。下自注:“时外子梅叔将赴杭州节署”。梅叔,阮亨的字。则燕生又为阮氏家族中人。燕生是王家女儿,阮门媳妇,一身而跨家族,身份特殊,作用也特殊,且阮元是嘱咐阮亨购地建房筑亭的,曲江亭诗社,两家闺秀的联络人非燕生莫属。加上有诗才,选诗之责当无旁贷。又,阮亨,乾隆四十八年(1783)生,比王琼至少小七八岁,所以王燕生自称宗妹。
王廼德、王廼荣是王豫的女儿。二人皆工诗词,王廼德著有《竹净轩诗选》《竹净轩诗话》,王廼荣著有《浣桐阁诗选》《浣桐阁诗话》,惜皆失传。
季芳,字如兰,季云崖之女,王豫之外甥女。著有《环翠阁诗集》。
张因(1742--1807),字净因,一字淑华,人称净因道人,甘泉人,是学者黄文旸的妻子。平居与丈夫相唱和,或赌记书籍策数典故以为乐。著有《绿秋书屋诗集》1卷、《拓垢山房倡随集》1卷、《淑华卷》1卷[7]204。黄文旸长阮元27岁,阮元对黄文旸夫妇非常敬重,“曲阜衍圣公尚幼,余荐居士往为之师,道人与居士以《六十自寿诗》相唱和,山左盛传之。”“岁癸亥(嘉庆八年),邀二老来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泛莺脰湖,皆有诗。余于署中开别馆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舆小舫,秋衫白发,潇洒于湖光山色间,余内子孔亦以诗与道人相唱和。”[5]531-532张因卒,阮元特撰《净因道人传》以纪之。张净因年龄长于其他人,文学水准在曲江亭诗社诸人中,当属上流。在诗社中应该是顾问、指导一类角色,唐庆云就曾“师事净因”。她的入社提高了诗社的层次。鲍之蕙的《挽张净因女史》中提到“予读《绿秋轩稿》,竟一夕不忍释手”,并赞叹其“慧业编成绝妙辞,清才不愧女宗师。广陵花月供陶写,闺阁文章仗主持”[8]。
而对外交流交往的网络则以王琼为主编织而成,主要有江秀琼、朱兰、鲍之蕙、张少蕴等。
江秀琼,字瑶峰,安徽歙县人。有《椒花馆集》,已佚。王琼《名媛诗话》中提到:“女史工诗,兼善丹青、鼓琴,真吾党韵士也。闻予兄有《群雅集》之刻,以书介予,乞选,并订曲江亭之约。今春二月以微疾端坐,口诵《心经》七遍而卒。丁卯冬,张净因殁,今女史又殁,悲悼何如耶?”[9]江秀琼曾经希望能够亲临曲江亭,并参与诗社活动。她对自己的诗才比较自信,且期望能够得到王豫的认可,她的“乞选”之举与“定约”之盟,都展示她积极投身诗文创作的决心。她有《题王碧云闺秀联珠集》诗“年来消尽旧诗魔,愧我阳春白雪歌。明月一窗梅几树,幽香清影为谁多”。而王琼的“悲悼”,既是对诗友的哀悼,也是在新成员增补的失败,及张因去世而造成曲江亭诗社衰微之势,表达出的伤感。江秀琼对曲江亭诗社仰慕已久,且有约定。她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诗书作联接的,这个约定不仅是友人之约,更应该看做是入会的盟约。而王琼能够与之结约,也是对她水平的认可及接受。虽然江秀琼女史早逝,但是亦应将其看做社员之一。
朱兰,字清畹,甘泉人,程绮堂室,著《梦香集》。朱兰与曲江亭诗社核心成员王琼是酬唱最密的友人,两人亦师亦友,她有《题王碧云女史诗集》“西风飒飒闪残缸,把卷高吟月浸窗。今夜灯前如有梦,应随寒雁到京江”之句。从《曲江亭唱和集》来看,朱兰曾经亲赴曲江亭。另外,从朱兰留存的其他一些诗作中也可以看出她与曲江亭诗社的渊源。《翠屏洲诗呈王柳村先生》:“门对寒江万岫青,幽人吟啸倚窗楹。诗思怪底清如许,一镜波光冷翠屏”,又有“及时须订兰亭约,梦到江干又落花”(《春日寄王子一、子庄两女史》)之句。她临卒谓其诗必得王豫选刻[7]196。她甚至在自己家附近,模仿曲江亭周围风景,手植新篁。她的《种竹轩》直抒胸臆,“自锄幽径种新篁,个影离离枕簟凉。遥想诗人吟倦后,好教清梦入潇湘”。这首诗不妨看作是诗人以在自己居所附近种竹林的方式,向远方的闺友们遥遥致意。
鲍之蕙(1757--1810),字仲姒,茝香,鲍皋次女,为鲍照后人,著《清娱阁吟稿》。《群雅集》中称:夫人幼颖悟好学,与其姊之兰、妹之芬皆受经于母氏陈逸仙(蕊珠)夫人,闺中唱和。《种竹轩余话》称其家族风雅之盛,江左词坛传为佳话。[9]鲍之蕙的诗在《曲江亭唱和集》中共收录《寄翠屏洲诸女史即和江瑶峰夫人原韵》及《夏日和爱兰夫人见怀韵》等5首。由于女性出行受种种条件限制,所以鲍之蕙似乎并未能亲自赴曲江亭之约,所以对张净因有“与夫人神交已有,未能一晤”[8]的遗憾。张少蕴小谢的情况不清楚,从唱和情况看,当属鲍氏外子,张弦家族中人。
其他还有一些与上述女性人物有定交结盟或者诗文唱和的女性,如毕慧、金逸等,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表明他们的活动是否与曲江亭诗社有关,故暂不列入,有待进一步考辨。
就他们的身份和资格来看,以孔璐华为代表的阮氏女眷,和王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女眷,他们互相之间又有互通姻亲的关联。而张因年辈教长,与阮氏女眷是半师半友。朱兰、江秀琼等与曲江亭王氏一族较为亲密,是唱和殷勤的诗友。不可否认家族内部的亲属关系是诗社成员构成的基础,但是曲江亭诗社已然突破了单纯家居式的创作模式,具有了一定的社交关系和公众认知度。
三、曲江亭诗社的诗文创作及特色
《曲江亭唱和集》中收录了36首诗。这些诗作大抵是唱和联吟之作。唱和集中所录之诗无功利的关注,她们沉醉于曲江亭的秀丽风光中,纵情地去捕捉美的形象,体味诗社生活本身给她们带来的强烈情感冲击。
诗歌较为集中地展示了诗歌创作主体对曲江亭美景的热爱,对诗社生活的珍惜,对友谊的珍重等情感诉求。但不同的诗歌又有各自侧重的表达。如江秀琼的《寄翠屏洲王爱兰夫人子一子庄季如兰三女史》:
冰雪聪明绝点尘,芙蓉出水句清新。联吟雅集珠成串,一代诗才属美人。
尽是翩翩林下风,颂椒赋茗雅相同。恍如玉女来香阁,散满天花一卷中。
年来消尽旧诗魔,愧对阳春白雪歌。明月一窗梅几树,淡香清影为谁多。[6]
该诗是侧重赞赏诗友的才华,点评诸位的作品。再如孔璐华的《忆曲江亭寄答翠屏洲诸女士》侧重于怀想和期待:
遥想曲江亭,云烟望缥缈。今见瑶华篇,益知风景好。高柳自成林,清流媚幽筱。亭中月自明,芰荷香满沼。我欲听涛人,更怯西风香。明年桃李开,交交飞黄鸟。来读诸君诗,春光照光表。[2]
曲江亭诗会的举行离上一次曲江亭聚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诗人用了“遥想”二字,表达了对过往盛会的回味和追忆。而在诗人写这首诗之前,翠屏洲诸女史可能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诗会,并将诗会所得诗篇寄给了孔璐华。而他们又订下了来年再聚的盟约。明年桃李开,交交飞黄鸟。交交黄鸟,出自《秦风·黄鸟》,孔璐华说明年桃李盛开时,黄鸟翻飞,鸣声悠扬,春意盎然,而这正是赏读诸君诗文的好时机。还有的诗歌侧重细节,如“闲坐启南窗”“敲诗与煮茗”“论诗细煎茗”等等。诗歌感情真挚,具有感染力,这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作诗技艺和审美情趣。从个体层面来说,差异性是明显的,但是从文学群体的角度来看,共通性特征也很明显。
从创作技巧来说,她们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诗人们擅长营造意象。诗中多选“竹”“云”“雨”“树”“花”“柳”等清新脱俗的意象。初步统计,在唱和集中“竹”出现11次,“雨”出现16次,“云”出现18次,“树”出现8次,“花”出现23次,“柳”出现10次。如王廼容《和瑶峰夫人原韵》:
书堂抱竹绝嚣尘,诗思闲随野草新。文选楼中好旧雨,才人都是扫眉人。
椒花芳气媚春风,自愧庸才未敢同。同此相思不想见,笛声偏在落花中。
兰窗捡点遣吟魔,忽接瑶华发浩歌。知否故人江阁上,双峰深处碧云多。[6]
诗中出现了“竹”“草”“雨”“花”“风”“云”等组合意象,幽竹环绕着厅堂,春风中的落花,远山深处飘动的白云,曲江亭在诗人的笔下如此清幽雅致,让人怀念。而更令人向往的是,那里有“旧雨”“故人”“瑶华”“浩歌”,在远离嚣尘之所,与惺惺相惜的朋友诗文唱和,展示才华,这样的交流,让人身心俱醉。
上文提到,曲江亭种植了大片竹林,而诗人笔下的竹子不仅是实景,也体现出了她们的追求。与男性文人不一样的是,她们爱竹并非是强调竹象征的人格理想,她们所描绘的“浓阴盖深竹”“竹深涤尘氛”“竹林深处发高歌”“书堂抱竹绝尘嚣”“凤生竹韵影娟娟”“萧萧竹韵助秋声”这些诗句,更多地展示了她们追求精神世界的理想。在竹意象营造出的自由宁静,与世隔绝的文化环境中,感受诗书生活的愉悦和逍遥。
另外,“花”也是诗人笔下较为突出的意象。有兰花、梅花、芙蓉、菊等不同种类的花,也有幽花、落花、残红等不同形态的表达。她们或者以花意象来营造雅致的意境,如“满砌幽兰香袅袅”(季芳《和经楼夫人见怀韵》),“入座山光宜薄暝,隔簾花气媚初晴”(王廼容《和书之夫人见怀韵》),“梦回花外径,春尽水边亭”(张少蕴《夏日和爱兰夫人见怀韵》),“残红落已尽,芳草绿和烟”(王廼容《夏日见怀》);或者以花来比拟彼此的诗作,如“江皋秋思正无边,惊喜琼华到眼前”(季芳《和经楼夫人见怀韵》)。琼华,是古代神话中琼树的花蕊,这里以世间难见的花来比作朋友的新诗。还有“多君如芙蓉,松菊难再并”(张净因《怀翠屏洲诸女史即和元韵》),用花来形容才华出众,锦心绣口的女诗人们。更有江秀琼的《寄翠屏洲王爱兰夫人子一子庄季如兰三女史》“冰雪聪明绝点尘,芙蓉出水句清新”“恍如玉女来香阁,散满天花一卷中”之句既用花来比人,也比拟诸位的大作。
难得的是,无论何种意象,多是为营造出雅致的环境,抒发的情感毫无凄凉忧惋之音,这在明清两代女诗人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女诗人们创作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擅长使用具有表象能力的语词。曲江亭诗社成员重视语言的锤炼,尤其是具有表象能力的语词的选择。她们不仅描绘出生动丰盈的物象,还显现出细腻充沛的情感。比如《怀翠屏洲诸女史即和元韵》唱和之作中,她们面对相同的物象,却描绘出不一样的风光和感受。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诸位女史在面对曲江景象时,分别用了不同的动词。
遥望翠屏洲,江云叠虚岭。(张因)
遥识幽亭外,江光接云岭。(孔璐华)
浓阴蓋深竹,隔江排翠岭。(刘文如)
遥忆曲江亭,伊人阻云岭。(唐庆云)
幽居喜此中,青送隔江岭。(王琼)
结屋曲江边,云开见遥岭。(王廼容)
我爱竹里居,闲门对焦岭。(王廼德)
闲坐启南窗,树杪出高岭。(季芳)
诗中描绘翠屏洲的山岭,用了“叠”“接”“排”“阻”“隔”“见”“对”“出”等字,各自侧重了景观的不同方面。“叠”字显示了江水、云气及山岭的映照之美;“接”字展现了水光与山岭的交接融合之像;“排”字写出了绵延山岭的气势;“阻”字是实写山岭隔断之势,也指诗人们心理上一种幽怨的情绪,山高水长,各自一方,但是我们期盼能够再次曲江聚会;“隔”字描绘了此处的静谧清幽,将之作为诸位女史遗世独立之所,“对”有衡宇相望,想看两不厌之意;“见”字俨然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境与意会的格调;“出”字赋予了景观动态美。她们有意识在用字上进行锤炼和雕琢,在她们的唱和中,展现了曲江亭多层面、多角度的美。有静有动,有虚有实,在景色的描绘中体现了她们的情感深度。
除了动词之外,她们还擅长使用叠字。有些叠词能够描摹出景物的形态美,如王廼德的“飞飞梅片逐香尘,几日风和柳又新”,描摹出片片梅花花瓣随风漫天飘落之貌。季芳的“丝丝垂柳拂香尘,红雨飘残万绿新”直接化用了宋代王迈的《和马伯庸尚书四绝句》中的“丝丝垂柳拂金沟”,表现了柳树的纤细妖娆之态。有的叠词的使用使得画面有了味道,如王琼的“风定溪荷香,馥馥透衣领”,化用陆游《双清堂夜赋》“风定荷更香”,“馥馥”二字把“荷更香”的“更”字托出来了,形容香气浓烈,似乎能够浸透衣服。再如孔璐华的“露湿稻花香细细,凤生竹韵影娟娟”。“细细”二字有轻微之意,而这轻微并非是指形态,而是指香味。陆游的《芳华楼赏梅》中有“出篱藏坞香细细”之句,讲梅花的香气清幽淡然,但在这里,稻花的香气与花香比起来,更是隐约若有似无的,非静静者是体味不出的,此处叠词用得甚是巧妙。还有女诗人用叠词将形色味一并描摹出,有通感的效果。季芳的“满砌幽兰香袅袅。隔簾明月色娟娟。”前半句中“袅袅”二字,是形容香味的,但是这里似乎能看到在空气中有无形的芳香在缭绕上升。后半句的“娟娟”本来是指姿态柔美,而这里用来形容月色,将月光的皎洁和夜色的美好展露无遗。还有些叠词描摹了诗人细致的心态感受,如季芳的“遥天烟树芜城夕,一水迢迢别恨多”,讲水的遥远而漫长,实际上是讲离愁,是女诗人内心细腻缠绵的情感体验。写水的回旋曲折,实际是写情感的绵长深厚。不仅如此,叠字的使用使得诗歌音韵协调,具有了回环往复的节奏美。
四、曲江亭诗社的文学接受探源
古代诗学的理论准则和评价标准,是男性主导的。这就决定了女性创作的文学必然接受来自男性文学理论体系的影响。要探寻曲江亭诗社的文学渊源,就要在扬州文学历史的纵横坐标中去寻找。
第一,王士禛的“神韵说”在扬州文坛影响深远,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女诗人的创作中。
王士禛在扬州任上六年,“论交遍四方”,结交了一大批文朋诗友,并成为扬州,乃至全国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正式标举“神韵说”,即在扬州仕官之初。“神韵说”的盛行,为当时纤仄缛艳的清初诗坛引入一股清流。
不仅如此,王士禛还推动了妇女创作文学的热情。“清初诗人,颇喜奖挹妇女文学,其最著者,梅村、西河、渔洋三人……渔洋诗标神韵,笼盖百家,尽古今之奇变,其声望披靡天下;当时士大夫识与不识,皆仰之如泰斗。且喜奖掖后进,士女得其一言,声价十倍者……盖渔洋之影响于妇女文学者,实不在袁简斋、陈云伯下也。”[10]
扬州地区不少女性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王士禛的关注、点评奖掖。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王士禛途经兴化,读到扬州遗民诗人李淦妻子徐秀芬的遗诗《寄李季子》,深深为诗歌中表达的情谊所感动,于是作诗《昭阳舟中读闺秀徐幼芬遗诗兼寄李季子》,在诗中对徐秀芬的才情大加赞赏。王士禛还为扬州女子余韫珠作过《题余氏女子绣浣纱图》《赋余氏女子绣洛神图》《赋余氏女子绣柳毅传书图》三首词,以褒赞该女子的刺绣技艺和才华。王士禛曾经创作过《秋柳诗》,他说:“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11]这组创作是他“神韵说”理论的代表作,在全国都引起轰动,“广陵李秀娴、王璐卿、均有和作”。可见在扬州也有不少女性唱和者。
王士禛是台阁重臣,文坛领袖,他在扬州的这段经历,对扬州地区女性创作的推动具有特别的影响。斯人已逝,但诗学影响仍在,他的诗学观念在扬州这块文学场仍然被传播和接受。曲江亭诗社成员中的王子一曾经评价另外一个成员朱兰的诗,“清畹诗尤工七字,旨近情遥,不减渔洋风格。”[9]《曲江亭唱和集》所收之诗,都是以山水景物为关注对象,语言的提炼和意趣的营造是第一要务,从而传达思想韵味与艺术感悟。阮元曾经赞叹王氏家族的王爱兰、王子一、王子庄三位女史“所作诗得斜川、辋川之遗意”[12]452。诗歌是精神的栖息之所,让单调困顿的生活有了诗意的光芒。
第二,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也颇巨影响。他提倡诗歌应当发自本心,书写自我情感,这正与女性的创作思维特征相符。且袁枚大力提携女弟子,而随园女弟子又将其文学主张在同性中加以推广和传播。所以不少女性文人,即使未拜袁枚为师,也间接地受到“性灵说”的影响。曲江亭诗集的编撰者王琼,可以说是曲江亭诗社中创作风格最接近性灵派的一位,“一卷冰雪诗,字字本性灵”(张因《答王爱兰夫人》)。王琼确实与随园女弟子也多有寄答酬和,尤其与骆绮兰、金纤纤的关系最为密切,这在《梧门诗话》中有记载。所以戴健认为晚年“宗唐”的王士禛、标举性灵的袁枚倒是她们的老师[13]。袁枚曾经过访翠屏洲,对王琼的诗歌大为赞赏,意图将其诗歌采入《随园诗话》,他认为王琼的创作与他的文学主张是有一致之处的。王琼虽然拒绝了,但是她诗歌的审美理想对王氏家族中的女性影响颇深。王子一与王子庄两个小辈的诗歌创作有“才能异俗”“妙思总超群”等赞誉,这与性灵派暗合。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正说明了曲江亭诗社与性灵派也是有一定渊源的。
第三,扬州学派“性情论”的文学主张。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在“性命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性情论”,这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理论原则。他的“性情论”是由“节性”的主张阐发而来的,其结果必然回归到传统的文学主张,即要求在行文中体现出“性情之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性情”不是指文人的个性,而是指“雅正”的儒家审美观。阮元指导以孔璐华为首的阮门女眷的诗歌创作,他的文学主张就是他的指导思想。王豫出身诗学世家,是稽古佑文之士,也是阮元的得力助手。王豫编辑《江苏诗征》之时,他的长女王子一、次女王子庄都参与了编纂。她们的母亲徐佩兰是“腹笥博洽,诗不多作”的人,但是她对两个女儿的影响较大。王豫在《内子佩兰五十生日》中提到内子喜诵毛诗:“卅年好合关天性,除却毛诗不诵诗”。王氏家族女性与王豫是同调的,王琼选的《名媛同音集》的依据是“以风雅为宗”,且推崇孔子删《诗》的合乎礼义之旨,并直接提出“夫诗者,持也,所以持其志也。使不能持其志,流于秾纤新巧,淫佚邪荡,其害遂至不可言。”也就是说,曲江亭诗社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追求“性情之正”,即是立足雅正来谈性情,以雅正作为文学风格的评价标准,又以雅正规范文学创作,从这点来说,这是对传统儒家文统的继承,这也正是扬州学派的文学理想在女性文人中的传播。《晚晴簃诗汇》言孔璐华“待庶以惠称,为闺中诗友时相唱和,而谓风云月露,非妇人所重”[14]。张因在赠王琼的诗作云:“彼此勉阃德,足以垂仪型。”[15]如果说神韵说、性灵说是很难脱离当时风气影响所致,那么性情论的影响则是深厚的家学氛围和父兄丈夫的指导提点直接赋予她们的。总体而言,曲江亭诗社的文学追求和理论是复合式的,兼容并蓄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着开放的姿态和审美追求。
曲江亭诗社曾一度兴盛,女诗人的涵咏吟唱不仅满足了自我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而且为名城雅郡的扬州增添了丰富的文学记忆,使得曾有过历史辉煌的曲江亭平添了新的风流。曲江亭诗社的形成及发展,表明扬州一带的女性创作进入了社会性和公共性层面。曲江亭诗社是我们考察扬州地区女性文学整体风貌及价值的典型之一。通过对其群体成员,以及诗社创作做进一步的梳理,其价值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