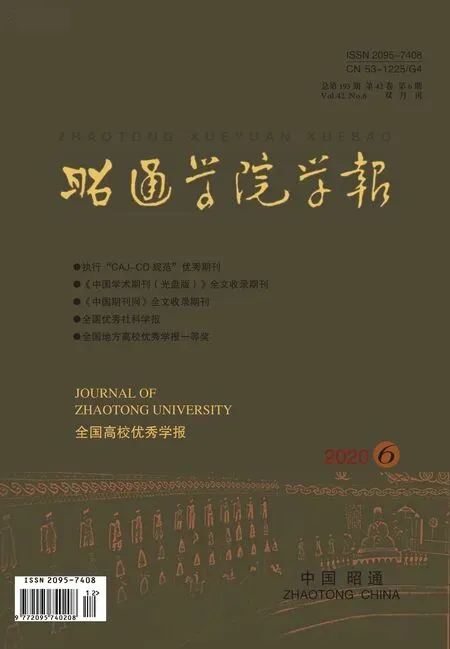维科与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内在关联探析
孟 芳, 李晓庆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一、维科《新科学》的诞生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20-121,意大利哲学家扬姆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风雨飘摇的转型时期。此时的社会矛盾尤为突出,不仅表现为两大对抗阶级在经济、政治领域间的较量,而且也明显的表现为思想领域的斗争。早在14 世纪时,意大利就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端地,人们逐渐意识到要重视现实生活、重视人的价值。但这场运动的影响十分有限并没有真正动摇封建主义统治的思想基础—经院神学,而这成为新兴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于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哲学批判并取代旧哲学,当时的哲学家把目光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扫清障碍,而对社会历史问题则采取普遍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与西方的笛卡尔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笛卡尔认为哲学应该是符合确定性和精确性这一原则的,而历史哲学不符合这一原则,是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而受到关注和重视的。维科对笛卡尔的历史怀疑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也是人类心智最能准确认识到的,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与原则的。因此,不应该把社会历史问题排除在人类的认识领域之外,笛卡尔的做法无疑是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把人的认识范围局限在自然科学的狭小范围之中。在维科看来,笛卡尔的物理学是“使物质受制于一种非物质而起能动作用的象柏拉图所设想的神”[2]660。然而,在当时理性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如柯林伍德所说:维科“确实是走在他时代的前面太远了而没有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3]80-81但不容质疑的是,维科对笛卡尔的批判首先扩展了人的认识领域,把社会历史纳入到人的视域中;其次,维科对笛卡尔这一传统权威的挑战也正是为其新科学奠定理论基础。
维科认为研究是始于问题的,他的《新科学》也不例外。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否具有某种共同性、一致性、规律性?这一问题成为维科《新科学》中的核心问题。维科认为,“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尽管是各自分别创建起来的,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很远,却都保持住下列三种习俗:(1)它们都有某种宗教;(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都埋葬死者。”[2]154可见,维科是从文化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回应,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与原则即共同的人性,这决定了原始状态下的人们必然具有共同的观念,而早期的历史又是由人们的观念创造的,因此,各民族的历史具有了某种共同性。更为重要的是,维科不仅看到这种共同性,同时也揭示出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与独创性,且各种偶然性因素导致的最终结果往往偏离理想的共同性。
二、维科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启示
(一)“民族世界”与“世界历史”
维科的社会发展理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维科认为,“过去所有的哲学家都认真地致力于建立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却忽视了反思各民族的世界或历史世界”[2]154,民族世界成为维科历史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他将历史科学视为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加以研究,他把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类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等的一个过程。维科是第一个试图在各民族历史背后寻找共同规律的人,他不仅通过远古时代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发现人类历史中存在着永恒的规律,而且认为人类历史要经历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维科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是有诸多闪光点的,对以后的赫尔德、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产生重要影响。但在维科的语境中,他的历史概念是等同于社会史和民族史的,他把历史拉进人的眼中,却将自然排除其外。维科还是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历史做出了他的解读,“自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仅能为上帝所认识,而各民族世界却是由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认识它”[2]154。维科把自然史与社会史作了一个截然的二分,把自然划给了“神”。这就成为他理论中的一个二律背反,他一方面承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同时又让天神作为最终因出现,虽然维科力图把历史“归还”给人类,但维科还未完全摆脱神学观念的影响;而马克思认为历史不是仅仅狭义的指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明确为我们指明了历史的两个维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66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是把自然与社会都彻底地“归还”给人类。马克思看到劳动和社会分工的巨大作用,各民族之间随着分工与普遍交往的实现使得历史逐渐成为世界历史,个人逐渐成为“世界历史性”个人。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107-108。各个民族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呈现某些个性特征,然而整个历史发展还是遵循一定逻辑和规律的。
(二)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虽然历史这一概念在维科和马克思这里有着不同的所指,但他们都直接肯定的一点是: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这也是维科历史哲学的基本命题。在维科看来,远古人类凭借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在距离我们那么远的最早的古代文物沉浸在一片漆黑的长夜之中,毕竟毫无疑问地还照耀着真理的永不褪色的光辉,那就是: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2]153-154。人类创造了历史也可以说是维科《新科学》的核心思想,“这个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已把这一点定为本科学的第一条无可争辩的大原则)”[2]609。维科的这一突出贡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提及,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器化大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区别时,马克思在脚注里提到维科的这一命题,“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更应值得注意与研究。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根基之上的,这就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和前提,有了人,历史才得以可能和延续。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通过实践而创造出整个世界,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就是起源于人的本体性需要,马克思正是从物质生产这一现实基础和途径出发来认识并理解人类历史。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在“人间”而不是“天国”。马克思和维科同时也看到,人类并不是在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尽管历史的发展体现着人类的目的性的因素,但历史的前进过程同时也受到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
(三)创造与实践
维科对语言学十分感兴趣,曾经对语言学做过大量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这对维科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拉丁文研究中,维科发现:verum 与 factum 是同一含义,前者是指真理或事实,后者指创造或事实。于是他提出了“真理即创造”这一命题,这也是对当时笛卡尔“我思”的巨大挑战。这个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人类对自己的创造活动是能够清晰认识和理解的。在维科看来,“真理的标准和尺度就是创造出事物本身”[6]62。创造的过程即为认识的过程。人不仅创造了外部世界,而且也创造人自身。在人的创造活动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个人正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而得以存在。在维科的《新科学》中,文化语言成为理解人类自身和人类历史的钥匙,只有理解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语言才能真正理解他们。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创造性活动即实践是一种感性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具有“革命的”和“实践批判的”意义。在第八条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56,这里的社会生活是包含着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广泛领域的全部人类活动,人的本质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进一步论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为满足新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生命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四个“原初的历史关系”之后,又提出了第五个因素,即语言和意识。与维科不同的是,马克思没有将语言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认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81。在马克思这里,语言并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只是伴随人的实践需要而出现的。
(四)历史前进的动力
与同时代的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一样,维科也认为人性本恶,而维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恶”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即对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这一点深深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把恶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手段。维科认为,“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欲和权势欲”[2]101。维科进一步将性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随着家庭和氏族社会的出现,也就产生了主人与奴隶,这意味着两大对抗阶级的产生,人们必然会为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而你争我斗,主要是对土地所有权和食物的争夺,“受统治的人自然希冀自己从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2]314,而处于统治地位的氏族首领等家长们必然要予以镇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与政权,国家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而出现的。可见,维科在他所处的时代已敏锐地猜测到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前进中的重要推动力。人性恶通过阶级斗争这一外显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三个时代的变革正是由于阶级冲突或阶级斗争。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在维科看来,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天神意旨,天意对人类的活动是起到规范作用的,是引导着人们“向善”的。维科的这一思想为之后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则不是从人性出发,而是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感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核心只能是人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人的活动—劳动、交往及其引起的分工”[7]9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斗争只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是阶级社会独有的,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272马克思认为,人类在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凸显,马克思、恩格斯也通过他们亲身的革命实践不断地丰富这一学说的内涵。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它曾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将承担起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三、对历史之谜的不同解答
维科认为,人同上帝一样,是凭借智慧创造世界的,远古时代的人类的心智正是通过“诗性智慧”与天意相连接的,维科把远古时期看作是漫长人类历史的儿童时期,是凭借“诗性智慧”来思维的,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只凭借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去创造事物,“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2]182。人类是凭借自己内心的感觉来体会天神意旨的,然而在维科这里,这一概念不同于中世纪经院神学中的天意,卡尔·洛维特曾指出,“维科的视角依然是神学的,但起拯救作用的天意的手段却是历史的—自然的。历史学有一个前历史学德开端,但却没有终结,没有实现;不过,它是由天意为了人类所指导的”[8]161。同时,维科认为,在发展至人的时代之后会再次回到野蛮时代,实现“复归”,三个时代(神、英雄和人的时代)是周而复始地发展的。在这里,维科的思想就具有了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克罗齐这样评价维科,他“恢复了关于循环(经过和重新经过)的古代东方动机,但把经过理解为生长和发展,把重新经过理解为一种辩证的返复;在另一方面,这种返复并不导致进步,虽则它似乎并不排除进步,也不排除自由意志的自律性或偶然性的例外。”[9]227-228李秋零认为,维科的这种“复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新的基础上的再经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由于发展快慢之别而出现“复归”现象。历史正是在这种螺旋式复归中前进的。马克思则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0]73。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入手,而是现实的指出人的本质是实践的,这种实践是不同于维科的具有心理主义色彩的心智活动的,并且把生产方式看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他既看到了人类历史中的客观必然性和客观环境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又强调人类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目的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是将历史的进步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每一“先进的”生产方式都是应运而生,都曾在某个时代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但人类始终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而这正是马克思终生追寻的一个目标。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最终将消除阶级、私有制,进入到人类的真正历史—“共产主义”。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都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