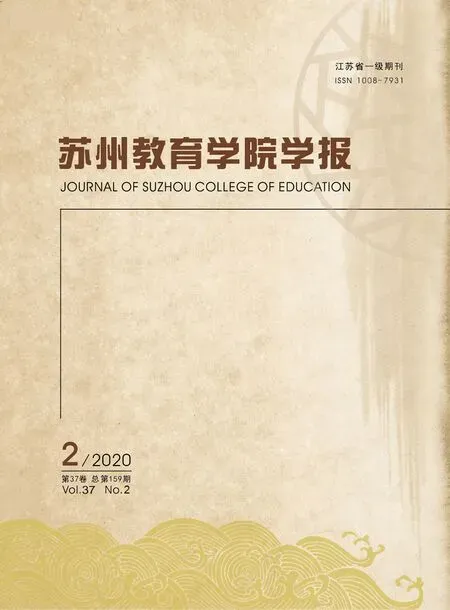《命子》:陶渊明人生价值取向的描述
梅大圣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作为一位具有文化精神的士人,陶渊明在大约二十六七岁时创作的《命子》诗,深刻思考并描述了其人生价值取向。这对于我们研究陶渊明平生出仕,最终选择归隐田园的人生历程很有帮助。
我们要解读《命子》诗所表达的人生价值取向,先必明其系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认为此诗当为初得长子俨时所作,暂系为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当时渊明29岁①王瑶先生主陶渊明63岁说,参见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3页。;邓安生编《陶渊明年谱》认为此诗必作于长子俨三岁以前,暂系《命子》诗当作于太元二十一年(396)前后,此年渊明28岁②邓安生先生主陶渊明59岁说,参见邓安生编:《陶渊明年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76页。;龚斌《陶渊明集校笺》指出,“此诗作于得长子俨后,渊明年约二十六七岁”③龚斌先生亦主陶渊明59岁说,参见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4页。。本文从龚斌说,不再补证。我们明确了此诗大致系年,这对于理解《命子》诗旨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命子》诗旨,古人多有评论。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云:“《命子》诗竟是陶氏家传,人有祖父功德堪述,是一乐事;人有功德著之于前,得子孙文采彰之于后,亦一快事。陶氏两得之矣。后人每于孩提之年,忽忽及长,漫无所成。《易》曰:‘蒙以养正。’可不慎乎!”[1]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一认为,组诗层次分明,“此诗自首章追溯唐、虞、夏、商,盖原陶姓氏族之所自来也。次章‘眷予湣侯’,言陶舍从汉破代封侯,因乱而获武功也。三章‘亹亹丞相’,谓陶青为丞相,能迪前踪也。四章言‘运当隆寙’,谓陶青以后未有显者,迨至中晋而业融长沙也。五章言长沙公勋德,并及其心期之高远也。六章叙祖若父,风规已见。七章以下方说生子、命子之意。然观其嗟自寡陋,自惭影只,谆谆诫勉,其切望诸子深矣。乃子俱不才,委之天运,究何尝有所牵滞于其意哉!”[2]上述评论对于我们理解《命子》诗旨自有帮助。我们通过陶渊明《命子》诗的品读,认为此诗描述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陶渊明《命子》诗表达了振兴家族的强烈愿望,这是其出仕以建功立业的内驱力。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制与宗法观念十分浓厚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生活在各自的家族中,而家族又受整个社会制约。早在西周之前,中国的宗法制度就存在了,并起着核心作用。《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3]6-8《尚书·皋陶谟》亦云:“惇叙九族,庶明励翼。”[3]77西周创建和实行严格的宗法制之后,就更加突出了血缘、家族的核心作用。这种宗法制与宗法观念转化为传统的处世文化后,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用它来指导每个人在处世时的一切言行。魏晋时期,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与家族命运的兴衰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中国人的思想里充满了强烈的义务观念,这义务观念就是责任感,而这强烈的责任感又是中国文化得以绵延的主因。陶渊明《饮酒》其十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4]240表明他自小深受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影响。《命子》诗表达的主要思想,就是希望陶氏家族能够“历世重光”[4]41。这是他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他此后几度出仕的强大动力。这与《孟子·离娄章句上》所强调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167的家国情怀也是相通的。在《命子》组诗中,陶渊明津津乐道于先世功德,重彩浓墨地赞颂曾祖陶侃的勋业,对祖父和父亲的功业亦进行了叙述。
如何看待陶渊明振兴家族的宏愿呢?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指出:“魏晋士大夫重门阀,多有言及祖德并自励者,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之类。渊明《命子》诗追述祖先功德,颇以家族为荣,亦属此类。”[6]六朝最重门第,这个社会大环境必然对陶渊明的人生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他具有强烈的家族情结乃是情理之事。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自述先世源于上古的陶唐,经夏、商、周、秦、汉、魏而至中晋,累世名德,功臣迭出,其目的一是要在当时讲究门第高低的背景下,显示陶氏家族的异常高贵,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价;二是陶氏家族延续至今,业已式微,宗族情结在此所反映出的另一种情势就是陶渊明心灵深处出现了浓浓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陶渊明产生了振兴家族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它是陶渊明热烈盼望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其中包括了儒家宗族伦理、个体意识等元素,是陶渊明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对先世的功业引以为荣。但是,我们从中更多地看到陶渊明对于家族逐渐衰落的深深忧虑。我们可从《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中看到陶氏家族自陶侃之后的迅速衰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7]243
《世说新语·方正》云:
王修龄尝在山东,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7]300
陶侃之后陶氏家族迅速式微,已成陶渊明所看到的真切事实。陶渊明这种对家族败落的忧患意识,是源于儒家文化的。儒家在其经典著作中,总是透露出沉重的忧患意识感的。《礼记·儒行》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8]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9]164这实际上强调了忧患意识在个体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孟子亦在《孟子·告子章句下》中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5]298的著名命题。陶渊明对于家族急剧衰落深深忧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尽快地延续陶氏家族的荣耀,所以,这种忧患意识使陶渊明建功立业的宏愿在心中激荡起来。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第观念的强化,家族教育也兴盛起来。陶渊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把对儿子的教育问题提到了振兴门第的高度来认识。他深感到自己的愿望可能难以实现,“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命子》)[4]42,因此,他在《命子》诗中希望儿子能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夙兴夜寐,愿尔斯才。[4]42
他殷切地期望儿子长大以后早日成才,做到如《诗·商颂·那》篇所说的“温恭朝夕,执事有恪”[10],学习孔伋,继承孔子盛德精神,以发扬光大家族的伟业与荣耀,完成自己的夙愿。
基于此,陶渊明大约在长子俨出生的当年或次年,初仕江州祭酒,投入到振兴家族的实践中,开始迈进了时仕时退而充满矛盾痛苦的艰难仕途。
第二,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提出了出仕的前提条件和为官理念。陶渊明既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又有效法陶氏先贤、振兴家族的强烈愿望,然而,陶渊明动必缘义,他的出仕是有原则性的。
一是《命子》诗中确立了出仕的前提条件,即在政治清明的好时代才出仕。若社会昏暗,则晦迹烟霞避尘世。在《命子》组诗中,陶渊明于第四章中用《周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11]语意,归纳出祖先仕隐情境,云: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4]41
诗人研究了陶氏祖先出处、显隐的规律,认为皆与时势相关。陶渊明认为,乱离之世,则失去出仕的条件,故在第二章说,“纷纷战国,漠漠衰周”,战国、衰周时期,“凤隐于林,幽人在丘”,社会昏暗,乌烟瘴气,只能隐居不仕。诗人所津津乐道的陶氏先贤建功立业的时代大多是政治清明之时、国运昌隆之世,如陶唐、汉高祖时代。如第三章云:
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
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4]41
诗人以豪迈之笔描写了陶舍追随刘邦建功立业,而其子陶青能继承父志,官至丞相。父子二人之所以能光宗耀祖,使家族昌盛起来,皆因为生在汉高祖盛世。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政治腐败,吏治混乱,难以施展抱负,虽然振兴家族、建功立业愿望强烈,也只能作罢。
二是确立了以德为本、施惠于民的为官理念。这是《命子》组诗揭示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命子》组诗中,陶渊明饱含深情地回顾了陶氏先世功德,第五首里追述其曾祖陶侃的勋劳: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4]41
第六章叙述其祖父功业: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4]41
这里,陶渊明赞颂祖先“伊勋伊德”“惠和千里”的美德和勋业,这说明诗人所认定的出仕价值追求是以德为本,施惠于民。这种为官之道,重在“德”“惠”的价值观,与儒家学说的“仁”紧密相连,蕴含了对于自己出仕的人格要求。
孔子学说的根本大义是“仁”。“仁”的含义深厚,且与礼相通。《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9]131《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16将爱亲人之心推及众人,倡导由己及人的仁心是孔子学说的基础、儒家学说的精华。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一度做过官,而且长期奔走各国,宣传他的治世之道。《论语·子罕篇第九》记载了其与门生子贡的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9]91孔子把自己比作待善价而沽的美玉,就是等待好时势,这很说明他对出仕的热心与价值追求。
孔子一生重视好名声,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9]166意为到死后而名声不被人称述,那君子必引以为恨,把生前留下好名声,为百姓所称颂作为君子立身处世的大事。儒家主张君子要有古人情致,要遗留风教和仁爱,让“民”怀思。这一传统世代相承:
死必遗爱,死民之思,不亦可乎?(《国语·晋语二》)[12]
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汉书·叙传下》)[13]
(乐)广所在为政,无当是功誉,然每去职,遗爱为人所思。(《晋书·乐广传》)[14]1244
(诸葛亮)治国以礼,人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晋书·袁宏传》)[14]2394
儒家强调的“遗爱”对象是“百姓”“民”。你的遗爱,百姓认可了,就会肯定并递相称述你的德行,感谢你的恩泽,而敬爱你、思念你。
由上可知,陶渊明《命子》诗所确立的以德为本、施惠于民的为官理念与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后来陶渊明在约作于义熙九年(413)的《形影神并序》之“影答形”中所说的“立善有遗爱”也表达了这个意思。陶渊明在注重完善人的道德情性的基础上,关注自我修持,追求自我道德价值的实现,要把仁爱洒向人间作为出仕的价值观,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陶渊明《命子》诗中展示了知天安命、委运任化的超然胸襟。这首先表现在肯定其父陶敏虚静恬淡的胸襟上。第六章云:
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4]41-42
《论语·公冶长篇第五》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9]49诗人于此称赞其父襟怀超然,或仕或隐,皆能虚静恬淡,不以为意,得之不喜,失之无怨。这种超然品性对陶渊明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其次表现在他对儿子教育的问题上。诗人用四章的篇幅专门谈儿子教育事,这说明他对于后代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自己“夙兴夜寐”的勤奋教育,使孩子长大成材。但在教子问题上,他又不刻意为之,展现出委之天运的襟怀:“尔之不才,亦已焉哉。”[4]42陶渊明这种旷达心胸,在其后来撰写的《责子》诗中也同样展现了出来。他对于“五男儿”不喜读书,难以成材,并不烦于心,而是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处之:“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4]262
综上,陶渊明《命子》诗中所提出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其此后仕途规划影响深远。事实证明,导致陶渊明仕途进退或仕或隐的成因,基本与此诗所规划的价值取向相符。我们知道,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有振兴家族、“大济苍生”的愿望,可惜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其实现。陶渊明在29岁那年才做了个州祭酒,但不堪吏职,自解去职。后又托身于桓玄,不久又厌恶出仕。两次碰壁,已近四十岁,终未消减济世之志。陶诗《荣木》:“先师有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4]13为此,他又相继做了刘裕的参军、刘敬宜的参军。这两次出任军职,他的内心都非常郁闷。陶渊明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后,壮志未酬,索性归隐了,而他那光宗耀祖的夙愿也就成了泡影。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他要振兴家族、济世惠民而必参政;但为官又要有一个清明时代,才能有可能做一个以德为本、施惠于民的官员。这就决定了在晋末道德沦丧、攻伐不息的社会里,陶渊明找不到实现振兴家族愿望的政治环境。于是在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后而毅然挂冠,远离官场,归隐田园。陶渊明平生的进退心态与仕途轨迹,我们已在《命子》诗中看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