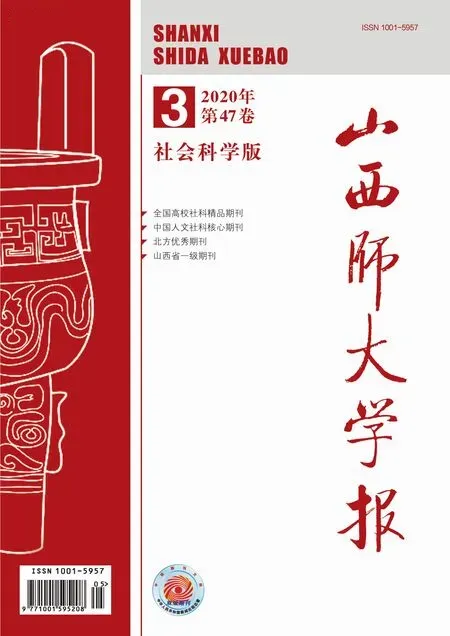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与民国时期的改良一脉
陈文新, 王少芳
(武汉大学 国学院, 武汉 430072)
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这两股对立思潮,对文学史写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果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代表了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那么,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订正)《中国文学史》(1929年)和《中国文学史纲》(1949年)则代表了“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改良派一脉。曾毅以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为蓝本,增删编改而成的《中国文学史》,因前作“颇掇拾东邦学者之所记[1]1”而做了大幅修改的(订正)《中国文学史》,再加上1949年左右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纲》所组成的文学史著作群,既反映了他个人文学史观念的变迁,也是改良派对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回应。
一、从《中国文学史》到(订正)《中国文学史》
曾毅出版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订正)《中国文学史》(下称《订正版》),其前身是“民国”四年(191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下称《文学史》)。从《中国文学史》到(订正)《中国文学史》,曾毅所作的修订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
这次修改版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纲目更为明晰,重点更为突出,即曾毅的改编大旨所说:“原书颇嫌芜杂,分章至百十五章之多,此编则并省不满八十。”[1]1凡可以合并的章节,《订正版》都做了合并,如将《文学史》中的“洛党与道学”“川党与文学”“鹅湖之会与朱陆异同”三章总为“洛党与川党”一章。有些部分则删繁就简,以突出主脉。如中古文学的“昭宣时代之文学”,由于其时文学不振,故在《订正版》中并入“刘向父子与扬雄”,只做简要论述。“大历十才子”等既不是文学史主要人物,在前后文学发展中也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的,都归并到了主要章节。其他如将近古时代的“古今体诗格之成立”换成“声律之完成”,突出声律在近体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和对唐代骈文的重要影响,不仅具有清眉目的效果,也表明曾毅对具体文学史事实的理解更为细致准确。
这次修改版的显著特征之二,是文学史之“史”的意味更加浓厚。在《订正版》中,曾毅不再只是分别评述每个朝代的作家作品和文体,而是对跨朝代的文体的演变更为关注。例如《订正版》关于小说史的叙述。《文学史》分别叙述各朝代的小说,近乎目录解题,而《订正版》除了包含目录解题的内容外,还致力于揭示各朝代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订正版》的处理方法是:将汉代小说并入唐代一章,从汉代小说到唐代小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间有哪些意味深长的小说史现象,都成为重要的叙述内容。之后,又在元代小说一章对通俗小说兴起的背景加以说明。宗旨所在,是加强纵向的文体脉络的梳理。不仅如此,在作家作品的叙述方面,《文学史》拘泥于作品本身的品鉴,而《订正版》则有意与文学评论、文苑传一类体式相区别,减少作品本身的评论部分,更为关注作品的形成过程以及作品在“传统”中的位置。“文学史与文评诗话不同,故关于空洞之品题,务从省节,而着眼于大体上之迁变,得失,兴衰,与其风会趋舍之所由。”[1]2曾毅认为,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不是单个作品的优劣,而是在纵向发展上所处的位置。这个观点与新文化人郑振铎的见解倒是有几分相似(1)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道:“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曾毅重视史的论说,其理论资源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清代的章学诚。曾毅的著作不仅常常引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其行文也透露出章学诚学术理念的影响。二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历史研究。文学史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国别文学的兴起,也离不开历史学的发展。中外无不如此。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历史研究在中国蓬勃开展,而其研究对象扩大的结果,是将文学史作为专门史纳入史学的范围,由此更为强调文学史在历史层面的呈现。三是胡适提出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胡适认为,文学史的历史意味不仅体现在对作品、作者等的考证上,也体现在利用历史研究手段书写文学史上。胡适的观念影响了诸多学者,如谭正璧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强调“史法”,穆济波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文学“本身已属于史学的科学研究之一”,并且要“以历史的方法追溯其原因”[2]1。对“历史”概念的重视与运用,是20年代诸多文学史著述包含曾毅《订正版》在内一个共同特点。
这次修改版的显著特征之三,是对文学与传统经史子集作了更为明晰的区分。“经学、史学渐趋而与文学日远,故较原书多从删汰”[1]2,大量减少了有关学术发展的论述而集中在文学发展层面。在《文学史》中,唐代十八学士的经学、史学两部分与文学殊不相干,却占了足足两章的篇幅。在《订正版》中,唐代十八学士仅一笔带过,不做多余论述。清代史学也被《订正版》全数删去。部分史籍如《史记》虽仍被收录,但主要着眼于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其他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并不显著的历史著作亦排除在外。再如子书,“东汉之诸子者流”改为“东汉之专门著述”,原本单列一章的训诂学内容仅作为小节内容被归并在内。虽然仍以经史子集作为分类依据,但已明确从子书视野转换为著述视野。用“魏晋间文风之嬗变”代替“魏晋之非儒教主义”,删减“鹅湖之会与朱陆异同”等思想史论述,也是这一宗旨的体现。在曾毅看来,学术的发展只有对文学有所作用,或作为文学背景时才有必要加以说明。
这次修改版的显著特征之四,是俗文学得到了较多叙述。随着文学革命的推进和纯文学观念的流行,白话文学,或者称为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平民文学等,被视为文学的主流,新文化人的文学史著述,也多以“纯文学史”“俗文学史”为主体。[3]1以曾毅为代表的改良派学者,则一方面与新文化人展开竞争或论争,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新文化人文学史写作的合理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俗文学的重视。在论述元代戏曲时,《订正版》不仅讨论了词、曲的分别,曲文的进步,还分析了南、北曲的差异与分合等,对戏曲的发展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在小说方面,《文学史》对元代章回小说一笔带过,《订正版》则进行了详细分析。曾毅将小说分为文、白两种,指出元代章回体袭自平话,改汉代之短篇而为长篇,开创了小说史的新纪元。唐末口语体文学的发现、《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形成、元代白话小说兴起的背景、《西游记》《金瓶梅》的评述,都是《文学史》所没有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曾毅对俗文学的重视是建立在小说有利于社会风教的基础上的,与新文化人宗旨不同。他肯定《西游记》“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认为《金瓶梅》是“意主惩戒,而无奈其讽一而劝百也。……虽其间描写社会情伪,淋漓酣畅,深入隐微,供人针砭不少。实过于秽亵,足为风俗人心之害”[1]242,从这些观点可以发现,曾毅偏于从社会功效看小说,沿袭了他一贯的“文以载道”理念。如他在《文学史》中所说:“文以载道也,实所以弼教。……(或以为通俗文学)无当于明道之文,而不知其力之浸染,比于研经葄史者之所为,尤为通遍而渗漉。希腊文明,有耶世希罗之悲剧家,亚黎士多夫之喜剧家,而愈显其色。法兰西革命,有福禄特尔之小说戏剧本鼓吹,而益促其功。盖其感发警醒,有使人转移于不自觉者,明道弼教之用,为独至矣。”[4]238这种“文以载道,明道弼教”的观点,始终包含在曾毅的文学观中。
二、从(订正)《中国文学史》到《中国文学史纲》
尽管曾毅的《文学史》及《订正版》出版后都大受欢迎,但他本人并不满意,仍有“纂组寻常,无甚深意”之感,常思以新作“掩覆旧著之芜陋”[5]4。不无遗憾的是,在修订文学史时就已有打算的《中国文学史纲》(下称《史纲》),不仅未如期与《订正版》同时完成,甚至到1936年也才完成前两卷,直到1949年左右方完成最后一卷即第四卷。对于原创性的高度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文学史的深入思考,使《史纲》呈现出迥异于早前著作的风貌。
《史纲》不同于前作最突出的一点,在于文学史的分期。曾毅指出,文学史的时段划分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而不同的方法所导致的结论会有所不同。如以文学工具分,则可分为文具粗笨、纸笔发明及印刷通行三个时期。就文学类型分,则可分韵文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等。曾毅《史纲》将文学史分为“文学混合期”(周—秦)、“文学分化期”(西汉—隋)、“文学发达期”(唐—清)、“文学专别期”(民国以来),与《文学史》及《订正版》都不同。
曾毅的这个新的分期着眼于“文”“学”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着眼于“文学”从学术混合体中独立出来并发展壮大的过程。曾毅强调,“文学混合期”是文学与学术混合的时代,文学是作为孔门四科中的一门,文人同时也是学者。这个时期的文章多用于政事,属于贵族文学。“文学分化期”则是文学与学问逐步走向分离的过程,学者与文人开始分离,平民文学产生。在“文学发达期”,不仅文与学分,甚至出现了文重于学的情况,各类文体都得到极大的发展,灿然可观。在这时期,除了文学创作增多,文学的研究也渐次发展,传播愈广。最后的“文学专别期”,则文学完全不与经学、史学、哲学等杂糅,纯粹作为单独的门类发展。可以看出,最初曾毅是认同儿岛氏的四分法的,到《订正版》时或许对这种四分法已有不满。所以,尽管他在《订正版》中仍旧以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来对文学史进行分期论述,但绪论中的“文学史上之时代区划”整章内容都被删去。而在近十年之后的《史纲》中,曾毅索性舍弃了儿岛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四分法,采取了新的分期。
从《史纲》目录来看,其特点之二是强化了文体的独立性和文体发展的连贯性。之前的《文学史》及《订正版》是以一个时代为完整周期分述不同文体,这样的结果是牺牲了文体的连贯性以达成时代的完整性。因此,诗文在一个朝代经常被分为几个部分,而难见一个朝代诗文的连贯发展。《史纲》则以文体为主,以文体的纵向叙述为优先。典型的如卷三“文学发达时期”中,第五篇“声律之扩展上”主讲唐至清的诗的发展,第六篇“声律之扩展下”述词、曲和戏剧的纵向发展,第七篇“书系文学之特别发展上”论唐至清的古文发展。当然,这种先文体后时代的取舍是建立在已将文学史分为四期的基础上,在每一个大的时期内先纵向叙述文体的发展。这种以时代为经、以文体为纬的论述方式,多少受到同时期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张振镛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即在《弁言》中说道:“编次采用分类,合而总之,则曰文学史;分而别之,则为诗史、文史、词史、曲史、小说史、戏剧史。[6]1”(2)刘经庵1933年的《中国纯文学史》也采取每个文体单独为一章的模式。随着文学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文体的独立性和连贯性逐渐受到更多关注。
《史纲》的第三个特点是,在以“文”“学”关系的演变为依据对文学史加以分期的基础上,曾毅将中国文学分为《诗》《书》两个大的系列。曾毅认为,文学源自五经,《诗》《书》的作用尤巨,故后世的文学也分别向“诗系文学”与“书系文学”两方面发展。“吾窃以为文学之用,但有《诗》《书》两派。[5]36”这两个系列中,前者主文,后者主质。这种分类,毋庸说是建立在章学诚文史论之上的创新。在曾毅看来,诗词、戏曲、弹词等属于《诗》系文学,而诸子散文、历史著述与小说则属于《书》系文学。“老、庄、管、孟、荀、韩,著述类也。《国语》《左传》《国策》所记,则辞说居其大半也。是二者,本‘书’之流,而‘诗’之义寓焉。”[5]60针对当时以小说戏曲等为纯文学而摒弃古文的观点,曾毅指出这是“强为分属,转多杆格而难通。而今之人,未察此义,乃排《书》之流于所谓纯文学之外,则其道未免大觳矣”[5]36。曾毅强调,纯正的文学应该是“兼综《诗》《书》”[5]43。
曾毅的两分法,近似托马斯·德·昆西所提倡而经由中国学者变形的“情的文学”与“知的文学”之分(3)托马斯·德·昆西将文学分为“知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力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power)。前者教育读者,后者打动读者。中国学者则表述为“知的文学”与“情的文学”。。曾毅的“《诗》系文学”对应的是情的文学,“《书》系文学”对应的是知的文学。稍有出入的,是他将以辞说居多的小说也归入知的文学,因此不能接受新文化人将小说纳入纯文学而否定其他古文作品的做法。他的文学观近于近代广义的文学,包含了知、情两类。而同时代的新文化人的文学史著作,诸子的文章多被有意忽视,如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与《中国文学史新编》、梁乙真的《中国文学史话》,其先秦部分只提及《诗经》和《楚辞》,仅有谭正璧在周秦小说一章的“寓言”中论及庄子、孟子与韩非子(4)刘经庵在1933年编写的《中国纯文学史》的《例言》中,也说古代的散文“多失去文学的真面目”(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只收诗、词、曲、小说。。其他如郑振铎,虽然将诸子纳入文学范围,但根本上是不重视的(5)郑振铎指出,诸子的作品“不惟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54页)。但他认为,文学的中心仍应该是俗文学,只有俗文学“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是“文学史的中心”(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而且,从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史走向来看,先秦的比例逐渐减小,唐及以后的文学成为文学史的中心,这与早期对先秦著作的重视完全不同。。稍早的胡适的文学史著作甚至直接从汉代写起。新文化人这种文学观,在数年后就受到了同一脉学者的批判、扬弃(6)实际上,早在1929年刘半农的《〈梅兰芳歌曲谱〉序》就说道:“正如十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刘半农:《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胡适也自言道:“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朱德发,赵佃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五四时期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又“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第222页)可以说,早期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而有意抹杀所谓国文文学(贵族文学)。而一旦革命已有成效,自然可以用包容态度对待国文文学。,而作为改良派代表的曾毅,则大力肯定以经为中心的知的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曾毅《史纲》的“文学观”显然建立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尽管也认可文学在发挥人的感情方面的作用,但更强调情必须有所止以及“道”的效用,坚持文学“皆关乎政情、民俗、伦纪、物宜,非讽刺,则自勉,所为兴观群怨,要不出此数”[5]231。在早期的《文学史》中,曾毅并未过多渲染“道”的价值,并且强调文学是情感的发挥,这或许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3]但是,从他早前写给陈独秀的信来看,传统知识结构对他的影响仍是根深蒂固的。他在信中写道:“道之本义极宽泛,当古人学术未发达之时,一切名词,皆极含混。道而属于文,即凡事事物物,莫不该之,不必专谈孔孟之道者,始谓之为道也。……文以载道之道即理,即今之所谓思想,特不过古人之所谓道,比于思想,则寓有限制作用之‘正当的’条件在内耳。……论古人得失,而其言必求衷诸至正,至正即道也,事之所存,即莫不有道之所存。”[7]3—4陈独秀的回信写于1917年4月1日,由此可以推测曾毅“文以载道”的观点早已有之,不过在早期的《文学史》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直到《史纲》方才明确断言:“文之所存,亦即道之所存。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今人言文,妄辟‘载道’之说。不知‘道’者,大而兵、刑、农、工,小而米、盐、丝、枲,深之宇宙万有,浅之里巷戏谈,何适而非道?”[5]4可见,在经由日本接受西方文学理论之后,曾毅最后又返回了传统的中国文论,偏于从中国传统去理解“文学”。当然,他的观点是经过西方文论陶冶的,与传统的“文以载道”有所区别。
之所以有上面说的这种“倒退”,除了曾毅自身学术结构的原因之外,也与他反感当时过分强调西方文论,忽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相关(7)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五四时期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第54页)。他批评的对象大部分都是西化论者,即他所谓“窃取西说”者。也是因为这种不满,曾毅前所未有地在《史纲》中特意论述了古今文体与现代的矛盾。他还不容置辩地说:“今之自命为新文学家,排《书》之流之古文于文学之外,与简文一派相同。而又排《诗》之流之今体文,有若干谓须推倒,似又与韩愈一鼻孔出气。并拉入其所为白话体者,号之为新文学。论理既以白话为文学,即不得排斥古文为非文学;既排斥古文为非文学,即不得认白话体为文学。矛盾如是,皆由盲从他化,而未尝辨知自己之源流也。以论文学之主张犹不可,况论史而有所弃取焉?”[5]348胡适以这些“守旧”的改良派们为“不肖子孙”[8]336,郑振铎以曾毅的文学改良为“凡庸的折衷论”[7]5(8)尽管郑振铎在《我的一个要求》中评论各家文学史时,以曾毅与谢无量略为可观,并说“曾毅的较谢无量的还好些”(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63页)。但是他仍以曾毅为凡庸的改良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说道:“这些折衷派的言论,实最足以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第5页)。曾毅则以为,这些新文学的倡导者,“将自身猛力地抽离于传统,带来的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文化意识的断裂”[9]97。而曾毅所思考的,是如何补救这种文化割裂,如何使传统能够自然地过渡到近代。
三、从曾毅的文学史著作群看改良一脉的学术理念
曾毅向传统回归的“倒退”,体现了改良派一脉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理念。在以曾毅文学史著作群为代表的改良派文学史中,确乎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在文学史上肯定经的价值,重视先秦文学的地位。曾毅指出,五经是可信的、最为古老的文艺,并且后世所有文体都是通过五经化合而来的。由此,曾毅将中国文学发展归总为《诗》《书》两条路线,强调经在文学史上的源头作用。经作为文学的来源,乃是改良派在文学史上的共识。陈兆鼎斩钉截铁地说:“夫六艺不独为两汉以上文学之中坚,实亦中国文学之心本。”又说:“经一代之因革,即成一代之文学,所不变者,弗限时代后先,均是六艺根性之文学也。[10]”张之纯则以经传作为文学的正宗,认为一切文章体例大都是本于经传。为了强调经的重要性,其《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首论尊孔对于文教的作用,将《五经正义》放在作品论述的首要位置。汪吟龙甚至这样嘲讽大胆疑古、否定经之地位的新文化人:“今之作者,远后古人,而乃矜断片之异闻,攻经典之阙失,搜出土之琐物,傲前哲所不知,欲据考古之枝谈,尽删文学之本位。[11]”伴随着对经的重视的,是对先秦时代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肯定。清代章学诚有文体皆备于战国的说法,强调了先秦时代在文学史上的源头作用,使先秦文学的重要性有了理论依据。而曾毅等人提出模拟剽窃起于汉代的观点,也提高了作为原创的先秦文学的地位。尽管随着白话文学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20年代末以降,文学史中先秦所占比重总体上逐渐减小,唐及以后作品分量逐渐增加,但曾毅等改良派健将仍我行我素,不仅坚持经的中心位置,也强调先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
第二,在认可文学主情的前提下坚持“文以载道”。随着文学理论的深化或规范化,文学发乎情以动人心的本质逐渐得到广泛认同。不仅新文化人承认,改良派也同样肯定这一点。两者的区别在于,新文化人因此更加理直气壮地否定“文以载道”,而改良派文化人却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文以载道”。典型地体现了双方分歧的是对《诗》的理解。改良派普遍赞成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兴观群怨”说来理解《诗》。其著作被新文化人讥讽为“一团糟”[12]的顾实认为,《诗》虽属于抒情诗,却是在道德法则之下的克制的抒情。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也指出,《诗》虽是感兴的,是情的发现,但只能是在道德羁轭下的思无邪,必须用道德来束缚放逸的情感。[13]18林之棠在《中国文学史》中,也通过阐释《山有枢》,揭橥“诗教”的“温柔敦厚”。曾毅则直白地表明,《诗》的效用在于“乐”,在于安上治民,《诗》是“修齐治平”所寄寓的要道。文学的道德教化和社会功用,伴随着“文以载道”说被改良派视为不刊之论。
第三,主张文学应兼含知、情两种,倾向于广义的文学。随着文学概念的重新厘定,新文化人或是将文学分为广、狭两种,或是将文学分为纯、杂两类,从而将包含诸子散文在内的诸多作品断然归入哲学、经学或史学,甚至将部分古文作者斥为“桐城谬种”“十八妖魔”。改良派则一方面注意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重视诗文的独立性和小说戏曲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认为新文化人彻底否定四部分类的观点是偏颇的,与《文选》排斥经史子的做法一样狭隘。作为对新文化人的回应,康璧城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不仅列入诸子作品,对《史记》大加赞赏,对所谓的“十八妖魔”也予以肯定。羊达之则在《中国文学史提要》中,对被斥为“桐城谬种”的古文作了肯定评述。曾毅《史纲》不止承认诸子作品为文学,更对孟子、庄子的文章有极高的评价。他还指出,史是古文学的发动机,不能将史、文判然分离;小说的来源可上溯由五经分化的辞命等文体,即便是为了厘清后世纯文学的发展,也不能尽弃知的文学不论。以曾毅为代表的改良派学者,对于被新文化人所鄙薄的“古文”以及孕育了古文的经、史、子,感情很深,让他们放弃大文学观,是不可能的。
尽管改良派和新文化人在文学观、文学史观上有种种龃龉,前者鄙薄后者只知模拟西方,后者嘲讽前者只懂泥古,但对于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文学,改良派也是肯定的。他们承认,随着文学进化,古文或许已不适合新的时代,但是,他们的“一代有一代之学”与其说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观,不如说是平等的发展观:后一代文学不代表比前一代更为优秀,只是何种更适应时代的问题;不适应新的时代并不代表没有任何研究的价值,也不代表可以弃之不顾。面对当时中国落后的现状,新文化人想推翻一切造成这种局面的旧文化,以新文化代之;而改良派们则希求连接旧文化与新文化,以旧文化作为根底开出新文化之花。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手段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