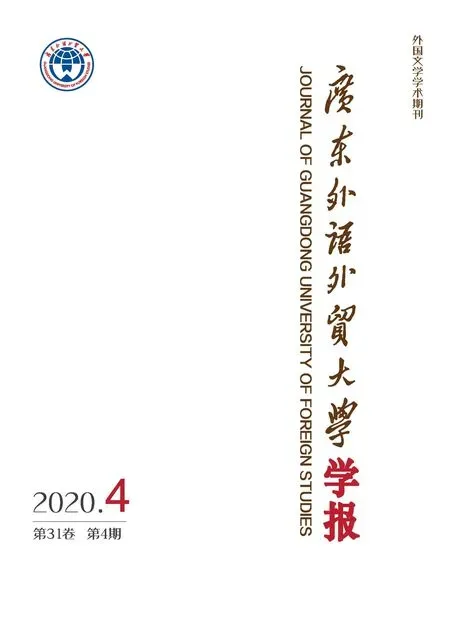桑塔格研究“新浪潮”中的特点与走向
——芭芭拉·秦访谈录
顾明生
近年来,美国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作品在中国获得持续关注,她的小说、随笔、戏剧作品被尽数译成中文,并几次再版重印。二○一八年上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新版布面精装的《苏珊·桑塔格全集》,共十六卷,计二百八十余万字。随着译介工作的深入开展,桑塔格的作品逐渐成为国内美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桑塔格日记、笔记以及几部学术传记的出版也激起了美国桑塔格研究的新高潮,其研究模式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研究成果呈现出全新的样态。近期,美国桑塔格研究专家芭芭拉·秦教授(Barbara Ching)就美国桑塔格研究中的最新动态、范式演变、发展趋势等问题接受了中国学者的采访,现将部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顾明生(以下简称“顾”):亲爱的秦教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邀约。二○○九年,您和詹妮弗·瓦格拉-罗拉(Jennifer Wagner-Lawlor)共同编撰了论文集《苏珊·桑塔格的争议:公共事务及私人生活》(TheScandalofSusanSontag:PublicandPrivateAffairs, 2009),这一文集是桑塔格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桑塔格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趋向多元化的标志性成果。我们的访谈就从这部文集出版后美国的桑塔格研究谈起吧,您能否谈一下美国桑塔格研究的最新情况?
芭芭拉·秦(以下简称“秦”):早期的研究,比如索恩亚·赛尔斯(Sohnya Sayres)的《苏珊·桑塔格:忧伤的现代主义者》(SusanSontag:TheElegiacModernist, 1990)和利亚姆·肯尼迪(Liam Kennedy)的《苏珊·桑塔格:心灵的激情》(SusanSontag:MindasPassion, 1995)阐释了这两部专著出版前的桑塔格职业生涯,主要讨论当时桑塔格已经出版的作品。一九九五年前研究桑塔格的学术文章常围绕着她的一、两篇论文或小说进行探讨。从二○○八年起,桑塔格日记选集以及最近两本传记的出版,激发了或许可以被称为桑塔研究的“新浪潮”,它更加关注影响桑塔格创作的学术、社会和历史语境。同时,越来越多的非印刷品资料可以通过网络轻松获取,学者可以接触到更多桑塔格的电视采访和公开露面的资料。简而言之,我们能够查阅的档案文件已经在形式和内容上被极大地拓宽了,这不但直接带来了桑塔研究的新浪潮,而且促进了桑塔格研究的范式演变。
顾:您认为桑塔格研究“新浪潮”中最重要的“新奇之处”是什么?
秦: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在《法国之梦》(DreaminginFrench, 2012)一书中,巧妙地引用新获取的(包括旧的)文献材料。卡普兰(2012: 83)指出,桑塔格首访巴黎时还是个研究生(1958年),这一经历塑造了她的职业生涯,并帮她“褪去了学者的茧”。她还讨论了桑塔格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岁月(1949-1951)。卡普兰仔细查阅了桑塔格就读芝大时的笔记和课程论文,发现她曾修习过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开设的课程,并以评析杜娜·巴恩斯(Djuna Barnes)的小说《夜林》(Nightwood, 1937)的文章作为伯克课程的课程论文。卡普兰的发现激发出关于桑塔格前两部小说[尤其是关于《恩主》(TheBenefactor, 1963)]的有趣问题。例如,如果说,除了受法国新小说影响,桑塔格的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还源于那个让她痴迷的亲法派美国作家杜娜·巴恩斯(她是个很早便在巴黎居住的双性恋女作家),那将会是怎样的研究图景?或者说她的《恩主》受到其非常美国化的老师,特别是作家、修辞学家的肯尼斯·伯克及其小说《朝着更好的生活》(TowardaBetterLife, 1932)的影响,那又会导致怎样的研究走向?
当卡普兰聚焦桑塔格的教育背景时,历史学家乔治·科特金(George Cotkin,2016: 2)则将桑塔格的作品和成功放入“1952-1974年的美国文化背景中”,这背景便是“挑战边界、藐视期待和买卖夸张”。他的《饕餮盛宴:新感受力的文化史》(FeastofExcess:ACulturalHistoryoftheNewSensibility, 2016)中的一章描绘这二十三(1952-1974)年中的一年;每章讨论一位或者两位艺术家。例如,一九六八年这一章讨论的是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一九七二年这一章讨论的是艾瑞卡·琼(Erica Jong)。桑塔格在一九六四年那一章,那年她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批评檄文《反对阐释》(AgainstInterpretation)和《坎普札记》(NotesonCamp),并因此声名大噪。科特金注意到桑塔格兴趣广泛,但同时也注意到她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最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疏离:例如民权运动、越战的升级和让人身心俱疲的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科特金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桑塔格在“新感受力”问题上的矛盾态度,认为桑塔格很快餍足于新感受力的饕餮盛宴,并最终否认了她的部分新感受力偶像。科特金引用琼·阿克塞拉(Joan Accocella)刊载于《纽约客》(NewYorker)文章中的一段话说明上述问题。在这段话中,桑塔格坦率地告诉琼:“我曾经认为我喜欢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还有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但是我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Accocella, 2000)。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不同,桑塔格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八年间热切提倡艺术的情色学和新感受力,然后在《河内之行》(TriptoHanoi, 1968)中转而呈现一种更少见、更严肃的政治感受力。桑塔格对美学和政治的矛盾誓约已被研究者广泛关注,但科特金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认真审视那些易被忽视、却对桑塔格的成长和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历,比如桑塔格和许多其他艺术家共有的冷战经历,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桑塔格其人其作的理解。
黛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也像科特金一样强调桑塔格创作的文化和历史语境。在《足够坚韧》(ToughEnough, 2017)中,尼尔森把桑塔格归入二十世纪中期的女性艺术家、作家这一群体中进行研究。她不仅把桑塔格关于疾病、感受力、性欲、摄影等的观点放置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流知识、艺术风潮中观照,还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桑塔格最引人瞩目的批评术语——“情色学”(erotics)的重要性。尼尔森(2017: 119)认为,这个词语概括了“桑塔格曾经持有过的前后最一致的立场”。尼尔森通过细致阅读桑塔格的主要作品,特别是《反对阐释》的浮夸结尾:“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情色学”(Sontag, 2001: 14),总结出“情色学”是一种结构,“能驾驭强烈的感情,即使它也增强感情的强度”(Nelson, 2017: 111)。她还描绘了桑塔格在职业生涯中将强烈感情控制在关键点的努力,展示了《论摄影》(OnPhotography, 1977)、《疾病的隐喻》(IllnessasMetaphor, 1978)和桑塔格关于9·11事件的评论如何再次使用《反对阐释》的论证结构:桑塔格的“坚韧”是一种感官意识,它不会退化为那种通常与女性相关的纯粹非理性反应,相反,它会产生一种更具力量、更有见识的反应,防止绝望(对待癌症)、防止愚蠢(对待9·11恐怖袭击事件)、防止任何情形下的反应过度甚至是爱和欲望的泛滥、膨胀。
凯蒂·洛芙(Katie Roiphe)在《弥留之际: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光》(TheVioletHour:GreatWritersattheEnd, 2016)中研究了桑塔格的死亡观(还有另外五位作家的死亡观,都是男性)。桑氏的死亡观既是一种管理强烈情绪的途径,也是一种“正视死亡,减少恐惧”的途径(Roiphe, 2016: 15),也许尼尔森会将之归类为“死亡情色学”(erotics of death)。正如我们从桑塔格的儿子大卫·里夫(David Rieff)的回忆录《死海搏击》(SwimminginaSeaofDeath, 2008)中得知,桑塔格在罹患疾病的过程中通过保持乐观心情、坚定战胜病魔的决心甚至否认死亡来控制恐惧情绪。她相信可以找到——或者可以期望找到治愈致命癌症的方法。为此,洛芙(2016: 63)不禁思忖:“这个一生特立独行、努力成为佼佼者的桑塔格是否在灵魂深处坚信她永远不会死去?她的长篇小说中有很多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死亡”。洛芙的观察和黛博拉·尼尔森对桑塔格批评散文的分析打开了审视桑塔格最后几部作品的新视角,特别是桑塔格将作者型叙述者“我”置入《火山情人》(TheVolcanoLover, 1992)和《在美国》(InAmerica, 2000)故事中的方式——好像叙述者“我”经历过她想象和叙述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大事件一样,并且以此类推,她好像能够使这些故事无限地继续下去。确实,《火山情人》强调“我们回来”,就像小说中的维苏威火山和其他火山会在无法预知的周期里爆发一样。
最后,新的(和即将出版的)传记进一步拓展了解读桑塔格作品的语境和阐释路径。丹尼尔·施莱伯(Daniel Schreiber)在其德语传记《苏珊·桑塔格:智慧与魅力》(SusanSontag:GeistundGlamour, 2007)的二○一四年英译版序言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证据,我也曾在《苏珊·桑塔格的争议》中暗示过相同的内容,即桑塔格滥用药物。二○一四年,施莱伯(2014: ix)在写作序言时声称,他将“强调桑塔格从一九六四—— 一九八○年沉迷于安非他命的事实”。卡利·罗利森(Carl Rollyson)和莉莎·帕多克(Lisa Paddock,2016: 97)也在更新版的未经桑塔格授权的传记中,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指责桑塔格沉迷于安非他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心为身役》(AsConsciousnessisHarnessedtoFlesh, 2012)的几篇日记中,桑塔格曾提到自己在服药,这可能引出她是瘾君子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的论述者施莱伯和罗利森都没有提供确定性的证据。大卫·里夫在《心为身役》撰写的编辑评论中避开了“成瘾”这一贬义词汇。里夫解释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桑塔格因为写作“变得依赖(安非他命的虚幻)……而且一直服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过剂量在逐渐减少”(Sontag, 2012: 11)。如果桑塔格真的是位瘾君子,她就像她全面隐藏了她的性取向一样隐藏了此事——但是读者也许可以在本杰明·莫沙(Benjamin Moser)的授权传记和桑塔格的第三卷日记(最后一卷)中找到关于上述两方面更为全面的信息。
顾:在《法国之梦》中,卡普兰(2012: 85)曾这样强调杜娜·巴恩斯对桑塔格的重要影响:“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可能对从阿娜伊斯·宁(Anais Nin)到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老一辈女性知识分子很刻薄,但是有这样一位女性作家从未被她嘲笑,她就是杜娜·巴恩斯,这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成为桑塔格的文学幸运神”。然而,桑塔格研究者很少讨论这位影响了桑塔格的美国作家,您认为这种影响研究可能成为桑塔格虚构作品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吗?
秦:我曾在《甚至不是一个纽约人》(NotEvenaNewYorker)中讨论过理解桑塔格作为一名美国作家的重要性,我的确认为如果我们阅读桑塔格的虚构作品时能联想到美国的其他作家,将会使我们的理解更为丰富。我时常会想到的两个美国作家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和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一九九五年,在与爱德华·赫希(Edward Hirsch)的访谈中[刊载于《巴黎评论》(TheParisReview)上],桑塔格指出《火山情人》的副标题“一个传奇”来源于霍桑对小说和传奇的区分。桑塔格将《在美国》的副标题定为“一部小说”,它与霍桑的《福谷传奇》(TheBlithedaleRomance, 1977)具有同样的主题,即集体的、乌托邦的生活实验;《死亡之匣》(DeathKit, 1967)似乎在映射霍桑的《红字》(TheScarletLetter, 1850),两部小说的女主角都拥有不同寻常的名字“海斯特”。很明显,桑塔格仰慕霍桑,但她和玛丽·麦卡锡的关系则被描述为同性劲敌。据说(而且常被重复说),麦卡锡曾说桑塔格是“山寨版的我”。一九六八年,麦卡锡和桑塔格都出版了关于北越旅行的小册子,桑塔格的作品是著名的《河内之行》,麦卡锡的则叫《河内》(Hanoi)。麦卡锡也出版过一部简短的小说——《绿洲》(TheOasis, 1949),讲述一个失败的乌托邦社区,里面居住的人物很清楚是在影射当时为《党派评论》(PartisanReview)撰稿的作者。
顾:刚才您提到那些可在网络上获取的非文本材料也值得探究,例如桑塔格的电视访谈,这些新媒体材料可以对桑塔格研究做出怎样的贡献?
秦:戴娜·海勒(Dana Heller)最先在《绝对严肃: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苏珊·桑塔格》(AbsoluteSeriousness:SusanSontaginAmericanPopularCulture)中所描述的玩家艺术(fan art)和学术评注创造了桑塔格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文本。最好的例子就是玛利亚·波波娃(Maria Popova)的网络日志。她经常和插画师合作发布关于桑塔格的博文,插画师给波波娃笔下的评论增加了另一个思考维度①。
多媒体剧院也为探索桑塔格其人其作提供了平台,它们尝试把非传统叙事和桑塔格研究中的批评视角相结合。二○一三年,女演员、剧作家莫西·安琪洛(Moes Angelo)创作了戏剧《重生》(Reborn)。安琪洛扮演年轻的桑塔格,在剧中夸张地朗读桑塔格的日记《重生》(Reborn, 2008)。舞台布景是桑塔格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其中一张是中年桑塔格的照片,目光犀利、冷峻。精巧的舞台布局正好使照片上的中年桑塔格审视式地凝望着舞台上安琪洛扮演的青年桑塔格。这是一幅道林·格雷(Dorian Gray)式的肖像照,它能神奇地表达出桑塔格对自己早期激进宣言的反讽式评判。西比尔·凯普森(Sibyl Kempson)的《现在让我们颂扬苏珊·桑塔格》(LetUsNowPraiseSusanSontag, 2015)是一出歌剧,我想说它类似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WaitingforGodot, 1953),既向桑塔格的摄影批评致敬,又在贬损它的价值。它描绘了桑塔格借助时间旅行去拜访詹姆斯·艾杰(James Agee)和沃克·伊文思(Walker Evans)的作品《现在让我们颂扬伟大人物》(LetUsNowPraiseFamousMen,1941)中的佃农,再一次探索了非传统叙事和研究桑塔格的批评视角相结合的可能性。艾杰和伊文思(剧中的杰和本)作品的聚焦对象——佃农迫切地期待星期日的到来,这样他们便可暂停劳动、获得休息;而观众则可能一直在期待桑塔格(Sontag是德语星期日的写法)的到来。正如舞台提示所说,这种“拜访”将出现两次。桑塔格两次出现在杰和本的工作间,并告诉他们:“你们为这些家庭拍摄的照片太美以至于无法促使我们做些事来补偿他们所受的苦难”(Kempson, 2015: 83)。然而,最后一幕保留了一些希望,正如佃农们咏叹他们翘首期盼的一切就在未来,舞台灯光变暗,桑塔格出现了……。
最后,我想谈谈“数字文本分析”这一研究手段在桑塔格研究中的应用。数字文本分析具有“数字人文”的特点,它可以快速提供关于桑塔格的风格和主题的新信息,这些信息依据桑塔格选择风格的数据来确认、区别甚至反驳目前我们对桑塔格的艺术和思想的既定理解。例如,我们把“典范的”“严肃的”“情色学”和“贪婪”等词语与她的作品相结合进行数字计算分析,便能确定哪些词语出现频率最高,以及以何种组合形式出现。由此分析提取的信息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断演进中的桑塔格艺术和伦理观点,并识别其一致的、核心的观点。
顾:说到非文本材料,最近我观看了一份桑塔格和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于一九八三年为英国广播公司《声音》(Voices)节目录制的访谈视频资料,话题关于如何讲故事。桑塔格对何为虚构作品以及如何讲故事提出了有趣见解。她说她写虚构作品是为了探索“道德困境”和“打破禁忌”(Sontag, 1983)。中国的桑塔格研究者很少讨论这份视频资料。您如何评价她在这次访谈中陈述的关于讲故事的主张?
秦:美国学者也没有研究过这则访谈,所以我很感谢你让我注意到它。当阅读桑塔格的虚构作品时,我们很难说它们打破了多少禁忌——至少从二十一世纪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她最初的两部小说没有为她赢得很多拥趸,但是它们也未因为打破禁忌、呈现令人震惊的价值观而被批判,令评论家和小说读者不满的是它们的沉闷乏味。在电视访谈的对话情境中,桑塔格也许一直在努力变得更有趣!她或许选择了一个更具刺激性的词语——“禁忌”突出她和伯格在讲故事方面的不同观点。
伯格先提出了他的模式:“如果我想到某个人在叙述故事,我看见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我而言,讲故事的真正概念就是得有一个栖身之所”(Sontag, 1983)。桑塔格(Sontag, 1983)对这种舒适并不感兴趣,而且确信读者也不感兴趣:“人们想要拥有超越自己的旅行,人们需要体验他人的经验,这经验没必要与对真理的需求完全一致……(有)一种渴望,渴望看见禁忌被打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非常重要……它更吸引我……我认为虚构作品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幻想;我对道德幻想感兴趣”。的确,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由主人公的一系列梦编织而成,可以被描述为道德幻想,《死亡之匣》讲述的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个也许(也许没有)打破禁忌的主人公犯下的凶案。她强调作家成为创造者的重要性,而伯格举例他所写的故事是基于他认识的农民的生活(他的原话)。同样,桑塔格把自己定位为现代、都市作家,利用文学传统而非自己熟悉的生活创作。另外,把这次访谈放到桑塔格职业生涯的时间轴上考察会使我们更加理解她作为虚构作家的成长历程。一九八三年,她没有发表虚构作品,自《我,及其他》(I,etcetera,1977)出版后,她便没有发表过任何虚构作品。直到一九八六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书简情景》(TheLetterScene)和《我们生活的方式》(TheWayWeLiveNow)。一九九二年,她出版了《火山情人》,那时她对虚构作品的说法又完全不同了。
顾:您曾经说过,“……桑塔格的文学概念……虽来自欧洲的大师,但融入了她的美国理想”(Ching, 2009)。中国的桑塔格研究暂未涉及这一内容,您能详细谈谈她的文学作品是怎样呈现美国理想的吗?
秦:美国理想(American Ideal)是在她的作品中渐渐出现的,到她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它已经变得无法回避了。如果我们去读桑塔格最初出版的书《恩主》和《反对阐释》,她的美国人身份或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在随后的两本书中,小说《死亡之匣》和她的第二部散文集《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ofRadicalWill, 1969),桑塔格将美国和她的理想作对比。《激进意志的样式》更加公开地批判美国生活:它以《美国现状》(What’sHappeninginAmerica)和《河内之行》两篇散文结尾。《美国现状》由桑塔格于一九六六年参与的问卷调查的回答组成。在《美国现状》里,她谴责越南战争,赞扬反战的年轻人。在《河内之行》中,她做了更多的自我检讨,从接待她的越南人身上看到的质朴、单纯和真诚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是个外国人:“我关于这个地方的全部认识就是一个来到河内的美国人带来了非常复杂的自我,至少我这个美国人是这样的”(Sontag, 1969: 229)。她用含蓄的誓约来总结她的河内旅行故事,发誓将河内经历根植于体内,让这经历使她激进,让这经历使她重拾自己的根:“在北越时发生在我身上的转变并没有随我返回美国而消失,而是还将继续下去”(Sontag, 1969: 274)。将这种理想带回美国就是她激进意志的样式。
当“围攻萨拉热窝”侵蚀了她对欧洲的理想时,桑塔格的创作和社会活动更加清楚地展现出一个改革派美国人的倾向。桑塔格的最后两部小说探索美国理想(尽管没有完全实现)在小说谋求道德和美学平衡时扮演的角色。当她写到移民时(离开欧洲去成为美国人),即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她把它题献给了“我在萨拉热窝的朋友”。 尽管她看到美国文化和美国历史里的瑕疵,但依然使用卷首的乐观题铭——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让美国再度成为美国!”来架构故事。休斯的话确信美国将会实现它在《独立宣言》中宣告过的人人平等的文化。我认为,桑塔格如此乐观看待、如此倾心投入到美国可能发生事情与她早年对美国时政漠不关心以及她在《美国现状》里展现的悲观论调完全不同,那时她曾经强调美国种族屠杀的历史,并预言这个国家注定会灭亡。
顾:当我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访学时,我们每周进行一次“桑塔格研讨”,我们谈论到桑塔格对“静默”(silence)的兴趣,以及“静默”在她早期虚构作品和最早的两部电影《食人者二重奏》(DuetforCannibals, 1969)和《卡尔兄弟》(BrotherCarl, 1971)的情节构建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纵观她的批评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制作,是否可以将桑塔格的创作看作是一个探索“静默”的工程?
秦:在她的日记中,桑塔格(Sontag, 2008: 101-02)将说话和非写作联系到一起。一九五七年初,她解释道:“说话的漏损。我的脑子通过我的嘴巴喋喋不休……我的嘴巴像得了腹泻,但是打字机却像得了便秘”。她想象如果她说得越少,她可能就写得越多。在我看来,桑塔格认为静默是创作的一种条件:写作始于静默。过去,我和其他桑塔格研究者都没有在《苏珊·桑塔格的争议》中讨论过“更好地言说”(Speaking Better)这一论题,目前,我正尝试从整体上思考它,“更好地言说”也许才是桑塔格创作中最重要的工程——尤其是当我们把“言说”放在掌握个人语言这一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考虑时。是的,无声和静默引起了桑塔格的兴趣,她的晚期创作对“更好地言说”颇为着迷。它凭借各式相关主题在她的小说中得以呈现,比如减少口音,《火山情人》里的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和《在美国》里的玛琳娜·扎温佐夫斯卡(Maryna Zalewska)都曾努力减少自己发音中的口音。这也许在暗示:更好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有效地驾驭修辞情景,以便使勇敢说出的话语改变听众或读者的思想和心灵,我认为这对桑塔格尤为重要,《火山情人》的结尾也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上述观点。这部小说的结尾是爱勒纳拉·芳斯卡·皮明特尔(Eleonora Fonseca Pimentel)的独白:“我不会承认我曾为正义而不是为爱所动,因为正义也是爱的一种形式。我确实知道权力是怎么回事,我真的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但我不接受。我想要树立个榜样……我不能宽恕那些除了自己的荣誉或幸福什么都不关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文明人。他们是可鄙的。让他们全见鬼去吧”(Sontag, 1992: 419)。在这个结尾中,道德和美学一起发声。
顾:秦教授,再次感谢您为本次访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秦:谢谢你,明生,谢谢你深思熟虑,提出了这么多好问题。
注释:
①详情请见:https://www.brainpickings.org/tag/susan-son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