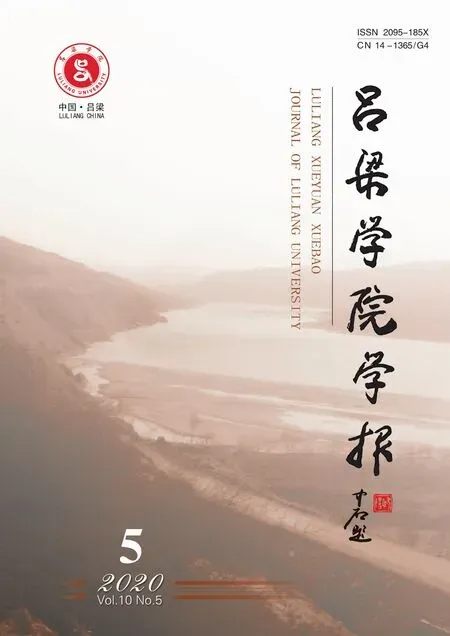审丑狂欢与极致表达:新型二人转的四重“突围”
陈丽妍,白 薇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1)
文化遗传理论认为:“文化由于稳定、变化和遗存而产生的上下承续的阶段性联系,”“文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和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从文化现象之间前因后果的合乎规律的联系来看,不难看出新型二人转脱胎于传统二人转,对传统二人转既有所继承,亦有所扬弃。本文所说的新型二人转指的是以歌舞、说口、绝活、杂技为主的现代二人转,传统二人转指的是以传统题材为唱段的二人转作品。
新型二人转抛弃了传统二人转的审美追求,更加倾向于“审丑”。“审丑”一词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新型二人转突破了传统二人转对高雅的、美的无限追求,从角色到主题都力求对“丑”的极致化表现。确实,在观看二人转的过程中,观众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暗示:谁丑谁是主角,丑的才有看头,越丑越值得期待。
新型二人转对“丑”的展现是全方位的,从表现形式到主题内容,而且追求对“丑”进行极致表达。二人转演员的扮相为了凸显丑,极尽打扮之能事,并通过丑角与旦角的疏离,进而强化丑角形象。采用碎片化的艺术处理,将若干以性爱为内容的“丑”的桥段,通过唱词、说口、舞台动作等进行极致化表现。对“丑”的极致化表达是新型二人转对传统二人转的重大突破。
一、脱掉“彩扮”——新型二人转更纯粹
传统二人转的旦丑二角“彩扮”(第一代二人转研究专家王肯先生说:“二人转是一男一女两个彩扮的演员又说又唱又跳又舞,跳进跳出地演出一个叙述兼代言的诗体故事。”[2]20-21)他人的戏份多,而以演员自己的身份存在于舞台上的戏份少。新型二人转恰与之相反,二人转演员常常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从而淡化了传统二人转扮他人演故事的演出形式。
新型二人转丢弃了传统二人转的“彩扮”,舍弃了传统戏剧中的脸谱,摘下了与喜剧表演如影随形的面具,完全靠二人转演员的本色出演,以最真实的自我来展示“丑”,最终收获喜剧的艺术效果。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第五章就曾指出 : “喜剧是对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 。”[3]24新型二人转选择了这条模仿丑的喜剧之路,而且选择了喜剧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条。无论是歌剧、舞剧、话剧还是诸多其他的戏剧形式,或者是利用脸谱,抑或是利用面具,也可以像传统二人转利用“彩扮”的形式,这些外在的道具都可以使戏剧本身的戏剧性更强烈,更容易达到追求的艺术效果。“当你带上面具时,你就已经有一半生命的入戏了。”[4]153-154新型二人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所有外在的道具,取而代之的是演员最本真的出演。
新型二人转演员也会用一些特殊的扮相来彰显“丑”。如刘小光的劳动服配红袜子,大背心儿扎领带,魏三儿的吊腿裤佩斜挎包。但是这些确实都是东北人田间地头的穿戴,只不过是被胡乱搭配夸张放大之后搬上舞台。这样的扮相,让我们看到了新型二人转艺术的质朴,看到了二人转演员对观众的无限真诚。新型二人转演员正在用他们的表演向观众展示东北人的幽默,这种幽默是属于每一个东北人的。东北二人转艺术灵感来自东北民间,使用的语言符号是东北话,表现的内容是东北人的生活,展现的是东北人的性格,彰显的是东北人的文化。新型二人转看似选择了一条最窄的路,但必将越走越宽,市场前景必然越来越好,正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新型二人转完成了对东北人最极致的诠释。这样的诠释,才最符合东北人大胆质朴真率的性格特征,才最符合东北人的审美期待。东北人看不惯“戴面具”的人,对于艺术,他们更喜欢这种脱掉所有演出服饰对“丑”进行极致表达的喜剧表演。
脱掉“彩扮”看似简单,却是新型二人转对传统个人转最本质的突破,因为这意味着新型二人转找到了自己最新的艺术定位——纯粹的的东北民间艺术。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能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才能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而要达至文化自觉的境界,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并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5]1-12不言而喻,新型二人转对自己准确的艺术定位就说明它对自己的文化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能在转型过程中具有自主能力,并顺利完成从对传统二人转的成功转型。我们姑且将这一突破称作新型二人转对传统二人转的第一重“突围”。
二、拉开距离:丑角对旦角的疏离
传统二人转旦角居于中心地位,丑角围着旦角转。在这种看似简单的表演中,其实完成了二人转向原始艺术的复归。王国维先生说戏剧起源于巫,但好多戏剧是离开了巫的原始基本形式的,主要标志就是演员的不断增加。传统二人转与新型二人转最大的同质性在于二者均保留“二人”的形式,这是二人转同其他剧种的最大区别。即东北二人转因为仅有两个演员可视为最好地保留了巫的原始基本形式。杨朴先生在他的论著《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中,对二人转形式进行追根溯源,也力证东北二人转源于东北远古神话原型。神话原型的展现形式就是萨满跳神,萨满跳神既是对创世女神的模仿,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达到娱神的目的。在历史的演进中,萨满表演的男女“二神转”原型丧失了,二人转发展成为独立的表演形式。所以二人转本身是对女性美的展现,尤其是在表演过程中男角表现出对女角的痴迷状态。诚如杨朴先生所言:“传统二人转中有一种统一的造型方式,女高男低,女美男丑,女中男侧,男绕女转等”[6]78-85,这显然是为了突显女性形象。新型二人转则不然,新型二人转中丑角并非旦角的配角,在表演中,丑角和旦角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比旦角更出风头。所以,旦角不再是丑角爱慕欣羡的对象,甚至在一些桥段中,旦角成为被丑角戏耍的对象。旦角的中心地位随着丑角与旦角关系的疏离而被消解。
新型二人转对这种去中心化表演形式的大胆尝试,使得表演内容呈现出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这是对传统二人转的重大突破。同时,丑角对旦角的疏远,无形中提高了丑角的地位与作用。“无丑艺不全,有丑转的欢,喜兴加俏皮,全仗此一观。”“三分包头的,七分唱丑的。”“旦是一条线,丑角一大片”。“旦是一棵菜,全仗唱丑的卖。”[7]12-13可见在新型二人转中,丑角地位的重要。
新型二人转故意拉开丑角与旦角距离,使丑角成为舞台表演中独立于旦角之外的重要角色,甚至丑角才是二人转舞台上的核心人物。无论是走进二人转小剧场还是坐在荧幕前看二人转,一种共同的心理期待是对丑角的期待,甚至可以说,谁丑看谁,越丑越有戏。比如:宋小宝、小沈阳、小黄飞、孙小宝、魏三儿、刘小光等,每一个都丑得与众不同,每一个都丑得独一无二。丑角对旦角的疏离,使其成为舞台上的聚焦点,这是新型二人转可以进行审丑狂欢的基础,是新型二人转对传统二人转的第二重“突围”。
三、情节贬值:碎片化的的艺术处理
“碎片化”是一个新兴词语,是对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前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化描述,是一个中性词,不存在褒贬色彩。新型二人转以形式松散、目的明确的碎片化表演来迎接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主要表现为新型二人转对传统二人转完整故事情节进行化整为零的艺术处理,而且以“混乱”的组织形式将其结构。碎片分散式的处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娱悦观众作为表演的最高标准与终极目标。
新型二人转将传统二人转完整的故事情节进行碎片化,其艺术处理手段是在冷场的地方或者是演员主观认为可能冷场的地方,迅速进入下一搞笑桥段,或以现场互动的形式使得审丑狂欢得以继续。在演出实践中,二人转演员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搞笑片段拼接在一起,丝毫没有违和感,最终完成了演出的碎片化和接受的碎片化。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曾这样描述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8]184-186巴赫金指出的第二种世界即新型二人转通过高潮迭起的演出所带来的狂欢世界。对这一世界的回归是新型二人转淡化艺术性和碎片化的艺术呈现共同作用的效果。而这一世界恰是现代人所需要的,人们走进二人转小剧场或者透过荧屏看二人转,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缓解紧张的生活节奏带来的身心双重压力。放松是观众对二人转唯一的期许。二人转演员不虚伪不造作,它目的单一,指向明确,将观众视为上帝,把自己无限放低,帮助观众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
余秋雨说:“中国人太喜欢那种民间性的片段性的说唱加表演的又是游艺性的小型戏剧了,因为只有这种形式中才能强烈地表现着民间搞笑的喜剧效果和狂欢化精神。而戏剧一旦到了专门化的戏剧家编写的成熟的完整复杂的故事,在以‘剧本’的形式表达另外的主题时,戏剧效果和狂欢化精神就几乎被剔除干净了。”[9]51-54东北人更是喜欢的不得了,东北人有属于自己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东北人喜欢激情的、热烈的、直接的、张扬的新型二人转。东北人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对二人转的热爱等同于对自己的认可和喜爱。新型二人转对其他剧种视为至宝的故事情节进行贬值,对传统二人转完整的故事情节进行碎片化的处理,才能使搞笑此起彼伏,娱乐持续进行,只有这样才更符合东北人爽利的性格特点——够味儿、够劲儿、够直接。新型二人转在它荒诞无稽而又难以理解的表演中,以一种极度的不得体的演出形式散播了一种极端欢乐的思想,它以娱乐作为终极目标淡化完整的故事情节可视为是对传统二人转的第三重“突围”。
四、主题丑化:从经典唱段到性爱展现
新型二人转的主题内容比较单一,几乎是剥去社会因素及文化因素,抛开人性与审美,对于性爱孤立且赤裸裸地进行展现。其中充斥着大量巴赫金称作“物质——下体因素”的东西。这些今天看来十分低级恶俗的粗言秽语、肢体接触成为新型二人转关键的搞笑元素。我们不应片面地将其视为低级下流的兽性发作,或是招揽生意的卑劣手段。传统二人转虽然唱段经典、主题高雅,演员虽然不唱不演污秽的内容,可是社会对传统二人转演员的认可度并不高。“优秀的二人转演员”也许就是社会对二人转演员的最高评价,最终传统二人转演员随同传统二人转一起被时代所淘汰。新型二人转虽被人指指点点,甚至恶语相加,但丝毫没有影响新型二人转的市场,反而市场前景越来越好。一些二人转演员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也时常参演电视剧,混迹于娱乐圈的正规军中,而且片酬相当可观。
以性爱为主题的演出内容能在当下如火如荼,只能说明它与当今时代节奏和审美需要合拍,它与快手、火山、抖音等娱乐App一起共同促成了当今的狂欢文化氛围,同时它也深深地植根于当今社会的狂欢文化中。它与当今火爆的真人秀节目无异,都追求一种极致表达。当然,深入现象的背后,以性爱为主题的新型二人转,之所以能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还在于它其实反映了人的本质存在,或者可以说它是植根于生命意识的艺术话语。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断言:“力比多”将具有道德和精神上不受压抑地自我升华的无限可能性,人在自然本能的驱使下,将摆脱理性的制约,发展到自我享乐的那个“理想王国”里去,这后者才是人的内在本性的高度文明,也是人类最高审美理想的实现。[10]
新型二人转通过小剧场的演出形式,对性爱主题完成了极致表达。虽然,性爱主题也常常被写进文学作品,亦或者搬上荧幕,但这两种方式使得“身体意象被象征化、隐喻化”[11]88文字和荧幕自身如同一块遮羞布,无形中拉开了性爱表达与观众的距离。小剧场的演出形式使得观众与演员、观众与表演之间零距离。新型二人转虽然颇受诟病与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型二人转审丑的形式满足了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艺术上的审丑可以揭示较之审美更为深刻的主题,用不和谐的方式‘引起逆受的心理快感’。”[12]58-60尤其是新型二人转通过对“丑”的极致表达更能引起观众强烈的心理快感。
对丑的极致化表达,带来的艺术功效是可以使观众刹那的忘我,酒神精神的复活。新型二人转在其大俗至丑的表演当中,完成了酒神精神的复归,充分地肯定了人的非理性,消除一切隔膜,彰显醉狂式的力。这种原始力量不受任何限制,毫无节制的放纵,以一种狂欢化的表演,瞬间达到台上台下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新型二人转通过台上台下充分互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巴赫金在狂欢化诗学所提到的“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在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的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中的某些规范和禁令的条件下,形成了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自由接触”[13]242。快节奏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紧张、压抑、焦虑、孤独等情绪困扰着现代社会的的每一个个体。大城市的生活更是如此,他们更需要二人转来缓解压力,所以新型二人转的市场已经不再局限于东北民间,已不仅仅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它已悄然无声地向大城市进军。看罢表演,虽然有人对它说三道四,虽然有人表示后悔,但谁也不可否认在演出过程中,二人转确实使得观众达到忘我的状态,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仅就这一点,新型二人转已完成了它至高无上的使命。新型二人转通过对丑的极致化表达对传统二人转产生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完成了对静穆理智的传统二人转的第四重“突围”。
综上所述,新型二人转脱掉传统二人转的“彩扮”,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最新的艺术定位——纯粹的东北民间艺术;通过丑角对旦角的疏离完成对丑角的强化,奠定审丑狂欢的基础;利用舞台动作、绝活展示对传统二人转的完整故事情节进行碎片化处理,使得审丑狂欢可以持续进行,以达到对娱乐的极致追求;通过对性爱主题的展现完成对传统二人转经典唱段的变形,配合以二人转小剧场的演出形式,完成对丑的极致表达。现代人需要审丑狂欢,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恰恰说明现代人缺少倾听者,所以自媒体应运而生。现代人虽然看着距离很近,但是关系很疏远;现代人看着娱乐活动很多,但是能忘我的娱乐机会很少;现代人看起来很自我中心,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成为群体中心的退而求其次……新型二人转通过审丑狂欢来打破一切现有秩序进而破坏和谐,寻找揭示潜意识深处的原始状态,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与疏离。极致表达可视为在一种成熟而稳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之下,一种被压抑和束缚的生命诉求,尤其是现代人的无力、无奈、甚至是无望需要用极致表达的形式进行宣泄。新型二人转将审丑狂欢与极致表达二者充分融合,也许恰可以通向美学的终极价值。诚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之怪石:“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14]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