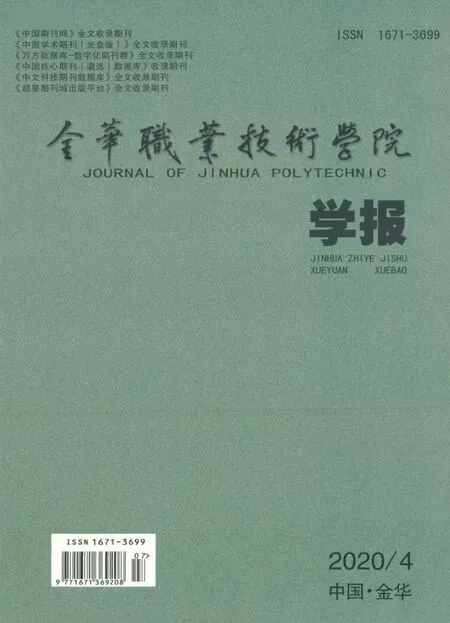师生交往的失真与重构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
许波乐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321004)
师生交往是教育领域中一种最基本的教育交往,是学校环境内最基本的人际交往,它直接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水平,甚至对师生发展的现在与未来有着潜在影响。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师生交往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失范现象,如师生间形色各异的交往冲突、关系疏远、目的功利化,甚至于师生暴力伤害现象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师生交往开始走向异化的交往状态,逐渐遮蔽原有的教学相长的教育旨趣。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关注个体生命间的不断理解、对话,以及“视阈”与“视阈”的不断融合。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没有理解,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目的,且人的生活从某一层面上而言可认为是理解的生活。哲学解释学中的“理解”是指解释者们带着自我的“前见”借助“对话”实现“视阈融合”的过程。交往中的解释者们凭借自身已经存在的知识经验,即“前见”,指出“视阈融合”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经由“视阈融合”对话双方获得了对事物,尤其是超越他们“前见”的更深层面的理解。因此从哲学解释学角度探讨师生交往,对师生交往的内在旨趣进行阐述,同时针对现实中师生交往的失真表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师生交往改进策略,这对推动师生交往走向良性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解释学下师生交往的内在旨趣
(一)意义理解式的主动交往
哲学解释学将理解看作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理解是意义的根本。对于师生交往而言,首先须建构对其意义的理解。在师生交往意义理解中,主动交往至少存在三层含义:其一,它是师生共同成长、主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教师主动通过交往活动,不断给予学生积极的态度,引导学生持续向前,这便是在帮助学生逐步形成个体的自知与自觉,以此体现人生价值。其二,它是师生理解人生意义,主动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过程。在意义理解式的交往过程中,师生之间交往应是主动、双向、平等的,它所体现的是主体间的和谐关系,这有利于建构和谐师生关系。其三,它是师生理解人生意义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师生主动体验人生的过程。对于师生来说,彼此之间的主动交往是彰显人生意义的最重要的活动方式,“体验不仅是指人经历了某件事,而且在这种经历中获得某种体悟、有了某种深切地感受;否则,便只是有了某种经历而非获得了体验。”[1]师生交往通过主动体验人生、克服交往中的种种疑惑,才能真正建构属于师生间的意义理解,使得师生情感体验彼此交融,并延续整个人生阶段。它有效克服了传统被动式的交往,将教师与学生灵魂中的“意义理解”彻底解放,它不单单是一方一厢情愿的态度,而化被动变为主动的积极态度。
(二)视阈融合式的互动交往
哲学解释学将视阈融合看作理解的本质。它将“前见”纳入其中,将现代与传统、过去与未来有机融合,为解释者创生出新的理解视阈。换言之,解释者在视阈融合过程中克服已有“前见”,悬置固有理念。“视阈融合”是指理解者的视阈与理解对象的视阈不断进行沟通,二者分别于新的高度扬弃隶属于自己的原有视阈,从而使自身视阈得以生成并延展,产生新的意义。教育领域中,师生之间的视阈融合意味着师生须将以往的认知、情感、经历等互相融合,形成一种师生互动的依存关系。教师通过学生的反映彰显自己,学生通过教师的关照而得以存在,反之亦然。这一互动交往过程体现了一种双向扩展、互相依存、相互包容的特征。双向扩展即师生的理解方向是从二者出发,而非一方压倒另一方,这便扩大了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互相依存则体现了师生是有机联合的主体,是相互联合的关系;相互包容则体现了双方情感交融的程度,越是相互包容,情感愈发深厚。师生交往的过程不是主体“前见”的自我表达,也非由师生一方向另一方的单向流程,它着重展现了师生自由表达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理解和视阈融合,最终促成互动交往的正式形成。师生在其中不断地丰富、拓展、改变自己的理解范式、思想、观点。
(三)对话交流式的平等交往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回到对话辩证法,实现了从独白主义向对话哲学的转变。”[2]理解以对话交流为前提,对话交流又体现着交互主体性。伽达默尔倾向于突出主体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他将阅读者与行文者、文章与理解的关系看成一种对话关系。理解是跟随问题延展而进行的对话,在一问一答的进程中解决问题,这时对话也就成为理解的路径。同时理解不是独立个体的行为,它在不同主体间进行,因而在视阈融合过程中,存在着可逆双向的主体交往功能。在教育领域中,学生是有思想、有意识的鲜活个体,传统的“主客二元”已不能够重新囊括,师生之间的交往应是一场平等对话的交往。师生在交往中相互体认、相互对话、相互感悟,这是一种超脱“主客二元对立”的平等交往,这三个“相互”意味着师生在交往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双方中的任意一方都不能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对方,双方在对话交流过程中应同时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以及视阈融合。从某种程度上讲,平等是构成师生良好交往的灵魂和核心。师生双方在平等交往中对话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在回应对方的观点,并最终达成共识。
二、现实师生交往的失真表征
(一)生命意识淡薄导致师生交往目的功利化
师生交往的本质可以看作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间的沟通交流,然在现实教育领域中师生交往主体意识淡薄、功利主义思想至上。哲学解释学将理解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解应帮助人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教育的目的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帮助人去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领悟人作为自我的存在。现实中师生交往的目的仅在于知识的记忆、存储、再现,不关注师生作为主体存在的意义实现[3]。功利化、工具化的教育活动使得师生双方间的活动,不论是正常的教学活动,还是师生简单的交流,都变成是对固有知识的复现过程。师生交往在这样的过程中异化成了以某种考试为目的的知识交往,使得原本教师、学生间的主体意识、个体情感、自我精神在交往过程中被层层遮蔽。基于功利化的师生交往目的,师生被物化为纯粹知识性的个体,师生交往的个体情感被简化成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甚至于自我情感精神在这过程中被驱逐,师生主体意识与人的存在意义相互割裂,转而被动去追逐功利。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许多家长会在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并嘱托老师多多照顾自家孩子。个别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从最初的犹豫到最后的屈服,背弃了教书育人的初衷和教师的职业道德,一部分学生被教师选择性忽视,最终导致师生交往恶化。
(二)工具主义主导致使师生交往地位对立化
现今,社会工具主义、技术理性甚嚣尘上,师生之间的情感体验被剥离,师生交往的主体地位缺失,交往价值发生偏离。一方面,教师的主体性地位被过度赋予,学生观发生背离。教师在教育大环境之中被赋予绝对的权威,师生交往中以教师作为唯一主导对象,学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使得师生交往失去了教学相长的交往价值。教师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却脱离学生。另一方面,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被极度压缩,支配于“考试理性”。学生群体相对于教师来说属于尚未成熟的个体,缺少充分的生活经验和人际交往体验,学生的主体性因学校“考试理性”在师生交往过程中被动屈服。“考试理性”是指“工具理性在教育中的具体化”,其主要特征就是把考试当作教育目的,一切教育手段都是为考试服务,讲求机械化训练的普遍性和追求效率的绝对性,将教育局限于认识论范畴,导致对师生存在的遗忘[4]。在工具主义主导的工具理性、考试理性的高压下,学生被当作是“工具人”,不能成为“个体人”。总之,工具主义驱动师生交往逐渐异化,沟通交流被闲置,师生在交往过程中相互背离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由双方建构的生活情感体验被遮蔽。
(三)教育对话空洞导致师生交往内容狭窄化
哲学解释学视阈中教育对话包括三种类型:第一,主体性对话,即“人与人的对话”,包括师生对话、生生对话。第二,理解性对话,即“人与文本的对话”,包括教师与文本的对话。第三,反思性对话,即师生的自我对话[5]。师生交往集中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主体间对话,从某种程度上可认为是上述三种对话的相互融合。
然而现实的教育对话却是由于三者的对话空洞导致师生交往内容狭窄化。首先,主体性对话缺失。传统教育使得教师居于师生对话的前端,且过于权威,教师的话语居于主导地位,学生的话语居于被控制的处境,在师生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导致对话内容严重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其次,理解性对话空疏。基于哲学解释学,师生应在各自“前理解”的基础上,使师生在研读文本中使课程与教学生发出全新意义。然而,现实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对课程教材唯首是瞻,无“前理解”参与,致使所讲授的课程教材文本处于表面化、整齐划一化,毫无个性化。最后,反思性对话粗浅。反思性对话本质上是个体与个体本身进行交流对话,现实教育领域一直强调教师须反思性教学、学生须反思性学习,然而受制于传统教学模式,只能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复演,无法超出。
三、理想师生交往的建构路径
(一)重新审视过往交往目的,彰显师生生命价值
理解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自我生命价值持续追问的过程,换句话说,人在理解中感悟生命,在理解中寻找未来。“教育的本质在于生命的成长,在于培育独特的精神自我和有活力的生命个体。”[6]因此师生交往目的应从功利性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促进学生主体精神的建构,从而提升学生的生命价值。在这样的转向过程中,师生交往应基于认知、情感、精神等方面来提升师生的生命意识。教师是审视转向的主要实践者,一方面,教师须关心学生生命价值,拉近师生双方之间的距离。学生渴望被老师关注,他需要的是能够触动其心灵的教化,而不是腐朽的教条,关心爱护学生,教师唯有放弃功利性的灌输和束缚,才能使学生主体精神自发外显,学生生命健康自我成长。另一方面,教师须倾听学生生活经历,以学生生命体验开展交往。师生间生命价值彰显的实现需要以学生的经历作为基础,唯有师生在这过程中真诚地相遇,师生之间才能够相互打开心扉,走入对方内心世界。“教育中追求的相遇即自我与自我的相遇,只有师生都真诚地展示自我,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教育领域,才能有助于真正的‘人’的诞生。教育者首先须真诚,尔后才可能高尚。”[7]师生交往唯有淡化功利化的交往目的,才回归教育本真,彰显师生生命价值。
(二)回归师生情感交往体验,变单向为双向理解
针对师生交往过程中,教师主体地位被放大,学生主体地位被压缩的弊端,与传统师生交往主客二元对立的单向理解思维方式不同,师生交往应倡导从单向控制转为双向理解,将工具主义、技术理性抛弃的情感体验重新纳入交往过程之中。哲学解释学的理解观认为教育过程是一种体验[8]。对师生的情感体验予以关切,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师生交往主体地位彰显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够对学生学习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也能够关照教师自身教学成长。师生交往只有回到情感交往体验,将单向理解转为双向理解,师生的主体地位才会得到应有的彰显。一方面,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须关注学生情感的独特性,仔细观察学生课堂中的细微表现,从学生情感体验出发,了解学生想法,之后才能凝练出教师的教育智慧,生发出师生交往的意义。一般而言,学生课堂中的表现正是他们内心思想、情感的外在显现。另一方面,教师须主动去了解、欣赏学生,在其完成学业之余淡化“考试理性”的诸多要求。学生是有生命的个体,不是工具人。教师要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真心实意去与学生交心,让学生知晓自己的想法,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将自己的情感托出,理解教师。师生双方不必为了所谓的“目的”而去单向虚伪交往,而是呈现双向理解,即角色互换,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三)构建多元师生对话方式,变规训为心灵对话
哲学解释学认为对话是理解的主要方式,在教育领域中理解的意义是在教师与学生主体间性对话关系中显现和生成的。传统师生对话充斥着规训的阴霾,教师身不由己,因为他本身也是从规训中成长的,学生更像是在进行着教师传承一般。在师生交往过程中,主体性对话、理解性对话以及反思性对话其本质都是为了促进意义的生成,只有将三种对话的规训性质转为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师生交往才会向纵深发展。因此,师生在构建多元对话方式上,首先,在主体性对话中,师生须积极地以文本为基础,不断地丰富固有课程教材的意义,使师生的“前理解”与文本的“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视阈融合,师生间的主体性对话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会有的放矢。其次,针对理解性对话,教师需消解自身的话语霸权,使对学生的话语规训转向倾听学生的心声。“师生对话是理解型师生关系形成的必然途径。”[9]教师要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成为理解性对话的主体。最后,师生需重新审视反思性对话,适时营造良好的沟通情境。师生交往中往往会出现各种矛盾,师生若在矛盾解决过程中创造有利情境,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不足,有助于师生之间心灵的对话,使得师生交往通过多元的对话方式,继续深化双方的“视阈融合”。
四、小结
总之,哲学解释学视阈下师生交往是个体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不断交往对话;是超越“前见”的视阈之间不断融合的过程。在教育领域中,师生之间的关系不论怎样改变,二者都不会脱离“理解”这一范畴,更不会失去“教学相长”和“育人”等一系列永恒追求。师生交往的存在及其理想化的追求都将以整个师生的生命价值作为其基本诉求,而回归师生生命价值是重筑师生交往的必然选择。因此,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其交往过程中都应重新审视过往交往目的,回归师生情感交往体验,构建多元师生对话方式,这将有助于彰显师生生命价值,变单向沟通为双向沟通,变规训为心灵对话,从而消融工具主义给师生交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终促进师生共同成长,实现完整人的意义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