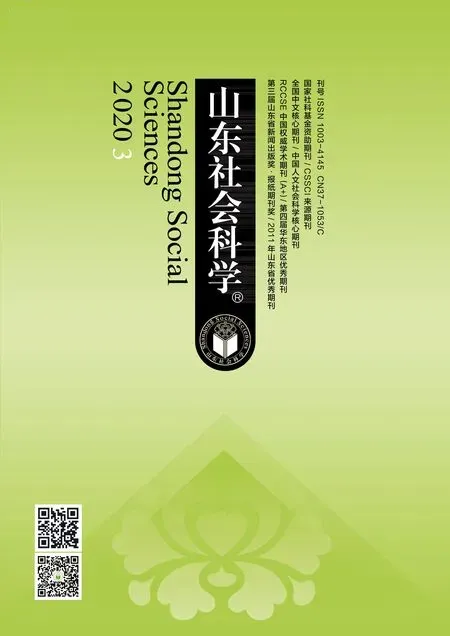从不平衡消费到平衡消费
——对“富裕失范”以及消费失衡的社会学分析
王 宁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涂尔干认为,在社会或个人的急剧转变过程中,容易发生某种连续性的中断。这种中断意味着过去对人们起着调节作用的道德原则或规范不起作用了,而新的调节规范尚未形成。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就出现了调节规范的真空。这种状态就是失范(1)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33;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依据默顿对涂尔干的解读,这种急剧变化导致两种失范:一种是源于经济萧条、不幸或“财富皱眉”的失范,它可以叫做“萧条失范”;另一种是源于财富的突然增加或“财富微笑”的失范,它可以叫做“繁荣失范”(2)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88.。后来,西蒙和加格农分别把这两种失范叫做“匮乏失范”(the anomie of scarcity)和“富裕失范”(the anomie of affluence)(3)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7.。
尽管涂尔干同时揭示了“萧条失范”和“繁荣失范”(或“匮乏失范”和“富裕失范”),但他所说的“繁荣失范”(或“富裕失范”)却被学术界忽略了。例如,默顿虽然注意到涂尔干同时提出了萧条失范和繁荣失范,但他自己在讨论失范时,主要是集中讨论萧条失范或匮乏失范,而忽略了繁荣失范或富裕失范。可以说,大部分学者在讨论失范时,主要都集中在萧条或匮乏失范上,或多或少忽略了繁荣或富裕失范。
就我国来说,当我们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因此,在那种情形下,学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匮乏失范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与富裕相联系的离轨现象以后,涂尔干所说的“富裕失范”就值得引起我们关注了。事实上,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口基数不小的富裕人群或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尽管带来了人们的福祉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但与富裕相联系的各种离轨现象却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醉生梦死、声色犬马、吸毒嫖娼、炫耀斗富、奢靡浪费、穷奢极欲、为富不仁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富裕失范”的表现。
可以说,发展的一个目标是迈向经济繁荣和富裕,但发展过程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社会转型或社会的急剧变化。这种转型可能同时带来两个结果:其一是不少人的财富和收入的迅速增加,其二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失范。这二者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一部分人在财富和收入增加以后,陷入了“富裕失范”状态。它构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社会问题。这说明,对“富裕失范”进行研究,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富裕失范”及其所引起的消费失衡现象进行研究。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涂尔干、默顿、西蒙和加格农关于“富裕失范”的观点;第二部分讨论涂尔干针对“富裕失范”所提出的约束性平衡机制;第三部分区分富裕失范中的两种消费失衡,并揭示涂尔干的“约束性平衡机制”在解决第二种失衡上的不足;第四部分针对富裕失范所导致的第二种失衡,提出了解决这种失衡的“超越性平衡机制”。
一、对“富裕失范”的经典社会学论述
涂尔干把失范看作是社会转型或社会急剧变化的一个后果。社会转型导致原有的规范的调节性作用被削弱,但同时新的调节性规范还来不及形成。在这种失范状态下,离轨现象就可能增多。他把与失范相联系的自杀现象,称为“失范性自杀”(4)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1-239.。在他看来,社会急剧变化不但包括令人痛苦的危机,也包括对人有利的突然转型。在这个历史连续性突然打断的阶段,原有的道德调节力量就会削弱。相应地,在这个阶段,自杀率曲线会明显增加。一方面,以经济灾难为例。一些阶层突然掉入到更低的阶层位置上,他们原有的优势荡然无存。但是,社会却无法同时教会他们按照新的行为模式来生存,他们无法适应自己所陷入的境地。另一方面,社会急剧变化导致的另外一种“危机”是权力和财富的突然增加。由于生活状态已经改变,原有的用来调节自己需要的规则和标准已经不再适用。旧的调节性尺度已经失效,而新的调节性尺度却无法立刻形成。在社会转型导致的阶层地位重新洗牌过程中,社会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形成新的公共意识,从而重新为人们进行阶层分类,并把不同的阶层与不同的生活标准联系起来,使之具有相应的调节规范。只要新的调节规范还没有达成,社会就会处于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形下,面对财富突然增加的人们,就不知道可能和不可能之间、正义和不正义之间、合法的索要与希望和过度的索要与希望之间的界限。于是,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的渴望的约束(5)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
这种伴随着财富增加,但同时却失去了对自身的欲望和渴望的规范性调节和自我约束的现象,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富裕失范。他指出,一些在转型中得到了命运眷顾的阶级,不再受制于过去的命运安排。而他们突然增多的财富导致其他阶层的妒忌。人们的不受公共舆论所控制的欲望,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且不再接受各种道德限制。于是,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欲望也膨胀了(6)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
但是,在涂尔干看来,一旦欲望不受约束,他们的满足就变得不可能,因为人的欲望的增长速度常常会超过其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由于没有道德力量遏制欲望的无限膨胀,人们永远处于不满足中,因为一旦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马上形成更高的欲望。人们陷入了一场追逐不断升高的欲望和目标的竞赛中。一旦欲望的满足过程被中断,他们就处于一无所获的心境中。于是,欲望就会以更为报复性的方式增长。同时,也正是由于欲望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人们之间围绕欲望满足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所有的阶级都陷入欲望满足的竞争中,过去的阶层划分已经不再适用。人们通过消费竞争而重新洗牌。然而,人们在竞争中付出越来越多,回报却越来越少,因为阶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7)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
涂尔干指出,与富裕相反,贫困不会导致人们在欲望满足上的竞争。相反,贫穷本身会让人对自身的欲望形成自我约束;贫穷是教会人们自我约束的最好的学校。贫困强加给我们一种自我纪律,它让我们以平静的心态接受集体规制。与之相比,富裕因其所具有的赋权功能,会让我们形成一种能力强大的虚假信念。于是,我们减少了对物欲的抵制,仿佛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获得所欲的所有物品。一个人越是感觉到不受限制,就越会觉得限制是不可忍受的(8)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由于财富提升了个人的力量,它会激起财富拥有者的叛逆精神,而它正是不道德的根源。当然,涂尔干认为,这不是人类不需要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的理由。但他提醒人们,财富增长可能会引起道德风险的后果(9)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
在涂尔干看来,富裕失范具有连锁效应,并扩散到全社会。他指出,在转型期间,危机和失范变成了常态。从顶层到底层的社会各阶层的贪欲都被激起了。人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终的立足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贪欲平息下来,因为它的目标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达到的境地。与狂热的想象而形成的梦想相比,现实显得没有价值(10)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但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新奇、未曾体验过的快乐、不知名的感官刺激(sensations)的渴望,一旦被体验过了,立刻就变得没有味道了。尽管如此,从此以后,人们却不能忍受体验的逆转。显然,所有这些新的感官刺激在量上的无限增长并不构成生活幸福的坚实基础。那些把希望永远固着于未来,并死死盯着这些希望的人,无法从过去中找到应对当下痛苦所需要的安慰。过去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急匆匆体验过的一个阶段而已。让他们迷失了方向的恰恰是对幸福的期待,而这些期待的幸福其实已经在过去获得了,但被他错过了。万一他在人生轨道上停滞了,他就既没有过去所留下的东西,也没有可以寄托希望的未来。厌倦本身就足以带来幻灭,因为他终究无法避免他们的无休止的追求的徒劳无用(11)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3、214、214、214、215、216、217.。
可以看出,涂尔干把富裕失范看作是社会转型期因为缺乏有效起调节作用的社会规范而存在于那些富裕突然增加的人群中的一种现象。在他们那里,财富的突然增加导致他们的欲望无节制地膨胀和升级,因为他们摆脱了约束自身欲望的调节性规范。而他们对满足这些欲望的无休止追求往往只带来片刻的满足感。一旦停止对欲望满足的无休止追求,立刻就会陷入幻灭状态。
涂尔干的“富裕失范”观点也引起了默顿的注意。在讨论到“退却主义”时,默顿注意到涂尔干所说的失范不但与萧条相联系,而且也与富裕相联系。默顿并因此把失范区分为与“财富微笑”相联系的“繁荣失范”和与“财富皱眉”相联系的“萧条失范”(12)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88.。但是,在默顿关于失范的论述中,主要集中于讨论萧条失范或匮乏失范。所谓匮乏失范,在默顿那里,指的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脱节情形。这种脱节导致人们无所适从,即失范。人们面对失范,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他区分了五种适应模式:“遵从”“发明”“仪式主义”“退却”和“反叛”。“遵从”指的是行动者循规蹈矩的模式。行动者既接受社会所赞同的目标,也采取制度化手段(13)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除了“遵从”,其他四种类型都属于离轨式应对模式。“发明”指的是当社会行动者面临社会所赞同的目标(具有文化合法性的目标)与可得的制度化手段脱节的时候,行动者不择手段以实现该目标的情形(14)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仪式主义”指的是行动放弃或降低社会所赞同的目标,只是在制度化手段之内按部就班地行动(15)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退却”指行动者不但放弃社会所赞同的目标,而且也放弃制度化手段(16)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反叛”则是指反对或抵制现存秩序的行为(17)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表1)。

表1 个人调适模式的类型(18)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
西蒙和加格农推进涂尔干关于富裕失范研究的。他们提出了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双重失范:匮乏失范(the anomie of scarcity)和富裕失范(the anomie of affluence)(19)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7、356-378、356-378、356-378、356-378.。他们认为,“二战”之前的美国所面临的失范主要是匮乏失范。但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进入富裕社会阶段,美国社会同时面临双重失范:较低的阶层面临匮乏失范,而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则面临富裕失范(20)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7、356-378、356-378、356-378、356-378.。
在西蒙和加格农看来,默顿所说的离轨式应对模式,均是成就导向下的应对。默顿所说的文化性目标(社会所赞成的目标)成为人的能力、美德和运气的证明,尽管有人采取遵从模式,有人采取离轨模式。但是,他们认为,在富裕阶段,原先那种成就取向的目标变得容易实现了。相应地,与制度化手段不足相联系的失范(匮乏失范),逐渐转化为与目标相联系的失范(富裕失范)。在这里,失范不再源于手段不足,而是源于目标失去了意义。这就是说,目标即使实现了,也不能获得像匮乏时代中目标实现以后所能具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匮乏时代那种因成功而带来的感官快乐所具有的意义,在富裕时代改变了(21)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7、356-378、356-378、356-378、356-378.。
依据涂尔干所说的,感官刺激或感官快乐在量上的无限扩张并不能构成幸福的坚实基础(22)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17,西蒙和加格农揭示了“富裕失范”的含义。在他们看来,富足而空虚,就是富裕失范的体现。随着富裕的普遍化和“成功”的人数越来越多,财产占有的意义下降。旧式的对成功人士的崇拜和妒忌,因为占有物(如汽车)获取的普遍化而变得弱化了。随着成功的普遍化、富裕的常态化以及物所代表的快乐的廉价化,过去那种崇尚成功(财产占有)、炫耀性消费以及追求物的占有(它代表快乐)的价值,逐渐让位给追求人的存在的价值。在匮乏时代,物不容易得到,物的占有以及对物的使用所带来的快乐,被赋予重要的价值。但是,一旦物品很容易得到,人们赋予它的价值和意义就会相对下降。这意味着过去被崇尚的目标,现在对人们的吸引力下降了。如果说,在匮乏时代,人们崇尚物质性成就(成功),那么,在富裕时代,人们崇尚一种新的价值,即个人体验(23)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7、356-378、356-378、356-378、356-378.。如果说,在匮乏时代,手段不足成为主要问题(24)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41、141-149、149-153、153-155、155-157、140、 .,那么,在富裕时代,则是目标成为人们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目标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往往是因为目标的实现未必能带给人们以满意感。可见,主流社会所认可的目标的问题化,就是一种富裕失范(25)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7、356-378、356-378、356-378、356-378.。
人们是如何应对目标所带来的问题的呢?在西蒙和加格农看来,一共有九种不同的应对模式。相应地,存在九种不同的人(表2)。第一种是“最优的遵从者”(Optimal conformists)。他们投身于社会所崇尚的目标,并从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体验到满意感。他们在目标上的投入,是自发的,没有借助自我反思。第二种是“超脱的遵从者”(detached conformists)。他们认为社会所认可的成就性目标是满意感的来源,但他们不愿意投入激情或热情。他们只是简单地接受这种目标。第三种是“冲动性成就者”(Compulsive achievers)。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社会所赞同的目标上,但缺乏从中获得对应的满意感的能力。第四种是“遵从的离轨者”(.Conforming deviants)。他们投身于社会所赞同的目标,但是同时也会在快乐的维度上进行探索,以探寻创造性的满意感来源。在探寻超凡体验过程中,他们或许接近了离轨的边缘。第五种是“超脱者”(detached persons)。他们是一种不带情感地既拒绝社会所赞同的目标(成就性价值),又拒绝由此带来的满意感。他们类似于默顿所说的“退却者”。不过这种人无需采取离轨方式。第六种是“逃避者”(escapists)。他们接受社会所赞同的目标(成就性价值),但发明了新的获取满意感来源的方式。但这种获取满意感来源的方式,有可能是离轨的。他们也类似于默顿所说的“退却者”。不过,他们所要逃避是富裕带来的空虚状态,与匮乏失范者的退却不同。第七种是“传统的改良者”(the conventional reformer)。他们发明新的目标以替代主流社会所赞成的目标(成就性价值),并因此获得满意感。第八种是“传教士”(missionary)。在寻求激进的变化上,他们与前一类人很近似。但他们自己可能只是成为历史使命的工具,导致去个人化的经历,常常要牺牲个人自己的生活,从而未必能获得满意感。第九种是“全方位的反叛者”(the total rebel)。他们既要替换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目标,也要替换与成功相联系的生活质量标准,并相应地从创新性的生活模式中获得满意感(26)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6-378、370.。

表2 调适性应对的类型(27)Simon, W.and Gagnon, J.H., “The Anomie of Affluence: A Post-Mertonian Con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1976), No.2., pp.356-378、370.
二、克服富裕失范:涂尔干论约束性平衡机制
尽管西蒙和加格农推进了涂尔干所提出的富裕失范的研究,但是,他们没有揭示富裕失范的本质所在。要回答富裕失范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涂尔干。在涂尔干看来,富裕失范与匮乏失范一样,其本质在于物质欲望增长速度与物质资源增长速度的平衡被打破。要分析人何以会产生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失衡,可以对照动物的平衡形成机制来加以分析。涂尔干指出,在动物那里,至少在正常条件下,平衡是通过自动的本能而建立的。有机体要定期更新它所需要的等量的物质和能量。动物一旦感觉身体亏空,必须立即弥补亏空。这些亏空一旦填补,它们就不再有进一步要求。它的反思能力还没有进化到可以形成对不同于生理满足目的的其他目的的想象(28)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7、207-208.。
但人不是这样。涂尔干指出,人的大部分需要不是由身体所决定,或者说,人的需要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的程度,没有动物的那么高。严格来说,人的生理生存需要多少物质(能量和营养)可以精确计算。但是,在生存所需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就会提出更高的需要标准或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具有反身性。那么,人能否无限制地提升需要标准或目标呢?在涂尔干那里,答案是否定的。人的欲望或迟或早会达到一个不可超越的限制点。但是,如何来决定人们所追求的合法的福祉、舒适和奢侈所需要的量呢?涂尔干认为,人的有机体不会施加这种限制,人们的心理构成也不会施加这种限制(29)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7、207-208.。
涂尔干认为,这种限制来源于社会。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对不同等级的阶层施加相同的限制。然而,人性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但人性无法对我们的需要添加限制。如果没有外在的调节力量,我们的欲望膨胀过程就会永不休止。不但如此,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来约束人的欲望的膨胀,不断膨胀的欲望就只能变成自身痛苦的来源。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欲望注定是无法满足的,而欲望无法满足则可以看成是一种病态的信号。欲望之火不会熄灭。而永不熄灭的欲望则是一种持续更新的折磨,因为它为自己确立了不可达到的目标。人没有目标不行,但目标(或欲望)无限制也不行(30)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因为去追求一种注定达不到的目标注定就是让人陷入到一种永久的不幸福的状态中。但是,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多,就越是渴望拥有更多,但这种欲望是无法满足的(31)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
在涂尔干看来,要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人的欲望进行限制,从而达成物质欲望的增长速度和满足这种欲望的物质资源的增长速度的平衡,或更简单地说,达成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平衡。但个人无法限制自己的欲望。要达成对物质欲望的限制,必须借助个人之外的力量。这种调节人的欲望的外部力量,只能是道德力量。人的欲望膨胀打破了动物的自发的平衡状态。只有通过良知,才能提供再平衡所需要的手段。生理上的克制是无效的。生理化学力量无法触动心灵。只要贪欲不是由生理机制自发抑制的,它就只能由人们认为是正义的限制力量所终止。人们不会自发地形成正义的法规。因此,他们必须从所尊敬的权威那里接受,并自发地服从这种正义的法规。社会或者以直接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代理,对个人发挥着这种调节性角色。它是唯一的在个人之上的道德权力,是个人所接受的权威(32)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
涂尔干认为,道德调节力量为某种生活方式同时设定了上限标准和下限标准。上限标准是人们渴望通过努力而改善生活的目标,而下限则是人们力图避免陷入其中的标准(33)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由于道德力量设定了上限标准,这就避免了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于是,通过道德力量的调节,人们确保了“幸福的平衡”(the equilibrium of happiness)(34)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在这种平衡状态中,人们不是由强加于自身的物质环境所支配,而是由位于个体之上的,但个体又感知到的集体良知所支配。由于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身体,人们就摆脱了身体的羁绊,而服从于社会的约束(35)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在这里,人的“幸福的平衡”是借助社会的约束性道德规范所达成的。这种达成平衡的约束性力量,可以称为“约束型平衡机制”。
可见,涂尔干非常强调位于个人之上的社会道德力量对个体欲望的约束作用。正是这种外在于个体的道德力量,帮助个人恢复了物质欲望增长速度与物质资源增长速度的平衡。人们借助道德规范设定了生活方式的上限,从而不至于让欲望进入无休无止的膨胀轨道,并因此导致欲望与资源、欲望与满足的失衡。很显然,道德规范是让个人实现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或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平衡的社会条件。如果没有这种道德性调节力量,人们就会陷入失范状态。社会转型阶段那些财富突然增多的一些人,有可能会由于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的弱化,而陷入富裕失范。
涂尔干对富裕失范的分析是非常精准的。他正确地看到了富裕失范的实质在于,由于缺乏道德规范的有效调节,财富突然增加的一些人出现了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的失衡。事实上,这种失衡与默顿所说的匮乏失范中的失衡有相似之处。正是由于合法化的物质欲望(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的脱节,才导致各种离轨反应(36)Merton, R.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131-160.。因此,不论是匮乏失范,还是富裕失范,均是欲望(目标)与满足欲望的手段(或资源)的失衡的体现。差异在于,在匮乏失范这里,失衡的体现在于手段不足。在富裕失范这里,失衡的体现在于目标失控或欲望不受节制的膨胀。
在涂尔干看来,克服富裕失范中的物质欲望(目标)与满足欲望的物质手段之间的失衡的办法,在于通过位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所施加的道德力量的调节。借助这种道德调节力量,人们对自己的欲望进行适度的约束和抑制,以避免欲望的无休无止的膨胀和升级。一旦欲望被适度地控制住了,人们就实现了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之间的平衡。很显然,这种“约束性平衡机制”有助于解决富裕失范的问题。
三、富裕失范中的两种消费失衡
但是,仅仅凭借约束性平衡并不能整体性地解决富裕失范问题。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人们的失衡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之间的失衡,而且还体现在物质生活欲望与精神生活欲望之间的失衡。换言之,人们面临双重失衡:一方面是物质欲望的增长速度与满足这种欲望的物质资源的增长速度的失衡(或简要地说,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失衡),另一方面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事实上,我们不能说涂尔干完全没有注意到第二种失衡(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37)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p.208、209、209、210、211、213、208.,但至少关于第二种失衡,他没有展开讨论。因此,总体而论,涂尔干所建议的措施是通过道德规范来约束物质欲望或感官欲望的无休止的膨胀,以实现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平衡(针对第一种失衡)。但关于第二种不平衡,他着墨甚少。然而,要解决不平衡消费问题,不但要解决第一种不平衡,而且也要克服第二种不平衡。事实上,第二种失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的解决有助于克服第一种失衡(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失衡)。所以,消费平衡的实现应该同时在两个方面进行。但是,涂尔干所说的约束性平衡只适用于解决第一种失衡(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失衡),不适用于解决第二种失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
既然涂尔干的约束性平衡机制只能解决第一种不平衡,不适用于解决第二种不平衡,那么,要解决第二种不平衡,需要借助什么机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人的需要或欲望。在涂尔干那里,物质生活需要往往呈现为物质欲望,即对感官刺激或感官快乐的追求。但是,这种基于有机体的感官而形成的物质需要或欲望,只不过是一种低层次需要。人的需要还有更高的层次。如果一个人沉浸在这种低层次需要而不能自拔,那么,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就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心理学界已经提出了非常成熟的答案。马斯洛的理论则是其中最经典的需要理论之一。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有高低不同的层级的,位于底层的是人的基本生理性需要,在此基础上依次上升的需要层级是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更高层级的需要的满足,必须建立在更低层级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低层级的需要具有满足的优先性,相应地,需要的满足采取了依次逐级上升的模式(38)Maslow, A.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vol.50(1943), no.4, pp.370-96;Maslow, A.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但是,马斯洛在1970年再版的《动机与人格》(原版1954年)中对早先提出的需要理论做了修正,在原有的五种层级的需要上,增加了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其层级位于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之间(39)Maslow, A.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此外,他在1964年出版的《宗教、价值和高峰体验》中又增加了“自我超越”的需要,其层级位于自我实现之上(40)Maslow, A.H., Religions, values, and peak experiences.In the Kappa Delta Pi lecture series.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尽管许多学者批评他的需要理论(如:遗漏了许多需要、需要的满足并不采取线性模式、存在方法论问题,等等),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还是被认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写进了多种心理学、管理学的教科书。
按照麦克里奥德的解读,马斯洛的五种层级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需要:匮乏性需要(deficiency needs, i.e.,D-needs)和增长性或存在性需要(growth or being needs, i.e.,B-needs)。马斯洛的前四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属于匮乏性需要,而第五种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后来追加的自我超越的需要,均属于增长性需要。匮乏性需要如果未满足,就会驱使人们去追求其满足。这种需要的满足被拒绝得越久,人们追求其满足的动机就越强。例如,人们饿得越久,寻找食物的动机就越强。一旦人们的匮乏性需要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习惯性地追求更高层级的需要的满足(41)Maslow, A.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与匮乏性需要不同,增长性需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不是源于缺乏某种东西,而是源于人们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欲望。如果说,匮乏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会让人转移到其他类型的需要的满足上去,那么,增长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其需要依然会被持续地感知到,满足其需要的动机会越来越强(42)McLeod, 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Simple Psychology”,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maslow.html(updated 2018)。
马斯洛早期关于需要理论的表述,让读者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人们只有先百分之百地满足低层次的需要,然后才能接着去满足更高一层级的需要。马斯洛在1970年版的《动机与人格》中澄清了这种误解。他认为,人们无需让低层级的需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而是只要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究竟是多大百分比的满足,则是一个有待经验研究确认的问题),就可以接着去追求更高层级的需要的满足(43)Maslow, A.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这一澄清十分重要,因为它隐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既然人们无需在低层级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就去追求更高层级的需要的满足,那么,人们也有可能借助更高的精神性需要的满足来弥补物质需要满足上的不足。
但是,马斯洛的另外一个潜台词是,在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如果低层级的需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人们就会去追求更高层级的需要的满足,并进而追求自我超越。但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反例:一些人已经衣食无忧,过着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但却安于现状,陷入无休无止的追求感官刺激的陷阱。依据他的需要理论,既然人们无须等待低层级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以后就追求较高层级需要的满足,那么,如果低层级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以后,人们更应该会去追求较高层级需要的满足。然而,人们或许会问,这种升级是否必然发生呢?如果人们在匮乏性需要的各个层级上会逐级而上追求越来越高层级需要的满足,那么,到了增长性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层级,人们能够上升到多高的层次?理论上,不同于匮乏性需要(其满足遵循了边际效用递减律),增长性需要的满足效用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律,它的满足可以是无限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问,在人的各种匮乏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能进一步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吗?如果能,会在多大程度上追求这种满足?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人之间显示出差异。有的人可以在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的满足上形成无止境的追求,有的人则可能浅尝辄止,甚至退回到匮乏性需要得到满足的安逸状态,甚至退回到无休无止地只追求感官刺激的失衡状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人们要从匮乏性需要的满足进入到增长性需要的满足,尤其是自我超越需要的满足,需要借助超越性平衡机制。如果缺乏这种超越性平衡机制,人们可能停留在满足匮乏性需要的层级而无法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
事实上,即使是在匮乏性需要的各个层级中,物质占有和消费的功能不仅仅在满足生存需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经济保障),同时物质占有和消费也或多或少地可以满足更高层级的需要,包括爱与归属和尊重。例如,赠与恋人金项链是爱的表达,促进了与恋人的爱情关系。拥有必要的物质产品,还会促进阶层归属感,并因此获得社会的尊重。可见,物质占有和消费是匮乏性需要的典型体现。为了讨论的简便,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当讨论到匮乏性需要时,我主要是指物质的占有和消费的需要。
涂尔干所说的“富裕失范”不但是一种物质欲望和物质资源的失衡,而且也是一种物质生活(物质占有和消费的欲望)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失衡。要从这种失衡实现再平衡,不但必须从对物质占有和消费的过度追求中摆脱出来,而且还必须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层级,从而避免让人们只把精力集中在追求物质的占有和消费的需要的满足上。然而,在缺乏超越性平衡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停留于物质的占有和消费的需要的满足活动上。它导致人们在物质生活(物质占有和消费)和精神生活(精神追求和精神文化消费)上的失衡。
这种失衡的一个后果就是物质主义的盛行。贝尔克指出,所谓物质主义,指的是消费者赋予世俗占有物以重要性的一种心态。在最高层次的物质主义中,这种物质占有在个人生活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并被人为地建构成满意感或不满意的最大的来源。他认为,物质主义有三个维度:占有性(追求对占有物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不慷慨(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占有物)、妒忌(对别人的占有物状况超过自己的占有物状况的反应)(44)Belk, R.W., "Materialism: Trait Aspects of 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2(1985), pp.267-268.。
四、超越性平衡机制
可以说,物质主义是涂尔干所说的“富裕失范”的一种结果。由于没有更高的道德规范的调节和更高的精神追求,人们赋予物质的占有和消费以核心的重要性(即物质主义),并相对贬低了精神文化追求的重要性,从而陷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状态。同时,物对于人的意义,必须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这势必导致人们在物质的占有和消费上展开竞争或竞赛。物质占有和消费上的竞赛和攀比进一步强化了物质占有和消费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物质主义。要克服物质主义,恢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必须寻找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超越性平衡机制。换言之,所谓超越性平衡机制,就是借助超越行动来克服物质生活(物质占有和消费)和精神生活的失衡的机制。但是,超越行动有多种类型,只有特定类型的超越才可以成为克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失衡的机制。
超越行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应对现实的办法,即借助某种方式来摆脱现实或现状的羁绊。人们之所以要超越,是因为人们不满于现状。换言之,现状让人感觉不满,人们就会试图做出改变。但是,并非所有的改变都可以叫做超越行动。自发或本能的改变不是超越,而是一种反应性行动。只有那种通过反身意识或反思精神而达成的改变,才成为超越行动。反身意识或反思精神是超越行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特征。超越行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对更好的生活的想象力。没有一个理想目标,人们就无从超越。超越行动的第三个特征是具有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的意志力。仅有改变的想法和目标,没有采取行动的意志力,依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行动。
因此,超越行动是一种经过反身意识或反思精神而达成的对现实进行改变和提升的行动。由于现实世界往往存在令人不满的方面,因此,人们常常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超越现实。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采取超越的态度来应对现实。对于那些安于现状的人来说,超越现实没有必要。但对于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来说,现实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加以超越。可见,“现实维护”(安于现状)与“现实超越”(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是人类社会中两个对立的倾向(45)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现实维护”的倾向注重现存秩序的保留。而“现实超越”的倾向则注重改变现实。“现实超越”的倾向意味着人们具有了反身意识,能对现实进行反思,并试图依据反思的结果来改变现实。
但是,尽管超越行动是要去改变,不同的超越行动所要改变的内容却不同。依据所要改变的内容或对象,我们可以把超越行动区分为两种:客观超越和主观超越。客观超越要求改变客观现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同时也要超越自己(如:从无知或迷信转变为理性思考)。与之不同,主观超越不要求改变客观现实,而只要求改变人的主观现实或状态。尽管主观超越没有改变客观现实,但它让人们获得了应对客观现实的某种方式。
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看,超越行动可以分为四类:宗教型超越、启蒙型超越、升华型超越和利他型超越。
1.宗教型超越。面对人间苦难的现实,人们的一个应对方式是采取宗教型超越。宗教在对待客观现实上,采取了宿命论的态度。它认为现实的困难是命中注定、不可逃脱、不可改变的,人类的唯一希望在于死后进入来世的理想世界(如基督教所说的“天堂”)。但是,这个来世理想世界不是谁都可以进入的,而是必须在生前采取各种修行,避免各种恶行,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用基督教的话说,就是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宗教型超越是人类应对现实(苦难)的一种方式。它没有消除苦难,而是通过幻想出一个让自己在死后可以脱离苦海的希望世界,以让当下的苦难变得可以忍受。在这种超越方式中,人们不去改变现实,而是借助人们所构想的来世世界,使他们从现实的苦难中获得活下去的希望,让充满苦难的现实生活变得有盼头和有意义。这种宗教意识让宗教徒改变了自身的主体性状态,并因此达成与苦难现实的和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宗教型超越是一种主观超越,它没有改变客观现实,而是通过改变人的主观现实或主体性状态(对来世的憧憬),来使人适应客观现实,忍受客观现实中的苦难。
2.启蒙型超越。从历史上看,它主要是人们在启蒙时代所实行的一种超越行动,即借助理性反思和批判精神所进行的超越行动。韦伯所说的西方现代化中的理性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世纪时代的宗教型超越的一种反弹。宗教实践尽管是一种超越,但其代价是让人套上了禁欲主义的桎梏。从启蒙时代开始,人们便借助反身性意识或理性反思精神,对中世纪的各种过度压抑人性的现实进行批判。这一批判启动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它不但导致宗教衰落,而且也导致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相应地,实证主义取代神学思辨和形而上学,构成科学实践的内核。借助科学理性和理性批判精神,人们不但改变了主体性状态(怀疑、批判、审问和实证精神、),而且改变了客观现实——现实变得越来越可控了。相应地,物质替代神灵,财产替代天堂,物欲的满足替代祈祷和忏悔,成为现实生活的主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插上理性的翅膀”以后,改造客观现实的能力越来越强了。理性精神带来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而现代科学技术则导致人们改造客观现实的能力的提升。同时,在理性的拷问之下,借助人们的想象和信仰来支撑的来世世界和神灵世界的空间日益萎缩;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社会变得世俗化了。可以说,正是由于启蒙型超越,现代性才得以产生。启蒙型超越是一种客观超越。它通过改变主体性状况(摈弃神学思维和迷信,坚持理性思维),来达到改变客观现实的目的,从而让客观现实被不断改进或超越。但是,启蒙型超越在摆脱了宗教型超越所带来的过度注重心灵生活,轻视物质生活的同时,却走向了矫枉过正。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过度重视物质生活,轻视精神生活的后果。而物质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让许多人陷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状态中。
3.升华型超越。升华型超越同样是人们用来应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但是,升华型超越不同于宗教型超越和启蒙型超越。一方面,不同于宗教型超越,升华型超越不是去构建一个来世世界来帮助人们应对现实中的苦难,而是去建设一个可感触的美好世界以弥补客观现实的缺憾和不足。另一方面,不同于启蒙型超越,升华型超越并不去改变客观现实,而是在客观现实中追加一个“美好世界”(即现实世界中的美好“飞地”)。这个美好世界既不是宗教型超越中的“来世世界”,也不是启蒙型超越中的被改进的整体客观现实,而是被附加到现实世界,但同时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充当弥补现实世界的缺憾和不足的一个可感触的理想世界。在升华型超越中,美好世界不在彼岸,而是在此岸。它包括高雅的文学、艺术(美术、雕塑、音乐等)、游戏、娱乐、旅游等活动。通过在美好世界中体验美感愉悦和精神享受,人们暂时地获得对现实世界中各种不适和痛苦的超越(47)Wang, Ning, “Logos-modernity, Eros-modernity, and Leisure”.Leisure Studies,vol.15(1996), no.2, pp.121-135.。在升华型超越中,人们要凭借感觉体验来获得美感愉悦。但它不同于满足物欲的感官体验。满足物欲的感官体验是一种生理性快乐,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没有采取精神升华的方式。与之不同,升华型超越尽管需要凭借感觉器官来体验美感愉悦,但感官体验直通心灵,并因此实现了精神升华。升华型超越同时让人们获得了感官快乐和精神愉悦。而感官快乐成为通往精神愉悦的通道。
升华型超越的概念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让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求快乐,遵循“快乐原则”。但是,正是由于本能所驱动的人们追求快乐的行为具有“不顾一切”的特征,它可能会伤害他人的利益,因此,这种行为常常会遭到社会的惩罚。为了避免这种惩罚,人们在现实中对本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以牺牲一部分本能快乐以换取社会环境的接受和认可的做法,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由于“现实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遵循“快乐原则”的行为便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被分离出来的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所允许奉行的“快乐原则”并不会对现实构成威胁,因此不会受到现实的惩罚(48)Freud, S.(1963)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rans.by J.Riviere, revised and newly edited by J.Strachey.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但是,假如它要突破边界、扩展到更大的现实世界中,便不被社会所允许。于是,文明社会所形成的对本能的征服和控制既保证了社会的秩序,让人们获得了安全,但它同时也常常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这种秩序和安全是以牺牲一部分快乐为代价的。而且,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人们可能常常过度奉行“现实原则”,并对“快乐原则”形成过度抑制(49)Marcuse, H., Eros and Civilisation.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5.。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可以借助升华的方式,来克服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对立和冲突(50)Freud, S.(1963)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rans.by J.Riviere, revised and newly edited by J.Strachey.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在升华中,感性原则(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理性原则)实现了统一。升华遵循了快乐原则,但它并没有采取与现实相冲突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现实保持一致的方式。升华也遵循了现实原则,但它并没有放弃快乐,只不过,人们所追求的快乐不再是纯粹本能的快乐,而是精神的快乐。这种精神快乐需要借助感觉器官,并引起感官快乐,但它却不仅仅是感官快乐,而是上升到精神快乐的层次。
如果说,物质主义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追求“快乐原则”的心态,那么,升华型超越则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升华型超越是一种主观超越。它没有改变客观现实,只不过是在客观现实之中添加了一个美好世界。人们通过对美好世界的感性体验,来补偿客观现实的缺憾,并让人们在获得了物质生活的安逸之后,还能进入到可感触到的精神世界,实现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升级。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升级有助于扭转物质生活和精神社会的失衡。
4.利他型超越。这种超越行动与宗教型超越具有血缘的联系,因为在历史上,宗教是一个主要的慈善救济的供给者。但当代的公益慈善等利他型超越,并非都来自宗教。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公民精神。利他精神体现在慈善、捐赠、志愿者服务等利他行为中。它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从追求物欲满足转向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精神满足感。如果说,升华型超越可以是个人性的,那么,利他型超越一定是关系性的。它是通过帮助他人或某个群体而获得的一种自我超越。这种超越带来了精神上和价值上的满足感。如果说,升华型超越是通过提升感性化的精神生活来实现与物质生活的平衡,那么,利他型超越则是通过提升价值性的精神生活来实现与物质生活的平衡。但是,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利他行为。一种是工具性利他,另外一种是自目的性利他。工具性利他是把利他当作提升自己的利益的一个手段。例如,由于志愿服务有助于在高校入学申请中被录取,一些人就把做志愿服务当作进入高校的敲门砖。一旦目的达到(被高校录取),就放弃了做志愿服务。自目的性的利他则是把利他本身当作目的,尽管它客观上有时也有利己的后果。只有这种自目的性的利他,才具有自我超越的效果,才能让人们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并因此摆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
上述四种超越机制都有着各自所要超越的对象。仅仅就富裕失范中的第二种消费失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而言,它的超越机制主要是升华型超越和利他型超越。前者从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后者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超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并进而达成二者的平衡。不论是升华型超越机制,还是利他型超越机制,其目的都是要通过让人们上升到文艺性精神生活和道德性精神生活的层面的方式,来超越物质性快乐、生理性快乐或单纯的感官刺激性快乐对人的消费行为的支配。就升华型超越机制来说,那些让人们沉浸在感官刺激性快乐层次而不能自拔的传播色情、物欲、暴力刺激的文学、电影、电视剧等低趣味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并不属于这种升华型超越机制。相反,它们有时可能成为物欲的诱发机制。如果说通俗文化产业受制于市场的盈利最大化原则,常常会更多地诉诸物欲刺激,那么,高雅文化则往往能超越这种物欲的羁绊。但是,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边界划分,是充满争议的。而且,高雅文化的消费预设了消费者必须具备必要的品味和鉴赏力。但是,正如布迪厄所说的,不同的阶层的品味和鉴赏力是不同的(51)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1984.;拥有高雅趣味和高雅艺术鉴赏力的人数是相对较少的。如何能让大众也能借助升华型超越机制以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构成一个挑战。由于篇幅限制,这些问题留待未来讨论。就利他主义型超越机制来说,那种工具性的或以功利为目的的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严格来说,也不属于利他型超越机制;只有自目的性的慈善、捐赠和志愿者服务,才属于利他主义型超越机制。当然,工具性和自目的性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还涉及更复杂的关系。不过,限于篇幅,它只能另文讨论了。
五、结论
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丰裕化的过程,因为现代化不但包括经济、技术和物质的现代化,而且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则涉及人成其为人所需要的各个维度的平衡。在前现代阶段,由于物质的短缺,我们或许侧重其中一个或少数维度,而放弃其他维度。因此,在前现代阶段,我们作为人,还是不完整的,我们过于抑制人的正当的物质欲望,并过于抑制人的自由。但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经济、技术和物质层面的进步,我们解除了过去套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禁欲主义约束,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到另外一种不完整性或不平衡状态当中,即过度追求物欲和感官刺激的满足,而放任自己陷入低层级需要的满足中而失去必要的自我约束。这种状况,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富裕失范”。
涂尔干的“富裕失范”理论告诉我们,仅仅凭借经济增长或物质产品的增加,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它由各个维度组成,对应的是人的完整性。人是一个多维度的人,而不是单维度的人(即物质维度或生理维度的人)。人需要有精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和道德生活。相应地,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但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文化和道德的发展。如果我们一味强调经济、技术和物质,而忽略文化和道德的建设,忽略人之为人所需要的多维度的有机结合,那么,我们将陷入与富裕相联系的痛苦。这种痛苦源于我们缺乏道德规范的调节。它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富裕失范。
就消费生活领域来说,与富裕失范相联系,我们陷入了两种消费失衡:第一,物质欲望的增长速度与满足这种欲望的物质资源的增长速度的失衡,或者说,物质欲望与物质资源的失衡;第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这两种消费失衡都导致某种痛苦。要克服消费失衡,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涂尔干分析了约束性平衡机制在克服富裕失范中的作用。但他说的约束性平衡机制只能解决第一种消费失衡,而不能解决第二种消费失衡。要克服第二种消费失衡,我们必须借助新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超越性平衡机制。它包括升华型超越机制和利他型超越机制。借助这些超越机制,我们才能实现人性化消费(52)Ger, G., “Human Development and Humane Consumption: Well-Being beyond the ‘Good Lif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Vol.16(1997), No.1,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Law and Public Policy, pp.110-125.。单方面强调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化消费,因为它并不能带来人的福祉的最大化。只有让物质消费和其他维度的消费(包括精神消费)实现平衡,才算是人性化消费。但人性化消费不但涉及物质欲望和物质资源以及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平衡问题,也包括家庭消费和公共消费、个体消费与共享消费、自我导向消费和社会导向消费的平衡问题。而迈向人性化消费,应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