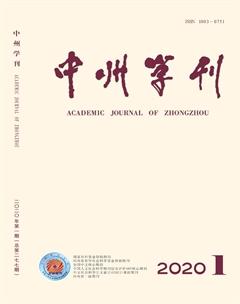“能源正义”及其中国化
王明远 孙雪妍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先驱的电力市场改革,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去监管化”“资产私有化”手段,强化市场在能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电力行业经济效率提升。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力量扩张使立法与政策制定以经济效益、财产权保护和法的工具理性为“风向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权利分配不平等、环境与生态成本过大等“市场失灵”问题相继出现。在此背景下,近期兴起的“能源正义”理论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同,它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代际间能源利益和负担,是一种应用于政府能源决策的分析框架,为电力市场改革提供道德目标和价值理性。《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我国电力法制的中心思路从高度行政管控逐步向自由市场下的适度监管过渡。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电力体制存在的“非正义”现象多是计划经济下政府过度干预所致。电力法制的发展要兼顾两个面向:确立市场机制下竞争自由的能源分配制度,对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不平等进行制度性预防;保障公民能源权利与人们的环境权益、代际利益,在能源分配中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关键词:能源正义;电力市场;能源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1-0060-10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30年间,市场自由化成为全球电力改革的基本趋势。三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客观现实引发了人类对能源结构转型及能源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深思: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面临电力供应安全的挑战,虽然能源供应根源于经济发展,但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治威胁、社会动乱甚至恐怖主义等多重因素使能源供应更为复杂和棘手①;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人权观对能源分配的公平性提出疑问,隐藏在科技文明塑造的繁荣图景背后的是能源匮乏和分配失衡的真相。②
以资产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电力市场改革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等工业化国家,基础设施国有化、供电特许经营、垂直垄断和发电计划等传统的能源监管手段逐步被以经济效率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倡导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的监管所取代,能源法学者将这一新的趋势概括为“市场竞争导向的政府监管”③。从长期效应来看,开放的市场有助于引导电力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以及电力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两方面的理性投资,最终向消费者传导福利。④然而,市场手段存在调整失灵的风险,纯粹经济价值与社会普遍福利之间的矛盾难以弥合。电力行业的国家战略性及公共事业属性决定了适当程度的政策干预和法律保障的必然性,此种调控手段不能完全以经济效率为导向,而必须从社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的角度对市场失灵引发的利益失衡进行纠偏,以达成一种个体权利受到有效保护的电力市场。
在电力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决策以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为偏好,往往忽视个体权利保障和对政策正义性的关切。“能源正义”这一能源法领域的新兴概念不仅提供了法哲学层面的思考方向,其基本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还可以指导立法者与监管者在市场规则制定、法律实施、能源类型选择、项目决策等场景中采取一定行动,将公众普遍接受的正义、平等价值理念融入决策,进而积极影响个人、企业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行为。
“能源正义”的本质是正义特别是“分配正义”这一古老议题在新兴的能源社会关系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能源正义”的根本价值立场是什么?在其价值维度上构建的政策分析框架如何指导电力领域的立法与政策制定?这一西方舶来的理论话语,其内涵能否适应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现实土壤?回归到规范立场,我国电力领域存在何种“非正义”现象亟待电力法制⑤介入纠正?
二、“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与体系:西方观点
(一)“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
“能源正义”代表现代能源法制构建中的一种基本价值立场,它以“正义”原则评价能源政策制定、能源生产体系、能源消费、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转型中政府决策的正当性。⑥“能源正义”追求能源法律、政策制定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回归个人权利的“正义”,强调人类个体是道德、价值、权利与义务的终极单位,每个人在能源法秩序下享有平等道德地位和权利义务。⑦
由此可见,“能源正义”与“个人所应得的权利或利益”紧密相关。为保证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事物,需要运用政策或法律的强制力量完成物质财富及非财产权利的分配,这就涉及历史上不同“分配正义”观所争论的焦点问题:在分配的依据上,个人权利、贡献、需求或才干,将何者作为基础最合乎道德标准和要求?在分配的限度上,平均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代表严格程度不同的正义,更暗示着国家强制力对市场分配的不同干预程度,以何者作为原则最符合当代正义观的诉求?历史上,关于“分配正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最早产生的“分配正义”理论被称为“严格平均主义”(Strict Egalitarianism),它以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分配的正义性,提倡物质财富、负担和社会服务的平均分配,数量上不均等即可视为非正义。⑧尽管该主张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自然法观念高度契合,颇具道德感召力,但其注定只能存在于一种理想化的社会蓝图之中而无法充分融入现实生活。这是因为,它忽视了个人能力、效率、贡献的差异性,一味强调财富的平均化。即使财富的初始分配达到了平均主义,在人类劳动创造的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能者与弱者在消费与积累财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平均结果。以时下的观点来看,“严格平均主义”在道德基础上亦欠缺说服力,它纵容无能与懒惰,缺乏对劳动的必要激励,客观上只会导致社會普遍贫穷的后果。⑨
第二种“分配正义”观以平等为价值取向,认为最理想的分配方式既可以激励社会总体财富增长,又尊重个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平等权利,“正义”一词在此等同于权利平等而非数量平均。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由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依其所见,“分配正义”包含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的调整对象是公民基本自由权(包括选举与被选举的自由、集会与言论自由、良知的自由、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免于受到恣意逮捕的自由),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这一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其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权与他人的同类型权利是相容的。第二个原则的调整对象是物质及财产权利、劳动权,它又包含两个子原则:其一,各项职位及工作机会应当均等地对所有人开放;其二,在不损害公民基本自由权和公平就业权的前提下,允许以差别分配调整经济、社会不平等,使社会中的最劣势公民(“最少受惠者”)受益最大。⑩罗尔斯理论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对“最少受惠者”以特殊保护的“差别原则”上,他主张通过有限的差别待遇纠正因个人能力、机遇不同而造成的实质不平等,为了改善“最少受惠者”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度牺牲社会总体效率。但是,差别分配的目的仅限于将“最少受惠者”的绝对经济水平提升至其基本人权得以保障的程度,并不改变个人之间相对的经济地位。B11不难看出,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观更关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前提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反对以公共利益为名盲目追求社会生产效率提升。
第三种正义观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反对“平均主义”“平等主义”的根本逻辑,不赞同将实质平等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目标。实质平等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人为地追求平等会增加政府在生产要素流通上的约束条件,降低扩大生产的动力,最终会导致对多数人更大的不平等。自由分配原则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对于依赖何种力量实现“分配正义”,哈耶克曾作出经典论述:“市场机制是最自由、最有效、最公正的,由此产生的财富分配状况无可厚非,自由必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B12回到前文提及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关系,自由分配正义要求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和最强意义上的市场。申言之,在这种观念下,市场机制被认为是天然正义的。威尔·金里卡曾经对自由主义倡导者(如哈耶克、诺齐克)所持观点的逻辑正当性作出总结。他指出:在初始状态下,世上的一切物品都是无主物,而人只能以自由意志支配自己。此种条件下,每个人可以不成比例地对某些物品拥有绝对权利,此种占有若不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即被视为正义的;一旦私人财产的所有权被初次确立,就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来保障交易的进行。只要财产所有者的初次取得行为合法,判断“分配正义”的标准就变为转让行为是否符合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自由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刺激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总量迅速扩张;在对个人经济权利的态度上,它更倾向于经济与价值无涉的立场,体现了一种“患寡而不患不均”的哲学思路。
能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首先作为一种商品存在于市场交易中,同时又对现代社会的福祉至关重要,能够为人类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等基本人权之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一事实不因地域、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从这一角度理解,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个人获取能源的权利得到保障。有学者这样定义“能源正义”:它旨在为不同地域的人类个体供应安全的、价格适当的、可持续利用的能源;每个人享有能源权利的基础在于,人类个体是人类普遍共同体的成员,不因国籍、身份、宗教信仰、种族或出生地等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对待。B13可见,“能源正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实现“分配正义”。
笔者认为,“分配正义”中的“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并非决然对立;“能源正义”理论是能源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產物,它试图用“平等正义观”矫正、补充“自由正义观”。在依赖市场力量创造社会总体财富达到较高水平之后,市场自由势必不断加大个体之间的贫富差异,“最少受惠者”的基本能源权利受到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意识到能源市场的角色应当定位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手段而非天然的道德目的。当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不符合能源普遍供应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性目标时,必须依靠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整。由此,“平等”更有助于解释“能源正义”的重要道德意义:它强调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考虑每个人的福利,避免对个人或群体的完全忽略,使纯粹的经济总量增长让位于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更符合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包容式增长的基本理念。B14
(二)“能源正义”的结构框架:“分配正义”“法律承认”与“程序正义”
1.“分配正义”
如前所述,“分配正义”是“能源正义”的最基本内容,其调整对象主要是能源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如能源项目的选址及服务分布是否能够公平地覆盖不同的社会群体,同时关注项目产生的环境负担如何分配。B15能源的自然分布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分配正义”呼吁通过制定政策来缩小能源富集地区与能源匮乏地区之间能源获取机会的差异。在实践层面,“分配正义”除了评价基础设施建造的选址正当性,还关注能源产品和能源服务的可获取性。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分配正义”的标准超越简单获取电力,上升到对消费者能源服务自由选择权的保障。
2.“法律承认”
“能源正义”认为:强调个体的人权与尊严,通过能源供应促进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基础权利实现是能源政策与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法律承认”解决的是“能源正义”的本源性问题,即判断一项能源决策是否顾及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者、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律承认”特别重视平等参与,不允许以威胁、忽视、曲解、控制等手段损害弱势群体的参与权。B16贫困人口、老年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往往在能源决策中被贴上受教育程度低、非理性、保守主义等歧视性的标签;政府往往更信赖专家的结论而忽视弱势群体的意见;企业往往依靠经济及科技优势,故意向社会公众散布误导性信息或迫使公众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使弱势群体被迫承担过重的义务。“法律承认”是建立在“平等正义观”之上的一个群体识别过程,即识别“谁”在能源决策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虽然各国宪法没有明确要求立法者给予弱势群体“特殊优待”,但的确应当关注他们的能源权利,保证市场竞争不会在事实上加剧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因为“市场遮掩着社会偏见,不但对消费者在市场中的不平等沉默无语,而且还对其加以强化”B17。
3.“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能源正义”的第三个框架性内容,是“分配正义”的实现手段。“程序正义”的核心是为能源政策的一切利益相关群体提供平等的程序保护。根据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学界通称《奥尔胡斯公约》),缔约方必须在立法框架内向公众散发环境方面(包括交通、能源、矿业、农业等领域)的行政措施、环境协议、政策、立法、计划方案等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相关项目、计划的透明、公正的框架,并尽力促进公众参与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规则和法律(其中包括能源领域的项目和计划)的制定。B18这些规定被认为是“能源正义”得以实现的程序基础。达伦·麦克利等学者特别强调保障“程序正义”的三种主要方式。B19
第一,动员地方参与。能源项目所在地的居民是能源决策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居民包括一些原住民,其生产生活极大地依赖当地的环境和生态系统,贫困程度越高的地区,居民对能源项目的环境负外部性的承受能力越小。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以保证当地居民尽早参与能源决策流程,并使其意见得到合理的反馈与采纳。当地居民参与能源决策程序,还可以对专家的知识提供有效补充:当地居民基于长期的生产经验,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性和资源禀赋特征具有高度敏感性,其经验性的知识往往比一般科学规律和理论更为实用。与工业城市中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不同,当地居民对世代居住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乡土情结,这使他们成为最关心自然保护的群体。将当地居民的知识与经验作为能源决策的考虑因素,可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逐利性能源政策出现。
第二,从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个层面建立自下而上的信息公开机制。“程序正义”的两个抓手是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将调查公众意见、召开公众座谈会等作为能源与环境决策的常规程序。传统的信息公开机制主要由企业作为信息提供方、公众作为信息获取方。德尔玛等学者认为,公开居民能源消费信息有助于加强能源普遍服务和能源可持续利用:居民可以将其电力消费习惯反馈给地方电力供应机构;电力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智能电表等新设施的普及,收集并公开居民的能源消费习惯;居民也可以获得区域电力消耗的日期信息,通过“价格信号”错峰用电,以节约能源支出。B20
第三,建立实质公平的代表机制以反映不同群体的诉求。公众参与中的代表构成会影响能源决策结果。根据2010年的一项统计,在瑞典、德国和西班牙,超过64%的能源公司没有女性管理人员;在世界前250强的能源公司中,董事会席位和高级管理人员中白人男性的数量超过84%。B21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观点缺乏表达通道,最终会导致政策的中立性丧失。能源决策的正义性并不局限在经济平等这一个方面。“程序正义”之所以要求无歧视地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参与权,深层原因在于公民身份不应因性别、种族、社会阶层等因素而有所差异,这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它可以保证决策过程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与高质量的决策结果是同等重要的。
(三)“能源正义”的评价指标
有关“能源正义”的学理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该理论对推进实践发展有重要意义,欧美等地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2017年,英国能源研究委员会(UK Energy Research Council)将“能源正义”列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B22基于“正义”内涵的包容性与价值判断的多样性等特点,对“能源正义”给出一个精确的、描述性的概念并非易事。
2016年,本杰明·K.索瓦库等能源政策专家将“能源正义”定义为:“一个公正分配能源利益和能源负担的全球能源系统,以及一种广泛代表民意的、中立的能源决策机制。”B23相较于其他观点,该定义更偏重于建立“能源正义”的核心评价指标,以构建具有适用性、较强可操作性的决策评价标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能源正义”仅限于道德口号的问题。他们认为“能源正义”包含8个评价指标,即能源的可获取性、价格可支付性、决策程序正当性、政策透明性及问责制、可持续性、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共同责任。
在法制语境中,抽象的正义并不存在,制度的正当性取决于被其干预的基本权利的样态。B24对于由上述指标组成的评价框架,需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法律和政策,以多元化路径保障个体能源权利的实现。具体而言,该框架中每个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制度路径如下:“可获取性”通过引导资本投向提高耗能效率的项目以及升级基础设施而实现;“价格可支付性”通过对贫困人口、老年人口住宅的取暖和制冷设备免费改造计划(weatherization assistance program)以及对老旧房屋的设备改造而实现;“决策程序正当性”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能源项目信息的免费公开而实现;“政策透明性及问责制”通过“采掘业透明度计划”,由政府定期向大众公布能源公司缴纳的能源、资源税费和政府从石油、天然气、采矿公司收到的所有收入信息,改进能源企业的信息披露而实现;“可持续性”通过增加零售端电价、对新能源项目给予补贴以及为后代建立自然资源基金而实现;“代内公平”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七)B25倡导的路径实现;“代际公平”通过激励环境友好型项目、建立绿色债券市场而实现;“共同责任”通过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筹集绿色气候基金而实现。B26
三、我国电力法制中的“能源正义”
(一)“能源正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西方电力市场之差异分析
“每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正义范式都建立在一个共识上:任何一个社会规范理论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或全球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政策的选择偏好。”B27一方面,能源贫困、能源决策机制不民主、环境与生态价值受损等全球性问题普遍存在,要求能源政策遵循一种普遍性的、无地域差别的正义观念,保障个体在全球能源秩序中平等的道德地位和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地方性的、国内或国际层面的能源制度都涉及具体的正义问题,相关决策必须顾及能源类型、地域、社会制度与经济水平等因素,因而难以构建统一的政策评价指标。从这一现实出发,笔者认为“能源正义”概念应当同时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宏观“能源正义”是一种普遍的能源正义观,可从道德标准、价值目标上为一切能源决策提供引导,解决的是能源法制的立场判断问题;微观“能源正义”则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决策工具存在,从不同制度路径保障个体的能源权利,强调正义的规范性表达。亦即,“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和结构框架不因国别、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具体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需要从历史的、差异化的视角分别建构,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该理论之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結合。
“能源正义”的实现以及能源利益与负担的公平分配,需要凭借现代能源领域中社会、市场与政府这三种机制与力量的合理分工和适当配置。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渗透到能源领域,形成了电力市场化改革浪潮。在电力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资产私有化”“去监管化”成了电力市场改革的两大特征。电力资产私有化改变了长期存在于电力行业的国有资产垂直一体化格局及由此引起的高度垄断,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相应地,电力监管的重心从价格管制转移到竞争秩序维护。在有效防控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前提下,“去监管化”要求政府尽可能减少市场干预,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提升经济效率。电力监管改革的深层逻辑在于,尽可能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利用市场的价格信号平衡供需,激励经济效率最高的投资,同时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技术。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英美等国家的电力竞争市场已具相当规模,如竞争性批发市场已占美国电力供应超过60%的份额,其余由垂直垄断性电力公司供应的电力中也存在竞争性的第三方新能源供应商,多数发电商和售电商已经适应不断提升经济效率、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然而,市场总是存在失灵的风险,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政府监管名义上以“提升经济效率、实现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实则可能因疏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而偏离公共利益。更少的政府干预可以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效率,但往往以牺牲电力行业的长期稳定性、能源的普遍服务等社会福利为代价。抽象的公共利益不等同于个体利益的总和,其承载着公平、正义、和平等价值功能,在特定情况下致力于遏制自由主义的过分发展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等消极影响。B28弱势群体承受着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环境负担,却往往无法享受到能源发展的经济效益,甚至不能获取充足、透明的信息,在能源决策中的参与权有时也会被剥夺。这些现象使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公共利益”难以充分实现。在现阶段的西方国家,“能源正义”理论的首要任务在于保护弱者的权利和机会公平,以“人本化”思维遏制自由市场的过度膨胀和公共服务的不当萎缩。
在我国,历次改革并未建立起真正的电力市场;在价格机制方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称“9号文”)发布之前一直采用发电上网定价方法,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固定的上网电价;B29在发电数量上,主要由主管部门采取行政命令手段为燃煤机组分配指定的发电小时数;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电力辅业集团均以国有企业形式拥有绝大部分电力资产B30。显然,“资产私有化”“去监管化”这两项西方电力市场发育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并未出现。事实上,我国电力领域长期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呈现出行政高度干预的产业特征,主要表现为“政企合一、管办不分、垂直一体、垄断经营”B31;省级政府的地域保护阻碍了跨省区域市场的发展B32;电力行业没有形成多买多卖的竞争性格局等。
电力市场建设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英美等国面临的“能源正义”挑战根源于市场过度自由,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市场化不足和行政干预带来的“分配正义”问题,核心问题是由“政府失灵”导致的监管理念偏离、行政干预价格、政府控制企业、电力监管中的裁量权滥用等。西方学者提出的“能源正义”理论意在解决能源法治的立场判断和价值目标问题,目的在于抑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理性过度膨胀以致阻碍能源系统发挥增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弊端,保障公民通过获得充足、清洁的能源而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这种理论下宏观意义的“能源正义”对我国电力市场改革与电力法制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与传统理论相比,“能源正义”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为长期主导能源决策领域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多元化的新思维,在经济利益与成本考量之外,将能源开发使用造成的环境负外部性、社会不公正计入能源成本,将能源服务的社会福利效应、能源转型的环境效益计入能源效益。“能源正义”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有同样的价值诉求,都对电力的绿色发展有所助益。
其次,虽然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基础条件与进程落后于英美国家,但市场自由化已经成为电力行业的发展趋势。《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电力现货市场;B33“9号文”也将坚持市场化改革作为电力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不难想象,如今英美国家面临的“能源正义”问题,在我国电力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时也会出现。以“能源正义”理论的精华来指导我国下一步电力改革方案,可以起到杜渐防萌的作用。
最后,“能源正义”理论呼吁一种以市场为能源分配的基础力量,同时优化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源决策模型。就我国而言,政府对能源产业的强势入侵是改革进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科学有效的能源监管要求政府行为有法可依且各职权部门的权责利相统一。近几年来,我国能源行业要求国家进行“放管服”改革,即尽量尊重市场规律,减少政府对能源行业资源配置的干预,并特别强调权力运行的规范性。B34“能源正义”理论框架特别是其中的“程序正义”部分,提供了一种以程序规范实体权力的思路,即要求政府将公平程序作为评价其监管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且减少其过度干预市场和滥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在我国“大政府、小市场、小社会”的能源产业格局下,上述理论特别有利于强化政府责任。
当然,价值目标可以赋予“能源正义”正当性和实质理性,却不是“能源正义”规范性的直接表达,只有将“能源正义”的价值目标落实为调整社会关系,规定公民、企业和政府机构之权利(力)、义务的能源法律与政策,“能源正义”理论才具备法规范的一般形态及相应的工具价值。考虑到英美国家政治体制、市场成熟度、现实问题与我国存在高度的差异性,微观层面的“能源正义”(即“能源正义”的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不适宜直接指导我国电力立法与政策制定。下文结合我国电力行业的现状,厘清我国电力法制背景下“能源正义”的核心内涵,探究“能源正义”理论的本土化路径。
(二)我国电力法制中“能源正义”的内涵
1.“分配正义”之一:适度市场化
“9号文”是当前我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指导文件,它要求改革必须遵循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安全可靠、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保障民生、坚持节能减排、坚持科学监管”B35。该文件重启了电力改革,其核心措施是:通过电价改革带动电力市场化,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自主调节,输电电价和配电电价由国家独立核算确定。电力市场改革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进“直接交易”试点,实施发电厂与需求体之间通过中长期合同直接竞价交易;二是逐步放开售电市场,允许所有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开展售电业务,构建多元化售电主体;三是压缩主管部门对发电机组运行时间的分配,逐步放开发电计划。
发达国家电力市场的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在发展中国家,电力资产公有化、垂直一体化降低了市场效率,但客观来说,其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国有发电公司及电网公司将其大部分利润上缴给国家,由垄断经营产生的盈利即可转化为公共福利而非私人财富;从系统性效率的角度观察,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可以减少发、输、配、售电环节公司谈判与合作的成本;建设电力资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由于资质与规模上的优势,融资成本会远低于私人公司,对电价调控的承受能力更佳。除这些竞争优势以外,囿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本市场完善度、电力行业的巨额沉没成本、信息透明度、区域壁垒等现实问题,电力资产的完全私有化(即發、输、配、售电环节全部向市场开放,放弃零售电价管制)会遇到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挑战,因此,适度市场化路径更利于实现“能源正义”中的“分配正义”,路径设计应该围绕下述重点展开。
第一,实行发电与输电分离,组建独立的电力交易机构。在“9号文”的配套文件《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中,交易机构的基本职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政府监管下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公开、透明的电力交易服务”B36。独立性的交易机构以维护竞争性、中立性和透明化的电力市场运行为目的,负责电力供需之间的协调,按照输电、需求的实时波动来平衡系统,在电力现货市场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美国,跨州的电力市场以区域输电组织(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RTO)为核心,这些组织拥有电网控制权,按照“输电开放准入”政策,以一定的输电费率,向发电者提供无歧视的服务,任何发电商都可以获准输电。RTO按照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批准的输电价格进行计划、运营和调度,提供开放式输电服务。RTO拥有多家买卖方,可以组织实时市场竞价并接受最低市场报价,即时开展调度和清算,使电力价格真实反映发电成本,从而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服务需求,传递真实的价格信号。独立交易机构的长期价值在于引导理性投资,将高成本、高排放的过剩产能自然淘汰,并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适当调度,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转型。B37电力交易机构的中立性在实现分配公正中尤为关键。在匹配交易双方时,该机构不得对某些资源拥有方提供特殊便利。2016年,我国首家电力交易机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采用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形式组建完成,随后,二十余家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相继成立,其中除电网全资子公司外,还存在少数股份制公司形式的电力交易机构。B38为平衡电力交易机构中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国家能源局指导组建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作为交易机构内部制定交易规则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构。B39该委员会由来自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电网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代表组成,这一机构组成方式可以确保电力行业各主体的利益在竞争中得到平衡,对保证电力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流动性具有突出意义。B40
第二,规范售电侧市场。售电侧开放是指在售电环节引入竞争,允许所有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开展售电业务,赋予电力用户自由选择权。与依托电网企业或发电企业的售电公司相比,独立售电公司存在“先天不足”:既不像电网供电公司一样拥有成熟的服务网络和服务渠道,也不像电厂售电公司一样具有锁定低价电力的天然优势,因而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我国已有300余家独立售电公司注销,这些企业多为民资背景,另有50余家售电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B41独立售电公司的存在对于丰富服务品种、构建多元市场、防止垄断损害用户能源服务选择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独立售电公司完全退出市场,售电侧企业事实上形成发、售一体化及输、配、售一体化两种格局,就会增加垄断的风险。在发达国家,独立售电公司的经营优势主要在于向中小用户提供精细化、综合化的电力服务,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套餐式电价、分时段或季节定制电价套餐,根据用户消费习惯,提供经济分析及节能方案等,这些对于保证居民以公平、适当价格用电有显著价值。B42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向新生的独立售电企业提供适当政策扶持,加强监管措施以规范售电市场,重点着力于防止传统电力企业凭借规模优势,通过恶意竞争而挤占独立售电企业的生存空间。
2.“分配正义”之二:电力市场生态化
正义的能源政策会合理安排能源结构,控制能源消耗速度,保证能源永续、稳定、安全供给,满足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于不可再生能源,强调以保存和不耗竭的方式予以利用;对于可再生能源,强调在保持其最佳可再生能力的前提下予以利用。在我国,清洁能源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能源结构总体优化的主要阻力并不是科技水平滞后,而是可再生能源政策与传统能源体制机制衔接不畅、全局性能源规划缺失以及政策目标的定位存在偏差等。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密不可分,正义的决策会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我国电力市场“生态化转型”阶段,有若干具体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协调能源规划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使二者合理衔接,重视可再生能源对并网灵活性的需求。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但在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如2017年我国风电年发电量3057亿千瓦时,弃风电量419亿千瓦时。B43“弃风弃光”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尤为严重,2017年甘肃、新疆两地的弃风弃光率都超过20%。B44可再生能源具有天然不稳定性,风力、日光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及发电的非持续性,都大大增加了储能和跨区域输送的难度。而我国电力现货市场薄弱,对煤电机组发电小时数均以年度合同形式进行调度,导致调度系统僵化,很难与新能源上网政策相兼容。
第二,善用价格调节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合理的电价不仅应当包含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应当包含相应的环境成本。申言之,符合可持续性要求的能源政策必须处理电力生产的环境影响。但是,电力政策往往是按照用户的偏好架构的,尤其致力于降低工业终端用户的电价,在产能过剩的现实下,电价补贴将使电价更加偏离真实成本。在我国,政府定价过度补偿了煤电投资,价格机制不利于落后产能的淘汰。在未来改革中,应当在电力价格机制中强化环境因素。
第三,从长期规划的角度制定综合能源规划,从更为广泛的公众利益层面衡量能源的成本收益水平,理性考虑各种能源类型是否符合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要求。任何一种能源消耗都不是“免费的午餐”,一定会带来某种形式的负外部效应,或体现为环境损害,或体现为人权、发展等方面的社会风险。如风电场建设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并造成土地功能退化、水土流失等损害,其运营过程中会造成噪声等形式的污染,干扰居民生活和野生物种栖息;核电站运营隐藏着核泄漏和爆炸的风险,会产生难以处置的放射性核废料,从而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使人们承受事故威胁和生态代价。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审慎地按照能源的特点,规划能源结构,避免非正义后果的发生。
3.“程序正义”:监管法制化与监管透明化
电力监管是连接法律、政策与产业运作的纽带。监管机构承担着日常监管职责,能够把握行业的变化动向与政策实施中的现实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电力监管机制的缺陷表现在:监管原则与权力依据模糊;执法手段单一、强制力不足;监管程序不透明。英美等国的电力监管规则通常都确立了层次分明、功能多样的执法手段,根据企业违法的形式与后果,设置了严格细致的处罚标准,并特别强调监管行为的程序合法性,防止监管机构滥用行政裁量权。
现代能源监管以法定化、人本化、柔性化为发展趋势。法定化与“能源正义”中“程序正义”的内涵相似:一切监管流程必须是有法可依的、可预见的、公开透明的。我国电力监管的常用手段包括披露典型问题、约谈监管对象、电力稽查等,执法缺乏统一的制度性规范,在规则适用上缺乏一致性。监管机构“闭门操作”的模式,实质上增加了滥用裁量权的风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监管机构的行为通常会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例如,英國燃气和电力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执法指南为该机构的日常执法工作提供了详尽的行为准则与程序性规范,其中的具体法律依据主要包括能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个方面的法律。B45在美国,联邦和各州能源监管机构的权力、职责和执法程序均受法律规制,相关企业的证据和证词也要受到利益相关方和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监管机构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企业对监管机构的决定不服,其只能通过州法院或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出于对专业意见的信赖,法院会支持监管机构的决定,但如果监管机构滥用权力、曲解法律或有执法程序上的瑕疵,法院则会推翻其决定。这既保证监管机构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以履行职能,又能对监管机构行使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B46
监管的柔性化与人本化是对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传统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柔性化与人本化的监管则提倡双方之间良性、有效互动。电网公司、发电厂、售电商不应该被迫回应监管要求,而应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自发地选择对企业及社会公众有利的行为。这从源头上要求政策制定部门了解监管对象的实际需要,设计激励性的监管措施,对企业符合公共政策的行为进行实质奖励。同时,监管是为市场服务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监管机构提供的并不是“制裁”,而是“服务”。现代监管强调在沟通与协调过程中达成规制目标,赋予执法手段一定的“弹性”与“柔性”,创新执法手段往往能以最小的执法成本和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最小的方式,达到充分的执法效果。如在英国电力监管领域,对于涉嫌存在不正当竞争、垄断市场、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企业,燃气和电力监管委员会常要求其作出经营者承诺,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如果被调查企业向监管机构作出停止、修正或从事特定行为的承诺,并且承诺内容足以消除相关影响,执法机关即接受承诺并终止案件调查。B47上述措施可以迅速解决纠纷,节约大量执法成本,并且经由执法机构提供的对话平台,使受损害的消费者、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可以通过协商参与到案件的实质决策中,有利于保障救济措施对各方利益的平衡。
四、结语
“能源正义”理论为能源法制建设提供了人本化、生态化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也提供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有利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保证能源产业创造的社会福利普遍化。我国电力市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政策与法律导向对于改革成果事关重大。公正分配电力改革的利益与负担,保障不同社会群体的基本能源权利,创造公民平等参与能源决策的程序,是“能源正义”的核心内涵,也是我国电力立法、政策制定中必须着力改进和加强的。
注释
①B22Kirsten Jenkins, Darren McCauley, Alister Forman. Energy Justice: A Policy Approach, Energy Policy, No.2. 2017.
②World Bank. Global Tracking Framework: Energy Access,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energy/publication/global-tracking-framework-2017.
③④Peter Duncanson Cameron. Competition in Energy Markets: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7-12.
⑤本文中的“电力法制”包括电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电力改革中的重要政策性文件,实际范围涵盖电力法与电力政策。
⑥McCauley, Darren Heffron, Raphael Stephan, etc. Advancing Energy Justice: The Triumvirate of Tenets,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Review, No.3, 2013.
⑦参见蔡拓:《世界主义的理路与谱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⑧O.C Ferrell, Linda Ferrell. A Macromarketing Ethics Framework: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No.3, 2008.
⑨Arneson, Richard. Egalitarianism,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3/entries/egalitarianism/.
⑩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p.60.
B11Julian Lamont, Christi Favori. Distributive Justice,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justice-distributive/.
B12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页。
B13Gagon L., Belanger C., Uchiyama Y.. Life-cycle Assessment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ptions: the Status of Research in 2001, Energy Policy, Vol.93, 2016.
B14参见阳芳:《五种分配公正观及其当代价值》,《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B15B16B19Kirsten Jenkins, Darren McCauley, Raphael Heffron, etc. Energy Justice: A Conceptual Review,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11, 2016.
B17S.Ranson. From 1944 to 1988: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Vol.14, 1988.
B18參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奥尔胡斯公约执行指南》(第2版),2014年,第110、184页,https://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pp/Publications/Aarhus_AIG_2015_Chinese.pdf.
B20B42Delmas M., Fischlein M., Asensio O.. In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Behavior, Energy Policy, No.2, 2013.
B21B26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ppointments to Boards and Equality Law, https://www.equalityhumanrights.com/sites/default/files/appointments_to_boards_and_equality_law_22-07-14_final.pdf.
B23Benjamin K.Sovacool, Raphael J.Heffron, Darren McCauley, Andreas Goldthau. Energy Decisions Reframed as Justice and Ethical Concerns, Nature Energy, Vol.1, 2016.
B24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和联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B2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七)即“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它倡导国家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优化节能实践,采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企业使用和进一步开发电力和生物能源的水力来源;投資者更多地投资于可持续能源服务,将来自多元供应商基组的新技术快速投放市场;个人采取低碳、低耗能的生活方式。
B27Young, I.M..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5.
B28参见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B29B35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
B30《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发布后,原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重组成11家公司,包括两大电网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国电集团、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2017年,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集团。
B31参见沙亦强:《电力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访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俞燕山》,《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07年第8期。
B32《东北电改启动艰难:省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需打破》,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50804/184222874978.shtml,2015年8月4日。
B33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B34参见国家能源局:《能源行业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能发法改〔2019〕5号)。
B36参见徐小东、凡鹏飞:《电力交易机构将是推动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标志——解读〈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http://www.ndrc.gov.cn/zcfb/jd/201512/t20151225_768694.html,2015年12月25日。
B37《美国电力市场发展史观〈基本规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http://www.cec.org.cn/guojidianli/2017-01-17/163853.html,2017年1月17日。
B382016年9月,重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其股权结构中引入了电网外的第三方机构,是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第一家股份制电力交易中心。
B39市场管理委员会是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的市场主体按类别推荐代表组成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构,在制定交易规则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中,发电方代表12位,由四川、山西、内蒙古等主要送电省(区)政府电力主管部门各推荐电力企业代表1位,五大发电企业及主要参与跨区送电的三峡集团、国投电力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华润集团各推荐代表1位;购电方代表7位,由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北、河南、河北等主要受电省(市)政府电力主管部门各推荐电力企业或用户代表1位;电网企业代表5位;第三方代表5位。市场管理委员会实行按市场主体类别投票表决等议事规则。
B40《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提出:“为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各方意愿,可建立由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组成的市场管理委员会。按类别选派代表组成,负责研究讨论交易机构章程、交易和运营规则,协调电力市场相关事项等。市场管理委员会实行按市场主体类别投票表决等合理议事机制,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派员参加市场管理委员会有关会议。市场管理委员会审议结果经审定后执行,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行使否决权。”
B41《大批售电公司黯然离场,留下的该如何前行》,能源新闻网,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4935263314109120&wfr=spider&for=pc,2018年8月20日。
B43B44《2017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2/content_5263096.htm,2018年2月2日。
B45The Government Regulator for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in Great Britain: Enforcement Guidelines, https://www.ofgem.gov.uk/ofgem-publications/89755/enforcementguidelinesdecisiondocument12september2014publishedversion.pdf.
B46参见谢开:《美国电力市场运行与监管实例分析》,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B47参见焦海涛:《反垄断法承诺制度的功能解释——从我国的实践案例切入》,《财经法学》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邓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