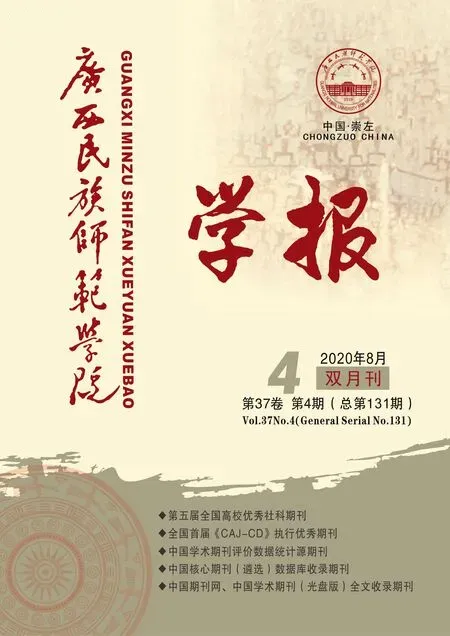经验与生命书写:吉小吉诗论
魏 巍 ,蒋 薇
(西南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00)
歌德说:“谁不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1]如今,诗人到底为何发声?是为“听众”还是为自己,抑或兼而有之,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个纷繁的世界,也是讨论文学如何成为经典的重要参照。歌德所说的诗人,显然是指经典诗人,而并非所有的诗人。单纯地说教或歇斯底里地呐喊势必不是好诗的标准,也无法达到寄寓情感的要求,如何让敏锐的诗心包罗万象,是诗人吉小吉作诗恪守的原则。在他的诗中,充盈着默默流淌的温情,没有声嘶力竭、矫揉造作。
“近年来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使得诗人所创造的形象多样起来,不再是单一的忧郁知识分子、精神启蒙者和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英雄主义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日常、卑微却真实的自我。”[2]有着“北流才子”之称的吉小吉将“故乡”和“亲人”作为诗写的泉源,从小处着手,感情细腻,从细微之处烛照大千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诗应该从小处入手,找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写诗需要把虚的东西通过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让情感的抒发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撑,切忌无病呻吟,空喊口号;要注重情感在文字内部的自然流动。”[3]在《声音》这部诗集中,也可以看出诗人写诗的一种情感流变,即逐渐跳出狭小的自我空间去追寻更广阔的诗歌天地,更饱满地完善自我,呈现自我对诗歌最真的认识,同时以诗性的关怀审视当下,感悟生命。
一、经验之诗
诗歌从来都不是神坛上不可触摸的东西,它源于生活,正如“马克·吐温的经历成就了马克·吐温”,诗人吉小吉的诗歌亦是基于个人丰富的生活经历,倾述内心,沟通自然,直至与灵魂相融的产物。
父母、亲人是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带来最真挚情感的意象,虽说诗歌总有一种非功利的因素在里面,但情感的交融可能并非仅限于此。其次是对家乡(或故乡)的叙写,诗人们总喜欢凭吊回不去的故乡和逝去的童年。熟悉的故乡承载着儿时诸多记忆,既是自己情感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回忆童真、感受童心最好的“场所”。在对这类事物的描述中,常出现一种口语化的写作,若口语化的程度没有控制好,则“容易失之油滑或低层次的欲望的宣泄”[4]。然而在对亲人和故乡的“重复”书写中,吉小吉并没有泛滥自己的情感,在该收的地方尽量收敛,该释放的地方完整展现,恰如其分地掌握情感流露的节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能听见诗人内心最真实的呼喊。
谈及诗歌日常化和口语化的叙述,议论最多的可能是第三代诗人于坚。作为“他们诗派”的代表诗人,于坚领导“‘他们’逆流立论,呼唤出诗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等极端性的声音,引发了口语化的集体性诉求;并且身体力行,大面积地展开了回到诗歌自身的纯语言实验”[5]77。诗歌的写作不需要彻底的客观化,在对事物进行原生性还原的同时,达到诗歌的静观朴素之美即可。用日常化的语言进行诗歌写作,一种生活化的语言符号会随之呈现出来,在感受诗歌真实性的同时能够体会到诗人心灵深处的自我独白,进而产生共鸣。
吉小吉的诗歌写作和于坚有着相似之处,不会刻意追求诗歌语言的神秘隐晦,以具体的事件进行写作,用最真实的情感串联起所有的语词。诗人刘春曾对吉小吉的诗歌评价道:“虫儿的诗歌和木沙发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朴实,他曾经迷恋过那种风花雪月,并坚持好几年,后来逐步祛除了花哨的矫饰和无关痛痒的自恋。”[6]此番评价可谓是对诗歌内容、诗歌语言和诗歌情感都做了总结。的确,吉小吉的诗歌有着“木沙发品质”,厚重有质感,并非是一种流于表面的轻浮。这和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用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进行写作有着很大关系。
吉小吉的诗歌以情感贯穿其中,日常生活中的细小琐碎的事物都成为他的写作对象。“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7]吉小吉的诗歌意象来自生活,是对平凡事物的记录和情感的写真,读来真实而质朴。正如于坚在《棕皮手记·1996》里提出:“诗人要关心大地、关心环境、关心日常生活。”[8]297当然“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但中国文化对日常生活、日常人生总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这种文化所提倡的是一种诗意人生、高雅文化,觉得日常生活总是毫无意义,没有可供书写的价值。创作者在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中,不得不把琐碎的日常生活归于雅的对立面,甚至无人问津,他们不认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也会散发出诗意的光辉、自有鲜活的诗意存在。而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平凡意象,通常与行为、细节、体验、经历有关,吉小吉很多诗作充满了过程、情节、结果的状态体验和诗意呈现。与此相对应的是,诗歌的结构突显叙述,即让自己的情感在作品中顺着诗行的顺序自由流动,让事件或人物随着语感、节奏行进,一种充满新鲜具体的日常生活诗意就在叙述的展开中诞生,而真正的诗歌正是由普通元素构成,并让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充满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诗中选用一些较为平常的意象表现日常人生具体与琐屑的特性,也使得汉语词汇与事物及常识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带有一种轻松幽默感。如同俞平伯所说:“我以为凡是能以平民的生活做题材的,除例外情形不计外,当然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平民的诗和通俗的诗根本上是二而一的,不过同义异音形两个名词罢了。”[9]634诗歌《赶鸭子的人》选取生活中赶鸭子的农人形象,把鸭子的叫声比作歌唱,而把赶鸭子的人比作交响乐团指挥家,混合着除夕和新年的足音;赶鸭子的人扬起鞭子,诸多升起的音符透过浓雾,山鸟、远山、太阳等意象都让整首诗歌充满温情,一幅鲜活的画面顿时出现在眼前,诗人内心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在音符的牵引下也跳窜出来,呼唤远方的游子。又如《满地青》,或许注意到这种植物的人很少,但在诗人笔下却对它充满敬意:“我,该怎么向你致敬呢?一些人,到世界之外,寻找活着的意义时/你还在田野里/还在拼命张开怀抱……向我的内心蔓延、在我的身体里生长/我卑贱的乳名‘田生’/霎那间光芒万丈/并将照亮我的一生/让我,深深地感激已离去的父母。”诗中的“满地青”作为一个引子,化用古诗词中起兴的手法,实则是为了抒发自己对逝去父母的思念之情。《爆米花》一诗也是选取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象,借物抒情。爆米花亲切洁白,在土锅里舞蹈、欢笑,这是诗人最喜欢也是最怀念的景象,整首诗借这些简单的事物传递出一种对过去的思念之情。
经验的借用使得诗歌回到了生活,回到了经验与日常,但这是否意味着日常生活就此充满了诗意?从吉小吉的诗来看,这两者间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经验的日常性书写事实上只是生活在场的标志,只是对过去生活与情感复原的一种手段。
二、生命之诗
诗歌是诗人情绪的一部分,是苦闷的象征。吉小吉有很多诗歌都是谈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彰显一种生命意识。“由于情感活动优势,作家极易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寄托在对象上,每朵花、每株草、每座山、每阵风在他们心灵里都能获得特殊的灵气。”[10]103物质性是生命的基础,也是诗人创作所依赖的主要泉源,如诗歌《山丘》《萤火虫》《小蚂蚁》中的描写对象都是世间微小之物,在咏叹它们的同时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抒发诗人内心不便直接叙述的情绪。中国诗歌本就有言志和缘情的传统,当然志的表述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情的发动与人的生理感觉有更多的联系,但这种生理感觉也受到社会意识的制约,人的喜怒哀乐总是充满着社会的内容”[11]。诗的创造是诗人内在人格的一种体现,不断地朝着诗人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理想行进。
人本性中对生命的敬畏使得诗人以文字形态呈现时,总不可避免地思索并试图从中得到启示。“生命诗学是以生命为根基,从生命出发来思考和阐述诗的本质、作用乃至技术的诗歌理论。”[11]诗人的创作过程在无意识状态下便会受到“生命诗学”的影响,他们常常淡化诗歌与叙事文本之间的界限,强调一种诗性的文学使命感,将生命的书写与社会文化的忧思结合在一起。当然“生命诗学出现,须要生命意识成为作家创作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生命意识指人类对生命存在状态、生命本体问题及永恒价值的体察、珍视与省思,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生命苦难的消释和超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追求”[12]。生而为人,总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情感,对生命的歌颂不是一首哀歌,而是以文字的形式帮助我们表达和交流。诗人的写作是沟通自我内心的过程,在不断追问生命的同时,让诗歌成为自己生命的一种本能,成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新的方式。
诗人吉小吉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写进诗中,以回忆性描述的方式寄托自己内在情感,同时联系当下外在的景,内外交织、今昔对比,读来更有动人之感。在吉小吉的诗中,触发自己情感最多的是父母。因为年迈的父母卧病在床,自己却生活在外,油然而起的是一种愧疚与无奈感,曾经背井离乡的勇气却成了如今漂泊他乡的孤独感伤。
生命是脆弱的,正因如此,诗人的文字带有诸多伤感的色彩。诗歌《如果再静一些》写道:“父亲紧闭双目。/输液瓶吊在床架上/如果再静一些,能听到药液/在输液管里,一滴滴滴落的声音/父亲轻轻呼吸着。异常响亮/偶尔咳嗽。异常响亮/平常都是这样:挑粪担水、犁田耙地/都爱咳上几下;走路、抽水烟筒/都爱咳上几下。如果再静一些/能听到烟圈碰响那些沉重日子的声音。”过去的苦日子不仅是诗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更是父辈一生的经历,他们的一生都在土地上挣扎,为温饱忧愁,盼望着儿女长大,却又在孩子们成年后变成了“空巢老人”。父母的人生有太多值得感叹的地方,诗人笔下的父亲母亲不仅是年迈的老人,更是时代的缩影,他们奋斗拼搏过,努力尝试过,却只能和土地牢牢拴在一起,在饥饿声中早出晚归。不需要用过多的文字去赞扬他们的伟大,更不需要以一种振臂高呼的方式为他们呐喊,短小的诗行足以让温情流淌。当诗人写作病榻上的父亲时,整个春天都带有悲伤的色彩,在《哭泣的春天》中,诗人写道:“这一切是我诗篇中最动人的章节/它常常感动天际。让春天/也无边无际地哭泣/父亲啊,我懂得我和我的诗歌/都是一尾游不出你苦难海洋的鱼”诗歌作为连接父子二人的载体,帮助诗人保存有关父亲的记忆,缅怀过去,借以表达对岁月无情和生命脆弱的感叹。
组诗《天堂为什么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出发,责难天堂留住了自己的母亲,表面上似乎是爱闹脾气的孩子发出的怨气,实际却是儿子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对母亲离世的悲伤情绪的混合物,甚至饱含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我,敲着键盘/窗外的乌云下/一个不知名的飞鸟/它在声嘶力竭地啼鸣——痛。痛、痛。痛、痛、痛!……”即便痛彻心扉,在死亡面前人类也是那般渺小不堪一击,五个“痛”字重复铺排,将此番情感表达到最强烈的程度,标点符号的更替变化则将这种“疼痛”推向高潮。又如诗歌《经过孝感》:“汽车,经过孝感/像有什么,将我,轻轻/抽打一下。我/蓦然想起,父亲/他,卧病在床/我身在异乡/一个地名,其中/一个字,就一个字/就令我,心灵震动、不安/并且,愧疚、无奈。”,孝感的一个“孝”字深深牵动诗人的心,不仅不安,甚至是愧疚自责:父亲卧病在床,自己却身在异乡。诗中最巧妙的地方是将“孝”隐藏起来,由一座城市的名字发泄出所有情绪。在对生死的描述中,诗人有动人和共情的地方,自身经历带给他诸多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只能借文字的方式呈现“生命可畏”。
除开对亲人生死的描写,吉小吉的诗作还有很多是对灾难的描写,以诗的形式展现一种对生的敬畏,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感。人类本能对生的欲望使得诗人有了更多的同理心,而这种同理心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且没有国界之分,将诗性的写作转化为一种人文的关怀。如诗歌《愿望》:“睡着了。海啸过后/他们,一个个都睡了过去/半个钟头以前,一直/在他们体内流动着的/血液,现在,也沉睡不醒/就连废墟上的瓦片,也唤不醒/他们,真的唤不醒。”这是写于2005 年印度尼西亚海啸后的诗,如同一曲缅怀逝者的哀曲。此时诗人是站在全人类的视角看待这场灾难,将悲悯情怀转化成“愿望”,缩短了诗人与诗写对象之间的距离,把对逝者的叹惋与同情体现得更为真实具体。
在每次灾难面前,诗歌因其短小易颂的特点,成为文学的急先锋,担任起抚慰心灵的责任。诗歌《洪水》记录的是2006 年4 号风暴“碧利斯”过后的灾情,诗人面对荧屏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生发的一种怜悯心和在灾难面前的无力感,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弯下身来/轻轻为儿子/拭去他脸上的泪水。”《看地震搜救新闻》《嫩小的手掌》《红书包》《列队的书包》都是以汶川地震作为素材,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包括对死者的悲悯、对生命的思考和对救援者的赞美。这几首诗都是诗人从自身角度出发,以“我”作为叙述者,从外部审视这场灾难后写下的悲痛之词。其中至关重要的点在于:如何将发生于外的景转化为内在的情,且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避免情感的流变太为生硬,吉小吉采用再现场景、对话逝者、反思自我等方式,不断拉近讲述人与事件以及读者之间的距离,这种由心底发出的痛惜之情是真诚而具有感染力的。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存在从容的审美感受,只有同苦难的共鸣,任何不真实的情感表达都经不起的时间考验,甚至无法打动人心。
三、诗歌何为
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歌应该是最敏锐的,不但能捕捉到事件中的细节,而且能反应诗人的心理和情感变化,再加上篇幅较短小,带有旋律节奏感,易于和读者的情感产生共鸣,也就更容易传播,所以每次在重大事件中,诗歌往往在文学中充当“吹号者”的角色,那么诗歌在诗人的世界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诗人写诗又出于怎样的动机?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里,这是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索的问题。
是否书写重大题材可能并非判断一首诗是否经典的重要标准。诗歌《我想听一听大街上嘈杂的声音》写于2003 年非典期间,这首诗主要是发泄自我内心的压抑和苦闷,是自我情绪外在化的附属品,没有批判,没有歌颂,只是“多想听一听/往日大街上的那些/嘈杂的声音啊。当然从另一个积极意义上讲,这首诗也是想借自我经历和情绪表达人类在这场疫情面前的无力感。
诗人李少君曾说:“……一方面为那么多逝去的生命感到悲伤,另一方面,觉得在大自然面前人很脆弱。这种感觉折磨着我,让我一段时间以来什么话也不想说,有气无力,接近衰竭。一直到 5 月1 9 日晚,突然有了写诗的冲动……写完以后,突然有了一种轻松感,好像把压抑在心头的东西卸下来……”[13]这段话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些灾难诗歌写作者的心理:人在灾难面前是渺小的。诗人的发声或许出于很多无奈,但这可能是对自我负责与认可的一种选择,毕竟在灾难面前人人都有抒情和表达的权利。
对于诗人来说,直面现实,通过写诗表达自我对生活、对社会独到的认识,是他们该有的职责,毕竟诗人也是时代的见证者,有责任直面现实,将自己置身其间,去审视和挖掘每个事态背后的真正缘由,而不是人云亦云逐大流。诗人吉小吉笔下描写了许多徘徊在时代边缘,游走于社会底层,抑或被生活所逼迫身不由己、奔波流离的个体形象,这些个体身上凝聚的是吉小吉作为诗人的情怀。在他笔下,这些“小我”完成了从个体生命到精神向度的转变,不停地诗歌的书写过程,也是诗人对自我内心拷问和救赎的过程。那些冷冰冰立足于土地的生命正是在诗人的笔下有了温度和依托,或许这正是诗人的力量和诗人该有的姿态。
文艺对于社会的作用或许不能同硬科技作比较,但对人类心灵的震撼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与建构可能又是硬科技不能比拟的。从近现代诗学史来看,诗歌已成为“匹夫有责”在文人领域的最强回声。用文字将个人与时代、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毕竟“诗人不应简单地做一个歌手去颂赞光明,而更应该做一个光明的生产者,做一个带来信任、信念、可能性与希望的人”[15]。当然,诗歌同新闻报道、政治宣传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诗人最重要的还是努力提高自己写诗的水平,用诗歌的价值来践行诗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如果只是为了追求时效性,为写而写,一般提供不了任何新鲜有益的内容,反而成了陈词滥调的重复或标语口号的堆砌,给诗歌带来污名化的形象。
诗歌对于吉小吉来说还有储藏记忆的作用。如诗歌《影子》即是诗人对饥饿的一种记忆性叙述:“母亲点亮的煤油灯让我/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影子/它摇曳在黑黄色的泥土墙上/后来我发现它一直跟着我/饥饿也一直跟着我/它跟着我抢两条红薯/……我就努力想把影子丢掉/但我一直没有成功……”“影子”是一种眷念过去的情怀,不仅丢不掉,随着年岁的增长还会越来越重,“它跟着我进城/它跟着我走过大街小巷/它跟着我哭泣,或者摇头晃脑地笑/……影子常常一动不动地陪着我,陪着我到天亮”。组诗《天南地北》如同诗人自己的行吟日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主要是记录当下情绪。诗歌对于诗人自身来说,还具有一种记录反思的作用。
诗歌不仅面向诗人自己,还能面向社会,反映现实。《在镇上遥望老家》,“……兄弟姐妹们都去了城里/他们在坚硬的机床前/一定把鸟鸣、童年、老家/统统塞进了思念里/一定把思念塞满生活……/今天,我回到镇上遥望老家/村庄还在半山腰上/山路还像一根绳子吊着它/像吊着一个/鸟儿早已东南飞的/巨大的空巢/也许,空巢注定就是/村庄的命运/”借诗歌之名为“村庄”哭喊。空巢的村落已成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普遍现象,青年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膨胀和乡村的空寂之间存在诸多张力,同时为诗人提供了想象与反思的空间。借用文字将抽象不可言说的事物陈列于诗行之中,诗人的情绪在里面,诗歌的作用也在里面。当然并非要用是否具有功用性去评价诗歌,但诗人的自觉性让诗歌不得不具有相应的社会性。
吉小吉的诗更多是向外部世界发散的,触及底层和弱势群体。他写被社会欺压、走投无路的妇女,如《九姑》,“后来,三叔告诉我/只有大河相信九姑的话,并且收留了她……”。所有情感都在几句简单的陈述句中,一串省略号不仅仅是未说完的话,更像是诗人无法说出口的叹息。他同情底层人物,如《三妹》,“虽然大家都没有看到三妹掉眼泪/但我知道,她的泪/其实比旮旯河里的流水还多”。他的诗取材日常生活,接地气的同时对现实进行冷静的思考,对诗人来说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四、余论
吉小吉的诗歌大都以“我”作为抒情主体,以自己的内心感受触及外在事物,这样的感情有真挚细腻之处,但总沉溺于抒发自我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一首好的诗歌并非仅包含诗人自己的小心思,它需要与外界有共通感,表达形而上的思想,若仅局限于自我,诗歌容易成为负面情绪的发泄物或者高扬口号的工具。这并非是混淆文学应具有的功用性,恰是希望诗歌文本尽量从“小我”的圆形闭合中跳出来,以物及物,将情感的沸点上升到一个稳定的值。毕竟世间可写之物甚多,附着其上的情感若不加以节制,只会泛滥成灾。
在吉小吉的诗中,他将人生经历作为写诗的素材,将对生命的感悟作为情绪的基点,密切联系现实。但现实和诗歌之间的关系不能太狭隘,毕竟诗歌是一门情感的艺术,除了外在的现实,也不能忽略内在的现实。一个诗人,如果只注重描述外在,而没有融入自己内心的深度体验,很难创作出动人的诗篇。
总的来说,诗人吉小吉的诗歌是动人的,有着细腻的情感以及诸多熟悉的意象。正因为他对诗歌追求的这种极致,很容易让自己的诗歌写作进入思想的囹圄,甚或无法触及、开掘更多的诗歌素材。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家乡和亲人是自己的诗写源泉,这样的诗歌会让读者更感亲切、引起共鸣,但一直在这样的意象或素材中进行创作并不是最完美的状态。好的诗没有物与我的分别,是主观客观的联合,凡是作诗都和一种情绪、一份情感结合在一起,所以作诗要顺着动机迅速自然地写出来,万不可因为知识或习惯上的成见占据自我认识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