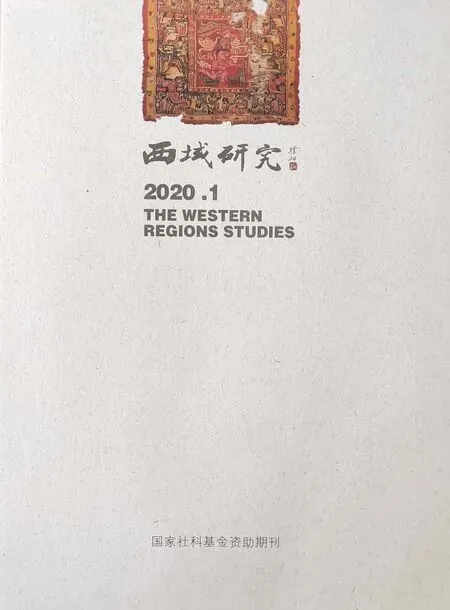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①
殷盼盼
内容提要: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麹氏高昌国麹伯雅统治时期的公元614年十一月十九日前不久,(1)“义和政变”发生的时间学界尚存分歧,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76~379页)对诸家观点进行了详细评论,提出614年十一月十九日前不久之说,颇为可信。高昌国发生“义和政变”,国王麹伯雅逃亡西突厥避难,政变集团暂时取得胜利。然政变集团的构成,至今为止仍然扑朔迷离,未有定论。吐鲁番文书义和五年(618)和伯姬写《法华经》题记中,和氏称“夫人”以及“愿国祚永隆”的祈愿词,说明和伯姬与政变集团关系密切,是政变集团首脑的夫人。(2)孟宪实、姚崇新最早将义和五年(618)和伯姬写《法华经》题记用于“义和政变”集团研究,推测和伯姬为“义和政变”的重要支持者,且以命妇制为依据,认为和伯姬为“义和政变”首脑的夫人,同时对高昌义和以前和氏人物的任职情况进行了介绍,怀疑和氏家族与“义和政变”有关(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页,写经的出处见此文184页注释﹝8﹞。该文后收入孟宪实著:《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277~280页)。王素进一步指出政变的首脑出自高昌王族麹氏,说明和氏与王族麹氏有姻亲关系(王素:《高昌国史稿·统治编》,第380~382页)。《麹建泰墓志》公布后,王素据之认为麹建泰家族为“义和政变”的领导家族,是与王族麹嘉同宗异支的另一支西平亭麹氏(王素:《唐麹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7~164页)。虽然姜伯勤认为和氏是高昌国的门阀之一,(3)姜伯勤:《高昌世族制度的衰落与社会变迁——吐鲁番出土高昌麹氏王朝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2页。但是有关高昌和氏的材料却支零破碎,孟宪实、姚崇新二氏在其论文中即称“高昌这支和氏的来源没有特别的资料说明,就和氏在高昌的政治地位,也只有一些蛛丝马迹。……但和氏这些资料皆见于义和以前,而义和以后特别少见”。(4)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第166页。由于和氏与“义和政变”关系密切,对其研究有利于增加我们对“义和政变”的认知,因此对其来源进行追索,利用已有资料勾稽其在高昌国的发展状况仍然十分必要。
一 汉到前凉间的河西和氏
尽管吐鲁番所出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和氏的来源,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古高昌国的世家大族多从河陇地区迁入的事实,那么探讨高昌和氏来源,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高昌一隅,而是要向吐鲁番以东的河西地区延伸。通过对传世典籍及河西出土汉简资料的搜罗,我们梳理出一条和氏在河西地区发展状况的大致线索。
河西地区自上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的汉简,为我们探讨汉代河西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我们在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肩水金关出土汉简中发现了两枚记有和氏人物的汉简,是和氏在西汉时期已经定居河西的可靠证明,它们分别是:
(1)73EJT30:10号汉简:氐池敬老里和焉息年廿三。(5)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叁·下),中西书局,2013年,第104页。
(2)73EJT30:152号汉简:氐池敬老里和铁柱年廿五。(6)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叁·下),第116页。
二简具体年代不详,大体属于西汉后期。(7)黄艳萍:《〈肩水金关汉简〉(叁)纪年简校考》(《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指出《肩水金关汉简(叁)》所收的纪年简,时间在汉昭帝元凤二年到汉平帝元始五年之间。“氐池敬老里”表示和焉息与和铁柱的籍贯,氐池为汉代河西张掖郡辖县,(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3页。由此可证在张掖氐池县西汉时就有和氏人物居住。
东汉末年中原内乱,豪强势力并起,相互斗争不断。河西各地豪强也乘势兴起,控制当地社会,仓慈于太和年间(227~233年)出任敦煌太守时,敦煌“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9)《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512页。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情势与敦煌相当,《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记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
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祕又杀鸾。(10)《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第474页。
颜俊、和鸾、黄华、麹演四人名字前均被冠以郡名,唐长孺指出“魏晋以来惯例往往在姓名前加上郡名,……称某郡某人不仅表示他的籍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里,更重要的是表示他的门阀,标识着他是特定的某个郡的某姓,而不是泛泛的某郡人,而这个特定郡的某姓一定是当郡大姓”。(11)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第342页。肩水金关汉简的记载已经揭示出有和氏人物定居在张掖氐池县,《张既传》不仅进一步说明张掖有和氏定居,而且说明西汉以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东汉末时和氏已经成为张掖豪强。在武威颜俊与张掖和鸾的对峙中,和鸾占据优势,武威颜俊遣其母及子到曹操处为质,希望得到曹操的帮助,但曹操采纳张既的意见坐山观虎斗,颜俊终被和鸾杀害。
西晋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保据河西,开启前凉政权。张轨家族统治河西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联合河西当地大族豪强,和氏也在张轨家族拉拢联合的对象之中,在前凉政权中多以武将的身份出现。前凉建兴六年(318)焦崧、陈安进攻陇右上邽(今天水),与刘曜相抗,致使雍、秦之人死者十之八九,镇守上邽的原西晋南阳王司马保遣使告急于张寔,张寔遂派兵相助:
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威远将军宋毅及和苞、张阆、宋辑、辛韬、张选、董广步骑二万赴之。(12)《晋书》卷八六《张寔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9页。
张骏统治时期,又有和驎为前凉武将,《晋书·康帝纪》载建元二年(344)春正月:
张骏遣其将和驎、谢艾讨南羌于阗和,大破之。(13)《晋书》卷七《康帝纪》,第186页。
前凉建兴四十一年(353)张祚废掉自己的侄子张耀灵,僭位前凉君主,并于次年(354)废晋建兴年号,改元和平。随即:
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14)《晋书》卷八六《张祚传》,第2247页。
和苞、和驎、和昊均不具郡望籍贯,但三者均为武将,与为乱河西的武装势力张掖和鸾具有共同的品质,应同出于张掖地区的和氏家族。
二 出土文献所见高昌和氏人物及其来源试析
以上材料虽然零碎,但足以说明到前凉时期,和氏已经成为张掖豪强。但颇值注意的是,前凉之后和氏在河西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传世典籍再未出现相关记载。在时代稍后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了诸多和氏人物,前人制作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索引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15)李方,王素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石墨林编:《三种新出版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8~252页;石墨林编:《〈大谷文书集成〉(壹)人名地名索引——附录与其他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九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2年,第232~268页;石墨林编:《〈大谷文书集成〉(贰)人名地名索引——附录与其他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3年,第284~207页;石墨林编:《〈大谷文书集成〉(叁)人名地名索引——附录与其他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二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5年,第236~253页;“《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人名索引”,载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附录第3~21页;石墨林编:《〈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大谷文书集成·肆〉人名地名索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八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2年,第303~308页。兹据诸家人名索引制作吐鲁番和氏人物统计表如下(表一):

表一 吐鲁番和氏人物表
注:1.表中的T表示四册图版本《吐鲁番出土文书》,T后的数字表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的册数;D表示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D后的数字表示《大谷文书集成》的册数;X表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册);XY表示《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砖志表示《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吴、胡表示《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16)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93~107页。。2.斜线后的数字表示人名所在的具体页码。
除了大量的和氏人物外,一个颇值注意的现象是在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发现了和虎威寺、(17)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16页。和郎中寺、和子落寺。(1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95、96、262页。虎威是高昌国虎威将军的简写,郎中也是高昌国的官职。虎威寺是以和氏某位任虎威将军者的称呼命名的寺院,和郎中寺是以和氏某位任郎中者的称呼命名的寺院;和子落寺则直接以和氏人物的姓名命名。在高昌国中,这种以个人姓名或称呼命名的寺院具有家庙性质,(19)严耀中:《麹氏高昌王国寺院研究》,《文史》第三十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132~133页。拥有这种寺院的往往是高昌国的大姓。
吐鲁番出土砖志为我们探讨高昌和氏与张掖和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雅尔湖古墓群出土《高昌延昌九年(569)袁穆寅妻和氏墓表》显示和氏与袁氏结姻。(20)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第109~110页。雅尔湖古墓群出土的《高昌建昌二年(556)任叔达妻袁氏墓表》记任叔达妻为“张掖袁氏”;(21)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0页。《高昌延昌元年(561)任氏及夫人袁氏墓表》又记“夫人张掖袁氏”;(22)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75页。然雅儿湖古墓群出土的《高昌延昌卅三年(593)卫孝恭妻袁氏墓表》记卫孝恭妻为“源州武威袁氏”。(23)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215页。武威为凉州辖境,且当时并无源州之设,“源”字应为“凉”字形近之误。前两方袁氏相关墓表的时代较最后一方早三四十年左右,记载应更为准确,袁氏应为从张掖迁入交河的河西大族。宋晓梅曾指出敦煌移民集团迁移到高昌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敦煌地域集团婚姻,(24)宋晓梅:《麹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51~152页。这提示我们高昌大姓之间的婚姻可能存在一种地域集团性。这里我们判断和氏的姻亲家族袁氏出自张掖,如果再结合张掖和氏的相关情况,那么推断高昌和氏来自张掖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董永强曾对吐鲁番文书所见人物的姓氏进行过全面统计,并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三个时期分析吐鲁番的姓氏构成和不同时期新出现的姓氏,和氏被划分在高昌国时期(442~640年)吐鲁番新增的汉姓。(25)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胡姓与民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页。以442年来划分显然是以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建立大凉政权为节点的,可备一说。另外,笔者注意到前文提及的和鸾、和苞、和驎、和昊等,均活动于前凉灭亡以前,前凉之后正史资料不见有和氏人物在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政权中活动,这说明很可能在前凉之后和氏人物已从张掖迁出。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在苻坚将领苟苌、毛当、梁熙、姚苌的进攻下,张天锡投降前秦。受前秦大军侵扰的影响,河西地区陷入纷争之中,《张礼臣墓志》叙述其家族西迁的历程时即称:“属苻坚肆虐,挻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地。”(26)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11页。为了保全家族,前凉末期河西地区的许多大姓家族向西迁入高昌,和氏很有可能在此移民浪潮中西迁高昌。
三 和氏在高昌国的婚宦
和氏与“义和政变”关系密切,前人从婚姻和仕宦两方面曾对这种关系进行过探索。就婚姻关系而言,关注点集中于义和五年(618)和伯姬写《法华经》题记反映的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的关系,但忽视了其他和氏人物的婚姻资料,故未能揭示和氏婚姻关系的地域集团性;就仕宦而言,一方面资料的搜集上可作进一步的补充,另一方面在某些资料的解读上尚留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一)和氏的婚姻
关于和氏婚姻的资料十分稀少,交河地区出土和氏女性墓志两方,是目前仅见的明确反映高昌国和氏人物婚姻状况的资料,分别是:
1.《高昌延昌九年(569)袁穆寅妻和氏墓表》
延昌九年己丑岁,十一月丙戌朔,卅日乙卯。袁穆寅妻和氏之墓表。(27)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109~110页。
2.《高昌延昌廿一年(581)氾神武妻和氏墓表》

墓表内容简略,但显示出和氏的配偶分别有袁氏与氾氏,二者均为吐鲁番地区的汉姓家族。氾氏原为敦煌大族,(29)冯培红,孔令梅:《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中)》,《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第62~63页。袁氏来自张掖。上文所引三方袁氏相关墓表又显示与袁氏结亲的有卫氏、任氏家族。其中卫氏为西平大族。任氏则很可能来自天水,天水任氏在十六国时期较为活跃,成汉李雄王后任氏即来自天水,《十六国春秋》记“雄妻任氏天水人,仆射任颜之姊也”,(30)〔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九《蜀录四·任氏》,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湖北官书局重刊本,第6页。在成汉政权中有多位任氏人物居于要位,《古今姓氏书辩证》还提到后秦天水任谦。(31)〔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一九“任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可见,与和氏有直接或间接婚姻关系的家族,多来自河陇,且均为地方大姓家族。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含有义和五年(618)和伯姬写《法华经》题记一则,吴织、胡群耘将“义和”判断为北凉年号,但指出北凉义和戊寅岁应为“义和八年”。池田温将其系于麹氏高昌国义和五年,为学界所信从。(3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第178页。题记内容为:
义和五年(618)戊寅岁十月十一日,清信女夫人和氏伯姬,稽首归命常住三宝。闻一谛幽昧显自九经之文,三空渊旨,彰于十二之说。弟子仰维斯趣,敬写《法华经》一部,冀金教永传于千载,玉瓮不朽于万祀,謶以斯福,仰愿国祚永隆,本枝万叶,愿过去先灵,面圣餐音。现在亲姻缘眷属,恒履休和,未来见佛,普共有识,同沾斯润。(33)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98页。
题记一方面使用了义和年号,另一方面又有“愿国祚永隆”的祈愿词,反映和氏是政变集团的支持者。尤为重要的是和伯姬自称夫人,《礼记·曲礼》记,“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34)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44页。加之和伯姬写经题记的祈愿词与麹氏王室人物所作《麹斌芝造寺施入记》中的祈愿词有相同之处,故孟宪实、姚崇新认为和氏为“义和政变”集团首脑之妻。(35)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第166页。王素指出政变集团以麹氏王室人物为领导,即认为和伯姬为王族麹氏人物之妻。(36)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80~382页。《麹建泰墓志》公布后,王素据之认为麹建泰家族为“义和政变”的领导家族,出自与王族麹嘉一支(西平亭麹氏发展形成的金城麹氏)同宗的另一支西平亭麹氏,即西平亭麹氏在东汉末分化成的西平麹氏。(37)王素:《唐麹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唐代西域史事考释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第149~152页。如果王素的推测无误,那么就可以认为和氏与高昌国的西平麹氏有姻亲关系。侯灿指出高昌国:
就其本体来说,则是一个地方豪族控制的以联姻为基础的封建割据王国。在这个王国中除了国王外,第一等级的官职令尹,只能由王家一族的世子所独占。第二、第三等级的高级官职除麹氏一族外,也只有世代与之联姻的张氏家族所拥有。第四、第五等级的官职,也为屈指可数的高门望族所拥据占,如高、氾、马、阴、焦、史、辛、孟等家族。而这些家族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与麹、张两家有姻亲关系的。如《麹斌造寺碑》碑额所书,与麹斌一家联姻的有高、使(史)、孟、辛家族。通过这些联姻的家族,便构成了一个以麹氏家族为首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集团。(38)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原载《文史》第22辑,1984年,第74页,后收入氏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侯灿的这一结论是在没有对高昌麹氏详细区分金城与西平二望的基础上提出的,(39)高昌国麹氏家族是否有明确的金城与西平二郡望之分,学界意见不一。王素在《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第15~29页)中认为高昌麹氏存在金城郡麹氏、西平郡麹氏之分,并且指出西平麹氏在高昌国的政治地位与王族金城麹氏存在明显差距,西平麹氏甚至政治地位不及高昌张雄家族。在《唐麹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第149~152页)一文中,王素认为东汉末年以后形成的金城、西平麹氏二望实际上均由西平亭麹氏发展而来,是西平亭麹氏的不同支系,魏晋以后金城郡麹氏和西平郡麹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西平郡麹氏具有明显的反叛性格,在高昌国中西平郡麹氏也与金城郡麹氏不同;王素关于麹氏有金城与西平二郡望之分的观点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施新荣的《也谈高昌麹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第53~63页)一文,在本文中施新荣认为高昌国的麹氏只有金城郡一望。根据下文,和氏人物的官职主要集中在四等及其以下,由此我们可以对和氏在高昌国的势力做一大致的判断。
在高昌国,敦煌移民集团势力强大,且如宋晓梅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保持了敦煌内部的地域集团婚姻。(40)宋晓梅:《麹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51~152页。通过对和氏婚姻的分析,我们看到和氏不仅保持着与张掖大族的婚姻关系,而且从更为广阔的地域层面分析,大多是与敦煌以外的河陇移民保持着直接与间接的婚姻。虽然氾氏源出敦煌移民集团,但高昌氾氏势力并不显赫,(41)王晶:《中古家族三调:唐帝国边境城镇的三个家族》,兰州大学敦煌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第14页。这很可能预示着敦煌移民集团与其他河陇移民集团在身份地位上的某种区分。
(二)和氏的仕宦
孟宪实从任官的角度分析和氏与“义和政变”的关系,检出建昌元年(555)和长史、(42)〔日〕池田温著;谢重光译:《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第152页。延昌十七年(577)和氏县令、(4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第170页。延昌二十七年通事令史和乐、(4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第339、342、343页。义和二年(615)和氏长史、(4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第91、92、93、96页。和氏侍郎与屯田主簿和住儿,(4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第388页。以及和郎中等人(47)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第95、96页。。其中和氏县令见于《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64TAM24:34),记作“和令”,“令”系人名或官职尚难判断,姑置不论。除以上诸人外,笔者亦检出十条高昌国时期任有官职的和氏人物,为便于讨论,先将高昌国时期带有官职的和氏人物统计如下(表二):

表二 和氏人物任官表
续表二

时间姓名官职出处622年、624年和住儿参军高昌重光三年张憙儿入俗租粟条记(T1/423);高昌延寿元年十二月张憙儿入俗租粟条记(T1/424)630年及其前后①和洛参军高昌张明憙入延寿七年七月剂刺薪条记(T2/264);高昌延寿七年十二月张明憙入十月剂刺薪条记(T2/265);高昌张明憙入剂刺薪残条记(T2/269);高昌张明憙入物残条记(T2/269);高昌某人入剂刺薪残条记(T2/269)632年前后②和某某通事令史高昌出用、杂除、对额役使车牛残奏(XY/72)高昌国后期③和某某参军高昌付张团儿等银钱帐(XY/73)高昌国后期④和子侍郎高昌国官厅文书断片(D1/65)①②③④《高昌张明憙入剂刺薪残条记》《高昌张明憙入物残条记》《高昌某人入剂刺薪残条记》未见纪年,时代应与同墓出土文书《高昌张明憙入延寿七年(630)七月剂刺薪条记》相近。文书纪年残缺,柳洪亮判断在632年前后,可信从。纪年亦缺,然文书中的高欢岳见于《唐焦延隆等居宅间架簿》,史元善又见于《高昌史延高作人阿欢等名籍》、《高昌诸臣条列得破被氈、破褐囊、绝便索、绝胡麻索头数奏》,康善财又见于《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说明文书的时代大概在高昌国后期。文书残损严重,第一行有“麹郎”二字,吐鲁番文书中“麹郎”广泛出现在高昌国后期,如《高昌诸臣条列得破被氈、破褐囊、绝便索、绝胡麻索头数奏》中的麹郎伯住(TI/430)、《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氾某等传供食帐》中的麹郎阿住(TI/377),以及《高昌将显守等田亩得银钱帐》中的麹郎文玉等(T2/42)。其中麹伯住所在文书的时间上文已有论及,可能在高昌国后期。《高昌将显守等田亩得银钱帐》未见纪年,但同墓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一年(634)主客残奏》(T2/39)、《唐贞观十四年(640)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T2/43),其余无纪年文书也多为唐西州时期,因此麹郎文玉所处的时代也应在麹氏高昌国后期。由此可知,大谷1467《高昌国官厅文书断片》的时代也应在高昌国后期。
注:1.表中T1、T2、D1、X、XY、砖志的含义与表一相同,“三碑”表示池田温著、谢重光译《高昌三碑略考》。2.斜线后的数字表示人物所在的具体页码。3.和都子“殿中中郎将”用斜体表示追赠官,与生前官职区别。
据上表,目前所见最早的和氏官员为《高昌新兴令麹斌芝造寺施入记》碑尾的和长史,侯灿认为和长史是高昌王都令尹府的长史,属高昌国第四等级官职。(48)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第43页。王素则从嶋崎昌之说,(49)〔日〕嶋崎昌:《麹氏高昌官制考》,《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上、下),第28、33号,1963年,第75~93页、50~74页;后收入氏著:《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53~310页。认为长史是高昌王府的属官,是高昌国执行机构中诸部的主事长官,在其之上有诸部郎中、高昌令尹和绾曹郎中,级别相当高,在《施入记》写就之时和长史没有差遣职务在身。(50)王素:《麹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文物》1989年第11期,第48~49页。高昌国的校郎有门下校郎和中兵校郎之别,门下校郎是高昌国出纳审查机构的长官,受高昌国王直接领导,中兵校郎掌武备,是高昌国中兵系统的长官,二者级别相同。(51)王素:《麹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文物》1989年第11期,第42~44页。通事令史为高昌国门下机构官员,级别不高,侯灿将其比定为高昌国第六等级官员,(52)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载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第54页。和氏担任通事令史一职者共有四位,其中三位在麹乾固统治的577年到587年前后,另有一位在632年前后。592年以前麹乾固统治时期,还有和都子新除虎牙将军,死后追赠殿中中郎将,(53)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211~212页。虎牙将军属于高昌第八等级的戎号将军,(54)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第48页。与通事令史相比,虎牙将军级别更低,然和都子卒后被追赠以第六等级的殿中中郎将,以表示对他的尊崇,似乎说明他和高昌王室关系不一般。和都子之后,直到“义和政变”发生以前,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和氏人物在高昌国中担任较高官职的记载。
隋大业五年(609)到大业八年(612)期间,(55)麹伯雅使隋并非一次就去了四年,实际上他在大业六年(610)三月二日前返回高昌国,后又于大业七年(611)五月四日之后入隋,麹文泰则从大业五年(609)入朝到大业八年(612)十二月归朝,一次性在隋朝停留了四年。详见王素:《麹氏高昌“义和政变”补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185页;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59~365页。高昌王麹伯雅和世子麹文泰曾长期在隋朝停留,国政委于国内大臣。大业八年麹伯雅父子归朝后推行变服改革,随即激起了一场政变,因发动政变的集团以“义和”纪年,所以学界称此次政变为“义和政变”。“义和政变”期间涌现出了多位和氏人物,《高昌义和二年(615)七月马帐》与年代相近的《高昌某年卫延绍等马帐》《高昌某年郡上马帐》《高昌买驮、入练、远行马、郡上马等人名籍》中均出现了和长史的记载。在《高昌买驮、入练、远行马、郡上马等人名籍》和同墓出土文书《高昌合计马额帐》中还出现了和郎中寺的记载,(5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第95、96页。两件文书的纪年均残,王素判断应在义和二年(615)七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前后,较为可取。(57)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43~244页。郎中是高昌国诸部的名誉长官,位尊权显,一般不实际授予,其相关职务主要是差遣王府长史负责,但被任为郎中无疑昭示着一种很高的尊崇。义和年间(614~620年)还出现侍郎和某与屯田主簿和住儿二人,侍郎属于高昌王府的属吏,是高昌国王的近侍之臣。和氏出任侍郎之职者共二人,另一人和子出现在高昌国后期,与义和年间的侍郎和某是否同一人尚不好判断。屯田主簿隶属高昌国屯田部,在侯灿所列高昌国官职等级序列中属第七等。
孟宪实、姚崇新论述“义和政变”时提出和氏任官的资料多见于“义和政变”以前,“义和政变”以后极为少见,(58)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第163~188页。说明在“重光复辟”以后和氏的势力的确再次下滑,但也不是无迹可寻,尤其是我们还看到了部分人物的官职升迁信息。《高昌义和三年(616)屯田条列得水讁麦斛斗奏行文书》(5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第388页。中和住儿的官职是屯田主簿,为高昌国中央的第七等级官。和住儿又见于《高昌重光三年(622)张憙儿入俗租粟条记》及《高昌延寿元年(624)十二月张憙儿入俗租粟条记》两件文书,(6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第423、424页。在这两件文书中,和住儿的官职为参军,为高昌国中央第六等级官。虽然和住儿任屯田主簿的时间,以及由屯田主簿迁为参军的时间不明,但义和三年与重光三年相差仅七年,且这一段时间内“义和政变”集团倒台,麹伯雅经过重光复辟重新掌握政权。如果和住儿的官职升迁发生在复辟前,则说明麹伯雅对于政变集团所提拔的和氏人物并没有降职或贬黜;如果和住儿的官职迁转发生在重光复辟以后,则说明重光复辟并没有影响到和住儿的仕途升迁。阿斯塔那116号墓出土文书《高昌残名籍》中有和子洛的记载,(6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本),第373页。但此名籍年代不详,根据文书整理者介绍,此名籍拆自重光二年(621)入葬的张弘震的纸帽,故此名籍的年代当在重光二年以前。《高昌残名籍》中没有和子洛具有特殊身份的记载,此时很可能是白丁或是级别很低的官吏。在阿斯塔那92号墓出土的《高昌某岁诸寺官绢捎本》中我们又发现了和子落寺的记载,同墓出土文书均从阳保救之妻张氏身上拆出,且此墓出有《高昌延寿十六年(639)阳保救妻张氏墓志》,说明《高昌某岁诸寺官绢捎本》的时代当在高昌延寿十六年以前。(62)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第255、261~262页。另外在阿斯塔那507号墓出土的《高昌张明憙入延寿七年(630)七月剂刺薪条记》等延寿年间的文书中又有参军和洛的记载。(6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图文本),第264、265、269页。和子洛、和子落寺、参军和洛出现在同一时代,颇疑和子洛即为和洛,和子落寺是和洛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寺院。此外,高昌国后期文书《高昌付张团儿等银钱帐》中也有位和氏人物任参军。(64)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第73页。
最后,在唐西州时期的文书《唐西州高昌县和义方等差科簿》中我们发现有和义方为唐西州的府史,和义方之子和思让为唐西州高昌县常平仓史,(6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二者均为高昌县的胥吏,差科簿均将其归为白丁,谈不上有什么家族势力,只是府史和常平仓史的职任暗示二人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可能与其曾为高昌国的重要家族有关。与之相似的还有《唐神龙二年(706)七月西州史某牒为长安三年(703)七月至十二月军粮破除、见在事》(66)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25页。中的和让任唐西州的典,亦为低级胥吏。
结语
西汉时期就有一支和氏人物生活在张掖氐池,经历两汉的发展,东汉末年时其势力增强,成为河西地区的豪强势力。前凉时期和氏人物以武将身份活跃于河西,高昌和氏很可能源出于此。和氏从张掖西迁高昌的具体时间点尚不确定,前凉末苻秦发兵进攻河西所导致的战乱,或北魏攻灭北凉的战役均有可能是其西迁的主要动因。
西迁到高昌的和氏仍然保持着与同郡大族袁氏的婚姻,使其与河陇地区的卫氏、袁氏、西平亭麹氏等大族联系紧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可能正是这种地域集团婚姻关系。从仕宦的角度看,和氏人物担任的官职主要是出纳审查机构的校郎和通事令史,以及高昌王府的长史、主簿、参军、侍郎之职,显示其与麹氏高昌国王室的关系较好,但是政治地位一般。和氏人物官职最高者为郎中,最晚出现于高昌义和二年前后,但是否因为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关系密切尚不确定。和住儿的官职从义和年间到重光年间的变化,以及和氏人物在“义和政变”以后的任职情况并不能证明和氏人物深度参与了“义和政变”。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平定高昌国后建立了唐西州,和氏在麹氏高昌国时期的政治特权丧失,沦为一般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