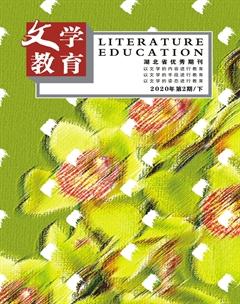唐诗《江雪》在英语世界中的翻译与变异
张大立
内容摘要:《江雪》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经典的诗作。目前已有十余位中外著名学者对《江雪》进行了翻译。本文通过三位英语世界学者的《江雪》译作,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分析《江雪》在英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江雪》 译介 变异 语言文化
《江雪》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经典的诗作。在中国,这首诗被选入国内小学课本和许多对外汉语教材之中,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随着各民族、各国家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江雪》也被众多外国学者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成为了民族间语言与文化交流的载体。本文将通过分析《江雪》在英语世界的三个译本,考察在《江雪》在译介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在考察三个译本之前,我们不妨先对柳宗元的原作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本诗为五言绝句。每句五字,节奏为2-2-1。第一、二、四三句入韵。这是五言绝句的一般形式。应该说,唐诗的这种整齐和谐的特殊形式正是基于古汉语多以单音节字表意的特点才得以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全诗押入声韵,不入韵的第三句尾字“翁”则为平声。通读全诗后,我们不难发现,短促的入声韵正与整首诗苍凉凄寒的氛围相称,取得了“音渲”的效果。而第三句的“翁”字则以响亮长阔的平声将一片荒寒死寂之中渔翁傲然独钓的高大形象凸显出来,也为全诗平添了几分苍劲。应该说,在这首诗中古汉语语音声调的特点与全诗的内容意境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极大的艺术张力。
其次,从内容上来说,全诗首颔两联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用寥寥数笔描绘出一个荒寒死寂,人兽绝迹的广阔天地。颈尾两联则进行近景的书写,将镜头从广阔的天地间聚焦于一舟一人之上。渔翁身披蓑笠,临寒独钓,既多隐逸者的远致,复有孤傲者的坚韧。天地的荒寒广阔与渔翁的渺小坚毅互为映衬,人愈小则天地愈广,天地愈广阔荒寒则渔翁愈坚毅高大。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这首诗的情感主旨。唐永贞元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在保守势力和宦官的反对下,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柳宗元本人被贬永州。这首诗正是柳宗元在被贬永州后不久所写,它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诗人在严酷凄凉的处境下消极心境的表达,也有其傲岸不屈的人格的彰显,多少也还蕴含着些姜太公渭水独钓而不遇文王的怅然。所以,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其所蕴含的语言、文化内涵却是广阔而深厚的。应该说。这正是它历经千载而流传不衰的原因,但同时也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提出了挑战。下面,我们就《江雪》在英语世界中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一是19世纪美国诗人Witter Bynner的译文1(以下称译文1),二是美国著名诗人、汉学家Gary Snyder的译文2(以下称译文2)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Burton Watson(文殊)的译文3(以下称译文3):
《江雪》的首颔两联描绘出一派空阔荒寒的景象,在翻译过程中,千、万、绝、灭这些词语是最大的难点,亦最考验译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千和万在诗中均非实指,而只是用极大的数量来虚写空间的广大。中国自古便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观念,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则要“立象以尽意”,这正是中国式的“无中生有”的言说方式。这与西方对于语言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在言说方式和话语规则上的根本差异造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困难,也给译者的翻译提出了莫大的挑战。在翻译“千山”、“万径”一类词语的过程中,优秀的译者应当尽量遵循这一言说路径,由“立象”而臻于“尽意”。以这样的标准考察三个版本的译文我们发现,译文1用更符合英语计数方式的a hundred和a thousand 代替了汉语的“千”和“万”,不拘泥于对千、万的直译,正确地理解了千、万的虚写意义。但细读之下,a hundred所延展出的意境空间似乎比“千”、“万”逊色不少。译文2则适度突破了英语语法的限制,用these thousand peaks和alll the trails,对原作进行了意译,笔者以为“these thousand peaks”的翻译方式既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又用违背英语语法的翻译方式实现了翻译过程中的“陌生化”,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原诗荒寒的闊大的意境。但all the trails的翻译虽然正确地理解了原诗的意义,但由于省略了从无到有,从立象到尽意的过程,所以略显直露而少韵味.不过若将该译文的首颔两联合而观之,则仍不失为一种上佳的译文。译文3出于忠实于原文的考虑采用a thousand和ten thousand的译法则中规中矩,是相对稳妥的一种翻译方式。
而在“鸟飞绝”、“人踪灭”两个短语的翻译上,三位译者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译文1着重烘托了“无鸟”和“无足迹”的环境,译文2则认为之所以无鸟是因为鸟被群山所阻隔,译文3则突出鸟和人迹消灭、消失的事实。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译文3的翻译方式。揣摩原诗的意境,柳宗元想要强调的并非群山本无鸟和人迹的事实,而是在大雪封山的情况下,原有的鸟与人都尽皆“绝”、“灭”,从而渲染荒寒死寂的环境,以此凸显后文渔翁的形象。在三个译本之中,译文1更偏重于前者,译文2对于“千山鸟飞绝”的理解显然出现了偏差,而译文三则相对接近诗作的原意。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对译文1和译文3进行进一步的对比。笔者以为,译文1中的“no”类似于中国“无”的概念,突出了诗作整体意境空、寂、静的特点,而译文3表面上看突出着环境的荒寒死寂,而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则以特征鲜明的环境昭示着作者主观人格和强烈情感的介入。译文1更像盛唐诗人王维那种“静观”式的山水诗,它的话语方式与初盛唐时期在北宗禅宗影响下产生的山水诗似更为契合。静观默照的北宗在开元、天宝间红极一时,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南宗在至德以后宗风大盛,而诗人的主体人格也随着南宗的大盛而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了诗歌的书写之中,在总体上形成了与初盛唐时期的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再结合前述《江雪》的写作背景,我们就更能理解这首诗实在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杰作了。因此,译文1与译文3的翻译方式在更深的层次上暗示着唐诗的两种话语方式也即意境的建构方式,作为英语世界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很难真正理解二者深层次的差异,也就难免会使译文相较于原诗发生变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变异也为诗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意境,为读者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自有其特别的益处。但从忠实原文的角度而言,译文3的翻译正是所谓“信有格哉”的一种,相较于其它译本无疑是更胜一筹的。
在翻译颈联中“孤舟”这一意象时,译文1将“孤舟”译为a little boat,隐去了“孤”的意涵而突出了舟之“小”。作为本国读者,当我们想象《江雪》一诗的意境时,会很自然地明白此处的“孤舟”必然不是楼船巨舰,而一定是小棹扁舟。惟其如此,“孤舟”才能和前两联的广大景象形成对比,收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也才能表现出作者孤傲的人格与飘忽的行踪。在这一点上译者的理解并无错误,且译出了诗作的言外之意。但与此同时,译者隐去了原作中“孤”的意涵却是极不妥当的。所谓“孤”者,强调的是大雪凌厉之际唯有渔翁的一叶扁舟凌寒独钓,是通过“孤”这一带有排他意味的词语凸显渔翁之独立不俗。倘若江面之上并非“孤”舟独钓,而为百舸争流,则不但原诗的意境全无,对于作者的主体人格与心性更是一种忽视。中国自古便有“诗言志”的文学传统,在诗作的意象、意境背后往往是主体人格的支撑与彰显。所以有一定文学阅读经验的本国读者在阅读分析诗歌时都特别注意从“披文入情”、“以意逆志”的路径入手进行分析。但作为英语世界的翻译家,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很难深入到这一层面理解中国诗歌,所以对文本的理解和翻译大多停留于意象意境层面,故而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舟“小”的特点,却错误地将“小”与“孤”等同起来。笔者以为,在翻译“孤舟”这一意象时,将孤与小两个特点同时展现出来似是更为妥当的译法。
此外,全诗的颈联由孤舟、蓑笠、翁三个意象并置而成。如前所述,这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多以意合的特点,是唐诗中常见的言说方式。而中国古诗词中这种特有的语言现象也无疑给外国译者的翻译造成了困难。针对这一困难,三位译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译文1根据英语的语法特点打破了原诗原有的语序,将孤舟、蓑笠两个意象并置作为颈联,而渔翁的意象则被移动至尾联,成为全句的主语。译文2尽力还原了中国古诗意象密集且多以意合的特点,直接采用违背英语语言规律的意象并置方式进行翻译,展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与意象组合的特点。译文3则兼顾了原诗的表达和英语的语法规则,将“蓑笠翁”译为了身着蓑笠的渔翁。应该说,这三种译法各有千秋,都体现了译者对于唐诗语言特色的熟悉和通过不同途径加以的表现的意愿。而笔者尤其赞赏译文1的英译方法。译文1通过将渔翁这一意象移至尾联,为“独钓寒江雪”一句提供了主语,弥合了汉语和英语语法的差异,更便于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在不同文化语境下阅读过程中的理解。同时,将渔翁置于尾联的句首就将渔翁傲岸高大的形象极大地凸显了出来,这一处理正与柳宗元的本义正相符合。虽然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诗的语言构成,但亦可谓“得意而忘言”了。
而在尾联的翻译中,三位译者也从各自的理解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译文1将“独钓寒江雪”翻译为了在寒江中钓鱼,而并未体现出“独”的意项。译文3兼顾了汉语的语义和英语的语法规则,用合乎英语语法规则的方式将原句译为了“在寒江雪上独钓”。唯独译文2创造性地打破了英语的语法规则,按照汉语的语序直接对诗句进行了对译。第一,译者将alone置于fishing之前,突出了“独”的意味,第二,在fishing和river snow之间并无介词“in”进行连接,从而忠实地将原诗译为“独钓寒江雪”,而非“在寒江雪上独钓”。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最能反映原诗意蕴的一种翻译方式。首先,将along置于fishing之前以突出“独”的意味,其效果与前述“孤舟蓑笠翁”中“孤”字的翻译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处不再赘述。其次,笔者以为“独钓寒江雪”这句诗不能对等地理解为“在寒江雪上独钓”,二者表面上差异不大,实则在语义、意境和情感表达方面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变异。从语义层面来看,“在寒江雪上独钓”的翻译中,“寒江雪”是钓的环境,而所钓之物则是“鱼”。“独钓寒江雪”则可以引发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与前者相似,另一种则可以将所钓之物理解成“雪”。“钓雪”的说法乍看之下似乎不可理喻,但细细品味,其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之下确有其独特的意味和妙处。中国有“姜太公钓鱼”的典故,强调太公钓鱼“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只是借钓抒怀,干谒自荐。从这个思路理解渔翁“钓雪”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理解,而这与渔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意味以及柳宗元当时的心境正相符合,“钓雪”这一“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正是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和高洁不俗的品格,它的“意”是深沉宏远的。进一步来说,渔翁钓雪,最终必然一无所获,从而进入空无的境地。这与全诗空阔荒寒的意境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亦表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禅宗思想对“有无”关系的思索及其对诗歌言语方式的影响。而对于外国的译者而言,他们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学的上述话语规则和言说方式,自然就会在译介过程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总之,翻译家在翻译异族的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由于各民族间民族心理、文化传统、认知方式、话语规则等的差异,必然会出现文学变异的情况。而文学的变异既是一个逐渐远离原初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开拓新的理解路径的过程。它在跨越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译介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促进着各民族间的交流与理解。我们对《江雪》的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例,还有无数相关的问题等待着我们的探索与解答。
参考文献
1.Wikipedia.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EB/OL].2010-05-17.
2.Witter Bynner, Kiang Kang-hu. The Jade Mountain:A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M]. New York:Alfred A.Knope,1929.
3.曹顺庆:南橘北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4.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版.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李言实:《江雪》的意象解剖及其英译[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06):54-58.
7.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8.孫芸珏.从经验理论看《江雪》译文[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6(02):90-91.
9.唐年青.古诗《江雪》《青青河畔草》英译译法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78-80.
10.汪春阳.俯仰自得 动静相生——从比较文化角度看《江雪》英译[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7(06):88-91.
11.文殊,选注.诗词英译选[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
12.辛红娟,覃远洲.格式塔意象再造:古诗英译意境美之道——以柳宗元《江雪》译本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02):92-96.
13.许渊冲.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7年版.
1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朱小美,陈倩倩.从接受美学视角探究唐诗英译——以《江雪》两种英译文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8(04):105-108.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