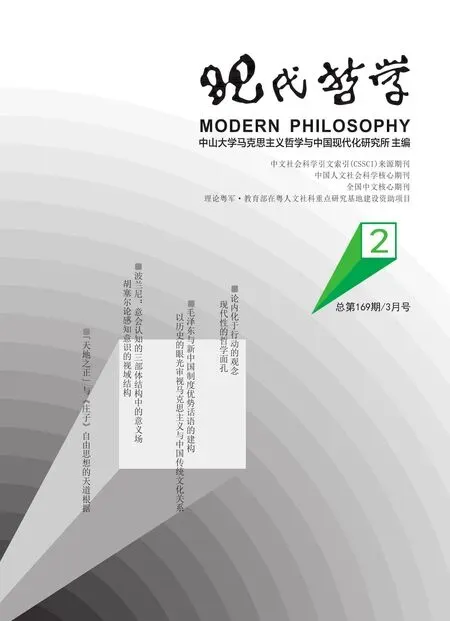从形训看为何要把Sein译为是
李 菁
一、引 论
Sein/Being/on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作西方哲学的“最高范畴”或“最基本概念”,然而相关汉译之争可谓旷日持久,迄今未有定论(1)参见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下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笔者尝试将争论各方粗略划分为“存在(有)”派与“是”派。而存在(有)派对是派最大的一项质疑就是:虽然是可以应对作为名词Sein意义来源之动词Sein(2)一般来说,存在(有)派和是派都赞同:名词Sein或Being之意义,根源于其相应的动词形式。因此,要理解前者,就必须回返考察后者。(参见王路:《西方哲学汉译的困惑与超越——响应孙周兴教授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28页;[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495页。)的普遍系词语法功能,但并没有存在的意思,从而难以应对动词Sein本身所明确包含的存在意义(3)参见陈村富:《关于希腊语动词eimi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第273页。。质言之,似乎只要是派能够无可争议地证明是确实具有存在的意思或用法,那么是派即可宣告译名之争大获全胜(4)笔者虽赞同是派把Sein/Being/on译为是的基本结论,但在具体论证理据上与传统是派保持重要分歧。传统是派多强调作为名词的Being来自作为系词的to be,因此翻译Being必须充分体现系词to be的意义用法,而现代汉语最常见的系词显然是“是”。笔者则更为凸显系词to be或是原本就有“存在/在场”之意。。那么,究竟是有没有存在的意思?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全面展开此问题(5)关于现代汉语的是有无明确的存在意义或用法,笔者认为显然是有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是)表示存在,主语通常是表处所的语词,‘是’后面表示存在的事物:村子前面是一片水田;他跑得满头是汗。”有些(存在)有派学者可能会认为,现代汉语的是虽然可以合乎汉语习惯地表示这样的“主语通常是表处所的存在”,但难以应对“上帝是”这样的情形。“上帝是”在现代汉语里是一句十分怪异、难以理解的“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甚至不符合汉语语法的”句子。笔者在这里只回应两点:(1)在西文里,“God is”也不是一句寻常易懂的话,也是足够“weird”;(2)现代汉语包括其语法仍在活跃地变易或与时俱进,我们理应对汉语应变能力保持极大信心和耐心。(《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56页。),只是尝试从“形训”(6)形训是指以形训义-以形示象的一种训诂学方法。视角出发,精细考察是之古汉字字形原象。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看,该视角迄今尚未引起学者们足够广泛深入的重视。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1935年夏季学期弗莱堡讲座)中,曾考证德语动词Sein的所有复杂变形情况皆由三种不同的古老词干来规定:(1)es,“生活,生活者,由其自身而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驻者”(das Leben, das Lebende, das, was von ihm selbst her in sich steht und geht und ruht: das Eigenständige);(2)bhu,“起兴,起作用,由其自身而来站立并在站立中持留”(aufgehen, walten, von ihm selbst her zu Stand kommen und im Stand bleiben);(3)wes,“居住,逗留,停留”(wohnen, verweilen, sich aufhalten)。前两种词干为印度日耳曼语所共有,而且出现在古希腊语的eimi、einai等和拉丁语的esum、esse等。最后一种词干只在sein这个日耳曼语动词的变形范围内出现。要之,这三种词干含混而成“生活,起兴,逗留”(leben, aufgehen, verweilen)之连带意义;质言之,三种词干可谓以不同方式含摄蕴藏了“在场”(Anwesen)或“让在场”(Anwesenlassen)之义(7)Vgl. M. Heidegger, GA40: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3, S. 75-77; GA14: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7, S. 9.。
那么,从字源形训角度说,我们汉语中的有、在、存、是,究竟有没有类似的原始意义?笔者认为,它们都有,而且各富特色,各擅胜场(8)关子尹的“On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Notion of ‘Be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Script”(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y 44 (3-4), 2017, pp. 212-229)一文,亦对古汉字有、在、存、是做了形训考察,但不如本文详尽,具体观点也有重大差异。比如,笔者并不同意关文将有、在、存、是“等量齐观”的做法。关文认为这四个汉字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应着to be的不同含义或用法,或它们共同印证着to be的“四重根”(fourfold root),但没有哪个字具有某种绝对的综观优势。笔者则认为在翻译to be的问题上,是相比于有、在、存具备多方面不可比拟的优势。不过,笔者亦非常赞赏关文的如下观点:首要的问题不是寻找一个最合适、最匹配的汉字来翻译to be,而是反思汉语(汉字)如何以其独有的方式来表达像Being这样的一般观念。。
二、有、在、存、是之字形原象

图1(9)本文所引古汉字金文和小篆图片均出自“汉语多功能字库”(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电算研究中心),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2月29日。中,《说文解字》云:“有,从月,又声。”(10)[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柴剑虹、李肇翔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390—391页。以下简称为《说文》,引用仅在文内标注页码,不再另行说明。有,从月(肉)从又(手),其象可训为以手持肉、手中有物。从其金文字形看,有或亦可被训为:在原肉上生长出原手,惟有通过此原肉-原手,周遭诸是者才可能是其所是或自行显隐;没有原肉暨原手,一切都是混沌昏暗的,一切都“不是”了。质言之,如果没有“手”(Hand),何来海德格尔所说的“上到手头之是”(Zuhandensein)与“现成在手之是”(Vorhandensein)?因此,有含摄在场或让在场之义。
图2中,《说文》云:“在,存也。从土,才声。”(第801页)其象可训为草木初生(才)于土上。在之原象颇可与古希腊之“physis”(起兴-涌现-萌生-生长)遥相呼应-共鸣。因此,在含摄在场或让在场之义。
图3中,《说文》云:“存,从子,才声。”(第864页)其象应训为生命(子)从地下向上萌发(才)。《尔雅》云:“存存,在也。”(11)参见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第87—88页。存即在,在即存也。可见,存、在之原象极为亲密相似,甚至就是“一回事”。因此,存含摄在场或让在场之义。
图4中,《说文》云:“是,从日、正。”(第94页)其象可训为日正在天,普照光耀大地,万物趁机萌发生长、游戏逗留。相比存在象,是象或可谓不仅是“有”(生活-起兴-逗留),而且是“大有”。因为存在仅描绘“草木生命破土初生之象”,是则大彰“天地上下交感、日正草生的阴阳对构互成之易象”。质言之,“是象之‘(让)在场’义”比“存在象之‘(让)在场’义”还要“强大-强盛-强烈”太多!我们甚至可以借用某种海德格尔式的口吻来说:是象比存在象更为“原始”,存在象之所以可能,全赖是象之包孕化育!


三、“是”与“大有卦”
因此,既可以把是依照其原始字形直接训作“日正”,也可依照其原始字义理解为直即“正见”。“日正”即“正见”,“正见”即“日正”。那么,“正见”之“正”或“日正”之“正”究竟意义何在?如此,追踪“是”之要义,最后落脚点似乎又全系于“正”字。

图8中,《说文》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第94页)因而,正象可训为:以一而止、守一而止,止于一也。那么,究竟何谓“一”?凝视正的金文字形,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个“一”从“源头”说来其实就是“日”(火在天上,日正于天)。因此,正之所谓守一而止,其实就是守日而止、守是而止、守直而止。是即直,直即是;直即正,正即直;是即正,正即是。这里显示着某种十分有趣的、有益的“解释学循环”。那么,日正于天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需要折回到周易之“大有卦”。是,从日从正,说的正是日正于天,实通周易之第14卦“大有”(图9)。
大有:元亨。(《周易·大有》)
卦名:大有。卦辞:元亨。大有卦,内卦为乾,外卦为离,下乾上离,乾为天,离为日为火,火在天上,日正于天,日离(丽)于天,让万物起兴、生活、逗留,因之可谓“大有”象。九二处下乾之中位,故曰“元”,上离中位之六五下应九二,故“亨”(亨通-亨达)。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大有·彖传》)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周易·大有·象传》)
综合彖象二传之疏可知,大有”说的就是:六五以阴虚入君爻位,身居中位正位主位,而为五众阳实所拱卫;六五中正有德,上下回应,厥孚交如,故享“威如”之大吉;内卦为乾,乾乃天,藏刚健之德;外卦为离,离为火,彰文明之象;因此,圣人自觉响应日正,顺乎日正,维护日正,从而兴造暨维持“大有-元亨”之“圆满”状态。亦可将大有卦与泰卦做简要比对。泰内卦为乾(纯阳),外卦为坤(纯阴)(15)这里“纯阳”“纯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合理道说的。换个方向看,坤中有乾,乾中有坤;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因此,何来绝对不变的纯阳、纯阴之说?《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下乾上坤,阴阳完全“错位倒置”,因此阴阳天地得以最大限度地交合欢乐,从而大吉。大有的基本格局其实可谓与泰相类,也是下阳上阴,只不过上阴从纯阴之坤易变为二阳夹一阴的离阴(日)。大有以六五唯一之阴柔统帅-君临上下五众之阳刚,可见周易中道中庸-高明智慧的极致。
那么,究竟何谓“日正之正”?大有卦所描画的“日正”原象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正”说的难道只是正午十二点太阳在天空最高挂起的那一时刻瞬间吗?或者“日正”说的只是某个静止的、孤立的、正确的、不偏不斜的、不动不变的、抽象的、终极的、最高的、最普遍的“形而上学的”本质状态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归根结底,“日正”真正要说的是原始之“时中”。质言之,我们应该把原始之“日”理解为原始之“时”,而把原始之“正”领会为原始之“中”。
四、“日正”与“时中”
《说文》曰:“时,四时也。从日,寺声。”(第380页)日即时,时即日,可谓“时日”,亦可谓“天时”。可训时象为: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日月周易而生生不息。每一时季形式指引(16)这里借用了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关键术语“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简言之,这是某种非-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非系统化、非普遍化的作为“(让其)自行-显示”的原始显示方式。Vgl. M. Heidegger, GA60: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55-65.的不只是每一时季,而是四季周易;每一时刻(比如日正当头)形式指引的也不只是每一时刻,而是日月周易。因此,时通易,日通易。
《说文》曰:“中,和也。和,相应也。”(第74页)因此,中象即为:正和中和,不偏不倚,合适适当,恰到好处,和谐协调,中庸中道。《周易·系辞传上》曰:“天地设立,而易行乎其中矣。”整个《周易》其实都在讲中。这个中是在天地之中,亦即在阴阳之中。而阴阳之中,亦即时中也。《礼记·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因此,时中即中庸,中庸即时中。
可见,所谓“时中”说的是:中于时,合适于时,应时顺时而不论时行时止。《周易·蒙·彖传》云:“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周易·艮·彖传》亦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因此,只要“不失其时”,即便“险而止”或“时止”,亦是“止其所”,仍在“时中”。因此,即便一时“日止-日正”,也未必不“时中”。实际上,真正的或原始的“日正”形式显示的正是“时中”。“中和”与“正直”虽构象有别,各有凸显侧重,但二象实为相互感应、“惺惺相惜”的天命关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来说,二者有着十分亲密的“诸家族相似性”(Familienähnlichkeiten)。因此,才有“正中”或“中正”的说法,其意象实与“中庸中和中道”完全贯通。说到底,惟有正,才可中;惟有中,才可正。中、正实乃相互构成支撑之本质关系。《周易·乾》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周易·离·彖传》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外,“实事求是”的“是”,其实也应训为“时中-日正”之原象。而所谓“止于至善”,即“止于时中”、“止于日正”。惟“止于时中”、“止于日正”,才可以“止于至善”,即“止于元亨”。

我们还应再返金文之是象(图10)。金文之是,其上体为“日(上)十(下)”(非“早”)。有学者将其训为“日晷”,笔者以为,或许可以更原始地来看这个“日十”。“日”不仅可以训为本义直义“太阳”,亦可形式指引出“日月(星辰)”或“时日”(天时)之周易象。那么,何谓“十”?《说文》云:“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第126页)因此,十意味着某种四方周行、全体俱备的中正-圆满之象。这样,“日十”可训为日月周易、四季周易的中正-圆满易道。其下体为“止”。《说文》云:“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第91页)结合“止”上之“日十”来看就是:在天地阴阳的交媾下,在中正之日的朗照光耀下,在日月星辰四季周易的庇佑恩泽下(日月丽乎天),艸(草)木生命萌兴生长-繁荣衍化,且其根基根系逐渐深扎广播固止于沃土之中(艸木丽乎土),而人则生活嬉戏、逗留悬止在这天地日艸之“中”。若以周易三道观之:止为初爻二爻(止最下面一横为地,占初爻;其上三枝为艸,居二爻),象地;日十为上爻五爻(日在上爻,十居五爻),象天;而其间空位“()”为三爻四爻,可谓象人。因此,十在金文是中之“位”实与大有卦之君爻(六五)“重合”。而十作为“数”,正好是阴数地数,合于大有之六五阴柔。因此,金文是之“日十()止”,贯摄天地人三道的原初易象。这是多么美丽的原初易象!这才是汉语是的本真原象!《周易·系辞传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本源易象与“日十()止”可谓极为亲密相近。
因此,如果一定要分别“原始高下”,有、在、存之象都不可与是象相提并论,是比有、在、存都要“原始通透-到底究竟”得多。因此,“大有”才被叫做“大有”,而不仅是“有”,“大有”(是)可谓“原有/元有/源有”。或可借用某种海德格尔式的行话(17)这里借用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关键术语“它给予”(Es gibt)。“它给予”形式指引的正是作为海氏后期思想的主导词“兴有”(Ereignis)。“兴有”与“大有”有若干有趣的诸家族相似性。Vgl.M. Heidegger, GA14: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7, S. 3-30; 李菁:《何谓Ereignis?——略论作为“兴有”的Ereignis》,倪梁康主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44—167页。说,由这个作为“它”(Es)的“是”(大有)才“给予了”(gibt)有在存。倘若没有“日丽(离)于天”,又哪来“以手持肉”或“草木起兴”的“大好事儿”(大好日子)呢?
扎根沃土的“止”(趾/脚)象征停驻、盘旋、悬停、逗留等。上日下止合观,可谓(永远)驻留-维持-悬停在“易道”中,(永远)驻留-维持在“日正-时中”的“元亨”态。其实,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也是“总能在-时-中”,即“总能恰到好处”,“总能维持中和中庸中道”,“总能实事求是”,“总能以日为正”。金文之是形式显示的正是“止于至善”之象,这个“至善”正是“日正-时中”或“生生之易道”。因此,通直通正、通时通易之是,不仅有“实事求是”的求真之象(求是即求真,求真即求是),而且有“是非分明”的求善之象(求是即求善,求善即求是),此外还有“日丽于天”的求美之象(求是即求美,求美即求是)。是有“订正-更正-改正-校正”的动词用法,这个“是-正”(动词)构造-悬持的正是“去假存真”“遏恶扬善”暨“抑丑彰美”的连带易象。要之,是与真善美完全相通,它们相互含摄、对撑对构。因此,与是亲密相关的即语文学家所谓的形声字中以是为“声旁”的若干汉字,如諟、禔、湜、媞、醍、崼、徥、瑅、鍉等,大概都各自形式指引着某种(由各自“形旁”来形式指引的)“物事领域”的圆满美好-大有元亨之原象(真善美之原象)。比如,“諟”(真言真谛、正言直言、善言美言等连带意蕴),可形训为“是于言”或“言之是”,言之日正时中-大有元亨态;而“湜”(清澈见底的纯净之水)可形训为“是于水”或“水之是”,水之日正时中-大有元亨态。《诗经·国风·邶风·谷风》曰:“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可见,作为声旁的是绝非对于形声字整体没有任何“意义”的贡献;相反,声旁是对形声字整体意义的贡献往往丝毫不逊于形旁(比如言、氵、金、女、山等),甚至有时(远远)超越后者,这也可谓(古)汉语作为表意文字构字造字之一大特色。
然而,这样的真善美原象绝不意味着任何抽象不动的静止极致状态,而是意指某种悬停-维持在“时中-日正”之中的中道中庸姿态。巧合的是,在西方哲学史上,On/Sein/Being也是与真善美亲密钩连在一起的,这在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关键”大哲那里尤为凸显,只不过西方哲人与中华哲人所领会的真善美其实大相径庭。比如,对巴门尼德来说,是或是者乃不生不灭、连续圆满之一,与真善美可谓同一;而对柏拉图说来,最高或最后的是或是者(理念或相)就是“善”(日),这个善也是至真至美之善。
丁耘的《是与易──道之现象学导引》(18)参见丁耘:《是与易——道之现象学导引》,《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17—300页。,力图以“是象”“易象”来形式指引-刻画比较“(西方)哲学”与“(中华)易道”,从而勾勒(未来)异于且超越-统摄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易道现象学”。这无疑是十分辽远深刻、极富穿透力的,对笔者也非常有启发,但笔者还是留有若干疑问。首先,“西方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可以用“是”或“大有”来简单刻画吗?难道没有些许某种以“东方圣人”的眼光来(蓄意)简化、曲化、弱化或矮化西哲的嫌疑?其次,是或大有的原初易象难道仅仅是“日头高照”或者“作为日行之停顿的日正”吗?依笔者之见,“日正”绝非(仅仅)意味“日行之停顿”。后者最多只能说是关于“大有-日正”的一个非常“表面的”(字面的)、“临时的”(作为“临时使用的阶梯-通道”的)便于大家理解的“初始”说法而已。归根结底,日行怎么可能停顿呢?《周易·系辞传下》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贞通正,因此“正观(示)”乃天地之道,而“正明”就是日月之道。正即易道,易道即正。因此,日正绝非易道或日月之道“停顿”之象。整个周易六十四卦都在讲日新月异、日月交替周行,所以日行怎么可能停顿?大有卦绝非意指日行之停顿,日行若停顿,那将是十足的“世界末日”,哪还有丝毫“大有”之“元亨”呢?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说,“日止或日正”绝不意味“日行之停顿”,而是意味“时中”之象。“以日为正”说的正是(努力)停留-盘旋-维持在“时中”的中庸中道之姿里。惟如是,君子才可能顺天应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再者,既然大有本身即为易道之内在一卦,大有本身即为易道之肉身,是与易原本就亲密钩连一体不可分(是中有易,易中有是),那么,怎么可能把是与易割裂开而分别用是代表“低级的”西方哲学、以易刻画“高级的”“高于”西方哲学的中华政教文明呢?是与易绝无任何“高下”之别,二者是完全互摄相通的“一体-关系”。在合理地道说“易含是而统摄之”的同时,难道我们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合理地反过来道说“是含易而统摄之”?因此,笔者以为,是易之某种“内在深刻同一性”表明二者完全不合适用来分别刻画“互为他者”的西方哲学与中华政教文明。
是,易中之大有卦,天地阴阳交通,日丽于天,万物生焉;居有思无,居富思艰……大有正好可“作为”易道之目的因(同时是动力因、形式因),正好可“作为”易道之宇宙论和道德论的终极理想。这个理想正好又自行镶嵌内含在整个易经六十四卦里。易里透着的是是,是里藏着的是易。易乃是之背景,是乃易之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或亦可谓易之“真理”(Wahrheit)(19)这里“真理”一词的用法确有来自某种黑格尔式的启发,但笔者的用法与黑格尔的用法显然有重要区别。笔者的用法更强调具体的语境化或时机化。比如,凭依不同具体语境,别的有些卦象(比如泰卦)“有时”亦完全可能被笔者合理“作为”易之“真理”。笔者认为,这里没有任何逻辑矛盾,关键是语境化或时机化的具体调校。Vgl. G. W. F. Hegel, Hegel Werke (Theorie-Werkausgabe) Band 3: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S. 23-24.。是即易,易即是。是与易根本没有本质性的、不可调和的、非此即彼的“矛盾”,完全可以和解为一。因此,似乎不必只能像丁耘形训的那样,仿佛是与易只能代表中西思想的某种根本差异或“差距”所在。丁先生似乎早已认定易代表的中华政教文明“高于”且“统摄”是或大有所刻画的西方哲学。其实,“互为他者”的西方与中华,可以也应该“平等”和解。这才是“人类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未来所期。
综上可知,从古汉语字源形训的视角看,是与时有着无比亲密的原初天命关系。《尔雅》云:“时,是也。”时、是皆可“近指”,相当于“此”、“这”。这样的“近指”完全是“时机化-处境化-具身化”的,因而可谓与海德格尔Dasein之Da亲密地遥相呼应。是之“日正”说的正是“时中”,而后者与海氏“时机化/到时候”(Zeitigung)亲密相通、相互印证。因此,单从翻译海氏思想说来,是也比有、在、存等“无时”之字合适贴切得多。要之,是不仅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德语动词sein之三古老词干(es, bhu, wes)中葆藏的诸原始(让)在场意象(生活、起兴、逗留等),而且可以完全自如地与“真善美”相通互摄、与“时中-时机化”相通互摄。在这两点上,有、在、存确实明显要“虚弱”许多。因此,相比于有、在、存等可能汉译,是实乃西文on/Being/Sein之最佳汉译选择。
- 现代哲学的其它文章
- “天地之正”与《庄子》自由思想的天道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