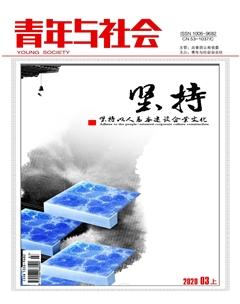人工智能视角下智慧法院审判权运行模式流程再造的必要性
摘 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推动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变革传统的审判权运行模式,积极对智慧审判权流程再造,对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在司法领域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技术被赋予很高的期待,它的发展对于未来生活,甚至对于国家组织运行方式改变有深远影响,文章站在人工智能辅助论的立场,探究智慧法院建设中对于法院审判权运行模式流程再造的必要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慧法院;审判权;流程再造
一、智慧法院建设的时代背景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将信息化与社会治理精密结合起来。201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以下简称规划),指导全国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同时也为智慧法院建设指明方向。智慧法院其实质上是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引入人民法院办案流程,是司法与现代科技的契合。从《规划》中可见,智慧法院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内部基础建设阶段。此阶段是改变传统的办案流程,用现代化技术补强传统办案方式和手法,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电子送达,远程视频作证等;2. 推动建设外网网站并建设智慧法院阶段。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建立四大司法公开网站:中国审判流程信息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网;3.“嵌入式数字化管理”和“互联网+”阶段。作为人工智能切入司法领域的重要场景,目前各种以“类案推送”为核心功能的衍生产品已见诸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和话题效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使得“互联网+”在司法领域掀起一股热潮。
二、传统法院审判权运行模式及诟病
我国法院的审判组织是由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组成,按照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划归为不同的审判组织审理。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是法定的审判主体,《法院组织法》中表明这些审判组织内部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具有密切相关性,一个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相互影响。法院内部的法官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是有等级划分的。由于历史因素,我国法官与公务员同质管理,套用行政级别,在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按照行政级别形成了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等级架构,即使人民法院吸纳有陪审员,大多数法院也只是“陪而不审,表决跟风”审判员的等级架构同样是法官,在审判上并不是真正的平等,有三六九等之分。从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所存在审判主体职责不明确、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基本秩序缺失、层级化现象明显。
三、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的概念最早来源于企业管理,由哈默与钱皮两位学者率先提出,并针对企业流程进行根本性反思并彻底地重新设计,以在成本、质量及服务等因素作为衡量组织绩效的重要指标。“流程再造”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绩效,后引起研究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所注意,开始在公共管理领域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为政府治理变革带来更多可能,政府应该以大数据时代为契机,重塑现有的政府治理结构,进行流程再造,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司法机关同为公共服务机构,在建设智慧法院的大潮中,在目前限定的技术条件以及实现司法体制改革成本最低化的前提下,将“流程再造”引入人民法院审判组织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政府治理进行流程再造取得了卓越成绩,可有借鉴的基础;其次,司法流程本身与政府流程再造的事项非常类似,它们同属于具体的事务执行存在突出业务主线,有明确的用户需求作为引导。流程再造具有两种模式选择分别为“强前台”模式和“强后台”模式。1.强前台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电子系统管理能力基础之上的所谓“强前台”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主张改变现有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仅仅通过一些现有的技术手段来优化现有的组织设计和运行模式,用通过技术手段加工过的程序来弥补现有“后台”的缺陷。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制度改革的成本小,前期效率高,对僵化的流程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2.强后台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政府实体组织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的“强后台”解决方案。所谓的“强后台”就是在“强前台”模式的基础之上,侧重实体组织设计导向的变革来取得内部效率。这种模式下,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可以根据公众和现实的困境对诉讼流程、环节和具体的规则实施变革,对审判组织的运行模式进行系统优化甚至是打破旧的组织形式建立新的审判组织运行体系,从而取得审判组织的内部效率。
四、审判权运行模式流程再造的思考
(一)定性选择:人工智能决定论or人工智能辅助论
探究智慧法院建设中人民法院对于审判权运行模式的流程再造需要明确人工智能在智慧法院中的定位,目前学界存在人工智能决定论和人工智能辅助论。人工智能决定论者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以人工智能为载体的平台可以取代现实中的法官,即使不能取代全部,但大多数的案件能够通过人工智能过滤掉。英国数学家图灵(A.M Turing,1912-1954)在其《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提出的“机器能思维”的测试(即图灵测试)所遭受的质疑之一在于该测试只反映了结果的比较并未涉及思维的过程。若由人工智能技术主导审判则可能挫伤法官的自我认同感和职业神圣感。法官对于纠纷的解决存在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目光需要来回穿梭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制,这个过程是有温度和法感情的。法律要素和案件事实属于无意识的“死”东西,它们的“灵性”只能凭借法官这个活的要素激发出来。
(二)人工智能具有改变审判权运行模式的可能
201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互联网司法白皮书》,为各地法院进行智慧法院建设指明方向。互联网的应用领域由司法公开向全流程方式拓展,平台载体由单一走向多元,诉讼模式走向集成开放,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互联网法院并不是智慧法院的全部,它在性质上是专门法院的一种,是“互联网+司法”的产物。从信息化角度来讲,互联网法院具备了智慧法院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并不是全部,智慧法院包括阳光法院、网络法院、智能法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智慧法院的三个维度。因此,互联网法院审判组織的运行模式是对流程再造的“强前台”模式。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下,互联网法院建设并未对审判运行模式进行很好的回应,传统的审判权运行模式的弊端仍然难以避免。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法院内部各审判组织间的协作机制。传统审判组织运行方式和审判人员组成呈现出程序、封闭、严谨的特点,而智慧法院则强调便利化、快捷化、开放化以及个性化,并要求对落后的运行方式、僵化的组织结构、低效的管理流程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未引进现代信息技术之前的法院内部各审判组织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即使法院对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管辖的案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事实生活中的案件并未仅仅包含条文上所列明的情况,审判人员为了逃避审判责任,该独任庭审理的案件,让其变成合议庭审理,该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能上审委会就上审委会,各审判组织之间相互推诿,协作机制僵化。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此次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解决法院内部各审判组织间的不协调状态,消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问题,严格落实各审判组织的办案责任,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这个方案已经在全国各地法院展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智慧法院以其独特的信息化、智能化、便利化等特点,对审判组织审判权运行模式进行流程再造具有先天的优势。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平台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目前智慧法院建设主要集中在立案阶段和执行阶段,审判阶段的信息化建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审判流程是智能服务技术最为重要的应用场所,也是“智慧法院”建设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智慧法院建设对公众来说更重要的是庭审阶段。目前的现状就是公众对法院的需求分散于案件审判、判决执行与审判监督等环节,这些环节并未受到更多的关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在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搭建一种信息处理平台,这种平台可以将从立案庭来的案件分流到各个审判组织之间,同时案件情况产生变化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审判组织之间转化。
(3)人工智能改变审判方式。在法律推理领域,从 1970 年开始探讨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的法律推理过程以来,一直遭到的质疑就是法律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无法通过计算机的形式进行模拟 。世界上第一台机器人律师罗斯(Ross)的应用是建立在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方面的重大突破基础上的,其基本技术依赖于IBM公司的沃森(Wat-son)機器学习技术。沃森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就是深度问答技术,包括IBM公司后续推出的“辩论者”应用程序也是采用这种技术。这种技术不仅能从文本中提取信息,还能“理解”信息并运用它们进行推理。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积极将深度问答技术等类似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法律实践,推动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审判方式变革,探索新的审判权运行模式。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是站在人工智能辅助论的角度探讨智慧法院审判权的运行模式。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技术仅仅是人类用以简化流程所用的工具,它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和无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平衡点。但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人类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审判权的流程再造文章选择“强前台”模式和“强后台”模式共同推进,在建立各种智能信息交汇的平台的同时,强化审判组织的构造,以迎合社会变化的需要。目前,我国智慧法院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即使设立了一些互联网法院,但究其性质可以把它看作专门法院的一种形式,并不能算作智慧法院的成型状态。
参考文献
[1] 吴涛,陈曼.论智慧法院的建设: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J].社会科学,2019(05):105-113.
[2] 本刊编辑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J]中国审判2016(05): 62-63.
[3] 陈琨.类案推送嵌入“智慧法院”办案场景的原理和路径[J].中国应用法学,2018(04):88-97.
[4] 刘祖云等.组织社会学[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2,251.
[5] 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1-87.
[6] 方乐.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改革的制度资源与模式选择[J].法学,2015(03):26-40.
[7] 胡国栋,王琪.平台型企业:互联网思维与组织流程再造[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02):110-117.
[8] 陈国猛.互联网时代资讯科技的应用与司法流程再造——以浙江省法院的实践为例[J].法律适用,2017(21):2-8.
[9] 陈蓉,孟庆国.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的必然性和选择性[J].情报杂志,2006(05):112-115+118.
[10] 王铭.论政府行政业务流程重塑的实施途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04):34-38.
[11] 高一飞,高建.智慧法院的审判管理改革[J].法律适用,2018(01):58-64.
[12] 唐旭,苏志猛.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理论证成、特质与困境突破[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33(08):95-103.
[13]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4.
[14] 于志刚,李怀胜.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历史意义、司法责任与时代使命[J].比较法研究,2018(03):103-118.
[15] 王小梅.“互联网+阳光司法”:智慧法院的重要维度[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0):63-66.
[16] 陈国猛.互联网时代资讯科技的应用与司法流程再造——以浙江省法院的实践为例[J].法律适用,2017(21):2-8.
[17] 孙海龙.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05):32-36.
[18] 周佑勇.智能技术驱动下的诉讼服务问题及其应对之策[J].东方法学,2019(05):14-19.
[19] 江秋伟.论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空间及限度[J].学术交流,2019(02):92-104.
[20] 邱昭继.文本解析技术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J].中国法律评论,2019(02):142-155.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人工智能背景下基层智慧法院建设探索”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CSW2019078。
作者简介:田杰(1995- ),男,土家族,重庆人,硕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