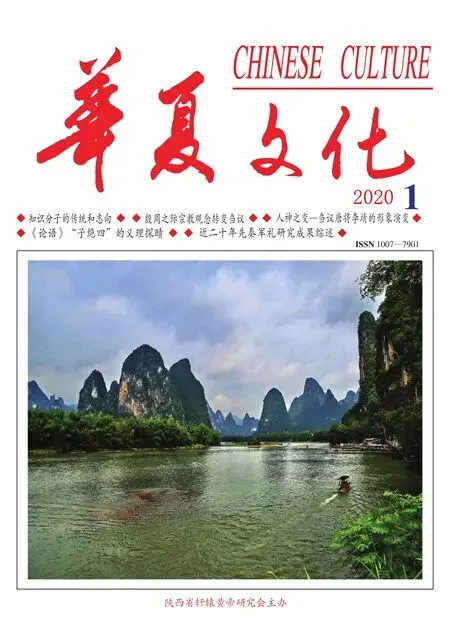《论语》“子绝四”的义理探赜
□毕孝珍
《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一部儒家经典,其中有很多语句意蕴深刻而又丰富,被世人视为至理名言。“子绝四”就是其中一句,它语出《论语·子罕》,原文是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但这一句与《论语》中其他语句相比,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笔者意欲在此探赜一番,以飨读者。
一


弄清了每个字的意思,“子绝四”这句话的大体意思也就好明白了,大体上是说孔子禁绝四种不良行为,所以他不主观臆测(毋意)、不极端、不绝对(毋必)、不固守自封(毋固)、不唯我(毋我)。可见,“子绝四”一句,意蕴确实丰厚而富有哲理。仔细分析其语句,可发现此句有些非同寻常。
第一,从语法结构上说,此句有特别之处。
“子绝四”这句话的大意应该说是很好理解的,但如果从语法的角度来解读此句,似乎就有些问题。
“子绝四”中的“绝”字是个动词,含有“断除、禁绝”的意思,它的宾语是“四”,那么“四”在这里是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还是“意、必、固、我”?假设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话,“子绝四”一句就变成了“子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此句的思想内涵大相径庭,因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好是孔子所推崇、践行的一种良好修为,孔子显然是不会禁绝此四种良好修为的;而如果“四”是指“意、必、固、我”,那么此句就变成了“子绝:意、必、固、我”这符合孔子的思想与言行,但语法上就讲不通了,既然孔子绝的是“意、必、固、我”,那后面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四”又是什么关系?“绝”字和“毋”字毕竟意思差不多,都含有“禁绝”的含义,两个半句岂不重复?统观《论语》全篇,即使是与之最为相似的三句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子罕》)“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都是简洁明了的语句结构形式,唯独此句如此,不得不让人深思。
第二,从语义指向上说,此句也有特别之处。
《论语》中的大多数语句都有明确的语义指向客体,有的指向修身养性方面,有的指向为人处世方面,有的指向理想追求、政治抱负方面,而这一句的指向客体似乎不那么清晰,是做人、做事、治学、教学?再者,“绝四”和“毋四”是说孔子自己禁绝、没有这四种毛病呢,还是说孔子要求弟子禁绝这四种毛病呢?语义指向的主体也不明确。
第三,从语境上说,此句也非同一般。
《论语》中的大部分语句都能挖掘出一定的语境,有的是记录孔子所言或弟子所言,有的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的应对问答,有的是记录孔子和弟子的周游出行,有的是记录孔子音容笑貌或生平举止等。也就是说《论语》大部分语句都能挖掘出一定的时空背景、人物对象、言语氛围等,而此句却一概略去,显得突兀、孤寂而又神秘。
第四,从语辞上说,此句也独具特色。
它笔法冷峻、果敢、绝决,言辞语气不容商榷,没有《论语》通篇的那种和风细雨、娓娓道来之风。而且用字极为精炼,短短11字,涵盖的内容却博大精深,非一般语句所能媲美。
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看出,“子绝四”一句在《论语》中风格迥异,不同一般,这种非同一般,值得让人探究。
二
对“子绝四”一句,古今不同的人也有各自的注解,在此仅选取代表性的几例,以期能探寻一些奥秘。
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对“子绝四”一句有过详细解读:
绝,无之尽者。毋,史记作‘无’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终始,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至于我又生意,则物欲牵引,循环不穷矣。
此注解对“绝”、“毋”、“意”、“必”、“固”、“我”各字作了解释,但对“绝”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只解释“绝”为“无之尽者”,是“意、必、固、我”无之尽者,还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之尽者?朱熹没做说明,他在句式上也没太多关注,只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在“意、必、固、我”的相互联系上,认为四者具有内在一贯性,由于人的私意和物欲的牵引,所以人才会有所期必、有所执滞、有所私我。显然他的注解是从心性和人欲的角度来解析的,合理与否暂不考虑。但有一点朱熹的解释是合理的,那就是认为“意、必、固、我”是人性的弱点,理应“绝”或“无”。
对“子绝四”的注解,大部分人都认为“绝四”绝的是“意、必、固、我”,但近代学者程树德和宋代大儒郑汝谐却有相反的结论,尤其是程树德,他引经据典达二十多个,旁征博引两千余言,认为孔子绝的不是“意、必、固、我”,而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程树德引用郑汝谐的话说:
“子之所绝者,非意必固我也,绝其毋也,禁止之心绝则化矣。此解最胜,恰合圣人地位。盖仅绝意必固我,此贤者能之。惟圣人乃能并绝其毋。姑以佛学明之,能不起念固是上乘功夫,然以念遣念之念,亦念也,并此无之,乃为上上乘。”
在这里,程树德和郑汝谐认为孔子绝的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不是“意、必、固、我。”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解决了语法不通的问题,可总览孔子思想,他不可能像佛家一样空绝一切,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世俗中的,是为社会解决问题的,用虚无或空无的佛家学说解读“子绝四”的大义,有些牵强不妥。
现代学者对“子绝四”的解释一般都是从其大意上来解释的,也都认为孔子绝的是如“意、必、固、我”这四种毛病或不良心理。如:杨伯峻先生把“绝四”解释为“没有四种毛病”,南怀瑾先生则直接阐发孔子如何“毋四”,他解释说 :“第一是毋意,这是说孔子为人处世,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第二是毋必,是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能适应,能应变。第三是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第四是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些著名学者基本上都是从阐发“子绝四”的微言大义出发,也没有就语句结构及语义背景做探讨。
通过检索古今诸说,发现对“子绝四”内涵的解读基本上都差不多,除宋代学者郑汝谐和近代学者程树德外,基本上都认为孔子的“绝四”是绝“意、必、固、我”四者,可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写成 :“子绝:意、必、固、我”或者“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写成“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一句式有何用意?
细读“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句,前半句“子绝四”,显然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言,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精炼概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后半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语气和内容上看,不像是一个弟子所言,像是一个老师在教诲弟子时所言。近代学者程树德对此也有过考证,他认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极有可能是孔子所言“子绝四”前半句之所以和后半句语法矛盾,语义重复,其原因就在于两个半句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前半句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写,是对孔子人身修为的精炼概述,后半句则是孔子所言,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孔子语录的直接引用,后半句极有可能是 :“子曰:(君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是由于两个半句的作者不一样,才会造成此句句式奇特、语境突兀不清。至于此语句为什么会如此设计,很可能正是作者的苦心所在。前半句,作者对孔子日常立行处事之态度作精炼概述,则能更好地凸显孔子高尚的人格修养及魅力。后半句直接摘录孔子所言,则能更好地凸显孔子睿智的教育思想和对学生严谨负责的教学态度。为此,作者煞费苦心,前半句作精炼概述,后半句巧妙引用,“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遂成为《论语》中一特殊语句。
三
“子绝四”尽管语句特殊、语辞冷峻,但其内涵精深切要,充分体现了孔子作为仁者、智者、师者的思想情怀与风范。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其思想的核心,是其积极推崇和孜孜追求的人道和社会之道。孔子的“仁”一方面注重人自身品德的内在修养,讲求“克己”、“修己”、“尽己”,另一方面更注重人能够“推己及人”和“尽己为人”,讲求的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绝四”一句则恰好印证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一方面人只有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会达到“克己”、“修己”的修养境界,另一方面只有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会更好地待人,更好地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也就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以道为度,故不任意(毋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毋必);无可无不可,故无固行(毋固);述古而不自作处,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毋我)。”
孔子不仅是一位仁者,他还是一位智者。孔子在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把握和处理上,能够摈除四种毛病,不以主观意识妄断客观现实,而是通过“下学而上达”做到“毋意”;不绝对不极端,“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做到“毋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深知权变不固守成规做到“毋固”;“入太庙,每事问”,不唯我是尊做到“毋我。”这些无不体现了孔子高超的处世哲学和智慧。中庸思想是孔子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客观理性的认知态度和处世方法,是孔子体悟世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孔子道德修为的原则和规范。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是贯彻了中庸思想,表明了认知世界判别是非的标准。孔子以高超绝妙的智慧将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人的思维与客观存在、感性认知与理性判断完美地结合起来。这种智慧不是建立在西方抽象的纯思辨的逻辑形式上,而是建立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社会现实生活中,通过对自然生命现象的观察与体验,以人性的目光来认识和把控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以理性的智慧来解决人在社会、自然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是一种更为思辨的、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更为睿智和实用的哲学智慧。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作为老师,还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一思想和智慧传给学生。孔子兴办私学,广招门徒,其教育宗旨就是为社会培养君子人才,他常常告诫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为实现这一目标,孔子建构了一套以培养君子为教学目标的教育体系,它以“仁”为核心思想,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三戒”、“三畏”、“三愆”、“四教”、“绝四”、“行五”、“九思”等为践行要求和规范。“绝四”就是这一体系的一个方面。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君子,就要禁绝“意、必、固、我”这四种不良品行。“意”使人主管臆测而妄断客观现实,“必”使人陷入极端而不能中庸,“固”使人固守成规而不变通,“我”使人自以为是而不知他人长处,这四种不良品行,不是君子所为,它既不利于学习,也不利于生活,既不利于为人处事,也不利于修齐治平。为此,孔子在“自无此四者”的同时,还“禁绝学者毋得有此四者。”这展现了孔子作为师者的人生境界和教学风范。
总之,“子绝四”在《论语》中确实非同一般,其不合逻辑的语法结构、模糊不清的语义指向、孤寂突兀的语境、冷峻果敢的语辞及其精深切要的思想内涵,使其在《论语》中表现的卓尔不凡。尤其是“子绝四”所展现的孔子作为仁者、智者、师者的思想情怀与风范,更使此句充满了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