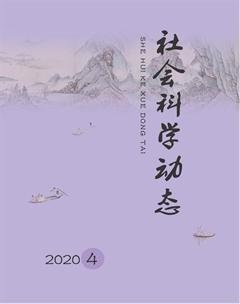家族、伦理与家族小说叙事的伦理性
摘要:家是人类社会的“细胞”,由家庭血缘关系衍生出的家族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聚合体,通常以一定的伦理观念和制度规范为基础。在传统社会,家族的兴衰荣耻和文化精神往往以“家谱”、“族谱”的形式记载与传承,作为以血缘、地缘和人情结合为纽扣的文化复合体,家族本身也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潜在内容。中外很多具有史诗气质的小说往往以“家族”为切入点,以“伦理”为叙事基点,并由此表达作者的伦理立场与生命观念。
关键词:家族;家族文化;家族小说;叙事伦理
一、家庭、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
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空间上讲,它是人类生息、繁衍和生活的一个常居住所。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家是以特定的婚姻关系为基础,并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相维系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①。恩格斯认为,“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②,实际上指出了家与社会的内在关系。《诗经·蓼莪》写道:“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③ 可见每个人从出生之时就离不开父母,离不开家庭。“家庭这个名词,人类学家普通使用时,是指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④ 马克思认为“家庭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⑤。还有学者指出:“家庭,是一种具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被认为是持久的并且跨越代际的。”⑥ 由此可知,从概念上看,家与家庭在社会学意义上是相同的,与婚姻、父母和子女有关,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
由一个家庭的成员扩大、分支与组合为多个家庭,就形成一种“家族”关系。那么,何为家族呢?从字面上理解,家族即多个家庭的聚合,但并不准确,因为这些家庭必须具有一定的血亲关系,往往是父族、母族或妻族中的某一种亲缘关系。因此,家族必以家庭为根基,这些家庭“虽然已分居、异财、各爨,形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的一定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⑦。显然,具有血缘关系的单个家庭是组成家族的基础,家庭与家族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通常而言,家庭成员往往是同居室、共财产、聚餐食,而构成家族的家庭往往分居别籍、异财各爨,相互之间以血缘关系聚合为群体组织。但家族又不同于宗族,宗是对先祖或身份显赫者的一种尊称,“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⑧。从概念内涵上看,宗族通常是由父系同宗的亲属家庭扩充构成,家族则包括父系、母系、妻族的亲属家庭,而且“家族以家族观念、系谱关系、人伦结构等观念意识为线索而繁衍,更多是一种情感性的联系;宗族则必须以其物质载体祠堂、族田、族谱为具体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它更倾向于一种工具性的联系”⑨。简而言之,宗族是在乡土社会中地缘靠近并合修族谱的同姓家门的大聚合,家族是以男性祖宗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群体,家族重血缘伦理的情感性,宗族重本族内部秩序和伦常的维持与管理。
其实,家族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存在,世界各地古已有之。“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以血缘关系划分居民让位于主要以地域关系划分居民,但血缘关系对各民族的影响仍然十分深刻”⑩,因此家族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在各家族长期的生息繁衍、日常交往与历史联系中,逐漸形成了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林语堂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11} 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法家族制社会,“殷代已有了宗族,产生了王族、子族”{12}。家族和宗族繁衍不息,在历史上曾形成“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室而居”{13} 的盛况。钱穆认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14} 作为社会的细胞和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家族承担着多种类型的社会功能,具有复杂的关系网络、礼仪规范和文化特征,“它不仅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连接起地缘的乡邻关系,而且它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其传承构成约束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15}。在乡土社会中,许多大型的民俗活动如祭祖、婚丧、扫墓、节庆等均以家族为单位进行,还有一些族内纠纷、祠堂维修、族田分配等事项也以约定的家族制度进行解决。家族因自身的血缘性、地缘性和历史性而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文化形态,它建立在儒家伦理基础之上。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16}说明家族文化对家族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家族成员逐渐形成了“家族至上”或“家族本位”的理念。家族本位的思想实际上跟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家族治理模式有关。在古代王朝社会,“家”与“国”是同构关系。古代帝王把国家政权视为私有,世袭相传,把整个国家当作一己的私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7},即为此意。故而有学者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际上是“十几家人”把持天下、轮流坐庄而已。秦始皇一统天下,到秦二世时国家分崩离析,“秦家”皇权仅沿袭十余年;汉朝几百年都在“刘家”牢牢统治下;隋唐两代分别是“杨家”和“李家”的天下,如此等等,古代“家天下”的皇权统治无形之中强化了家族文化与家族意识,“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的兴衰史”{18}。
既然自古以来“家族”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单位,而且“家族”存在的范围之广、历史之长都是既定事实,那么作为以血缘结合、地缘结合和人情结合为纽扣的文化复合体,家族本身就容易构成小说叙事的潜在文本。实际上,从古到今,无数曲折离奇的家族故事、波澜起伏的家族命运和风起云涌的家族英雄,都潜在地构成了家族小说的创作资源。
二、家族小说与伦理立场
何为“家族小说”?有论者指出:“家族小说就是以家族兴衰为透视焦点,以父子、母子、夫妻等人伦关系为描述中心,进而波及人情世态,通过家族社会生活的兴衰荣枯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本质生活的小说。”{19} 很显然,家族小说具有“类型性”,它以“家族”为题材,以家族故事、家族伦理为叙事基点。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家族题材与家族叙事“在我国汉代的史传文学中就已经孕育了这种小说的某些因素”{20}, 如《史记》中的“本纪”和“世家”分别记叙帝王的功德言行和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已初具家族小说的题材取向与叙事特征。汉乐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书写相爱的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长辈驱离后,被迫自杀殉情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所记的“干将莫邪”其实是写儿子为家父报仇的故事,涉及到一家之中的两代人与国君楚王的恩怨。从人物设计和故事情节上看,这些史传文学作品已有家族小说的雏形,但家族小说的成型与确立直到明清之时才得以完成。明代吴承恩《三国演义》看似在讲述魏、蜀、吴三国之事,实则是写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个大家族的历史与命运。后来的《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作品,则以家庭世态为题材,刻写家庭矛盾与纷争,被称为家庭小说{21}。实际上,“一树千枝”结构的《金瓶梅》由西门庆一家而写及当时的天下国家,波及很多家庭与家族,已完全具备家族小说的题材特征与叙事旨趣了,而《红楼梦》的面世则标志中国古代家族小说完全走向成熟。曹雪芹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构书写了贾家、史家、王家和薛家四大家族的兴衰,彻底打破了既往小说的窠臼,在思想与写法上均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对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的创作形成了深远影响。杨义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是一部曹雪芹没有写完,便泪尽辍笔的《红楼梦》。” {22}
的确,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沿用了《红楼梦》的质疑与批判精神,继续揭露封建家族的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再到路翎以苏州巨富蒋捷三为主角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以及端木蕻良书写北方草原家族的《科尔沁旗草原》,等等,这些小说都蕴藏着“反封建”的激切呐喊。此后,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金锁记》、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柳青的《创业史》、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小说,从对旧家族腐朽本质的揭露,到对革命家庭崇高人格的礼赞,再到对生命意志、家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从对封建伦理的解剖到对革命伦理的建构,再到对生命伦理与现代价值观的探寻,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实现了叙事风格和主题内涵的多样探索,“对家族生活与伦理情感的颠覆和解构走向了新的超越”{23}。
当然,家族小说不只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类型存在,西方也有不少经典的家族小说问世与流传。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6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年)、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1929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年),等等。这些小说要么以家族故事为框架,要么以人物命运为线索,既写开放型家族的兴亡,也写封闭型家族结构的发展,“作家们往往把家族盛极至衰的关口作为切入点或重点”{24}。在批评精神与叙事套路上,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与之大同小异,均以家族伦理为叙事基点。
既然家族小说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叙事的基点,那么以“伦理”和“叙事伦理”为关键词展开对家族小说的深入研究,就是应有之义。中国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礼制”社会,“大至治理国家、求学问道,小至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都有礼的规定”{25}。这种“礼制”其实是“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以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道德抉择为导向性作用的伦理体系”{26}。所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7} 构成了古代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不难发现,在封建“五伦”关系中,家庭血缘关系占有“三伦”,而贯通“五伦”关系的核心即是“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古人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德性修养、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个体与家相依,家与国不分,家族伦理往往可以上升为政治伦理,父权、夫权、族权与政权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有序统一的伦理体系。
那么,何为“伦理”呢?伦理与道德有何区别?从词形上看,“伦”从“亻”旁、从“仑”声,为形声字,本义指辈、类,引申为同族、同类之间的关系;理,本义指物质自身的纹路、层次,后来引申为条理、道理和标准等义。在西方,伦理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文的“Ethos”,原意为“本质”、“人格”,也指“風俗或习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三纲五伦”,“五伦”的主体是亲属关系,因此人们常说享受亲情的快乐是“天伦之乐”,而破坏这种关系的行为则被称之为“乱伦”{28}。所以,伦理的本义“就是客观的人伦之理,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原则和规范”{29},它必定跟道德相关、相通。从词源上看,两者“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都是社会道德现象”{30};但又有区别,“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31}。具体来说,道德以理性给人提出命令和要求,告诉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去做,让人形成内心自律,它是伦理规则的具体诠释,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伦理则是客观性和现实性的内容,“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的、客观存在的特殊关系,诸如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等”{32}。伦理关乎人性,通常渗透在政治、经济等一切社会关系中。
每个生活于社会集体或传统习俗之中的人,都会有一定的道德感,但道德以自律为根本,道德并不能靠国家机器来推行与运行,而是通过礼俗的教化作用和舆论的监督功能,让人对其产生敬畏和服膺之心,“一个人的人性与生物性的含量多少与比重大小,决定着人的道德的等次与习性的差比”{33}。当然,在家族社会里,个人一旦做了不道德之事,往往被视为触犯了家法、族规,会受到宗族势力的惩处。古往今来,宗族力量在“道德正确”的前设下,对家族子弟的道德惩戒与人性戕害不计其数,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惨剧。伦理道德本来出自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34},然而在古代宗法家族社会里,确实有“畸形道德是建立在践踏人的生命、尊严、价值即践踏人的人格基础上的”现象{35}。家族小说以表现家族命运的兴亡盛衰与个人遭际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内容,必然涉及家族儿女的道德生活与伦理关系,作者在讲述家族故事的时候,总会站在一定的伦理立场进行叙事,因此家族小说自然包含着巨大的伦理意蕴。
三、家族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家族小说要反映世道人心,当然跟人间的伦理紧密相连,每一个家族小说故事里面其实就包含着一个伦理事件,因为“文艺的使命在于探索通往人物心灵之路”{36}。伟大的文艺作品总能以涤荡人心的真、善、美精神让人产生情感共鸣,并纯化与升华人的灵魂,由此催人奋进。著名小说如《悲惨世界》《复活》就刻写了心灵的忏悔与改过自新,《巴黎圣母院》表现了伟大纯洁的灵魂与真实的爱,《罪与罚》《群魔》围绕“不可杀人”展开叙事,《红楼梦》从侧面探讨了自由心性与爱情自主的关系,等等。这些小说的故事虽为虚构与想象,但都内蕴着崇高的道德精神,激励人向善崇美。其实,家族小说同样可以通过虚构的故事再现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维关系,既鞭挞丑恶,又赞颂真善,既抚慰心灵,又弘扬正气,“因此也承担着与历史理性相对应的极其沉重的伦理道德责任”{37}。
可见,无论家族小说,还是其他类型的小说,它们都并非是超脱人间生活的海市蜃楼,只给人虚幻的审美感受,而是具有道德责任和伦理立场的叙事文本,常常拥有或明或暗的伦理性。那么,何为小说的伦理性呢?小说伦理是指作者必定以某种伦理价值观进行叙事,“是指小说家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时,在塑造自我形象时,在建构自己与生活、权力的关系时,所选择的文化立场和价值标准,所表现出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态度”{38}。一部散发感染魅力的经典小说,通常能给人以道德启悟、灵魂净化和审美愉悦,并揭示生活真相与人间真理。
当然,小说内在的伦理性需要借助外在的叙事形式表现出来。所谓叙事“指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39},或者说,叙事就是以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讲述故事,“叙事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将真实混乱无序而且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发展变得有序”{40},甚至叙事本身就含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它既能传达时代主流的伦理价值观,又能表达个体生命对宇宙人生的细微体察和伦理感悟。因此,小说的叙事也具有伦理性,所谓叙事伦理就是“在叙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41},或对故事本身所持有的道德立场与伦理价值观。叙事伦理“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42}。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书写世道人心,感应与呼应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以儒家伦理文化治理社会,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不同时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心理。古人倡导“文以载道”,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们心中大多有一个“立德、立言和立功”的共同理想,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文章与著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多是才子佳人与帝王将相的故事,文人的虚幻理想借以表达出来。这些小说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体现出一种“乐感”的文化情调,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贯穿始终,以封建道德为本位评价一切,极少关心个体生命与拷问灵魂。无疑,传统小说的叙事伦理融入了封建主义的家国情怀与忠孝思想,它采用了人民伦理的叙事视角,摒弃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立场。刘小枫认为:“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43} 在以群体价值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体寄生于群体,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44}。但很显然,无论采取群体叙事,还是个体叙事,小说叙事具有一定的伦理视角与伦理立场,这是公认的。
沈从文曾说:“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45} 可见,他也认可小说叙事的伦理性。“五四”时期的中国,注重个体本位的现代伦理与以群体价值为本位的传统伦理发生激烈冲突,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启蒙作家主张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家族小说因展现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神权对家族儿女的压迫,蕴含着巨大的伦理内涵,因而能承担起批判传统伦理的叙事功能。在很多现当代家族小说中,渗透着个性解放、婚恋自主的现代伦理思想,很多虚构的家族故事都采用了以生命和灵魂为中心的叙事视角,作者在字里行间潜在地呼吁尊重个体本位,反对抹杀个性的群体意识,小说叙事的伦理性不言而喻。
注释:
① 陈宗瑜:《婚姻家庭制度论》,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③{17} 《诗经》,韩伦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5、200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页。
⑥ 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彭铟旎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2页。
⑦⑩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⑧ 班固:《白虎通》,乾隆甲辰抱经堂版,卷3,第13页。
⑨ 江慧:《出世和入世:论家族和宗族的概念》,《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1} 转引自刘玉芳:《〈红楼梦〉对巴金张爱玲的家族小说创作影响比较》,《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6期。
{12} 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3} 杜佑:《通典》卷3《食货·乡党》,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1页。
{15} 赵德利:《家缘与诗思:家族小说的两难选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6} 《孫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0页。
{18} 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9} 楚爱华:《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20} 许祖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家族小说(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1}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
{22} 杨义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23} 曹文书:《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24} 邵旭东:《步入异国的家族殿堂——西方“家族小说”概论》,《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
{25}{35}{44} 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38、209页。
{26}{34} 张艳梅:《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7页。
{27} 孟子著,牧语译注:《孟子》,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28}{31}{32} 王明辉:《何谓伦理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8页。
{29} 朱海林:《伦理关系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30} 罗国杰:《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33} 王恒生:《家庭伦理道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36} 曾钊新、吕耀怀:《伦理社会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7} 祝亚峰:《叙事伦理:小说叙事研究的现代形态》,《东方丛刊》2009年第2期。
{38} 李建军:《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39}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40}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41} 徐岱:《叙事伦理若干问题》,《美育学刊》2013年第6期,第31页。
{42}{43} 刘小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45}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作者简介:徐汉晖,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凯里,556011。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