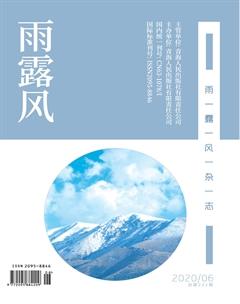《骆驼祥子》语言的地方特色研究
江琴



摘要:老舍先生是一位接地气的语言大师,是京味小说的开创者。《骆驼祥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他充分运用北京话的儿化音、口语、俗语,生动全面地展现了北京各阶层人的真实生活、风土人情,让小说具有鲜活的北京地方特色,使《骆驼祥子》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经典作品,历久弥新。
关键词:骆驼祥子;语言;地方特色;北京话
老舍先生善用北京话,在《骆驼祥子》一书当中,以浓厚的北京方言为特色,虽然没有运用华丽的词汇进行修饰,但是用词简单,语言通俗易懂,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老舍先生指出在写作过程中应该运用比较平常的文字,不过又应该在强调平易的同时,避免文章的死板,老舍先生比较擅长在原本平易的文字当中增加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感觉。在《骆驼祥子》当中,老舍先生就比较纯熟并且准确地运用了北京人比较常用的口语,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比较生动形象并且鲜明地表现出了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在下文当中,笔者就以《骆驼祥子》为例,对书中语言的地方特色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一、《骆驼祥子》中描绘的地方语言特色
在《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当中,从叙事、写景到人物对话、作者的议论,老舍先生运用了地道的北京口语。这不仅没有显得晦涩难懂,或过于华丽,而是每一个地方都透露出了一种亲切的感觉,给人新鲜活泼之感。老舍先生在一种俗白的写法当中,把精致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老舍先生还非常巧妙地将语言的通俗性以及语言的文学性统一了起来,使得文章异常干净利落,简单又不粗俗。
老舍先生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是非常讲求技术性的,并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俗”,一个是“白”。其中,“俗”主要是指老舍先生对最为普通的市井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与刻画,有风俗也有民俗。而“白”主要指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运用的语言通常都是比较朴实的,对于北京市民的口语可以说是非常重视的。
(一)儿化音的使用特点
“儿化”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中的一种语言现象,不要看这样一个小小的卷舌动作,却有重要的语法作用和词汇作用,儿化音既表示亲切、喜爱、轻松随意等情感色彩的,同时也使得北京话因而著名。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总共出现772种带有“儿化”的词组,其中多达417种以名词性质的儿化音,同时还有134种的量词、97种的动词、76种的代词、38种的形容词以及4种数词的儿化形式。《骆驼祥子》中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儿化音的写作,使得作品在合理运用儿化词后让作品的语言风格尤为亲切、生动、活泼,并很好地展现了语境氛围、人文性格。比如说,像“抄着根儿”“冒儿咕咚”“上下一边儿多”“搁在兜儿里”“没错儿”“黑签儿会”“不像回事儿”“赶明儿”“实诚劲儿”等儿化音比比皆是。
(二)“京味”口语的运用
老舍先生在写作《骆驼祥子》的时候,运用了很多代表着北京地方口语化特色的词句。比如说,“放鹰”是常用的一个北京方言,指的是清朝末年北京的八旗子弟经常会玩鹰,但是一些没有训练好的鹰放飞以后就不会再飞回来了,后来这个词被生动并且形象地用以比喻钱财借出去就还不回来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北京方言口语词汇,比如说“冒儿咕咚”“赶明儿”等等。这样的词语都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可以体现出人物的性格或生活的场景等,使得《骆驼祥子》这部文学作品更加具有“北京韵味”,也使得作品显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契合了语言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比如说在对祥子从军阀部队逃出来之后喝馄饨的场景进行描述时,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热汤像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这样的描写手法,基本上就是北京人日常会用到的口语,口中含汤、热汤传身这样的细节描写,给读者带来了非常具有生命感的心理体验。
(三)善用俗语
俗语是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被广泛运用,有着口语性、通俗性等特点,但是同时又是一种固定使用的语言。老舍先生的作品很多是描写中下层市民生活的,在老舍的笔下,这些平民化的语言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在《高妈》这个章节中就运用了很多俗语。当高妈对祥子进行了一番耐心的劝说,但是祥子却无动于衷的时候,高妈使用了一句歇后语,即“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充分体现出了祥子来自骨子里的倔强。再比如说,高妈用“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话对放高利贷的人进行了重点刻画。还有很多其他的俗语,例如“打水上飘”“海里摸锅”“晴天大日头”“堵窝掏”等,运用了这些俗语使得人物的形象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也使得文章的整体语言更加活泼、更加有趣。
实际上,通过老舍先生对高妈的描写可以发现,《骆驼祥子》这本小说的语言就好像是一杯上好的茶,需要细细品味,第一次读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平淡,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是越读就越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韵味。用老舍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骆驼祥子》的语言是“平易”且“亲切”的,同时又是“新鲜”“恰当”,而且又非常“活泼”的,非常耐人寻味。
二、北京口语与俗语展现出北京的风土人情
老舍用原汁原味的北京口语、俗语将北京的风土人情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事情在当时似乎是地域性的,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老舍的这种北京风格,特别是针对《骆驼祥子》中的对话、叙述、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在现代文学中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了,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老舍运用的语言方式和现代汉语如出一辙,因此在这里也不做过多的讨论。我们现在从不怎么被提及的方面,也就是写景的角度来看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骆驼祥子》这篇著作与现代汉语几乎是一样的,就像是“孪生”一样。
人们一直称赞《烈日和暴雨下》的写景,作者在此使用了不少北京方言中的口语词汇,也使用了很多普通话中的口语词汇,用“每一种气味都搀合着地上蒸發出来的腥臭”“铺子里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来形容酷热。运用了“搀合”和“攥”这样的方言词,再加上其他的描写方法,就可以让读者感到难以忍受酷热、盼望凉风的确是北京人。如果在这里将“搀合”换成“夹杂”,将“攥”换成“拿”,那么其语言的地方色彩和感情色彩马上就会被减弱。当然,老舍运用的北京方言,是经过提炼、挑选的,像这段描写里应用的“张罗”“吆喝”“成心”“利飕”“反正”“憋闷”等,现在已经成为普通话的词汇。所以即使是纯粹的北京方言,放在上下文中,南方的读者也能读懂的,例如“攥”“漾”等。至于只有老北京人才懂的“归了包堆”(总共一处),“磨炀(拖时间)”,“横是”(大概是)这一类话,在《骆驼祥子》里是极少数的,只有在很少的时候被使用。
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直都是很严格的态度,甚至严格到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这篇文章的语言,却是很满意的,他说:“《祥子》是可以朗诵的,因为它的语言是活的”。《骆驼祥子》中所采用的词汇,来自于北京话的口语、俗语,以及典型的北方方言,这些语言也是普通话文学的经典例子。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老舍就已经开始尝试用现代人的语言进行创作了,从这一点上看,老舍是普通话创作的鼻祖。
三、成串的北京地名呈现给读者一个鲜活的北京城
在文学作品中加入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地点、社会、阶级等,这些都是老舍文学著作的重要标志。比如老舍文学中大多数描写的都是老北京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北京在他的描写下非常的生动、写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地点、胡同,以及名胜古迹和各种风景,大多数都运用到了真正的地点的名字,读者都可以实地进行考察。在老舍的作品中,大多数都以具体的路径作为文章的一条线索,而这条路径是从始至终都非常清晰,非常详细的。像《骆驼祥子》这部著作就展现了这一点,这其中的描写也最为精彩。
比如在《骆驼祥子》这部著作中,重要事件中主人公所经过的地点就可以概括为七次行动路线,这也就构成了七大串地名。第一次,祥子拉着新车被大兵抓走时的路线就是由新街口出西直门过高亮桥;第二次,祥子牵着一匹骆驼一路出逃,先到了磨石山路口,往东北方向拐过金顶山,随后继续路过宝山礼王坟、八大处、四宝山平台、杏石口、南辛庄、北辛庄、魏家村、南河滩、红宝石出头、杰王府、静宜园、海淀,最后一路到达西直门;第三次,祥子拉曹先生回曹宅时从东城路过天安门,到南长街中了埋伏,摔了跤,伤了人,砸了车;第四次,虎妞找祥子谈话,由南长街贴着中山公园红墙往北走,一路走到北长街北头,又上北海大桥过金鳌玉,祥子回身走时,几乎碰到团城的墙上又被虎妞喊回去;第五次,祥子拉曹先生從西城回曹宅时,路过西单、西长安街、长安牌楼、新华门、南长街口、中山公园后门、北长街北口、进小胡同到了景山背后又到了黄化门最后到了左宅;第六次,祥子结婚后,从毛家湾直走到东西四街,再走到宣武门后再往南向东,再向南直走到地下天桥后再出来逛街散心;第七次,祥子在找不到小福子时,出西直门过北京高粱桥,到北京铁道北,到处是白房子。
这每一段描写都是北京的具体路线,读者不再觉得北京的每一处地点是自己遥不可及的,而是自己可以感知、可以感觉到,这会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触感。从另外一个文学角度上来看,从以上的关于骆驼祥子的各种故事地点的具体描写以及其他的文学作品的地点描写中,读者也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老舍所描述的大多数北京地点都应该是北京的西北角。而北京的西北角正南部属于正红旗,北部偏西属于镶红旗,老舍的父亲是清朝统治时期属于镶卫正红旗的一个护军,因生长地点等种种原因,他更多地了解北京西北角。老舍所描写的作品被拍摄为影视作品的,它们大多数拍摄地点主要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而在这众多地点中,老舍最喜欢的便是积水潭,就是以前的净业湖,它在净业寺的南边,因此该湖得名净业湖,后来因为西山的一处泉水从高亮桥向南流入城内外并汇集于此,因此将湖改名为积水潭。而这个积水潭在《骆驼祥子》中也依然有他关于它的感情描写,在《骆驼祥子》中积水潭是组织洋车夫罢工的阮明被国民党枪毙的地方。此时老舍对积水潭的描写悲惨感情描写之后,但是对于它的感情描写依然依旧保留着非常美的视觉体验,他对于湖中的绿色荷花和绿芦苇以及岸边和附近水面上的鲤鱼蜻蜓等的感情描写依然绘声绘色,也充分表达了老舍的极深的爱国感情。
老舍之所以对这些地名都有非常强烈的情感,是因为这是他生长熟悉的地方,他认为,一草一木皆是有感情的。从生长的地方写起,作者的描写与真实的情景之间是关联的,也是由于老舍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因此才让北京城在读者眼里鲜活起来。
四、“京味儿”十足的语言更丰富了小说的地方特色
用口述实录来描述老舍的小说是比较合适的。老舍用地道的北京方言,以风趣幽默的笔触使性格各异的人物跃然纸上。阅读老舍的小说,就好像是在与其勾勒的人物进行对话,仿佛观众在观影一般——老舍描绘的北京市井气息呼之欲出,让读者好似置身其中,成为小说中的一分子。
老舍用干练的老北京方言将《骆驼祥子》社会风气鲜活地描述出来,细腻地描绘北平地区平民百姓的言行举止,朴实自然,简洁明了。字里行间用地道的方言点缀质朴北京生活和北京人交谈时的亲切感与活泼感,使小说京味儿十足。
《骆驼祥子》仅仅只用2400多个汉字,完成了11万字左右的全书,老舍频繁使用常用字以及京味儿厚重的地道老北京话,使语言俏皮可爱。举个例子,北京方言中狭隘的四字语“秃尾巴鹰、海里摸锅”以及北京的重口味方言“搁下”,和儿化语“没错儿、一个子儿、兜儿”,都从侧面反映出老舍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语言的熟悉和了解的透彻。北京人口语化的表达,贴切地刻画出人物的地位、性格、教养,老舍在虎妞勾引祥子的话语中,将虎妞的泼辣老处女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骆驼祥子》中的语言动作描写都是极具个性的,没有冗杂的文言虚实词,也没有西式语法,只用通畅精准的北京口语,长短句交错相间,使小说阅读起来富有韵律。文字经过老舍的精心调度,使通俗浅显的北京味缀满新奇感,使读者如痴如醉。老舍刻画人物时,用犀利的笔锋干练的词汇将人物饱满化,让人对其文字的张力直呼过瘾,当描写刘四这位地痞流氓的过往和性格时,老舍如是描绘:“打过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言语简单明了,又饱含深意,文字像是刘四身上的装饰品,将一个无赖形象立体地展现在读者书前。《骆驼祥子》人物的心理活动鲜活于老舍的主观剖析和客观陈述。祥子结婚后的心理活动:“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桶也不如的人”既是老舍的客观描述,又像是祥子内心的思虑,两者水乳交融。一如书中描绘的烈日和暴雨,都是祥子的心中映射。
老舍在书中毫不吝惜北京口语,北京话的风趣、鲜明、活泼,老舍坐拥地利之和,老舍的文笔被尊为最俏皮、最富有乐感、最流畅上口的文笔丝毫不为过。些时还有人贬低其文字间地域气息太过浓重,但后来普通话和国语都恰好指定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北京话包含地域风情又具有大众色彩,这又成为老舍先生的一大助力,《骆驼祥子》中的文学魅力,充分体现了老舍于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造诣。
老舍生于北京的底层胡同,于京味儿十足的北京阡陌中成长,特点鲜明,如同他屡次书写到的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幼枣树一般,极度匮乏水分,营养甚至土壤,但它仍旧在巍峨城墙的缝隙中挺立而出,顽强地成长为挺拔的大树,别具风味,使人赞不绝口。
五、结语
《骆驼祥子》的语言覆盖了生活性和艺术性,老舍先生在用通俗易懂,同时又富有地方韵味的生活语言,把一个又一个有着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塑造了出来。无疑《骆驼祥子》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其经典之处不仅体现在运用了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上,更也体现在老舍先生运用了充满北京特色的语言艺术上。语言的地方特色是历史以及生活积累的产物,只要有人类生活的延续,地方特色就会永远存在。地方语言特色的优势体现在对文化氛围的传递上,使得文化经验以及语言表达得以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能够对文学表达的空间进行进一步的扩宽,不过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处理,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
参考文献:
〔1〕廖玉萍.论《骆驼祥子》语言的地方特色[J].教育与职业,2004(21):37-38.
〔2〕刘敬,尹领巧,马旭娟等.从《骆驼祥子》看老舍语言特色[J].金色年华(下),2012(7):12.
〔3〕杨帅.从《骆驼祥子》分析老舍语言特色[J].语文课内外,202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