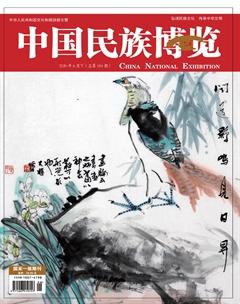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乐器——彝族阿乌
【摘要】阿乌,彝族撒马支系和子君人边棱气鸣乐器。通体用粘土和泥捏制而成,也有的经火烧成陶制。因吹奏发出“阿乌、阿乌”声而又称布里拉,是取古代《阿乌歌》的首句歌词命名。流行于云南省昆明市近郊官渡区彝族撒马支系和子君人中。
【关键词】阿乌;彝族;云南
【中图分类号】J632.2 【文献标识码】A
一、历史传说
关于阿乌的传说有很多,但其中流传甚广的是:很早以前,云南子君人住在龙宝山上,山下有个龙潭,潜居着两条龙。这里水清草嫩,人们放牧着牛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后来,龙潭干涸,草儿枯黄,连人的饮水都极为困难,原来是两条龙相斗所致。一个放牛娃抓起塘泥捏了一个空心饺子形的玩具,对着天空吹奏起来,发出“阿乌、阿乌”的声音,天天吹啊天天吹,突然,龙潭水满了,又疏通了滇池的泄水河,滇池水位下降,露出大片土地。原来阿乌声感化了双龙,它们不再争斗了。此后,子君人迁到平坝生活,每年到了栽秧时节都要制作和吹奏阿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二、阿乌与陶埙
阿乌:历史悠久,虽无实物记载,但也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主要流行于云南省昆明市近郊的官渡区彝族撒马的支系和子君人手中。是求雨、祭祀、沟通天人的神器,寓意风调雨顺、企盼来年五谷丰登。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 其作用和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1]
陶埙:中国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我国特有的古时期的乐器,[2]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距今约7000年,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埙。
(一)阿乌、陶埙两者的区别
在乐器演奏方面,由于手持方式不同,阿乌在吹奏时两手端于底部,使阿乌在演奏时稳定性较高,手指可以在乐器上快速活动,不但可以演奏速度较慢的抒情乐曲,也可以演奏速度较快的情感热烈的乐曲;而陶埙在吹奏时双手位置在乐器两边,乐器底部没有支撑,使陶埙在演奏时稳定性较低,如若演奏节奏较快的乐曲,乐器有可能掉落以至于造成乐器的损坏,所以,陶埙较适合演奏速度较慢的抒情乐曲。
在音色方面,阿乌的音色野性十足,张力较大,演奏时声音拥有一定的爆破力,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音乐魅力;而陶埙的音色偏向舒缓、柔美、古朴,其声音具有中国古代汉族音乐的特色。
在乐器制作方面,虽然阿乌存在年代久远,但因材质等方面的原因传世甚少,制作者较少,甚至几乎濒临灭绝,所以导致阿乌的制作理论缺乏,制作工艺不完善,音准问题、形制问题等还有待提高;而陶埙年代久远、流传广、制作工艺完善、制作理论丰富、制作者较多,吹奏者多,普及性广。
在音域方面,阿乌的音域较窄(以八孔阿乌为例),其音域区间为十二度,而陶埙的音域较宽(以十孔埙为例),音域区间为十五度。
在乐器音量方面,改良后阿乌的音量大约为埙的两倍,在舞台上无需借助任何扩音设备即可演奏,而陶埙演奏时音量较小,如舞台较大则需借助扩音设备。
(二)阿乌的乐器改良
1.原始的阿乌
原始的阿乌只有一个吹孔和两个指孔,仅能发三个音(大三度)。以F调的三孔阿乌为例可以演奏出:F音、降B 音、C音。原始阿乌音准问题堪忧,原本阿乌就是以用于祭祀的神器出现的,用于彝族部落祭祀求雨,并不是以乐器的身份出现,所以最早的阿乌对音准的要求并不高,而且制作材料也十分简单,只是拿水溏泥或者泥巴捏制成形制呈水饺状,下宽上窄的形状,捏制成后用工具把阿乌表面刮干净后,再进行开孔,完全没有调音过程,并且由于制作材料随意,乐器的保存性较差,基本都是一次性乐器,所以每次祭祀活动所用的阿乌都是现制乐器,在原来的部落祭祀活动中只有彝族的大祭司或是长者才会制作和演奏阿乌,导致传世的阿乌数量很少,缺乏实物,为后续对阿乌的调查和研究增添了许多困难(图1为后期仿制的原始阿乌)。
2.初次改良的阿乌
子君村村民李利春对阿乌进行的改良:在原来的基础上,由两个指孔拓展到六个指孔,使得音域变宽,但吹孔大小未改变。李利春对阿乌的改良是有相对局限性的:首先,李利春本人是子君村的民间艺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学习,对于乐器的发声原理、乐器的调音等方面是有待提高的,所以,导致他制作出来的阿乌音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次,他在乐器制作方面使用水溏泥或者是泥巴,由于制作材料的不稳定性,导致乐器的质量和美观程度都存在这一定的缺陷,并且制作完成后没有在阿乌上使用保护材料,所以阿乌的保存性较低,乐器容易发生形变的可能性提高。但是,通过李利春大胆的开孔,使人们突破原有阿乌的局限,开辟了对阿乌这个乐器改良的新思路。优点:易学易吹,音色深沉浓郁,古朴凝重;缺点:指法不易接受,音域偏窄,张力不够,音准还是最大的问题(图2为李利春改良制作的阿乌)。
3.现代的阿乌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张文俊老师的改良:在李利春的基础之上改良了指法,通过扩大吹孔增加了音量(大约是埙的两倍),并且增加两个后音孔,拓展了音域,音域扩展成为十二度,以C调阿乌为例,分别是:首先筒音全按,通过调整吹孔角度,以俯吹的方法可以演奏出小三度(D音、E音、F音),其次筒音全按,通过平吹的方法可以演奏出G音,最后依次将指孔打开,吹孔角度随着音阶上行,慢慢上扬(A音、B音、c音、d音、e音、f音、g音和a音)。改良后的阿乌整体呈系统化,共分高音、中音、低音三组,每组拥有十二个半音调的阿乌,共36只阿乌,包含了从大字一组F调——小字一组f调之间的任何调。对之前阿乌的音准方面又做出了较大改进,使音准更加准确,还使其音色更加厚重深沉、圆润优美。最后,民间的阿乌多用水塘里的泥巴制作,水塘泥形制松软,可塑性较差,粘合性不高,烧制成型率低,改革后的阿乌采用陶土制作,各方面属性都大大增强,沿用至今(图3为云南民族大学张文俊教授改良制作阿乌)。
4.阿乌的现状
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一件“神器”的地位,沦落为一件纯娱乐的乐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几近濒临失传和,处于灭绝的边缘。形制上拘泥于传统,千百年来没有太大的改进,鲜有人去发掘和改进,棘手的音色、音准和演奏技法等问题有待解决。几乎没有几首可传遍大江南北的代表曲目,往往都是移植葫芦丝、巴乌或歌曲以及西方曲目,由于原始阿乌音域的限制,存世作品本身就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阿乌的乐曲大部分已失传,《阿乌情》是目前流传较广的独奏曲;《布拉里》是由彝族祭祀求雨时所用的音乐进行改编创作的。新创作的专业曲目极少。
三、对于拯救阿乌的一些思考
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加大乐器的申遗和拯救工作力度,增加对传承人的保护,在音乐类院校中培养制作阿乌、演奏阿乌的传承人。加大对乐器的制作和改良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制作工艺研究,可以学习和借鉴陶埙的研究理论和制作工艺,学校要加强对于阿乌的普及和学习,将专业培养和乐器普及相结合(云南省昆明市子君中心学校组织师生正在进行学习),组织专业作曲人才和演奏人才相结合创作出一些适合和突出阿乌乐器特点的优秀作品,这样才能使阿乌被人们所了解、喜爱。
参考文献:
[1]陈汐.试论中国埙的文化意义[J].当代音乐,2019(9):143-145.
[2]于珊珊.音乐考古学在音乐学中的价值[J].当代音乐,2016(2):83-84.
作者简介:王键淞(1994-),男,汉族,山西太原,硕士研究生,民族器乐三级演奏员,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竹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