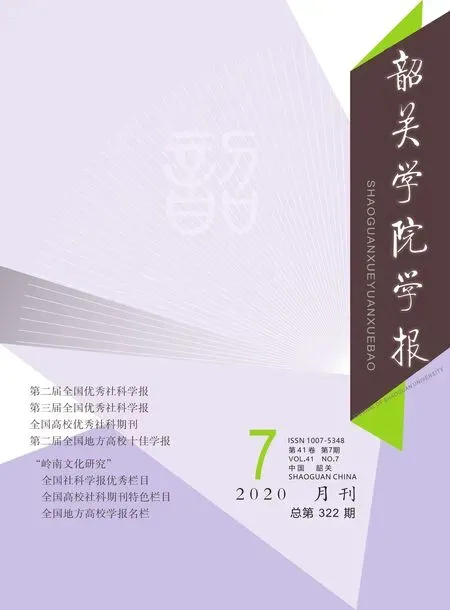轻动词理论视野下的现代汉语一元动词句
冯诗涵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Grimshaw & Mester在讨论日语中的suru结构时指出,suru的意义非常虚化,类似于英语中的do,它常和一个名词性成分组合,构成一个复合动词结构。这个复合动词结构的意义和及物性由结构中名词的内在属性决定,suru在这个复合动词结构中并不贡献词汇意义,它只起功能作用:当suru和一个名词构成一个复合结构时,suru则为该结构的屈折功能提供了一个着陆点[1]。鉴于suru在语义上的“轻”及其在复合结构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functional role),因此它被称为轻动词。Huang C T指出,日语中的“verbal-noun”在汉语中通常被看作动词[2]。而在日语中,“verbal-noun”必须与suru同现,构成一个复合的动词性结构。日语中的suru有两种形式:一种suru与一个带有宾格标志的“verbal-noun”同现。在这一结构中“verbalnoun”作为名词出现,带宾格的“verbal-noun”做suru的宾语,构成“o-suru”结构。另一种“verbalnoun”以光杆形式前置于“suru”,这时的suru才是Grimshaw & Mester所讨论的轻动词。当suru作为轻动词使用时,类似于Huang C T提出的“事件谓词”。它在语义上选择一个事态(eventuality),在语类上选择一个VP为其补语,同时底层词汇性动词提升至上层轻动词,构成一个复合谓词结构。
Larson的“VP-壳”(VP-shells)理论是为了解决英语中的双宾语结构而提出的,被认为是轻动词理论的前身。它包括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句法结构中的一个谓词可以有多层VP投射,每一层VP都是一个二分支结构,如果一个动词带有多个论元(超过两个),那么这些论元必须分属于不同的“VP-壳”;第二,句法结构中的论元分布是由一个普遍题元层级(Thematic Hierarchy)决定的,带有不同题元角色的论元按照题元等级分布在“VP-壳”的不同句法位置[3]。“VP-壳”为这些题元角色提供足够的句法位置。
Hale & Keyser在“VP-壳”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英语派生动词的分析,提出词汇化(conflation)本质上也是一种句法运算。L-syntactic是句法中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门,有其词汇关系结构(Lex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s)。他 们 还 提 出 了 事 件 结 构(event structure)的概念,指出句法结构是事件结构的体现[4]。
Huang C T和Lin T H结 合 现 代 汉 语,对Hale & Keyser的观点进行了发展。Lin T H认为:英语中的轻动词在表层句法上是隐性的,而汉语中的轻动词有显性的;英语的轻动词结构是在词库层面的,汉语的轻动词结构是在句法层面[5]。Hale & Keyser认为事件结构和句法结构直接关联[4]。Lin T H认为,句法结构和事件结构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他结合汉语和日语的例子指出,一个句法结构可以对应多个事件结构[5]。由于英语中的轻动词是放置在L-syntactic层面上的,词汇化在轻动词结构中是最重要的操作,因此一个句子中的论元要在词库中受到允准,汉语中的轻动词是放在S-syntactic层面上的,所有的轻动词全部被送到句法层面进行运算,所有的论元在句法层面上受到允准,而日语则介乎L-syntactic与S-syntactic两 者 之 间。Lin T H将 汉语、英语、日语的这一区别归因于语法参数的不同。在英语中,当一个非宾格动词与一个使役动词(隐性)合并,非宾格动词的主语可以是一个施事、工具、或者自然力(natural force)。而汉语中的非宾格动词只能有非宾格的用法,如果想让它有使役的用法,就必须增加一个有形动词到句法结构中去,形成一个复合动词(verbal compound)。其使役—施事成分与起始—结果成分将在事件结构中独立体现,比如Lin T H所示例句:
(1)The window broken.
(2)John broken the window.
(3)The wood broke the window.
(4)The hurricane broke the window.[5]
与之对应的汉语例句:
(5)窗户破了。
(6)张三打破了窗户。
(7)木头撞破了窗户
(8)台风吹破了窗户。
“打破”“撞破”“吹破”实际上是来源于多重VP结构,底层动词选择不同的上层轻动词进行合并。汉语中的相关运算都是在句法层面进行的,事件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对应体现在:当事件结构的核心是一个起始谓词时,就只对应一层VP,当事件结构的核心是一个使役—施事谓词时,就在句法结构中对应两层VP。根据Huang C T与Lin T H的观点,英语中的轻动词在语音上是空的,而汉语的轻动词可以有语音形式。当汉语的底层动词一样时,在上层增加不同的轻动词就会形成不同的复合动词,轻动词决定事件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Chomsky N在《最简方案》里所定义的轻动词是隐性轻动词,它没有语音形式,只有一个空位置[6]。Radford认为轻动词可以选择任何类型的动词作其补足语,所有动词的上层都有轻动词层[7]。笔者认为动词实际上是“轻动词+词汇性动词(Lexical verb)”的复合动词。在汉语中,所有VP的上层至少有一层vP。一元动词、二元动词、三元动词之上均有轻动词层,只是不同类别的轻动词选择不同的词汇性动词充当其补足语。进而我们假设,汉语动词在论元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是由于其上层含有不同的轻动词所致。Huang C T扩大了轻动词的使用范围,将轻动词定义为由纯动词表示的事件谓词,他指出当汉语的底层动词一样时,在上层增加不同的轻动词就会形成不同的复合动词,他将轻动词分为“DO(做)”“CAUSE(使)”“OCCUR(发生)”“BECOME(成为)”“HOLD(保持)”等几大类[2]。
一、轻动词理论视角下的现代汉语非宾格动词句
Perlmutter提出非宾格假说(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把一元动词分为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和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非作格动词无论在D-结构层,还是在S-结构层均只有一个施事外论元。非宾格动词则与位于补足语位置上且负载主题角色的论元共现[8]。Burizio将Perlmutter提出的非宾格假说加以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博济欧原则”(Burzio’s Generalization):没有外论元的动词不能指派宾格;不能指派宾格的动词没有外论元[9]。可见,非宾格动词没有外论元,也不能指派宾格。
一般认为,当现代汉语中的一元动词既能出现在“NP1+V+NP2”中,又能出现在“NP2+V”中,这个动词就是非宾格动词。曾立英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个诊断式:“使+N+V”和“NP2+自己+V了”作为判定汉语非宾格动词的标准[10]。杨素英提出不带地点的存现句、天气句、使役/不及物交替的句子都可以用来区分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能在这些句式出现的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11]。需要注意的是,非宾格动词可以出现在存现句中,但出现在存现句中的动词不止是非宾格动词。大部分非作格动词具有[+自主性]和[+可控性]等语义特征。我们可以将学者们提出的上述句法诊断式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结合以区别汉语中的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
根据Perlmutter提出的非宾格假说以及Burizio提出的博济欧原则,现代汉语中的非宾格动词,如“沉”“漂”“死”等,其名词性论元起源于补足语位置,但其表层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例如:
(9)沉船了。
(10)船沉了。
(11)长江沉船了。
(12)水手们沉船了。
在“沉船了”和“船沉了”中,“船”负载着“沉”施派给它的主题角色。根据题元施派一致假说(Uniform Theta Assignment),两个结构中的“船”在D-结构层一定起源于同一个位置,即“沉船了”和“船沉了”有一个相同的D-结构层。在例(9)中,“船”是非宾格动词“沉”的主题论元。“沉船了”这一命题表达的是一个事件的发生,我们假设,动词“沉”的上层存在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BECOME。我们所看到的“沉船了”其结构是:[BECOME+V]+N,见图1。

图1 “V+主题”
在这一结构中,轻动词BECOME是一个功能词,它具有强吸附性,吸引词汇性动词“沉”提升至轻动词处,形成“BECOME+沉”,词汇性动词“沉”释放出主题角色给论元“船”。由于“沉”是非宾格动词,故“船”在这一结构中,不能从动词“沉”处获得宾格,而是获得轻动词BECOME渗透下来的斜格①只有及物动词的上层轻动词才能施派宾格,其他类动词的上层轻动词只能施派斜格。。
在例(10)中,主题论元“船”位于非宾格动词“沉”的主语位置,这似乎违背了非宾格动词只与位于补足语位置上的主题论元共现的定义。其实,在“船沉了”这一结构中,“船”不是“沉”这个动作的主动发出者,结构中存在另一个实体“使”(CAUSE)“沉船”这一事件发生。“船沉了”的底层结构是“CAUSE+沉船了”,这样,“船沉了”和“沉船了”在VP层的结构就是一致的。在“船沉了”中,“沉”先跟“船”合并,后受到轻动词CAUSE的吸引,移位至轻动词层,形成“CAUSE+沉”,接着再移位至T,获得“时”特征。最后,“船”从V的补足语位置移至C的标示语(Spec)位置,满足EPP特征,并获得上层C渗透下来的主格。在“船沉了”中,“船”跨越了vP层和TP层,直接从V的补足语位置移到了C的标示语位置。这似乎违反了最简原则,其实不然,一是因为“沉”是非宾格动词,没有外论元,所以“船”不能移至vP以及TP的标示语位置(这两个位置均为外论元位置),故只能移至C的标示语位置。二是“船”在VP层已经接受了V施派的主题角色,不能再到vP的标示语处接受其他的题元角色。三是轻动词CAUSE释放的causer(致事)这一题元角色需要一个[+有生命][+可控]的名词性成分来负载,而“船”不满足这些语义特征,不能负载这一题元角色,因此不能位于vP的标示语位置,见图2。

通过以上两个树形图,我们观察到,无论是在“沉船了”还是“船沉了”中,“船”在D-结构层均起源于动词“沉”的补足语位置。“沉”是非宾格动词,在底层结构中,没有外论元,不能给“船”施派宾格,因此“船”要么提升至V的标示语位置,以尽量接近轻动词,得到轻动词施派的斜格,生成“沉船了”这一结构;要么直接提升至C的标示语位置,得到主格,生成“船沉了”这一结构。
例(11)有两个名词性论元“长江”和“船”,这似乎跟非宾格动词为一元动词的身份不符。其实,“长江沉船了”中的“长江”不是“沉”的施事论元,而是一个表示“地点”的外围论元。我们将一元动词严格地定义为:只与一个必有论元共现的动词。而外围论元通常表示附加信息,并不是必有论元,这样看来在“长江沉船了”中,仍然有且仅有一个表示“主题”的必有论元——“船”。
“长江沉船了”这一命题表达的是发生了一个事件。因此我们假设它存在一个轻动词BECOME。在这一结构中,轻动词BECOME具有强吸附性,吸引词汇性动词“沉”提升至轻动词处,形成“BECOME+沉”。词汇性动词“沉”释放出一个主题角色给主题论元“船”,轻动词BECOME释放斜格给“船”。“长江”作为表示地点的外围论元,不能生成在论元位置,故直接生成在CP层的标示语位置上,见图3。

图3 “外围论元+V+主题”
例(12)“水 手 们 沉 船 了”这 一 命 题 中,包含了两个事件:致使事件和动作事件,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动作事件是致使事件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其语义结构表达为:水手们CAUSE+BECOME沉船了。作为非宾格动词,“沉”只与位于内论元位置的主题论元“船”共现。“水手们”不是“沉”这一动作的主动发出者,不是“沉”的施事论元。根据我们的假设,“沉”之上有两层轻动词层,它们分别为BECOME和CAUSE,而“水手们”则是最上层轻动词“CAUSE”的外论元,即“致使者”(causer),见图4。

图4 “致使者+V+主题”
通过对上述结构的讨论我们发现,现代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可以出现在“主题+V”“V+主题”“外围论元+V+主题”“致使者+V+主题”四类结构中。从表层结构上看,现代汉语非宾格动词的名词论元并不一定在补足语位置,但在深层结构中,非宾格动词有且仅有一个主题内论元。造成其不同表层结构的原因在于,不同的非宾格动词上层包含着不同的轻动词层。
二、轻动词视角下的现代汉语非作格动词句
按照Perlmutter的定义,非作格动词是指与施事外论元强制共现的动词(“施事+V”)。汉语中同样存在这类动词,如:“笑、哭、飞、闹、跑”等,非作格动词只有外论元没有内论元,例如:
(13)孩子笑了。
(14)妈妈哭了。
(15)我睡了。
(16)一只喜鹊飞过来了。
(17)犯人跑了。
上文中,我们假设汉语的词汇性动词上层至少包含一个无音无形的轻动词,非作格动词也不例外。由于非作格动词只与一个施事性外论元共现,即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中包含一个动作的发出者,由此我们假设,非作格动词的上层包含轻动词“DO”,见图5。

图5 “施事+V”
在这一结构中,“笑”生成于词汇性动词V的核心处,它的上层有一个轻动词DO,DO是一个无语音形式的隐性轻动词。它具有强吸附性,吸引词汇性动词“笑”提升至轻动词DO处,形成“DO+笑”。非宾格动词的名词性论元起源于词汇性动词的补足语位置,那么非作格动词的名词性论元又起源于何处呢?Radfold假设所有的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的施事论元皆起源于轻动词的标示语位置[7]。我们也假设汉语非作格动词的施事论元起源于轻动词的标示语位置,如图5所示,“孩子”起源于DO的标示语位置,“笑”是DO的补足语。整个结构可以表述为:孩子做(DO)了一个“笑”的动作。轻动词只能给其C-Command的成分赋宾格,因此DO不能给Spec位置上的施事论元“孩子”赋格。图5中的结构图只画到了轻动词层,事实上,“DO+笑”还要往T层上移,以满足T上的“时”特征。同时,“孩子”也要从轻动词的Spec位置移位至T的Spec位置,以满足其EPP特征并得到主格。以上分析大致就是现代汉语非作格动词句的生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例句:
(18)郭德纲一开口,我们仨就笑了俩。
(19)妈妈哭了一上午。
(20)这节课太无聊,学生们睡了一大片。
(21)我睡了一整天。
刘探宙称这一现象为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12]。我们发现,在上述例句中,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宾语”全是数量(时量、动量)短语,朱德熙称这一类宾语为准宾语(动量词、时量词、数量词、数量名结构)。我们认为,准宾语不是典型的宾语,它在语义上通常是附加信息;在句法上,带不带准宾语,动词的论元结构都是充盈的,同时准宾语也常可以从补足语移至其他位置。因此,现代汉语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准宾语属于外围论元,不能将其看作非作格动词的宾语。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非作格动词带宾语这一现象,或者说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宾语”要么是附加性成分(Adjunct),要么是某种句式的变形。
三、结论
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是生成语法学派对一元动词所做的分类,其主要理论基础是Perlmutter所提出的非宾格假说和Burzio所提出的博济欧原则。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分类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一元动词,但现代汉语非宾格动词句和非作格动词句的表层结构均出现了一些例外。从表层句法结构上看,现代汉语非宾格动词所带的主题论元并不只位于动词的补足语位置,非宾格动词也出现在“主题+V”“外围论元+V+主题”“致使者+V+主题”这样的结构中。笔者认为在深层结构中,现代汉语非宾格动词只出现在“V+主题”这样的句法格式里,而其表层结构的多样化则跟非宾格动词上层的轻动词有关。典型的现代汉语非作格动词句是一个施事外论元和一个非作格动词所构成的小句,但有学者提出现代汉语中存在“非作格动词带宾语”这样一类例外现象。笔者认为,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宾语”都是外围论元,非必有论元,不影响谓语动词的论元结构。分析发现,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宾语要么可以作为附加语处理,要么是某种句式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