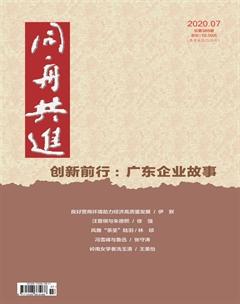浊酒一杯天过午
徐强

在汪曾祺一生广阔的交游中,如果说有一个最亲密的朋友,那非语言学家朱德熙莫属。
朱德熙是一代汉语学术研究的杰出学者。他习惯书斋生涯却绝非书呆子,他与汪曾祺二人,一样的绝顶聪明,一样的趣味丰富,一样的有情有义。
他们的友谊,是君子之交,平淡持久,堪称当代的伯牙子期。
【因戏曲结缘】
1939年7月,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坐船,经过广州、越南海防,转火车奔赴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当他从上海出发时,朱德熙身处这座半已沦陷敌手的远东大都市,也在备考西南联大。因为那一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实行国立大学联合招考制度,联大除在昆明设立主考区外,还在另外一些地方设分考区,上海正是其中之一。
不过当汪曾祺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朱德熙却进入了物理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朱德熙的舅舅、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在该系任教。朱德熙自幼喜欢自然科学,喜欢钻研,动手能力极强,痴迷组装矿石收音机等科技探索活动。但他的文科也不弱,文学感知和鉴赏力强,喜爱侦破小说,也曾一度创作侦破小说自娱。由于王竹溪坚持到中文系听唐兰教授的文字学课程,受其影响,朱德熙也慢慢喜欢上了文字学。这为他后来转学中文系、受教于唐兰设下了伏笔。
1940年秋季学期,朱德熙从物理系转入中文系,与汪曾祺成为同班同学。两人同龄,都生于1920年,汪曾祺的生日在3月5日,朱德熙的生日是10月24日,相差半岁。
汪曾祺和朱德熙结识,还有一层更早的因缘,那就是对京剧的共同爱好。
汪曾祺自幼喜欢民间戏曲,初中时就开始和同学一起唱京剧,他的父亲汪菊生能拉琴,有时汪曾祺和同学们举办演出活动,汪菊生也会携琴为孩子们伴奏。进入西南联大以后,汪曾祺延续了这一爱好,有时候在宿舍里唱几嗓子,同屋的广东籍同学郑智绵厌恶京剧,汪曾祺一开口,他就大骂。
朱德熙却喜欢和汪曾祺在一起唱京剧,有时则相携去看厉家班的戏。厉家班是来自上海的私家剧团,成立不久就因抗战爆发而转徙湘、鄂、黔、滇,这时正在昆明演出,声誉鹊起。刚转学中文系不久,朱德熙就突发急性小肠疝气,汪曾祺叫来人力车,把他送到东城的惠滇医院,当即留院手术。住院三天后,汪曾祺又到王竹溪先生家取了钱,付了手术和医疗费。后来有一次,朱德熙患上恶性疟疾,治疗期间也是汪曾祺照看,这就更带上一些“患难之交”的意味了。
逐渐地,汪曾祺与朱德熙的戏曲爱好转移到了昆曲上面。
1943年春季学期,词曲名家浦江清教授开设《曲选》一课,汪曾祺、朱德熙及低一班的好友杨毓珉三个戏曲发烧友相约同选,在一个班听课。杨毓珉在《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中回忆当时情景:“1942年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
【见证彼此的爱情】
朱德熙是著名學者,他的夫人何孔敬为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母仪典型。两人虽学识、地位悬殊,却不乏共同趣味(如昆曲),一生举案齐眉,堪称“金木良缘”、学林嘉话。而汪曾祺几乎见证了他们由相识、相爱到成家生子以至终老的全过程。
何家是安徽桐城籍,何孔敬的父亲在昆明文明新街开瓷器店。朱德熙和何孔敬结识于1941年11月,当时何孔敬在一家夜校补习班学习,而弟弟何孔先远在十七八里外的乡下没有书念,于是何父拟为儿子聘家庭教师。补习班有位洪老师为他推荐了朱德熙,于是,汪曾祺和洪老师陪同朱德熙到何家瓷器店,与何父见面商定。也就是这一次“面试”,何孔敬第一次见到朱德熙,她晚年回忆:“两个大学生都穿着灰色的长衫,十分潇洒,汪曾祺的头发特别长。”两人走后,何父说:“那位汪先生可真是个聪明人。”
1942年下半年,何孔先已在朱德熙的精心辅导下考取了昆明的名牌学校——天祥中学,但何父决定放弃入读天祥,继续延聘朱德熙为家教。为了照顾朱德熙在联大上课,何家在文林街租下一套小厢房,供朱德熙居住和教学,那里成了一众师友的文化沙龙,汪曾祺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首席常客,一来就吹笛子、唱昆曲,朱德熙不止一次对何孔敬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就在朱、何的爱情潜滋暗长时,汪曾祺也遭遇了一场爱情,这段经历比较隐晦,鲜为人知。据汪曾祺致同在昆明谋生的高邮同乡朱奎元信中透露的信息,他在1943年雨季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女孩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了苦闷:“现在,我的欢喜更是有增无已。我自从不找她以来就没有找过她。我没有破坏我的约言,我没有写一个字给她,虽然我是天天想去找她,天天想写信给她的……”1944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为送“蓝家女孩子”去医院,曾找一位叫任振邦的朋友借钱。而到当年7月29日,汪曾祺在信中宣布自己跟蓝家女孩子“算吹了,正正式式。决不藕断丝连”。
当时汪曾祺租住在民强巷,十分落魄,在白绵纸本子上随意写作,不停地抽烟,满地都是烟蒂。“有时烟抽完了,就在地下找找,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了火再抽两口”。没有床,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条棉絮“拥絮而眠”。失恋后,他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中午11点坚卧不起(何孔敬曾说他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是何孔敬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他吓坏了,以为汪曾祺想不开,正在发愁时,朱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事了。”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写道:
同学朱德熙见我到十一点多钟还没有露面,——我每天都要到他那里聊一会的,就夹了一本字典来,叫:“起来,去吃饭!”把字典卖掉,吃了饭,Wandering,或到“英国花园”(英国领事馆的花园)的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之类的虚无缥缈的胡话。
1945年中秋节,朱德熙、何孔敬结婚,婚事全由汪曾祺帮助操持。结婚当日,朱德熙来到孔家,查看是否还有什么遗漏的事宜。不久,汪曾祺给何孔敬拎了个滚圆粉红色的大盒子,交给朱德熙,朱德熙再转交何孔敬。何孔敬回忆说:我拎了粉红大盒子走上楼,迫不及待掀开。一看,天哪!是件水红色的艳妆礼服,着实好看。”但照镜子之后发现与自己黑里透红的脸色不配,就拎了盒子到楼下:
德熙和曾祺四只眼睛都朝着我看,德熙急切地问我说:“穿了礼服合适么?”我毫不掩饰羞涩地说:“我喜欢白的。”德熙听了,有点儿急了,说:“水红礼服是你母亲的意思,怎好反对母亲的意思呢。”我不说话,站在那里发愣。曾祺发话了,说:既然不喜欢,可以拿去换嘛。”
曾祺果真换来雪白的婚纱礼服,冲我笑笑说:“不合适,还可以替你去换。”
按桐城人的规矩,结婚第二天新娘子回门。汪曾祺也赶来了,陪同新郎新娘一路走回文明新街孔家。午饭后,三人到昆明最好的、专放美国电影的电影院——南屏电影院看《翠堤春晓》。看完电影,汪曾祺说:“夜饭不吃了,我得回去看看松卿了。”
说也有缘,在南洋长大的福建长乐籍女生施松卿,1939年考入联大物理系,也是朱德熙的同班同学。不过她后来曾休学一年,又先后转学生物系、外文系,1944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建设中学任教。这时,她已经和汪曾祺相恋了。
文明新街上有三家瓷器店,都是桐城人所开,何家的店在南头。朱德熙、何孔敬婚后,汪曾祺常常陪同朱德熙到店里玩,到瓷器店后面的仓库去挑好玩的小酒壶、小花瓶之类。后来朱德熙的长女朱眉诞生,汪曾祺和施松卿又成为染布巷24号小家里的常客。
【通家之好】
1946年7月,汪曾祺和施松卿踏上东归之旅。施松卿回到福建老家,汪曾祺来到上海谋职。茫茫都市,举目无亲,汪曾祺倍感失意。此时已任教清华大学的朱德熙全家北归,他让汪曾祺到自己在上海的家里寻求接济。朱德熙的母亲像对待儿子一样接纳了汪曾祺。
汪曾祺一度睡在朱德熙家的过道里。朱德熙的弟妹们当时都积极投身革命,虽然与汪曾祺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对落魄中的汪曾祺都彬彬有礼。朱德熙的妹妹朱然当时还是个小姑娘,每天一早就笑眯眯地跟颓在地铺上的汪曾祺打招呼。多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朱然成为汪曾祺长女汪明的同事与领导,汪曾祺谈起她来,還对这一幕记得清楚,说当时心里明白,朱然他们一定瞧不起家里寄居的这位——“简直没个人样儿”。汪明《往事杂忆》)后来汪曾祺在沈从文、李健吾的帮助下,谋得在私立致远中学任教的职位,总算安顿下来。
1948年3月,汪曾祺辞去上海的教职,追随担任北大外文系助教的施松卿,来到北平,暂时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一对好友分别两年后又能经常见面了。
1949年农历除夕,汪曾祺携施松卿到清华园,与朱德熙一家同过春节。此前,因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形势紧张,物资供应困难,囤积面粉成风,肉类奇缺。何孔敬也囤积了十几袋面粉。年底,她以30斤面粉从农村妇女手里换得一只鸡。有客人来,怎么也得多做几道菜,何孔敬一阵为难后急中生智,添了两个菜:一个粉丝熬大白菜,一个笋干豆,也就是酱油糖煮黄豆,主菜则是一道红烧洋葱鸡块。何孔敬带有歉意地对汪曾祺、施松卿说:这个年过得真够惨的了。”汪曾祺却心满意足地说:“有鸡吃就行了,还要吃什么。”
进入了新时代,汪曾祺和朋友们都面临着新的工作环境。
朱德熙先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随清华中文系一起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任务艰巨,朱德熙担当重任,他受命与语言学前辈吕叔湘先生合撰《语法修辞讲话》。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讲话》。全国第一大报连载一部语言学术著作,是空前绝后之举。一时间,举国掀起了学习汉语语法的热潮,朱德熙的名字也走进了千家万户。1952年底,这部28万字的著作合订本正式出版,牢牢奠定了朱德熙在语法学界的地位。汪曾祺、朱德熙的另一个同学李荣,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此时也凭借大量扎实的音韵学论文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三位同窗好友都淡泊功利,视学问为生命,朱德熙对文章有“洁癖”,总是细细打磨,精益求精,汪曾祺评价他搞学术研究“完全是超功利的”,“是把辛苦的劳动当成了一种超级享受”。
相对来说,汪曾祺进入状态慢了半拍。他从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1940年代发表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在文坛已颇引人注目。1946年在香港滞留期间,报端就刊登了“青年作家汪曾祺来港”的消息,说明他已有相当名气。1949年参加南下工作团,一年后进入北京市文联担任文艺刊物编辑后,写作节奏慢了下来。几年内,他只写了数篇带有人物特写性质的通讯文章。1954年,写了散文《国子监》。作品在查考文献、采访人物的基础上,围绕古代“大学”——国子监来写,熔游记、风貌速写、历史源流、典故于一炉,又暗示着新旧对比的主题,可以说是进入新中国时期汪曾祺第一篇分量厚重的散文作品。三年后,作品在《北京文艺》发表。胡乔木读到《国子监》后十分欣赏,一次碰见朱德熙,向朱德熙作了推荐,并问朱是否知道汪曾祺是什么人,朱德熙自豪地回答:“是我的大学同学!”
沈从文是两人的恩师,特别是汪曾祺文学创作上的第一导师。1956年3月,沈从文在《自传》中谈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列举了来往最密切的十数人,汪曾祺和朱德熙、李荣都在内。沈从文虽然放下了文学创作的笔,但从他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对学生成名成家的殷切之情。一段时间内,汪曾祺的作品少了,沈从文急在心上,当1961年汪曾祺拿出他沉寂多年后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时,恩师的欣喜简直难以言表,他也曾拿朱德熙、李荣的工作成就来对比,为汪曾祺的地位鸣不平。
约1970年下半年,部分高校在停止办学几年后恢复招生,北京大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在新华社工作的施松卿奉命到北大“蹲点”,采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情况,特地听了朱德熙的课。回家后,她向家人极力夸赞朱德熙的学识、风度、口才。汪曾祺骄傲地说:“德熙就是这样,做什么都做到最好。”
汪曾祺对于朱德熙的研究和教学能力极为欣赏,也总能从他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趣味点,并引为第一知音,一有心得,都是第一时间与对方分享。1972年11月,汪曾祺兴之所至,写了两首关于昆虫的诗《瞎虻》《水马儿》,当晚就致信朱德熙,还报告自己下一首创作计划是“花大姐”(瓢虫),在根据沙岭子劳动经验指出瓢虫的分类后,汪曾祺也谈到困难所在:记不清害虫、益虫背上的星的数目,所以托朱德熙推荐一位昆虫专家以便请教,还顺便教朱德熙做一个“精彩的汤”——“金必度汤”。
年末,汪曾祺在中国书店为剧团资料室选购图书,发现了两本奇妙无比的书,一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一是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当晚炒白果、喝黄酒、读“妙书”后,忍不住立即致信朱德熙极力推荐本日所购两书。对于赵书,说“比他译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对于《植物名实图考》,说“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并责问和感慨道: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
1976年10月以后,是汪曾祺一生最低沉的时期,除了以看闲书、画画为消遣,给朱德熙写信倾谈也是排解忧闷的方式之一。在这些信里,汪曾祺仍表现出对生活趣味的沉迷,如说自己“三个月来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介绍了新近发明的美食“塞肉回锅油条”。还描述了第一次杀鸡的过程:“汪朗前些日子在家,有一天买了三只活的笋鸡,无人敢宰,结果是我操刀而割。生来杀活物,此是第一次,觉得也无啥。鸡很嫩,做的是昆明的油淋鸡。我何时有暇,你来喝一次酒。”
汪曾祺的处境朱德熙时时放在心上。他和李荣因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熟悉,便几次向胡反映情况,并送上汪曾祺的几篇新作,希望能帮忙落实单位。李荣甚至推介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胡乔木说他只能在社科院范围想办法,拟把汪曾祺调到社科院文学所。但汪曾祺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学术研究,这事就搁浅了,后来还是回到了京剧院。
【戏曲是老友间的恒久话题】
1980年,汪曾祺和朱德熙均年晋花甲。但因为时势原因,他们都没有早早地归隐山林,差不多整个80年代都在各自崗位上持续工作。汪曾祺除了继续创作京剧剧本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以一篇《受戒》一炮打响,开启了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朱德熙则在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后进的同时,承担了繁重的服务工作,例如连年担任高考命题语文组负责人,1984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就在写完《受戒》一周后,汪曾祺趁热打铁地写了另一篇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同样以旧时代的高邮为背景,题材却是赞许同甘共苦的坚贞友情。汪曾祺后来谈及这个作品时,引用“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加以解释,他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内心想必有所比附,一定把自己和朱德熙大半生弥足珍贵的友情投射到了作品当中。
1981年6月,汪曾祺完成了小说《鸡毛》,小说取材于西南联合大学校园生活,主人公金昌焕表面斯文,背地里却偷善良校工文嫂的鸡。因有些事情是根据真人真事所写,汪曾祺有所担心,他先致信正在密云命高考题的朱德熙:
这件事是实事,联大很多人知道。我怕小说发表后,为此公所见,会引起麻烦。
但是,听说你到密云去出试题了,而索稿者又催迫甚急,只好匆忙寄出,文责自负了。很可惜,此小说没有让你和孔敬、朱襄先看看。小说写得很逗,一定会让你们大笑一场的。且等发表了再让你们看吧。
1982年4月到5月,汪曾祺有四川之行,行程中作诗多首以记录行程见闻感怀,其中《成都竹枝词》等多首得意之作,都先抄示朱德熙一睹为快。一返京,就迫不及待地写信,报告此行详情。信中还特意提出对近来文学写作中一些“很怪的语言”的看法:
随着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的出现,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其中突出的是“的”字的用法。如“深的湖”“近的云”南方的岸”。我跟几个青年作家辩论过,说这不符合中国语言的习惯。他们说:为什么要合语言习惯!如果说“深湖”“很深的湖”“近处的云”“离我很近的云”……就没有味道了。他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现代”味儿。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希望你们语言学家能出来过问一下。——你觉得他们这样制造语言是允许的么?
显然,他希望身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帮助自己解决语言上的疑惑。
1986年6月,小说《虐猫》在《北京晚报》发表后,有人提出标题不合语法的问题,认为“虐”字不能单独作动词。汪曾祺为此特意请教了朱德熙,朱德熙也说不很合适,但琢磨许久,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说法,后来一直没改。
1982年,朱德熙的新著《语法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他的身份,本来完全可以找语言学界内的几位学术造诣、书法造诣均臻上乘的前辈题签,他却单单请汪曾祺这个语言学界之外的朋友来题写书名。
两位好友始终保持着纯真的童心。1984年夏天,朱德熙应邀赴昆明讲学,这是他阔别昆明近40年后第一次返回,寻访了多处旧地。他在旧居所在的染布巷一家杂货店买回一个旧酱豆腐坛子,回京后做成一盏台灯。汪曾祺、施松卿来访,对之赞不绝口。朱德熙长期有气管炎宿疾,汪曾祺时时为他留意验方,某日从玉渊潭一个遛鸟人那里听得一方,立即写信奉告:“蜂蜜(好的)加鲜姜(多少随意)入笼蒸四十分钟,每晨及临睡时各服一汤匙。”
对戏曲的热情贯穿汪曾祺交游始终,戏曲是他和包括朱德熙在内的老友们的恒久话题。1985年8月初,朱德熙从昆明带回一块宣威火腿,何孔敬蒸了火腿招待汪曾祺,汪曾祺喝了大半瓶洋酒、大半瓶茅台。据何孔敬描述,两位好友谈着谈着,就谈到昆曲上来了。汪曾祺冲何孔敬一笑,说:“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欢哪出戏?”问得何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朱德熙说:“她会《游园惊梦》。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来唱。”汪曾祺说:“多年不吹笛子不说,门牙没了,还能吹吗?试试看。”汪曾祺试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说:“奇怪,门牙没有了,还能吹。”
1987年9月到10月间,上海昆剧团在人民剧场演出。同年12月中下旬,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昆剧抢救继承剧目汇报演出在北京举行,刚结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回国的汪曾祺,不仅自己或带女儿汪朝连日观看,而且多次买票请朱德熙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