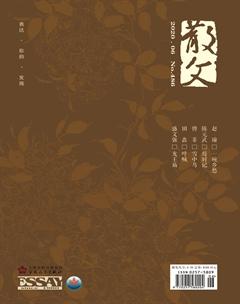奉川诗旅
高鹏程
早春札记
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暴涨
马头墙的墙皮脱落了,一匹隐藏在其中的马
似乎要破墙而出
道路泥泞,隔断了山外的讯息
湿漉漉的木椽里长出了木耳
杏花黑色的枝条变得肿胀
四野寂静,隐约透出不安
我在屋内给你写信
写到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暴涨
手中的笔,整个冬天它像一截枯枝
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了绿色的血液。
有一年冬末,我把自己“隔离”在一个小山村里。
村庄很小,也很偏僻。除了我和当地所剩不多的几个年老村民,罕有外人光顾。
因为过于偏远,手机信号也不好,打电话时常中断。上网更难,很卡,只能一直看着那个圈一直转着。但这正合我意,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原因,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想一些一直想不明白的事。
这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自我隔离。除了一日三餐,和偶尔的读书散步,我什么也不做,也不上网,整日静坐。我借居在一幢老房子里,这幢房子是一幢老旧的江南民居,垩墙黑瓦,还有高高的马头墙。因为年代久远和雨水冲刷,墙皮脱落,墙体也鼓出了一个大包,似乎里面有一匹马正在不安地跺脚,喷着响鼻。
因为雨,我活动的半径并不大,主要是在村庄周边。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屋子里。时至冬末,山野的风已经不是很冷,潮湿的空气中似乎夹杂着丝丝暖意,但也仅限于白天。转过午后,天很快就黑下来,气温也迅速降下来,这时候我就关了门窗,守在炉火旁,看着发红的火光发呆,偶尔写下几个可有可无的句子。
《早春札记》等诗大约就写在这个时期。那时我还在整理我的一部有关冬天的诗集,题目是我早早想好的——《冬天的秘密花纹》。写作这一批诗歌的时候,我整个人似乎沉浸在冬天里,以至忘记了时节是在流逝的。“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大约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雨脚稍歇时,我会去屋前山后稍远的地方散散步。暮冬时节,一切似乎都还在寂静和沉睡中,但又有一些事物,已经开始在蛰伏中潜行,蠢蠢欲动。我的房子前有一条黄泥小路,通往村口的大路和更远的山野。拐角处,有一片树木稀疏的的小树林。大多数树都上了年龄,木叶尽脱,在雨水的浸泡下,原本发黑的枝条显得更黑。有些断口的地方,居然长出了木耳,湿漉漉的,一攒一攒挂在那里,仿佛在聆听什么事物的到来。
现在可以稍稍说两句《早春札记》这首诗,原本的题目叫《山中札记》,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多数人已经用过,而且对我来说有些矫情,我还算不上居于山中,于是改为早春。整个诗题指向并不明确,并没有标明这封信札是寄自山中,还是来自山外。写信的人是谁,为什么要写信,信的内容是什么。一切看起来都是含糊其词,当然,这也是我有意为之。
诗的正文里也并不想交代标题里带出的疑问。我只想营造一个适合写信,或者适合读信的环境和氛围。于是,你们会看到,我写下了雨水、道路、杏花肿胀的枝条、带着耳朵聆听的木耳和一匹躁动不安的马。
最重要的,我写下了一支来自早春的笔,一棵柳树干枯的枝条,因为春天和雨水的到来而注满了绿色的血液。我想它肯定是来自我的身体。一个沉浸在冬天的人,因为感受到了某种遥远的春天的讯息而发生变化,这是季节或者自然来信和人间讯息的结合。我想一首诗到此,也就完成了。
顺便交代一句,促使我写下这首诗的直接原因,源自散步时看到的那几棵老树。有一棵枝条显得异常肿胀,我以为是梅花,用了“形色”,才知道是杏花。“杏花、春雨、江南”,這三个词带出了我记忆中贮藏的有关春天的古老的诗意。原来,春天就要来了。
物候
长久地盯在一处:一株梅树,一小片田地,一个小水潭
你发现,第一粒梅朵的爆出,比旧年迟了三天
而同一个小水潭,水位比去年同期升高了七毫米
在同样大小的一块田地里,数出的草木比去年
少了五种
同一棵枝丫上,一只鸦巢,去年还传出鸦叫,今年
像一幕哑剧
连日来的电影院内外,人们都在关心流浪的地球
但没有人注意这些,这些迟到的、消失的微小
也许明年,这块地方
梅花还会开,草也会长出来,潭水
还会漫过堤岸,但那枚
废墟般的鸟巢里会持续发黑,像一只眼珠
它会看到,去年站在
树下不远处看它的人
已经消失不见
这也是我在去年冬天自我“隔离”期间写下的一首短诗。
蜗居在那个小山村里时,除了每天坚持读书,保持安静思考之外,偶尔我也感到无聊。就像眼下很多隔离在家的朋友想出来的打发无聊的办法,有人绕着客厅餐厅阳台卧室循环做半日游,有人用瓜子壳粘小动物玩,有人把家里的大米粒数了一遍又一遍。我的选择是去蜗居的山村周围散步。
山村不大,也无多少风景可言。我就把有限的几棵树,一小块荒废的田野、一个小水潭翻来覆去地看。但如果稍加留心,还真能从熟视无睹的地方看出一些问题来。
这个小山村,之前我来过几次,诗中提到的几种有限的风物都是我熟悉的。在最无聊的时候,我曾经把门前的一小块荒地划出大约一平方米来,数里面包含了多少种植物。一数还真吓了一跳,区区一平方米,里面居然有四十多种我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但仅仅隔了一年,同样的一小块地里,植物的数量就比去年少了五种。当然,这些都是一年生的草木,依靠种子繁衍,它们的后代早已在别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原来的地方消失应该很正常。
但毕竟,在有限的空间里,很多事物发生了变化。很多事物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看不见的速度在变化,在消失,在增加。譬如,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和菌群,躲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秘密聚集,然后忽然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记得门前的一棵苦楝树,有一只鸦巢。去年我还似乎听到过从里面传出的聒噪,但现在,整个冬天过去,里面没有任何响动。它已经成了一个大自然中的哑剧剧场,一个时间的遗址。
写下上面这些,是以我观物,看到的是我眼中大自然细微的变化。但我知道,这样的观察是有很大局限的。事实上,大自然中,有更多的事物,都时时刻刻地处在变化之中。有些是以我们知道的方式,更多的,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它们也许毫无规律可言,也许,遵循着一种神秘的秩序,而我们有意无意中成了这种秩序的破坏者。
我想我必须学会自省。作为这个星球上一个普通的和其他物种平等的物种。如果我们真的有高于其他物种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具备了一种自省的能力,意识到自身的原罪。正如诗人大解写道的:
有两种暗物质比原罪古老:
退到体外的身影藏在体内的灵魂
还有一些轻物质同样古老:
呼吸 语言 目光 梦……
就像我写到的那一只鸦巢,在持续盯着它看了很久之后,我忽然发现,它也在盯着我。一粒黑色的眼球,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忽然意识到,它也是万物窥视我们的一只眼睛。在我们盯着大自然的同时,它同时也在盯着我们,盯着人类——这个星球上的一种傲慢无知和自以为是的物种。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警醒,并为此做出改变,也许下一个消失的,就是我们了。
补充一句:关于上一篇《早春札记》的诗,有朋友问我蜗居的小山村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事实上,它可以是任何一座小山村,可能在奉化,可能是别处某地,也可能就在你心里。冷西之夜
从冷西小栈出来
车子拐弯时,忽然看见了远处的灯火
我熄了车,点燃一支烟
远远地望了很久
温暖、金黄的光亮,让我
微微空白的大脑里,闪出了几个词:
乡关 驿站 歌哭
是的,歌哭。作为一个久居异乡的人
这些年
我已习惯摸黑赶路,穿行在
岭头暮雪和陌上轻尘之间
不再轻易为光亮的事物驻留,也不轻易揿亮体内的灯火
而今晚,在冷西,一幢孤零零的乡村小屋窗口
泼出的灯火,却让我有了无言的感动
如果此刻,在另一处观望
你会看到,漆黑夜色里的两处火光
一处明亮,金黄
另一处微弱、闪烁,却始终不肯被黑夜吞没
《冷西之夜》是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组诗《迷迭香》中的一首。这组诗里绝大多数都是以我目前工作的浙东奉化地域风物为背景创作的。
在奉化工作生活的这几年,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走村串户”上面。穿行在那些相对古旧的村镇之间,推开一扇扇柴扉,你能听到时光锈迹溅落的声音。其中一座村庄,名字叫冷西。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无来由地就产生了好感,隐隐觉得会朝向它写下点什么。
我所在的人大代表小组里有一位年轻人,叫宋小赞。大学毕业后起初在甬城打拼,后来返乡做起了一份农村淘宝的事业,逐渐风生水起。冷西是她的村庄,位于奉化尚田镇雨施山麓,盛产草莓,据说土壤含硒,村民相对长寿。
因为宋小赞的邀请,我去过冷西几次,在她的冷西小栈做过文学沙龙。那是位于雨施山脚的两幢房子,和周边的民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它原本就是由两幢相对偏远和独立的民居改造而成。几次冷西之行,我恰好见证了它改造——不,应该说是恢复“旧貌”的过程。
及至完工时,宋小赞央我帮她想个名字,我毫不犹疑地选定了“冷西小栈”四个字。
改造后的冷西小栈,暗合了我对田园生活场景的想象。屋子依旧保留了土坯的山墙、大块鹅卵石垒砌的围栏。窗台上的陶罐里插满来自山野的无名小花。屋后有一孔山泉,水色清冽。屋前是一条蜿蜒山径,向前,连接着旁边的村庄,向后,逐渐隐迹于山后茂密的竹林深處。
大致是去年冬天光景,宋小赞邀请同组的人大代表去小栈做客。已是深冬,天寒林肃,除了草莓大棚里仍旧春色流苏,外面已经是一派萧疏。冷西小栈偌大的茶室里,生起了一炉柴火。不一会儿,茶炉初沸火初红,纸窗瓦屋,一干人等,围着火炉喝茶闲谈,感觉整个冬天已经顺着小栈上空高高竖起的烟囱散去。
因为要赶回象山,我在大家谈兴正酣的时刻起身告退,开着车,驶出了冷西小栈。乡野黑如墨染,唯有稀疏的星光点缀清冷的夜幕。
车子自漆黑的村道上拐弯时,我忽然看到了身后的灯火。在四周一片漆黑的夜色里,从冷西小栈泼出的灯火,温暖、金黄,忽然就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我停车、熄火,靠着车子点了一支烟,对着远处的灯火看了很久。微微有些眩晕的大脑里,似乎是一片空白,又似乎闪现出了无数叠加的往事。无数曾经在雨夜赶路的人,无数心里念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漂泊者的面孔叠加在一起……
在上面这首诗的最后,你也许会看到,另一处微弱、闪烁却始终不肯熄灭的亮光。我想,那不只是我的,也是所有身处异乡或者精神上的漂泊者深埋在眼睑之间的一星光亮。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