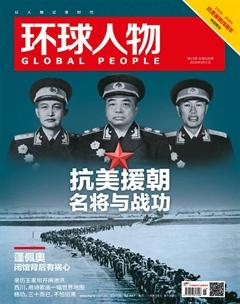任晓雯:新天地是浸了福尔马林的弄堂
毛予菲

任晓雯。小说家,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7年,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代表作有《岛上》《她们》《浮生二十一章》《好人宋没用》。近日短篇小说集《朱三小姐的一生》出版。
“开始了吗?”任晓雯询问《环球人物》记者,声音轻柔,尾音带着一丝上海话的软绵。在豆瓣网友的评价中,任晓雯一直“背负”着“温婉知性美女作家”的光环。有读者更直接地留言:“简直惊呆了。”
网友的诧异,源自他们对任晓雯文字的反差感受。在一系列的上海写作里,任晓雯细密地勾勒都市男女的隐痛、堕落、迷失和他们的爱恨离愁、情欲纠葛,书写城市变迁中,新老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与接纳、外市与本地人之间的猜忌与排挤……故事凄苦冷峻,语言精炼筋道,绝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上来气。
书评下的留言铺天盖地:“这位看起来十分温婉的女性,居然写出这样风格的文字”“我以为是位沧桑大叔,竟从中读出了看《活着》时的感受”。
从24岁创作处女作《岛上》,到新短篇小说集《朱三小姐的一生》出版,任晓雯一直坚持严肃文学写作。她的小说拿过数项大奖,任晓雯也由此成为“70后中生代作家”代表之一。
“我的文字融入了古语和沪语,读来有些吃力,肯定不是讨好读者的。我也不想创作那些阅读轻快的畅销小说,我更愿意书写时代,揭示幽暗摇曳的人性。曾经,我以一种天真的骄傲坚持自己的这种趣味,在小说圈一二十年摸爬滚打后,很高兴我还是那个固执己见的自己。”任晓雯说。
装满“沉思”的文件夹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任晓雯也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她的文学之路始于复旦校园,“在高冷的文学团体里,抒情是件被耻笑的事,先锋才是正确,所以我也赶紧‘先锋了起来”。

任晓雯处女作《岛上》(左图)。任晓雯第二部长篇《她们》(中图)。任晓雯新作《朱三小姐的一生》(右图)。
一批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是任晓雯早年的偶像,是她创作的启蒙导师。处女作《岛上》的灵感源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任晓雯由此构思了小岛上一群疯子的故事,叙述支离破碎,情节荒诞离奇,梦境与幻觉的描述交织其间,借此隐喻现代人“精神失托”的状态和生活。
那年任晓雯24岁,新闻系硕士生,发表过一些诗歌,若干散文,两个短篇,却没想过当作家。“当时的人生轨迹是读博,留校,从事学术研究,写作只是灵光一闪的想法。”《岛上》完成后,任晓雯按照原先的计划,报考博士研究生,“出乎意料失败了”。学术做不成,也不想做新闻,她更不敢冒险专职写作,“这看起来是个多么令人绝望的职业啊”。
徘徊了6年,任晓雯终于還是以小说家身份与读者见面了。《岛上》出版,华语作家圈开始热切讨论这个写魔幻现实的“20多岁小姑娘”。不久,这本薄薄的小书又出现在瑞典某家图书馆的中文区,被翻译家陈安娜(莫言《红高粱》、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等作品的瑞典文译者)读到并喜爱。安娜的先生、同为翻译家的陈迈平曾在微博上写道,“看见安娜翻译任晓雯一个小姑娘的作品,就气不打一处来,后来读完《岛上》,我说,好了,我不骂安娜了”。
懵懵懂懂一脚踏进小说圈,任晓雯开始创作她的第二部长篇,名为《她们》。这时的她,却不想写魔幻荒诞了。最终,《她们》虽仍延续了西方现代主义写作的一些特质,比如体系庞大,线索盘结,但内容逐渐回归生活;书中人物也不再是乖戾的“病人”,而是“上世纪的男男女女芸芸众生”。
写作的大转弯,最初因生活所至。徘徊的那些年,任晓雯加入了一家茶叶公司管理层,“每天睁眼,就要和营业员、广告员、场租方各色人马打交道,扯着嗓门大声喊。等真正想要表达的时候,很多现实的细节突然涌向我,兴趣点转移了,写的东西就转移了”。
任晓雯的写作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她在电脑桌面建立了一个收集素材的文件夹,看到有所感悟的文字,便随手保存,沉淀些日子再翻阅,然后挑出一些,进行创作。她觉得自己风格的转变,也是年岁增长的必然结果:“年轻时的写作来自激情与欲望,中年以后的写作要靠沉思推动。”
于近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朱三小姐的一生》,其中很多写作灵感、细节材料都来自她这个装满“沉思”的夹子。
数年前的某日,任晓雯偶然读到“横滨玛丽”的故事。这位面敷白粉、身着洋裙的日本老妇,年轻时是为驻日美军提供服务的慰安妇,老迈后拖着两包仅有的家当,游荡在横滨街头。她受尽孤独和歧视,也体会过怜悯和爱,最后在敬老院里默默死去。这故事让任晓雯感动落泪,回想良久,生出写作冲动。
于是几年后,就有了《朱三小姐的一生》。与“横滨玛丽”相似,朱三小姐年轻时是妓女,栖身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朱葆三路,老去之后,成为浓妆的怪老太,幽灵般游走在东方都市的街头。

任晓雯《阳台上》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小说中,她写老公房拆迁背景下的青年男女。
另一则故事《换肾记》,最初的灵感来自一段电视新闻。一名拒绝为尿毒症儿子换肾的母亲,与儿子儿媳在镜头前激烈争执,又迅速转换立场,互相体谅,皆大欢喜。任晓雯觉得自己看了则“虚假新闻”,“不,现实不会是这样的”。她以自己所认定的“真实”,创作了一则短篇,记录下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那里,新闻结束了,小说开始了。
以虚构写真实,大概是任晓雯现在的写作特点。“写小说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复述新闻,而是将庸常的生活细节捏碎、打乱、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一个人性的破口,底下有暗昧模糊的东西涌动。”任晓雯说。
从弄堂里走出的“浮生”
任晓雯生于1978年的上海,在凤阳路的小弄堂长大。在她眼中,“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就是上海的细胞”。那里电线错落,空间逼仄,“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开始崛起,城市面貌历经沧桑巨变:狭窄坑洼的弄堂被拆迁、改造,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人们从逼仄亭子间里搬出来,住进舒适却不免乏味的独立公寓;弄堂间的风月八卦,逐渐散落在都市人昼伏夜出的酒吧、午后光顾的咖啡馆……
带着写作者的敏锐触角,任晓雯一点点体察着这座庞大城市的日新月异,脑海里不同时代的新旧记忆,层层叠加,摞在一起。在一篇随笔中,她如此谈到自己眼中的新上海:
新天地是弄堂的標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高档公寓里邻楼的居民,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高档百货商场旁的小道,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穿着睡衣提着马桶的妇女穿梭其间……
“这是一座多元且有不同侧面的都市。”任晓雯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提到。书写这座城市的前辈们,张爱玲的上海往事“华彩霓裳皆浮影”;王安忆笔下是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安妮宝贝和卫慧的上海,则充斥忧郁与情色,小资情调弥漫。“而你看到我的上海面孔,大多是身处底层的小民。”
任晓雯的上海书写始于2008年,直到2013年的“浮生系列”,一个个市井小民,才真正从她的弄堂里走了出来。
当时,《南方周末》向她约稿,建议她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任晓雯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以亲友经历、口述历史打底的“浮生”,就这样写起来了。
第一篇《张永福》,任晓雯磨了整整30天。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有惊无险度过了半辈子。在他一地鸡毛的人生里,任晓雯找出叙述的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他被寡母压制,他受妻儿漠视,他夹着尾巴做人,皆源于懦弱。“故事原型是我的一位亲人,对于他我太熟悉了”“我能感受到主人公噼里啪啦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反响不错,任晓雯“拾掇勇气继续写”。 2017年,专栏中的21篇集结成册,《浮生二十一章》出版。这个短篇小说集子里,落魄的人生俯拾皆是:上世纪90年代,去日本打黑工的姜维民,染了一头黄毛,整顿整顿吃鸡皮和卷心菜;不解时事却热爱演戏的“老疯子”曹亚平,在知青们的下乡潮里颓荡;新上海人彭娇娇,剥削父母、耗尽家底出国留学,归国却一事无成……有书评人评价任晓雯的写作:荒诞、颓靡、薄情,把握住了这个城市根子里的东西。
几乎与“浮生系列”创作时间同步的《阳台上》,也是任晓雯的代表作。小说中,她写老公房拆迁背景下的青年男女,故事依旧发生在上海。素材与细节,源自任晓雯自己的“老公房生涯”,“我曾在一幢6层楼的老公房里,住了很长一段日子”。
“作家的童年塑造了他/她。”任晓雯说,“漫长上海岁月留下的记忆中,最重要的画面是:我从逼仄小房子里出来,走下阴暗陡峭的楼梯,推开一扇松木门,低头看见狭窄弄堂,坑坑洼洼满是水。我坐在巷子口乘凉,对面是红晃晃的‘跃进食堂,大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影婆娑。”
不动声色地把现实端给你看
在2015年出版的小说《生活,如此而已》中,任晓雯塑造了一个因长得丰满,被男友嘲笑的胖女孩。
一个冬天的清晨,任晓雯在银行门口瞥见一个路过的胖女孩,马尾辫扎歪了,在头顶拱起一块,手里拿着一张煎饼果子,边走,边吃,边哭。女孩的形象,触动了她内心深处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在这个人物身上,任晓雯投射了自己。

任晓雯作品:《浮生二十一章》《好人宋没用》
这在任晓雯的文字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写作对她而言是“另一回事”——都是别人的故事,鲜少有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任晓雯,有时候不免情绪化。她说自己“内心敏感,无意中瞥见一条感人新闻就会动容落泪,内心颠簸时,完全无法安静地作任何事情”。
落到笔尖却恰恰相反。她推崇克制、冷峻的文风,白描叙述,极少动情。她认为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就好比讲相声,能不动声色把人逗乐了,才是高强的本领。西方作家中我最喜欢福楼拜,他做过医生,很克制,很冷静,可以不动声色地把现实端给你看。”
回顾近几年的写作,任晓雯承认自己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克制中多了怜悯”。2017年创作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任晓雯第一次在写作时落泪。那段时间,一位老太太在她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一生执拗、敏感、心底柔软。”
在《朱三小姐的一生》中,任晓雯给书中爱晒太阳的孤独怪老太,添置了一把太师椅,“在街角老虎灶旁,有一米来宽的凹角,放了把花梨木太师椅。靠背板正面,雕有牡丹花……朱三小姐走累了,歇歇脚”。
这个新短篇集子出版后,任晓雯忽而惊觉,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自己,竟开始“如此密集地描述生命的衰败与终结”。《杨金泉之死》《别亦难》《换肾记》等都写到了人进入老年后的时光。《朱三小姐的一生》开头便是:“她已老瘦成一把咔吧作响的骨架子,却仿佛永远不会死。”但任晓雯并非有意为之。“进入不同人生阶段,有些变化连你自己都不能轻易察觉。”
任晓雯已经专职写作七八年,清晨5点随闹铃起床,6点坐到写字台前,每天创作3小时,状态轻松。“昨天那个打开空白文档,惶惶然敲下‘岛下二字的我,是无法想象今天的笃定和确信的。我希望在文字里重新找到当年的那个我,对她说:嘿,不要忧虑,努力去写,放心去生活。”
任晓雯最近在写一部新长篇。故事灵感源自“沉思”文件夹里的一则旧新闻。但这一次,她不再书写上海,而是将那则北方故事,移植到一个虚构的南方小镇。任晓雯觉得,最好的写作状态,应该像残雪、阎连科一样,到了60岁,还要不断否定自己,突破自己。
她说:“作家的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对自己满意了,人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