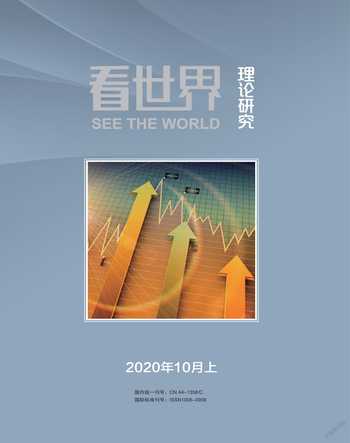浅谈果戈里《钦差大臣》中的讽刺艺术
王思琦
摘要: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钦差大臣》是果戈里于1836年正式发表的讽刺喜剧,其中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和对比的表现手法在荒诞与幽默中强有力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阴暗腐朽,讽刺了彼时社会官僚的丑恶嘴脸。其独特的创作风格给俄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俄国文学中的许多传统都能在他的创作中找到源头,因此他被很多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家奉为圭皋。
关键词:果戈里;钦差大臣;讽刺手法
对人、事、物的批评和愉悦受众(听众、观众和读者)是讽刺性文学作品的两个要素,讽刺性戏剧旨在运用恰当的技巧营造幽默的氛围,让观众在捧腹大笑之后回味反思,进而感到愤怒,使得批判深入人心,这样一部作品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现实主义的手法
果戈里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当上公务员后生活拮据,他在贫困的生活中切身体验过“小人物”生活的悲哀,所以《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果戈里采用平实逼真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当时俄国的典型官僚人物形象,不仅揭露了俄国偏远城市地方官吏的本质,而且对整个俄国社会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赫列斯达科夫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文章一开始对赫列斯达科夫的描写:“外表不难看,穿一身便服,脸上有一副沉思焦虑的神气……”见他饥肠辘辘,旅馆的老板施舍饭给他,他不但不领情,反而挑三拣四,骂骂咧咧;在旅馆住了一个多星期,“买什么东西都是赊账,一个子儿也不付……”寥寥数笔,只是客观陈述,果戈里就将一个表面上气韵不俗,实际上却爱慕虚荣、傲慢刻薄、身染彼得堡贵族官僚气息的青年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让读者觉得他可怜又可悲,可恨亦可笑。
市长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俄国官僚的自私自利、愚昧荒唐、横征暴敛、搜刮勒索、欺压百姓。当市长听闻“钦差大臣”私访的消息时,立马吩咐下属各级官员采取应对措施,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分配各项工作,“对症下药”的本事实属一流;面对赫列斯达科夫向自己的女儿玛利亚和妻子安娜求婚的无耻举动,市长非但不觉得这是一桩丑事,反而仔细盘算起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企图借此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作为官场老手,市长看人说话的能力毋庸置疑,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压迫勒索;当他最终得知钦差大臣是冒牌货的时候,惊讶中透露着尴尬,试图逮捕散布谣言之人来挽回自己的面子。
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比如慈善院长、法官、邮政局长等,或是迫于市长的压力,或是自身本就品行不端,都与市长同流合污,齐心协力应对这位假“钦差大臣”。但当他们依次单独接受赫列斯达科夫的会面时,为了弱化自己的责任,便在背地里恶语中伤。
果戈里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力求真实, 没有过多使用抽象手法便近乎完美的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欺上瞒下、谄媚钻营、腐败不堪的本质特征。果戈里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每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皆与自身的身份地位高度契合,人物之间的对话也都是原生态的语言,不加任何修饰,这样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将社会现实艺术化,让那些上流社会的观众在嘲笑剧中人物的同时也在嘲笑自己,彰显出意想之外的讽刺喜剧的艺术效果。
二、对比的表现手法
上文已经提到赫列斯达科夫的出场形象——穷困潦倒、身无分文、靠人施舍,而在被市长以及手下的官吏误认为钦差大臣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长对他极尽谄媚,邀请他入住自己的房子,提供厚实的羽绒被;市长夫人和女儿向他投去欣赏的目光;各级官员毕恭毕敬,在晚宴上陪着吃喝玩乐……突然间麻雀变了凤凰,赫列斯达科夫索性假戏真做,吹嘘有多少漂亮的女演员拜倒在他的脚下,有多少将军都害怕他,炫耀自己吃的食物是用“蒸汽船”从法国巴黎运来的,还说自己和普希金是好朋友。即便他的说辞漏洞百出,市长和官员们依然异常狂热的捧场附和。在与官员们单独会面的时候,赫列斯达科夫向他们借钱,官员们正巴不得用钱了事,一百卢布、二百卢布,直到八百卢布、一千卢布,赫列斯达科夫的胆子越来越大,钱越借越多,简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赫列斯达科夫前后生活境况戏剧性的转变,反衬出这些官员的愚昧无知,为小说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赫列斯达科夫怕东窗事发,准备逃跑,临走时又骗取了上等马车和充足的粮食盘缠,再次狠狠戏弄了市长一把。假钦差一去不复返,邮政局长遵照市长的吩咐,在拆看邮件时识破了赫列斯达科夫的假身份,戏剧发展达到高潮。赫列斯达科夫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说明了事情原委,给每个官员起一个外号,肆意侮辱嘲笑了一番。官员们得知真相后,气急败坏,纷纷破口大骂:“他连破抹布都不如”,“浅薄无知,根本一点不像钦差大人,哪怕是手指尖那么大的地方都不像……”众官员对赫列斯达科夫的态度与之前截然不同,这一对比也侧面反映了他们的愚蠢。
就在此时,有人通报钦差大臣即将抵达,众官员瞬时呆愣当场。至此,时间定格,落幕,剧终。“哑场”这种特定的艺术模式,与刚才的喧闹形成了静与动的鲜明对比。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哑场”成为最具穿透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为作品画上圆满的句号,发人深省。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说过:“无论看《钦差大臣》多少遍,尽管你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还是会为它的结尾所深深触动,被它惊人的美、感染力、非同凡响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形式以及充满灵感的舞台意图所吸引。”
另有一条暗线,自始至终贯穿着整部作品——理想与现实的对比。法官本应该是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表,但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却玩忽职守,卷宗乱堆乱放,不想看也看不明白,还在法庭这样庄严肃穆的地方悬挂打猎用的鞭子;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知,还扬言接受别人几条小猎狗,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算不上受贿;手下的陪审官嗜酒成性,他却视若无睹;法院的看门人在候审室里养的鹅到处乱窜,毫无秩序可言,法官也只是把鹅赶到厨房了事。慈善院长本应该宅心仁厚、乐善好施、宽以待人、心存大爱,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但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却将病人视如草芥,病人们像打铁匠一样,穿戴肮脏随意;有些病人经常抽烟,院长不但不劝阻,反而认为人的生死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不需要浪费贵重药品;医院的工作人员不会说俄国话,连与病人最基本的沟通都有障碍,但仍然可以伴随院长左右,得到重用。邮政局长本应该遵守职业道德,时刻督促职员保持细致谨慎的工作态度,安全准时收送邮件,保证客户所获信息的及时性,但伊凡·库兹米奇却只是因为处于好奇就私拆甚至扣留别人的信件,违反职业道德,侵犯他人隐私,将别人的秘密当热闹看。再说市长,本应该带领各级官员脚踏实地为人民造福,但市长却任由官员们胡作非为,甚至为了应对上级领导还帮他们出馊主意;街上垃圾成山,五年前就拨款筹备的教堂根本没有建造,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当街打人,士兵赤身裸体满街乱跑,整个城市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这些滑稽荒诞的行为发生在这些本该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官员身上,其间的巨大反差让读者和观众印象深刻,讽刺喜剧的效果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结语
鲁迅先生曾说:“果戈里创作文学作品的奇异之处在于他全方位地把当时的地主官僚们展现得极其平常,或者在常态下把寻常的事情变成悲剧。”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说:“果戈里文学创作特色,是将严肃与诙谐,悲剧与喜剧,平庸与伟大,美丽与丑陋交织在一起。”果戈里的讽刺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反复品味,并深入研究,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