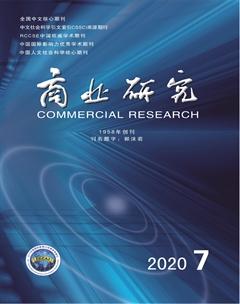演化博弈视角下企业组织冲突的诱因、升级与管理
张颖 张微 刘大维



内容提要: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类企业组织冲突呈现频发态势。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聚焦于有限理性下群体间企业组织冲突问题,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或企业员工的认知评价等私人信息发生变化,企业员工改变原先的行为策略,偏离原先稳定的均衡状态,导致组织冲突爆发。如果管理者没有注意到外部环境和内部认知的变化,仍然按照原有的思维模式进行处置,组织冲突将趋于升级扩大化。随着其他员工相互模仿学习采取新的对抗行动,原先处于稳定均衡状态的企业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发生危机,造成组织冲突升级和扩大化。企业管理者需要积极有效地管理群体间组织冲突,充分发挥组织冲突的积极意义,通过民主管理、直接沟通交流,或者推动组织变革,将功能失调型冲突及时转化为有益的功能型冲突,建立一个积极型冲突的和谐组织。
关键词:组织冲突;演化博弈模型;群体间冲突;积极型冲突;企业组织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7-0122-08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正经历着艰难、深刻的改革调整和体制转型过程,部分下岗企业职工生活困难,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劳动条件、用工制度、劳动时间等劳动权益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国企改革过程中进行资源配置与利益调整,必然导致劳资矛盾、群体间组织冲突。组织冲突在企业运作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企业组织冲突管理始终是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全国各地频发劳资冲突群体性事件,凸显剖析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演化机理和处置措施的重要意义。
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企业组织冲突事件的发生逐年增多。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加快,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国内市场,民营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整体上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和新特点。一些地区由于没有高度重视这种变化,未能及时构建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劳动者法律保障机制,导致企业内部组织冲突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劳资纠纷增加。1995年《劳动法》实施当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3万件,涉及劳动者12.3万人。2002年,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高达18.4万件,涉及劳动者60.6万人,劳动争议的数量是1995年的5.6倍,涉及劳动者的人数也增加了5倍[1]。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三部劳动法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的叠加效应下,因企业效益低下或破产而引发的裁员造成集体劳资争议等矛盾纠纷急剧增加。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各地频繁发生较大规模的集体停工等职工群体性事件,职工走出厂门堵塞道路、静坐、集体非正常上访等事件多达百余起[2]。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较大,劳动争议案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劳动争议案件调解空间缩小。发生冲突的企业以往仅限于“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现已扩大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面对我国范围越来越广、诱因越来越多样化的企业冲突状况,企业组织冲突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只有准确把握企业内部群体间组织冲突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和冲突升级的途径,才能通过有效的冲突管理实践,使之转化为功能型冲突,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劳资关系的矛盾较小,企业内部的群体间组织冲突并不突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港台学者开始了有关组织沖突的研究,9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开始涉足该领域,刘德海等运用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诱因、网络特征、演化机制、应急对策和评价体系等[3-7]。
组织行为学家Pondy在其关于组织冲突的经典文献里描述了冲突过程的五个阶段,并建立了组织冲突的理论雏形[8]。Thomas集中发展了冲突的两个模型:冲突的动态过程模型和冲突的结构模型[9]。Putnam和Folger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10],而Vliert更注重研究冲突的预防和升级[11]。但是现有文献集中在人际冲突和个体内部冲突,对群体间冲突研究较少。
虽然博弈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现有理论文献很少运用博弈论分析群体间组织冲突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传统博弈对参与者的强理性假设[12],参与者对博弈结构的完全认知、具有很强的预测、推理、分析能力,通过演绎推理达到具有“自我实施”特征的、可预测的纳什均衡。传统博弈论的个体参与者强理性假设,使得其难以适合实际管理所面临的群体间组织冲突问题。国际上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演化博弈理论着重分析了有限理性的群体参与者如何通过学习、进化过程达到纳什均衡。其中,主观博弈模型进一步对博弈均衡的演化问题提出了概念性分析框架[13]:在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或企业员工的认知发生变化情况下,其面临的行动集合发生变化;而作为组织规则的博弈均衡相应地经历了原认知均衡、认知危机、规则危机、规则转型和新的认知系统达到稳定等不同阶段,从而展示了运用主观博弈模型分析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可行性。通过文献梳理、实证分析和抽象思维后,确定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基本假设
本文主要分析群体间冲突中的组织冲突问题。组织中的冲突可以呈现出多种形式,包括组织间冲突、群体间冲突、人际冲突和个体内部冲突等[14]。发生在两个或者多个组织之间的冲突称为组织间冲突,例如企业接管、合并和兼并等过程中经常产生组织间冲突;当冲突发生在群体或团队之间时称为群体间冲突,组织管理者必须认真妥善地处理群体间冲突,努力避免使之发展成为影响组织绩效的功能失调型冲突,但是现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少;人际冲突是两个或者更多个人之间的冲突,许多个体差异都会导致人际冲突,包括个性、态度、价值观、理解力、情绪、沟通障碍和文化差异等;个体内部冲突包括角色间冲突、角色内部冲突和个体角色冲突等。
本文分析有限理性的群体行为导致的组织冲突现象。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对特定的组织在特定的时期所发生事件的环境和背景进行研究和考察的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实验式的或者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等数理分析工具对组织冲突进行分析时,必须将人的各种行为特征加以抽象,成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管理人”假设等一定行为范式的参与者。演化博弈理论在“管理人”假设的基础上,将群体参与者的有限理性行为进一步限定为具有惯性、近视眼和试错法尝试等特征[15]。
任何组织的成功都取决于管理者制定有效决策的能力。一个有效决策是及时的,能够为人们所接收并能够满足期望的目标。来源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决策模型,认为决策者是理性(rationality)的,追求最优化决策。由于事实上存在着时间的约束,人类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管理者的偏好和需要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理性模型只是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所追求的理想模式,但是并没有反应组织管理决策的现实[16]。
西蒙认为存在着种种限制使管理者无法达到完全理性,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管理人”理论。由于管理者面临着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经营环境,追求最优化所要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成本太大,管理者往往采用惯例等经验决策法则,追求的是满意解[17]。
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要求是在“经济人”理性假设的基础上,要求具有“完全理性的共同知识”,均衡是在博弈规则、参与者理性和收益函数等都是共同知识的充分条件下,通过参与者的分析推理过程得出的可自我实施的稳定结果。传统博弈论脱离现实的强理性假设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博弈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国外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生物种群的演化现象分析,并在90年代迅速兴起的演化博弈理论,突破了传统博弈对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认为“均衡是作为小于完全理性的参与者寻求最优化的长期过程的结果”。演化博弈的分析对象是有限理性的群体,其表现出具有惯性(inertia)、近视眼(myopia)、试错法试验(trial and errors or experiments)等特征的有限理性行为[18]。参与者在观察到对方的行动以后,根据实用主义的不同修正法则(对应着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有限理性),采取各种具体的模仿、复制等动态学习过程,包括单调选择动态、收益正性选择动态、弱收益正性选择动态等。有限理性的群体参与者,通过采取模仿、试错、复制等学习过程,利用时间弥补理性程度的不足,最终仍有可能实现均衡化过程,达到稳定的可自我实施的纳什均衡。
三、群体间组织冲突的诱因分析
企业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是在组织不同层级的群体之间发生,通过复杂的动态博弈逐步形成的,具有稳定预期的、可以自我实施的均衡①。从博弈视角分析企业组织内部的群体间冲突的产生原因,主要是管理者及其组织成员处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下,只能根据有限的经验进行决策,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其表现为惯例、模仿等行为方式。在组织冲突爆发之前,原组织体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即在管理者和企业员工的互动过程中,双方运用同样的组织规则(或依据特定的组织文化)推测所处的外部环境、预测不同行动的收益并选择相应的行动策略,同时他们对组织规则的认知也是一样的。只有当外部的组织环境或者成员内部的认知评价体系发生变化后,其影响积累到一定阶段,经营效益持续下降,或企业组织面临着内外部危机,则现行组织规则无法实现成员认定的应得权益,其将较大幅度地修改可行策略集合,通过扩大策略启用集合维度来搜寻和试验新的决策规则,造成原本稳定的、可自我实施的組织规则产生了认知危机,一旦成员采取新的行为方式并为周围成员所模仿,群体间组织冲突就产生了。
(一)外部环境因素: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改变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等一系列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转变,企业组织管理日益受到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
1.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以前国内封闭的经济交换域开始扩展到全球的市场交换域。企业不但要与国内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本地企业还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带来的强势竞争挑战。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面向海外投资的企业将进一步面临着文化差异、外国政府干预、所在国政治冲突事件等意外因素的冲击。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协调控制工作的难度日趋复杂,企业也要逐步调整其经营战略、市场营销手段、组织管理模式等,减缓由此造成的企业内部组织冲突。
2.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的迅速普及,大大加快了企业电子商务、ERP、SCM、BPR等信息化建设步伐[19]。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产品寿命周期越来越短,产品品种数目迅速增加,顾客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他们不但对产品的品种、规格、花色、需求数量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要求,而且对产品的功能、质量和可靠性的要求日益提高。
3.以2003年非典危机、9·11恐怖袭击、新冠疫情暴发以及近两年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下降等为代表的外部冲击表明,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将日益复杂,影响因素也呈多样化趋势,对企业组织管理产生了新的挑战。
4.政府的外部干预将使得企业经营环境发生根本变化。2005年中海油在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下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失利、美国对我国中兴和华为公司的打压案例,生动地表明来自政府的干预对企业经营环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5.从微观方面来说,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加之2020年初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疫情,导致传统的商业模式及办公模式发生转变。线上交易方式深化发展,网红带货主播直播销售方式兴起,打破了原有的销售模式;线上远程办公的技术支持日渐成熟,会议召开以及合同签署可逐步无接触式实现,传统销售模式下的“酒桌文化”、“客户服务”等营销手段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擅长于这类销售手段的从业人员在企业内部面临着收入水平急剧下滑、职位可替代性升高等危机,这也加大了冲突发生的潜在可能。
上述外部环境对组织规则带来的冲击可能仅仅加剧了组织冲突,尚不足以引发组织变革。因为在一个柔性组织结构中,组织成员在可选的行动方案的边界范围内可能成功应对外部冲击及其带来的内部冲突。只有当外部环境冲击和组织内部长期积累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普遍引发对组织规则的认知危机,导致在组织不同成员的群体间发生较大的冲突。
(二)组织内部因素:组织成员效用评价发生改变
Nelson和Quick列举了一些企业组织内部的冲突诱因,分为源于组织的性质和工作的组织方式的结构因素和源于个体差异的个人因素等[20]。其中,与结构因素有关的冲突诱因包括专业化、相互依赖性、公用资源、目标差异、职权关系、地位矛盾、管理权限模糊等因素;与个人因素有关的冲突诱因包括技术和能力、个性、观点、价值观与道德观、情绪、沟通障碍、文化差异等。
组织内部因素的作用机制有以下两种:
1.在企业原有的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的影响下,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按照现行规则进行重复博弈,有可能导致成员之间权力、资产、角色分配等方面的不公平。一旦这些组织规则的合法性在内部成员中受到广泛的质疑,并且超过了临界规模,组织内部的群体间冲突就爆发了。
企业员工在做出决策时,其拥有考虑各种个人因素的私人信息,常见的一种私人信息是公平原则②。我们将组织成员j考虑公平因素的效用函数定义为:
uj=pj+βj(pj-pi)(1)
其中pj為组织成员j的绝对收益,即根据组织规则进行博弈后获得的支付,为双方的“共同知识”。βj(pj-pi)为组织成员j的相对收益,即个体的私人信息;βj为相对收益系数,其绝对值的大小反映了组织成员j对收益差距的敏感程度;其值非负,反映了组织成员j追求收益公平的利己主义行为倾向。一旦由于公用资源、目标差异、职权关系、地位矛盾等组织结构因素导致的矛盾积累过大,该私人信息达到临界值以后,组织成员将改变原先的行动方案,组织冲突显现化。
2.在原先组织规则的安排下,那些采用新行动并获得较好的实施效果的成员,带动了其他组织成员效仿③。一旦其数目积聚到一定比例,根据KMR机制将引发成员对现有组织规则的认知危机[23];或者该成员的能力不断锻炼提高,并获得较快升迁,推动了现有组织规则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那些具有最好表现的行动方案往往并不是最成功,原因之一是难于为大多数人所模仿[24]。在现有组织体制下,那些能够获得最好效果的异类表现,却常常容易引发管理层更为强烈的抵制。
四、群体间组织冲突升级的演化博弈分析
(一)群体间组织冲突的表现形式
并非所有的组织冲突都是有害的。有些类型的冲突有助于产生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提高企业组织的创造力。因此,组织冲突包括良性的功能型冲突和恶性的功能失调型冲突。功能型冲突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一种有益的、建设性的对抗,有利于产生新的观点、改善工作关系、提高工作绩效,有利于个体间的学习和成长[25]。识别功能型冲突的关键是其源于组织成员认知上的差异。功能失调型冲突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一种无益的、破坏性的对抗。其源于情绪和行为上对立,危险在于冲突并不集中在工作本身,而是指向了冲突本身以及参与者[23]。
群体间冲突可能对每个群体的成员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增加对任务的关注度等。但也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带来相互敌意的增加以及沟通交流的减少。组织管理者必须积极管理群体间冲突,避免其发展成为功能失调型冲突。研究表明,当群体间竞争处于零和博弈状态时,就会导致某一群体以防卫、攻击和偏见的态度对待其他群体[26]。管理者应当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体间的合作行为,如调整绩效评价方案、增加对团队精神等群体间行为的评价内容、利用顾客满意度等外部途径评价群体间的行为、鼓励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合作,组建跨部门的工作团队等培养相互信任。
(二)群体间组织冲突升级的演化博弈分析
关于组织冲突升级的原因,现有文献研究没有将组织冲突产生的原因研究透彻。一些文献认为两者之间差异很小。但是,冲突产生和升级的统计模型表明,环境和背景变量在组织冲突的产生方面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冲突双方的互动关系则对组织冲突的升级起到更大的作用[27]。一旦冲突发生,包括主观博弈模型在内的博弈论等侧重策略互动的理论将会提供更为合适的解释。
如果企业的组织冲突管理机制(包括危机管理)的预警系统没有针对群体间冲突产生前的一些微小征兆,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积极管理,组织内的各种矛盾将不断积累并趋于激化。组织成员将尝试新的决策行为,组织冲突开始爆发。如果事态发展的结果证明选择新的决策行为的确给当事者带来更大收益,这种诱发条件和反馈机制将使得组织的其他成员进行模仿。一旦大量的组织成员采取偏离原纳什均衡的新的行动策略,那么现存的组织规则不再具有约束个人决策、节约信息加工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作用。此时,大范围发生的组织群体间冲突将引发组织规则、组织文化的危机。
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具有有限理性的群体参与者表现出来的惯例、模仿、试错等动态学习行为,其中常见的一种学习模型是模仿者动态模型[28]。每一个参与者只代表某一特定的同类群体,其长期坚持采用某种纯策略si,i=1,2,…,I,且采用某种策略的群体比例的增长率θ·i(t)是此策略效用πtsi与群体平均效用π-t差的严格增函数:
其中,不同策略si、sj的学习障碍为λi,λj,Bi(s)=j∈Iπj>πi为在群体分布比例s下具有比策略i更高收益的策略集合。
在组织成员的有限理性“管理人”假设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的一般化模仿者动态模型对组织冲突的升级过程进行分析,其表现为组织成员采取新行动的群体比例的增长。
因此,根据上述模型分析,企业组织内部的群体间冲突的升级强度θ·i(t)取决于:(1)当前状态下采取新行动的“异类”组织成员所占比例θi(t);(2)组织成员在考虑公用资源、目标差异、职权关系、地位矛盾、管理权限等私人信息后,对现有组织规则不满而准备采取新行动的预期收益πi,πj;(3)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实施难度,即不同策略的学习障碍λi,λj。那些能够收益最高收益的策略往往伴随着较大的风险,具有较大的学习障碍,难于被成功模仿。
根据(3)式一般化模仿着动态模型,可得图2所示的演化阶段示意图。在初始时刻t0,由于采取新策略的成员比例较低,因此增长速度较慢。但是,随着成员之间的模仿学习效应,该比例迅速增长,体现为逻辑斯蒂增长曲线特征。但是,当事态发展达到高潮后,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一种是事态得到有效处置趋于化解;一种是事态持续恶化。不同演化方向取决于关键因素是否得到有效应对处置。
五、群体间组织冲突的管理
(一)有效应对组织群体间冲突的管理技术
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将组织冲突转化成具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型冲突,企业的管理者需要采取一些能够有效应对组织冲突的管理技术。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作为长期稳定的均衡结果,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柔性。对于那些能够在现有组织规则下加以解决的群体间冲突,可以采取确定最高的合作目标以及当面进行沟通谈判等管理技术;而对于那些引发了现有组织规则深刻危机的组织冲突,则必须实施组织变革,通过改变组织人事或组织结构,形成新的、可以稳定预期的组织规则、组织文化。
1.确定最高合作目标。对于冲突各方来说,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比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目标都更为重要。当前,很多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组织内部群体间冲突的频发,劳资关系紧张,往往伴随着企业共同奋斗目标的丧失以及人心涣散。而以奇瑞汽车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艰苦创业环境中,正是通过建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汽车工业的组织共同目标,增强了企业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避免了功能失调型冲突。
2.当面进行沟通、谈判。很多组织冲突都是由于沟通渠道不畅产生的,通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进行直接的沟通谈判,可以使这些由于沟通不畅、信息失真、对工作方式、组织原则等产生误解引发的组织冲突立刻消解。即使不是由于沟通问题而产生的组织冲突,双方选择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谈判,也是一种理性解决复杂组织冲突的明智选择。在日本、欧美等国家产生较大影响的《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通过企业管理者、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紧密沟通和结合,有效地将功能失调型组织冲突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的组织冲突。
3.实施组织变革。当企业组织面临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成员巨大压力引发的组织体制危机时,进行组织变革则势在必行,变革方式主要有渐进式变革、战略性变革和转型式变革。类似于业务流程再造的变革程序并不能保证变革的成功,企业组织进行成功转型的关键是人的因素[30]。
Lewin提出了一個与主观博弈模型的解释比较接近的组织变革模型[31]。该模型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两种相反的力量作用的结果,一种力量试图保持现状;一种力量推动变革。变革步骤包括:解冻——接收变革的观念,打破维持现状的平衡点;转变——新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取代了原有的模式;固化——新的行为模式得到巩固和强化。
(二)冲突管理的时机和原则
1.在企业组织的群体间冲突的潜伏期,企业系统将会不断出现一些微弱的、与冲突有一定联系的信号。当企业出现一些矛盾激化的征兆时,如何处理这些信号将成为建立积极、高效的组织冲突应急管理机制的关键。如果企业管理者停留在现有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下的思维惯性中,根据“颤抖手均衡”思想[22],这些信号将被解释为企业员工由于意外原因造成的错误或干扰,而产生偶然偏离,其是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由于现存企业组织体制的认知均衡具有一定的柔性(稳健性),作为群体间组织冲突产生前的征兆,企业员工的小范围偏离行为并不会改变现存组织体制的稳定性。在这种惯性思维指导下的企业管理者在群体间冲突的潜伏期很难制定有效应对措施,将冲突遏制在萌芽状态。
建立企业组织冲突管理的应急机制,其预警系统在冲突潜伏期应及时、敏锐地捕捉到企业系统中各种矛盾激化的信号。企业管理者应采取“前向归纳”的思考方式[27],进行“最大灾害状态分析”,即根据现存组织体制中积累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尚处于潜伏期的各种信号,敏感地预见到企业员工将要采取的抵制、敌对、消极、对抗等各种可能态度和行动。据此,企业管理者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有效方案,迅速采取措施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群体间组织冲突进行积极地转化和引导。
2.在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升级阶段,企业管理者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推动冲突向着有利方向转化。企业管理者要保证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有效,尽早地收集到相关的真实信息,尤其是要着重分析那些决定企业员工态度、行为方式的私人信息,以便正确判断在现有组织体制下能否有效加以解决,由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影响群体间组织冲突的升级强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员工采取新的行动的比例(其决定了可被其他员工观察到的概率大小)和被成功地进行模仿的概率(即新行动的学习障碍)。因此,在组织冲突处于萌芽阶段时,企业员工采取新行动所占的比例较低,冲突行为的扩散速度较慢。此时,如果企业管理者判断在现有的组织体制下通过积极沟通、明确组织目标等能够有效化解冲突的危害,其应加大沟通的力度,使群体间冲突在初始阶段得到及时的转化,避免进一步蔓延。但是,如果管理者判断必须进行一场组织变革才能适应当前面临的内外挑战,则需要树立体现新的组织文化的学习榜样,鼓励企业员工改变原来的认知惯性和行为习惯,主动打破原有均衡状态。
3.企业管理者和不同层级的企业员工在冲突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模仿、适应、惰性、试错等相互作用的学习机制,多种可能选择的组织体制和组织文化相互竞争作用,并最终演化成为各方预期收敛的新的稳定均衡。此时,组织变革顺利实施,企业员工的行为向着新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稳定收敛,群体间的组织冲突进入恢复期。
在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升级阶段,企业员工的情绪和行为渗入很强的非理性因素。在进入恢复阶段后,其采取的行为方式将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企业管理者必须注意到这一现象,一方面应通过民主管理,主动解释变革的合理性,争取取得一致的认识,提供培训机会,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新的体制下所需要的技能,而不能简单地买断工龄后实施下岗分流,把负担推向社会;另一方面,应保持管理措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向企业员工提供新的稳定、可信的体制预期,让员工看到变革后的蓝图,尽力减少企业员工由于模仿行为的滞后效应造成的损失,同时保证新建立的组织文化和薪酬系统等组织体制具有鼓励企业员工采取新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激励相容特点,避免旧的行为方式在惯性支配下继续延续。
六、结论:建立一个积极型冲突的和谐组织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中美贸易争议较大,国内企业经营环境面临的问题较多,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也是管理层可以预见的。组织内部的小冲突如果不得以妥善解决与规制,有可能会扩大范围、愈演愈烈,甚至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正经历着艰难、深刻的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过程,下岗职工生活困难,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劳动条件、用工制度、劳动时间等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市场化转型改革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现象,劳资矛盾凸现、群体间组织冲突不断。如何分析社会转型期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诱因、升级途径与管理手段,已经成为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的关键任务。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系统研究了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诱因、升级途径和管理措施。首先,企业群体间组织冲突的诱因是由于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或企业员工的认知评价等私人信息发生变化,导致企业员工改变原先的行为策略,偏离原来稳定的均衡状态,而另一方面,因为市场环境、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包括管理者在内的组织成员只能限制于本身的经验条件来做出决策,加之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决策者一般会表现出惯例、模仿等行为方式,组织冲突有了发生的可能,而一旦多数成员对特例成员的行为采取模仿,群体间组织冲突就会产生。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互联网运营模式崛起,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得劳动及商品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逐渐降低,无论管理者抑或是员工的“寻租”行为越来越难以实现,员工对于自身价值的实现愿望逐步提高,如果管理者没有注意到外部环境和内部认知的变化,仍然按照原有的思维模式进行处置,组织冲突将趋于升级扩大化。因此,在冲突潜伏期,企业中会有微弱的相关信号来提示管理者,管理者需要及时发现组织冲突的苗头,建立企业组织冲突管理的应急机制,其预警系统在此期间要及时采取一些能够有效应对组织冲突的管理技术。“向前归纳”的思考方式应该受到管理者的重视,进行“最大灾害状态分析”,有针对性的、因人而异的将冲突进行积极的转化和引导,对于那些现有制度框架下可解决的冲突,可以进行有效的沟通谈判;而另一些本质上是不满于现有制度构成的矛盾,则必须实施组织变革,最终形成新型且稳定的组织文化与规则。
其次,从冲突产生和升级的模型可以看出,环境和背景变量影响了组织冲突的产生,而冲突双方的互动关系则对冲突升级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随着其他员工相互模仿學习采取新的对抗行动,原先处于稳定均衡状态的企业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发生危机,造成组织冲突的升级和扩大化。在冲突升级期间,企业管理者要具备能力使冲突向有利方向转化,如保证信息沟通渠道的有效畅通,以最快的速度收集到与冲突相关的真实信息,对组织解决冲突的可行性以及难易程度做出最快速的判断,最后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或改革相应的制度或组织结构。
最后,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并非所有的组织冲突都是有害的,某些类型的冲突可以促使组织成员对解决问题的方式产生新思维,有助于提高整个组织的创新性与创造力,所以我们要分清能带来效益的功能型冲突与带来损失的失调型冲突。企业管理者需要具备对不同类型冲突的鉴别能力,并积极有效地管理群体间组织冲突,充分发挥组织冲突的积极意义,通过民主管理、直接地进行沟通交流,或者积极推动组织变革,化危为机,将功能失调型冲突及时转化为有益的功能型冲突,建立一个积极型冲突的和谐组织。
注释:
① 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体制(或制度)看作是博弈的参与者、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均衡策略。青木昌彦(Aoki,M.)教授将组织体制看作是各种制度的集合,其中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summary representation)。
② Bethwaite, J.和Tompkinson, P.在利他主义的实验博弈(ultimatum game)研究中提出了非自利的效用函数(non-selfish utility function)[21]。
③ 根据进化生物学理论,在稳定的环境下,分子水平上的变异对于进化选择来说通常是中性的或者略为次优的[22]。
参考文献:
[1] 吴木銮,陈强.缓解劳资矛盾,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有望纳入法规[N].中国青年报,2005-10-20.
[2] 杨清涛.我国劳资矛盾的现状及和谐劳资关系构建[J].中州学刊,2017(1):72-75.
[3] 刘德海. 群体性事件的演变与评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刘德海,赵宁,邹华伟.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政府应急策略的多周期声誉效应模型[J]. 管理评论, 2018,30(9): 239-245.
[5] 刘德海. 基于最大偏差原则的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绩效评价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6, 24(4):138-147.
[6] 刘德海, 陈东, 黄静. 管理越位现象:医患群体性事件社会网络的稳定性与效率[J]. 中国管理科学, 2016,24(1):169-176.
[7] 刘德海,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劳资冲突信号博弈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0,18(s1):74-80.
[8] Pondy, L. R.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Concepts and Mode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67,12(2):296-320.
[9] Thomas, K. W. Conflic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A].In Dunnett, M. D., Hough, L. M.,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C].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76:889-935.
[10]Putnam, L. L., Folger, J. P. Communication, Conflict and Dispute Resolution[J].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8,15(4):349-359.
[11]Vliert, E.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Escalation[A].InDrenth, P. J., Thierry, W., de Wolff, C. J. eds. Handbook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C]. New York: John Wiley, 1984:521-551.
[12]Binmore, K. “Foundation of Game Theory”,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Sixth World Congress, Edited by Laffont, 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31.
[13]Aoki, M.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J].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1996,47(1):1-3.
[14]Deutsch,M. Sixty Years of Conflict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1990, 1(3):237-263.
[15]Aoki, M.,Okuno-Fujiwara,M.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Systems[M].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6:23-30.
[16]Harrison, E. E. Th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43-48.
[17]Smith, M.J.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volutionary of Animal Conflicts [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74, 47(1):209-221.
[18]Simon, H.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M].New York: Macmillan, 1957:33-40.
[19]Nelson,D.L., Quick,J.C.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oundations, Realities & Challenges [M].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23-33.
[20]Kandori, M., Mailath, G. J.,Rob,R. Learning, Mutation, and Long Run Equilibria in Games[J]. Econometrica, 1993, 61(1):29-56.
[21]Bethwaite, J., Tompkinson, P. The Ultimatum game and Non-selfish Utility Func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996,17(2):259-271.
[22]Kimura, M. The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M].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3-34.
[23]Amason, A. C., Hochwarter, W. A., Thompson,K. R., Harrison, A. W. Conflict: An Important Dimension in Successful Management Teams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95, 24(2): 25-35.
[24]Liu De-hai,Wang Da-gang. Weakly Payoff-positive Dynamics Considering Anticipation i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Proceedings of 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2004(1):475-479.
[25]Cosier, R. A., Dalton, D. R. Positive Effects of Conflict:A Field Assess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1990,1(1): 81-92.
[26]Sherif, M.,Sherif,C. W. Social Psychology[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45-50.
[27]Reed,W., A Unified Statistical Model of Conflict Onset and Escal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 44(1): 84-93.
[28]Smith, M. J.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25-33.
[29]Sethi, R. Strategy-Specific Barriers to Learning and Nonmonotonic Selection Dynamics [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8,23(2): 284-304.
[30]Cheyunski,F., Millard,J. Accelerate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Science, 1998, 34(3): 268-285.
[31]Lewin,K.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J]. Human Relations, 1947,1(1): 5-41.
(責任编辑:赵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