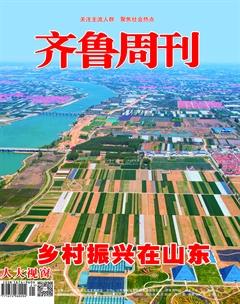颜炳罡:斯文在兹,以儒学重建乡村
米一
“在山东各地形成的乡村儒学,遥契孔孟原始儒学之精神,近承泰州学派人伦日用即道之传统,呼应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乡村建设之实验,重开宋明儒者讲学之风,让儒学为振兴乡村、建设乡村文明服务。”
——2013年以来,颜炳罡和尼山圣源书院的专家学者以儒学教化村民,引领了乡村儒学的山东实践。
“颜四书”的读经与“三堂”

▲颜炳罡倡导“三堂建设”,即:中堂、乡村(或社区)儒学讲堂和礼堂。
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现代新儒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颜炳罡,曾在山东大学的四书公益原典讲堂讲“四书”十六年。这个读经班,不设学分、公益开放,来者不究、往者不追,每周一次,风雨无阻。颜炳罡也因此被山大师生尊誉为“颜四书”。他不仅带着众人在课堂解读四书,还带着一众学子,登鹊山、渡黄河,再发“吾与典也”之叹。
在颜炳罡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四书,代表着儒家的价值观。颜炳罡倡导的“四书原典”的学习,一直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读经班就有很多社会人士参与,他们和参与过读经班的毕业生,又将读经诵典的传统带向了其它高校、带向了社会,还曾诞生过驻济高校国学社联盟、“明德天下”国学堂。
2013年,颜炳罡成为尼山圣源书院的执行院长。该书院位于山东省泗水县孔子出生地尼山脚下。他提出“打开院墙办书院”,让书院成为村民的书院,将儒家经典带入了乡村。学者们在乡村进行义务儒学讲习,宣传孝悌仁爱之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乡村文化氛围、人文环境、道德风貌等发生了很大改变。慢慢地,尼山圣源书院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西大院”。这就是乡村儒学最早的雏形。
颜炳罡喜欢说:“我们是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人。”在乡村儒学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不仅要身背干粮,有时甚至还要献出一块干粮。颜炳罡每年都会给尼山圣源书院所在的村2000元作为仁爱基金。
2014年2月,乡村儒学讲习由书院的几个村推广至圣水峪镇,设了北东野村、小城子村、小官庄村、庠厂村、营里村、南仲都、圣水峪镇等七个讲学点,覆盖十五六个村庄。另外,在泗水县城,书院学者每周开设国学大讲堂,讲授国学基本知识,同时组织经典读书会,以期提高县城教师、公务员和市民的儒学修养,培养乡村儒学师资。
在山东,已有济南、济宁、聊城、潍坊、德州、泰安、烟台、威海等8个地级市开展有乡村儒学活动。其中济宁圣水峪镇、聊城韩屯镇、青州侯王村、张家洼村、德州新四合社区、济南章丘文祖镇三德范村、淄博高青唐坊镇、烟台南水桃林村等开展的乡村儒学较为系统,效果也最为明显。
“我小时候的乡村,是一种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生活图景,一种互相信任、心无防范、真诚相待的文化氛围。但许多优秀的文化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甚至父子相仇、兄弟反睦、邻里互斗。”颜炳罡说,“我觉得圣贤学问对己有用,对生活有用,对协调人的身心健康有用,对处理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关系和邻里关系有用,对安顿我们的生命有用,应该以自己所学来回报父老乡亲,这是我从事乡村儒学的初衷。”
“我们要把乡村儒学持续发展下去,让乡村儒学真正成活,让新乡贤阶层在乡村崛起,让他们成为传承中华美德的示范者,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让我们的经典诵读活动真正发挥作用。”颜炳罡倡导“三堂建设”,他认为:每一个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社区,都应该建一个中堂。“中堂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场所,是教导孩子、开家庭会议的一个重要场所。”另外两堂是乡村(或社区)儒学讲堂和礼堂。“中国是一个礼乐文明的国家,礼堂可以和学堂融为一体,这个地方可以成为大家从事婚丧嫁娶的一个公共空间,有了这样的空间,中华文化的传承就有了载体,有了形式。”
山东各地乡村儒学讲堂都有固定的场所,有相对固定的讲师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教学内容包括儒家经典如传统蒙学读物、《论语》、《孝经》、《大学》、传统家训和现代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知识等等;以孝道为乡村儒学讲堂切入点,进而涉及夫妻、亲子、邻里和睦、文明礼貌等等。
有的村庄里设置研究会、红白理事会、小型的基金会。村里的老人到了80岁,就会收到一个蛋糕。这蛋糕一送,即便忘记父母生日的,全家人也由此而聚。这其实是一种客观可行、适合民众的“斯文重建”。
“三老”的血脉,“喊街”的传承
乡村儒学人认为,儒学是一种信仰,至上的天理和内在良知是儒家信仰的根据,而学堂、祠堂、中堂是儒家信仰建立的场所,祭天地、拜先师、祀先祖、敬先贤是儒家信仰的基本仪规。乡村儒学旨在守住乡村文化的沃土,重建乡民的信仰系统。
在学者看来,“乡村儒学”可以实现儒学由伦理道德规范向民众信仰的转化;实现儒学由精英文化对象向人伦日用之道的转化。乡村儒学既不是迷恋乡村的旧俗,更不是为了守住“破败”,也不是回到古代去,而是以开放的胸怀面对未来,面对世界,面向当下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乡村是儒学的原乡,是儒学不断发展与新生的根基。儒学是从乡土文化沃土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生存智慧、人生信仰、生活方式和思想学说,反过来,儒学是乡村文明的精神支撑、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生活方式。
自汉代起,三老制度的设计使儒学成为乡村治理的方式。刘邦明确提出:“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傜戍。”汉以后,无论朝代怎样更替,乡、里、闾、村等等名称如何变化,通过官吏设置、乡绅的道德示范、童蒙读物、宗族祠堂、家规家训以及礼俗行为的世代模仿等形式,从而使儒学深深地植根于乡村,中国乡村百姓须臾也没有离开儒学尤其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化浸润。
孟子所谓“井田制”包含着乡村儒学的原始方案:“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将孟子的“乡村儒学”由设计付诸实践、落实为真实生活,始于北宋蓝田吕氏兄弟的《乡约》订定及其实施。《乡约》明确要求村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已不仅仅是儒家理论在乡村的落实,而是形成了乡村儒学理论系统和与之相配套的实践流程,实现了由“儒学在乡村”到“乡村儒学”的转化。
到明代,泰州学派标志着民间儒学、大众儒学、草根儒学、乡村儒学的真正形成。20世纪,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泰州学派的现代版。
泰州学派的崛起是与朱元璋推动乡村儒学教化与儒化的基层治理分不开的。 朱元璋曾发布诏令:“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于阴阳拘忌,停柩暴露。……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明洪武三十年九月又颁布了“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次年,朱元璋又专门发布《教民榜文》,要求宣教员手持本铎,让一儿童牵引着,在乡社之间四处游走,高声叫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每月重复喊六次。直到20世纪在山东有的地方还保存著这一宣教方式——民间称为“喊街”。
在乡村儒学实践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三老”的血脉,“喊街”的传承。
——《四书释注》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