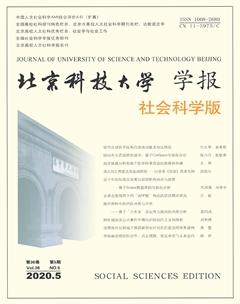论认罪答辩的审判规避效果
〔摘要〕 文章采用规范分析法,对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进行了研究。我国语境下的“认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同时包含了有罪供述和认罪答辩。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在于规避审判,而有罪供述只能够简化审判。换言之,“承认指控”是否会产生规避审判的法律效果,直接决定我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认罪答辩,而速裁程序是规避审判的典型例证。实现规避审判的路径在于:通过协商程序获取认罪答辩,同时解决定罪量刑,消除诉讼争点,并最终确保认罪协议对法官的拘束力。规避审判遵循以效率为导向的结果主义进路,即虽绕过审判但应当达到与审判相同的效果,使刑事司法系统在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关键词〕 认罪答辩;规避审判;认罪协商;结果主义
〔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5-0084-07
2018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速裁程序予以制度化,按照我国学者的解读,我国刑事审判已形成“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三级“递简”格局[1]。速裁程序是在简易审判程序的基础上,继续简化审理,即所谓的“简上加简”。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的基本前提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因此,在我国学者看来,被告人承认指控并作出认罪答辩,其程序性效果在于简化审判。但实际上,认罪答辩是在“未经审判的基础上定罪”已经成为国外学者的共识①。笔者提出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即被告人做出认罪答辩会产生什么样的程序性效果。对这一基础理论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教义解读,以及对认罪答辩的有效规范化。笔者的基本论点在于,“承认指控”是否具有规避审判的程序性效果,直接决定我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认罪答辩,而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在于规避审判。
一、 认罪答辩在刑事诉讼中的规范化
认罪答辩(Guilty plea)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指控的承认。“承认指控”这一事实性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程序性效果,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规范化处理。认罪答辩的规范化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认罪答辩的事实性行为进行规整并予以定型化,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作为认罪答辩的构成要件。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够成立规范意义上的认罪答辩。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法官会主动劝阻被告不要认罪,并建议他继续抗辩、接受审判[2](15)。因此,“认罪答辩”在早期的英美法系国家,并不具有刑事诉讼上的规范化意义。第二,赋予认罪答辩以法律效果,即认罪答辩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规范性后果或价值。例如,如果被告人做出认罪答辩,对指控予以承认,就实体法层面而言,会产生从宽处罚的效果。但是,就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而言,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笔者认为,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在于规避审判,通过认罪答辩解决案件,并没有审判发生。
“认罪”这一概念可以涵摄以下四种事实行为:一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二是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三是认可指控的罪名,四是愿意接受拟定的处罚。面对以上四种事实性行为,刑事诉讼法要制定相应规范,以便将不同的事实行为涵摄于法律条文之下,作为规范的构成要件。当特定的事实行为发生,并且符合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则相应的法律效果才有可能发生。但是,以上四种事实行为并非具有相同的规范属性。“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质上属于证据的范畴,刑事诉讼法将其定型化为“供述”,并将其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后三种行为则属于认罪答辩的范畴,刑事诉讼法将其定型化为对指控的“承认”。换言之,认罪答辩的真正意涵在于对指控的承认,其可以涵摄“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认可指控罪名”和“接受拟定处罚”这三种行为,认罪答辩应该区别于有罪供述。
“供述犯罪事实”本质上属于证据范畴,而非“承认指控”意义上的认罪答辩。作为证据的有罪供述只能简化审判,按照“孤证不能定案”的基本原则,必须综合全案证据,在审理的基础上做出裁判,不能仅仅依据有罪供述直接作出判决。因此,有罪供述不会排除法官的审理义务和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有罪供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举证程序,方便法庭审理。有罪供述的程序性效果在于简化审判,这应该不存在疑问,出现疑问的地方在于,被告人对指控予以承认,是否会产生规避审判的法律效果呢?按照我国的传统,“认罪”不会排除审判,虽然“承认指控”导致诉讼争点消失,法庭辩论和庭审对抗无法展开,但法官依然要依职权调查证据,在审理的基础上做出判决。
但实际上,2018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打破了“认罪不排除审判”的传统。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速裁程序“原则上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实质的法庭审理将不会展开,庭审中没有对抗和辩论,法官不会依职权调查证据。可以说,刑事诉讼法已经赋予了“承认指控”以规避审判的法律效果,在有限的范围内,确立了认罪答辩制度。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所言Kercheval v.United States, 274 U.S.220, 223 (1927): 223.“认罪答辩的目的和效果不同于单纯的承认或法庭外供述;这本身就是一种定罪。就像陪审团的裁决一样,它是决定性的,不需要更多;法院除了作出判决和进行量刑外,别无他法。”
如果“承認指控”没有被赋予规避审判的法效果,这就意味着被告人虽然可以无阻碍地承认指控,但承认指控对法官没有丝毫影响,法官依然要依职权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因此,有罪供述与认罪答辩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只能简化审判,而后者则具有规避审判的法律效果,可以根据认罪答辩直接作出判决,而不需要经过审理。言而总之,所谓规避审判(Trial avoidance),实际上就是指,通过激励被告人放弃针对控诉提出异议的权利,获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并消除诉讼争点,掏空对抗制审判的基础,并同时排除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义务,法官只需要从形式上审查认罪答辩的自愿性和准确性,就可以直接依据认罪答辩进行定罪与量刑,法庭之上不会再出现证据调查和质证辩论。
传统刑事诉讼法学以对抗制为主线,铺陈国家权力构造、诉讼权利保障与司法程序运行。对抗制审判程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催生了一系列繁复的程序性规则,保障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的双重实现。但是,以对抗制为发展主线的审判程序日益复杂。为了实现控辩平等对抗,辩方有更多的机会来提出异议、反对指控,而控方的指控手段则受到诸多限制,负担证明责任、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可以说,对抗制刑事诉讼越是完善,诉讼权利就越完备,其实践操作就越为复杂,为司法机关设置的障碍就越多,司法者越容易发展出“权宜之计”来规避对抗制诉讼,尤其是面对案件数量的暴增,这一选择成为了必然之举。因此,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分支,一方是以正当程序为核心,逐步臻于完善的对抗制诉讼,另一方是以获取“认罪答辩”为核心,规避对抗制审判。刑事诉讼中广为流行的辩诉交易或认罪协商,都是遵循后一路径而展开,“充满对抗的戏剧性庭审,正被私下达成的交易所取代”“审判正在消失”这一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所关注。例如,国际人权组织“公正审判组织”(Fair Trials)与其公益合作伙伴富而德(Freshfields)律师事务所一起,对全球范围内使用的审判弃权机制(trial waiver systems)进行了调查。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驱动因素,评估了所涉法律和人权问题。Fair Trials &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LLP: The Disappearing Trial: Towards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trial waiver system[EB/OL].(2019-05-07)[2020-05-18].https://www.fairtrials.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ReportTheDisappearingTrial.pdf。。
二、 规范分析:审判规避的路径指引
通过认罪答辩的规范化研究,笔者提出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在于“规避审判”。观察各国刑事诉讼法可以发现,以获取被告人“认罪答辩”为前提而展开的诉讼程序,都是为了达到“规避审判”的目的而设置。例如,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体制下,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可以规避陪审团审判而直接进入量刑程序。法官只需要审查认罪答辩是否有事实基础对事实基础的审查不同于对抗制审判下的证据调查和交叉询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规定,“在对认罪答辩作出判决之前,法院必须确定认罪答辩有事实依据。”但是,第11条对建立事实基础所必需的证据的类型、详细程度或证明标准,没有设定任何规范。John, G.D.Fatal attraction—the uneasy courtship of brady and pleabargaining[J].Emory Law Journal,2001,50(2):437-518。,做出是否认可控辩协议的决定。也无怪乎有学者将辩诉交易定义为“被告同意在法庭没有对其案件进行充分审理的情况下实施制裁”[3]。相比较而言,我国速裁程序也是遵循规避审判这一进路而设定的。
(一) 掏空对抗制审判程序的基础
在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学者们都是按照“简化审判”的惯性思维,认为速裁程序是在简易程序之上“简上加简”[4],改变“繁者不繁,简者不简”、程序分化程度不足的现象。但这一认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速裁程序中,并没有审判发生。虽然从形式上看,检察机关要提起诉讼,被告人要出庭参加诉讼,法官要在开庭后做出判决,但这只是形式上维持了审判的格局,实质的法庭审理并没有发生,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原则上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审判是指审理和裁判,速裁程序却只有裁判而没有审理。换句话说,裁判并不是在审理的基础上生成的,“裁而不审”是规避审判的一个鲜明特征。
不管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还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现代意义上的法庭审理都是在对抗制基础上展开的,而区别仅在于法官角色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是否被赋予澄清案情的义务。对抗制审判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基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提出诉讼主张,并且控辩双方的诉讼主张往往是对立的,以此形成了诉讼争点。诉讼主张可以分为事实主张和法律主张,因此诉讼争点也可分为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前者如,控方主张被告人存在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辩方则主张被害人非被告人所杀,被告人没有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那么是否存在故意杀人的行为成为了事实争点;后者如,控方主张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辩方则主张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由此形成了关于主观罪责认定的法律争点。事实争点的判定方法在于,出示与待证争点事实具有相关性的證据,并对证据进行展示或鉴定(物证)、质证或辩论(人证)。法律争点则通过法庭辩论的方式予以判定,控辩双方提出实体论题,展开法律解释和证据说理[5],以说服裁判者。
可以说,如果在对抗制审判中,控辩双方锋芒相对,所产生的诉讼争点越多,法庭审理就会越复杂、越繁琐。因此,如果说提高庭审效率的方法在于及时理清诉讼争点(如召开庭前会议),使法庭审理对象更加集中,那么简化审判的基础就在于减少诉讼争点,规避审判的基础就在于完全消除诉讼争点。简化审判的典型例证是英国的“同意无争议证据的义务”,即要求控辩双方各自确认任何“他认为不太可能引起争议的、不希望以口头证据(Oral evidence)来予以证明”的事实,另一方则应当采取一切合理措施达成协议。可以说,“同意无争议证据”的核心要点即在于通过达成审前证据协议,部分消除法庭审理的事实争点,减少在审判过程中的证据数量,或者加快其证据展示速度[6](30-34)。
基于相同的原理,规避对抗制审判的基础即在于彻底消除诉讼争点,被告人针对指控做出认罪答辩,全盘接受指控的内容,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但是,要达到完全规避审判的效果,还需要跨越一道障碍,即法官的案情澄清义务。换句话说,“如果检察官和被告实际上没有不同意见,就不再有任何争端需要解决,这更符合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3]。在保留有法官案情澄清义务的诉讼模式下,虽消除诉讼争点,但不会就此排除法官查清案件真实的义务。例如,在我国,虽然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但是依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保留了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释明案情的必要。在法官负有案情澄清义务的背景下,消除诉讼争点并不会必然带来规避审判的效果。然而,在速裁程序中,根据“原则上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规定,我们可以推断出,速裁程序已经排除了法官通过证据调查和法庭辩论来履行澄清案情的义务。
对于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即一方面这些案件实在是太轻微了,不值得付出太多诉讼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案件过于简单,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没有保留法官继续澄清案情的必要(或原则上保留但实际并不需要行使)。德国的处罚令(Strafbefehl)也是很好的例证。对于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前拟制好制裁决定(通常是罚款),并以书面形式申请法院批准,法院不經过开庭直接做出同意或驳回的决定[7](23)。
(二) 通过认罪协商解决定罪量刑
在被告人做出认罪答辩的基础上,导致对抗制审判程序消失,规避审判的第一个体现即在于“裁而不审”。因此,我们可以“顺藤摸瓜”继续思考,既然裁判并不是在审理的基础上生成的,那么必然存在一种程序机制,替代了对抗制审判,而这种程序机制就是认罪协商实际上,如果被告人基于真诚忏悔而自愿认罪,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经过协商就可以获取认罪答辩。此时,我们只需要通过认罪答辩的受理程序,正式接纳被告人认罪。此外,认罪协商作为一个概念,用以指代现实中替代审判来完成定罪量刑的程序机制。虽然认罪协商的概念用语掩盖不了协商中的交易成分,但认罪协商的外延要比辩诉交易更为宽泛,因为后者仅能指代控辩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而不能包含法官参与协商的情况。例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7条c,法院可以与诉讼参加人就程序进程和实体结果进行协商。。由于广泛采用认罪协商解决案件,也无怪乎有学者感慨“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认罪答辩的世界,而不是审判的世界”[8]。
认罪协商的种类有很多,如果仅从协商的形式上划分,可以将认罪协商分为明示认罪协商和默示认罪协商。明示协商或称为显性交易(Express plea bargaining)是指,双方明确提出交换条件(如控方承诺降低指控、减让刑罚,辩方则供述事实、认罪答辩以及放弃权利),各取所需,罪刑判定通过直接的谈判而达成。默示协商或称为隐性交易(Tacit plea bargaining)一般是指控辩双方心照不宣,被追诉人不待对方提出交易邀约(不论检察官是否有直接的协商需求),而主动做出认罪答辩,以期待对方给予量刑优惠,被追诉人的合理期待是基于认罪从宽的政策宣示而形成[9]。“被告不直接或明确地与司法官员进行谈判,但由于被告认为司法的政策是对认罪的人予以从轻判决,因而做出了认罪答辩。因此,即使没有明示的讨价还价发生,辩诉交易的要素仍然存在:提供利益以换取认罪。”[10]默示认罪协商一般发生在犯罪事实比较清楚的轻微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权衡量刑优惠和脱罪可能性之后,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般会放弃抵抗。一定程度上而言,我国所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遵循默示协商的进路。默示协商和明示协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并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谈判与协商。基于这种划分,我们可以认定,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结程序并不属于明示的认罪协商程序。其一,很多轻微刑事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使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依然可以迅速审结,检察官并没有协商的需求。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基于从宽处罚的政策宣示,对司法机关产生合理信赖,因而做出认罪答辩,以期待对方给予其优惠。实际上,直接的谈判协商并没有发生。其二,基于从宽处罚的政策宣示,犯罪嫌疑人往往在诉讼的早期阶段(侦查讯问期间)就主动供述了犯罪事实,之后才顺理成章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签署具结并非是讨价还价的结果。其三,在犯罪嫌疑人已经做出认罪答辩的情况下,具结程序也不可能存在直接的谈判或协商,因为犯罪嫌疑人做出认罪答辩就意味着放弃了谈判的筹码和协商的资本,犯罪嫌疑人的量刑优惠完全取决于检察官的“定价”。换言之,认罪仅仅是刑罚裁量的一个情节。除此之外,还要结合其他从宽、从重情节综合考量,“同向相加、逆向相减”,评定最后刑罚裁量,犯罪嫌疑人只有是否同意的选择权。当然,在犯罪嫌疑人没有做出认罪答辩、起诉案件质量又欠佳的情况下,并不排除存在明示交易的可能性将具结程序作为明示认罪协商程序,在实践中仅具有微弱的可能性。在2018年年末和2019年年初,笔者有幸参加了对东部3个省份24个检察院的调研活动,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的状况。在基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中,检察官普遍表示,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构确实充分的案件,他们是不会与犯罪嫌疑人展开协商的。一方面基于错案追究的考量,检察官不愿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轻微刑事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更加简便。除此之外,真正的认罪协商可能发生于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比如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时,就可以达成口头认罪协议,之后的具结程序只是固定前期协商的结果。。但是具结程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罪协商程序,而是认罪答辩的受理程序,正式接纳犯罪嫌疑人的认罪,并以书面形式予以固定,同时判定罪名并裁量刑罚,达成认罪协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明示协商做出立法规范,我们也没有实证数据来说明我国明示协商的适用情况。但是,如果可以大胆推测的话,明示协商的适用比例,一般在疑难复杂案件中较高,如环境犯罪、金融犯罪以及毒品犯罪。因为在这些案件中,检察官具有强烈的协商需求,如在犯罪主观方面无法确证的情况下,通过明确提出量刑优惠,换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和认罪答辩,可以提高定罪的可能性并减少诉讼阻碍。但是,在重大复杂的案件中(通常是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的案件),就算是犯罪嫌疑人做出认罪答辩并且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其规避审判的效力(不适用速裁程序)。法官依然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在审理的基础上做出裁判。对于法庭而言,唯有被告人的供述才具有诉讼价值,被告人对指控予以承认,不会排除法官的审理义务。
然而,这也仅是规范分析和理论阐释,实践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笔者在我国东部沿海S市某区检察院调研时了解到,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实际上与简易程序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名义上仍然是普通程序罢了。甚至在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由于刑事实体争议已经被消除,审判程序已经完全处于解决附带民事赔偿的状态。质言之,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虽然规范层面上并没有赋予规避审判的效力,但却不排除规避审判的效果已经在实践中悄然发生。一定程度上而言,“认罪认罚”所带来的规避审判效,并不会因为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而就此消除。
(三) 保障认罪协议的实际履行
延续上一部分的思路,无论是通过明示协商,还是默示协商而达成认罪协议,如果法官完全不受审前控辩协议的拘束,不采纳具结的罪名或量刑建议,那么审判规避的效果一定不会发生。这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如果要实现规避审判的效果,不仅要通过认罪协商达成定罪量刑的协议,还要保障该协议能够得到实际的履行。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①。
在美国,虽然不存在法官“原则上要采纳辩诉协议”的规定,法官可以随意否决辩诉协议而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法官不采纳辩诉交易,则必须给予被告人撤回认罪答辩的机会,并且恢复复杂且耗时的陪审团审判。但是,当他们面对巨大的案件数量时,法官会义无反顾的遵从“通过辩诉交易而终结案件”[11]的模式。在我国速裁程序中,如果法官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采纳量刑建议,微调刑罚裁量,以彰显手中的刑罚裁量权,此时会让检察官无比苦恼。实际上,除非法官直接参与协商并达成协议,否则更应该留给实践本身去解决,即面对足够多的案件数量,不由得法官不去采纳认罪协议的内容。
在我国速裁程序中,如果法院不采纳认罪协议,拟超过量刑建议判处刑罚,由于认罪答辩包含有罪供述,撤回认罪答辩对于被告而言不切实际,实践中通行的做法是恢复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审理,以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性利益。如果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只能通过上诉救济。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法院不采纳控辩协议的内容,规避审判以提高案件处理能力的实用主义目的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法官不采纳罪名或量刑建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重新回到规避审判的轨道上来呢?换句话说,法官不准备采纳罪名或量刑建议,此时是否可以在征求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不转换程序审理,而径行改变指控罪名、超过或低于量刑建议判处刑罚?这种程序性举措,本质上是法官直接参与了协商。或者,在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之前,检察官是否可以主动征求法官对量刑的意见,并依据法官的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间接参与了协商。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法官是否能够参与协商做出规范,人们一般也会认为法官参与协商会损害其中立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官直接参与协商更能保障认罪协议的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规避审判的效果。从立法例上来看,德国的认罪协商程序(Verstndigung)就塑造了法院在协商程序中的中心角色。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虽然禁止法官与当事人协商判决,但是在部分州,依然存在法官参与协商的现象。从学术研究上来看,也有学者[12]提出,如果法官积极参与其中,认罪协商能够以更公平、更直接的方式进行。
言而总之,通过一系列举措,保障认罪协议的实际履行,达到规避审判的目的,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结果可能就是“认罪答辩本身就是判决”。
三、 殊途同归:规避审判的结果主义进路
实际上,通过认罪协商或交易的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并以此规避审判,这种做法原本就不应该存在,只是面对沉重的案件负担,这一选择成为无奈之举。一边是对获得公正审判的保障,一边是鼓励认罪并规避审判,它们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司法呈现双轨制的特征,规避审判遵循以效率为导向的结果主义进路——虽绕过审判程序,但“更快地达到通过审判所能达到的相同结果”[12]。
如果规避审判的实用主义立场要获得最起码的正当性,那么它就必须实现同审判相一致的效果,甚至比审判更加高效和可靠。正如“审判阴影”理论(Shadowoftrial model)所主张的那样,交易主体在预期审判结果的阴影下进行交易,预测审判时定罪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量刑结果。虽然审判并非完美无缺,但辩诉交易的结果与审判结果应该大致相同,“辩诉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无论如何都会在审判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减去固定的量刑折扣[13]。从这个角度而言,规避审判不能放弃对实体真实、准确适用刑法以及刑罚相称性的追求。
1.关于实体真实。无论是经过审判而确定罪责,还是通过认罪协商解决案件,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排除错误定罪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只能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可靠性保障的制度。审判的可靠性建立在证据裁判之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最有价值的一种证据,并且孤证不能定罪,必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规避审判则放弃了司法性的事实认定程序,转而采用行政性的事实认定程序。但无论是供述的证据价值,还是认罪答辩的可靠性,都建立在这样一种推论上,即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有实施过的犯罪行为,从而损害自身利益,但前提是必须保障被告人从容且自愿的认罪[14]。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最为清楚案件的实际过程,如果可以保障其认罪答辩的自愿性,那么实体真实就有可靠保障。
2.关于准确适用刑法。“经验会充分说明,在我们的诉讼中,如果有一百多件是由有争议的事实引起的,那么其中就只有一件是对法律有疑问的”[15]。通常情况下,只要解决事实问题,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评定罪名,都会迎刃而解。但却不排除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事实清楚而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由刑法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犯罪行为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以及新型化的特点,常识已经不足以区分允许的行为和不被允许的行为之间的界限[16]。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而是要对行为做出规范评价以便确定罪责。一方面,在存有法律疑问而非事实疑问的案件中,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做出认罪答辩,但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认罪的能力——由于存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疑问,审判的結果究竟会是什么,没有可预见性。一定程度上讲,规避审判实际上就是规避这种定罪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结果主义进路放弃了审判中的证据调查和法庭辩论,无法通过实体上的论证,获得共识上的正当性。结果主义进路存在明显偏失,规避审判使得“通过程序获取正当性”的程序正义理念无处安放①。正如有学者[13]所言:“规则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做出选择,但它们不能协调或完全服务于所有利益。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幸的。”实际上,规避审判在常规的简易案件中更加可行。
3.关于刑罚相称性。要实现刑罚相称性,必须同时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行为刑法”相关联的报应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依据行为的危害程度来加以判断;二是与“行为人刑法”相关联的预防刑,强调刑法的重心应该关注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反社会人格,刑罚裁量应当考虑犯罪人的再犯罪可能性。法官需要综合构成要件内的事实,以及关乎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如初犯、再犯和累犯),综合判定最后的刑罚。然而,规避审判的结果主义进路正在重塑刑罚裁量的理论与实践,刑罚不再是裁量的结果,而是协商的结果。由于摆脱了审判中的条条框框,认罪协商中的量刑更加多样和随意。一方面,增加了新的独立从宽理由。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做出认罪答辩后减让刑罚的幅度,如我国司法实践中推行“321阶梯式”②从宽量刑幅度。有学者认为,认罪即代表悔罪,这意味着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并以此作为刑罚减让的理由[17]。然而,悔罪并不是认罪的必要条件,被告人可能单纯为获取量刑优惠而认罪,但没有丝毫悔意。
将认罪从宽披上悔罪的伪装,掩盖了认罪协商的实用主义立场。认罪而使得“诉讼效率提高”成为了独立的从宽理由,虽然这一从宽理由并不符合报应刑的基本立场,但只要在这一范围之内减让,就没有超过可以容忍的适度范围,不能说刑罚不成比例。另一方面,获得有罪判决的概率成为影响量刑的因素①。假使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控方对此有合理的怀疑,但案件质量欠佳、缺少获得有罪判决的确定性。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可能会提供更多的量刑优惠以换取认罪答辩,甚至有可能隐藏对量刑至关重要的事实,以突破从宽幅度或法定最低刑。在检察官看来,“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好”[18]。此外,检察官也有可能过度指控,以提高量刑协商的筹码来逼迫犯罪嫌疑人认罪,增加事实上无罪的人被迫认罪的风险。这意味着,检察官是否提出合比例的量刑建议,又反作用于认罪答辩的自愿性和准确性。
综上所述,通过规避审判的结果主义进路,可以更加高效的追究犯罪,实现有效的犯罪控制,而这正是通过审判实现全面程序保障,所力有不逮的方面。规避审判的实用主义立场,可以使刑事司法系统在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一方面,即使人们承认,刑事司法系统必须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以防止對个人权利的侵犯,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对公共秩序、犯罪预防的一般追求;另一方面,要通过规避审判实现更好的犯罪控制,必须建立在快速识别犯罪的基础上,及时排除无罪的人,并让有罪的人认罪。因此,规避审判也应当遵循必要的程序保障,实现认罪答辩的准确性。
四、 结 论
认罪答辩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化,对诉讼构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刑事诉讼的双轨制:一边是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进行,另一边是通过认罪答辩来规避审判。对抗制是审判程序的一般形态,而对抗制又是正当程序的一种体现,或者说,我们是按照正当程序的标准来设定对抗制审判程序。因此,在规避审判的路径上,虽然规避了对抗制审判程序,但并不意味着规避审判可以抛弃正当程序。我们应当按照“功能对等原则”进行认罪答辩的规范化,提供与对抗制审判相对等的正当程序保障。例如,在审判背景下,辩方在审前享有阅卷权或开示证据的权利,然而一旦被告人做出认罪答辩,检察机关不再允许辩方查阅案卷。按照功能对等原则,规避审判不意味着放弃正当程序,应当为做出认罪答辩的被告提供与审判相对等的程序保障,以确保认罪答辩中的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1]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J].法学研究,2016,38(4): 79-98.
[2]兰博约.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M].王志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Swart, B.Settling criminal cases without a trial[J].Israel Law Review, 1997, 31(1-3): 223-244.
[4]叶肖华.简上加简: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1): 72-78.
[5]迟大奎.法律论证及其程序理念[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42-46,92.
[6]Antony,D.The Trial on Trial (Volume 1): Truth and Due Process[M].Oxford: Hart Publishing,2004.
[7]Jehle, J.M.& Wade,M.Coping With Overloade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the Rise of Prosecutorial Power Across Europe[M].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6.
[8]Bibas,S.Judicial factfinding and sentence enhancements in a world of guilty pleas[J].The Yale Law Journal, 2001, 110(7): 1097-1185.
[9]Di, L.J.Expedient justice or principle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 review of plea bargaining in Canada[J].Criminal Law Quarterly, 2005,50(1-2): 14-66.
[10]Ferguson, G.A.& Roberts,D .W.Roberts.Plea bargaining: directions for Canadian reform[J].Canadian Bar Review, 1974,52(4): 497-576.
[11]Alschuler, A.W.The trial judge's Role in plea bargaining, part I[J].Columbia Law Review,1976,76(7): 1059-1154.
[12]Brown,D.K.The perverse effects of efficiency in criminal process[J].Virginia Law Review,2012,100(1): 101-142.
[13]Bibas,S.Plea Bargaining outside the shadow of trial[J].Harvard Law Review,2004,117(8): 2464-2547.
[14]Sheldon, J.C.Common Sense and the Law of Voluntary Confessions: An Essay[J].Maine Law Review, 2016,68(1): 119-160.
[15]Langbein, J.H.Torture and plea bargaining[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78, 46(1): 3-22.
[16]Rauxloh,R.E.Form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in Germany: Will the new legislation be able to square the circle[J].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1,34(2):296-331.
[17]刘伟琦.认罪认罚的“321”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J].湖北社会科学,2018,(12):147-154.
[18]Alschuler,A.W.The prosecutor's role in plea bargaining[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68,36(1):50-112.
(责任编辑:夏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