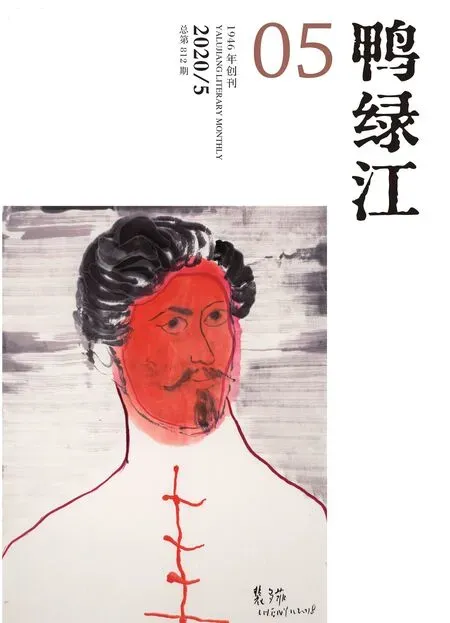同一个乡村,不同的风神
——读詹福瑞、大解、王海津的故乡散文
李文钢 张彩秋 于 竞
詹福瑞、大解、王海津,都是河北青龙的小山村哺育的文人,最近又不约而同地出版了几本涉及故乡的散文集,引人注目。他们的散文,单个读起来,可谓各自引人入胜;对读起来,则更具一番风味,愈能见出每个人的个性。
一、詹福瑞笔下的冷峻肖像
詹福瑞是国内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俯仰流年》是典型的学者散文,全篇以实写为主,以思想性见长,贵在真性情,却又以批判反思的视角贯穿始终。詹先生之前的著作主要以学术论著为主,也出版过学术随笔集和诗集,但纯正的散文集是首次出版。文体不同,对作者的要求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自然也很不一样。相较其他文体,散文实乃灵魂的赤裸,更少情节的遮掩、修辞的矫饰,更为依靠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启迪,故愈能见出一个人的真性情。一个“真”字,人们常常挂在嘴边,其实最为难得。1930年,周作人在为《近代散文抄》写的序言中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作为一个散文大师,周作人之所以会得出这一判断,自然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寻常境遇中,一个人要想做到脱尽束缚、写出真性情,何其之难!或许也只能寄希望于“王纲解纽”的时代了。而在詹福瑞先生的这本散文集里,最令人感动的,恰恰是一个最难得的“真”字,真得温暖,亦真得苦涩,真得让人心痛。也正是因其真,《俯仰流年》活画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肖像,亦呈现出了作者令人仰止的精神肖像。
《俯仰流年》全书共四辑,既有对当下热点话题的回应,也有对学问生涯的追思和对前辈学者的缅怀,而在笔者读来最为感动的部分,则是书中第一辑对故乡人、事、景的牵挂。中国现代文学的乡村书写,一般存在两种路子:一种是以沈从文、汪曾祺为代表的“神话”式的路子,一种是以鲁迅、萧红为代表的“肖像”式的路子。前者因其经过提纯、美化而浸人心脾,后者则因其典型、真实而锥人骨髓。詹福瑞的乡村题材散文,显然走的是第二种路子。他笔下的乡村世界,绝非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化,而是真实地书写出了心灵深处的无奈和苦涩。
塑神话当然也不易,但终究大体上可以随心所欲,而绘肖像则显然更难,因为要时刻把握对象的特征,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俯仰流年》中的乡村肖像的绘制,便是作者用他细密的笔慢工织就的,绝非肆意铺陈。全篇读下来,没有出现一个超过一行的句子,全都是简洁的短句,便可以看出作者在语言方面的雕琢功夫。不只人物的刻画常由家长里短、人情往来的细节入笔,更有很多事物的工笔细描不时穿插其间,宛若一幅农村百事的“清明上河图”。如《家常菜》一文中对“小葱蘸酱”“豆角熬土豆”“炖茄子”“蒸茄泥”“酸菜粉条汆白肉”“青龙豆腐”等家乡菜制作过程的细致描绘,简直能让人闻到扑面而来的香味。《跟着父亲闯关东》一文中,对于童年时代的饥饿感的描写,更是令人过目难忘,老鼠挠心、刀片旋转之喻,将饥饿的农民说不出的感受在文学世界中定了格。能有如此生动的描写,自然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在这土里生土里长,既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经验,更有着离乡之后萦绕不忘的思乡情怀,故能在写实时又常常燃烧起沸腾的情感。
置身事外的人,往往看到的只是乡村的风景,但正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所言:“劳作的乡村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风景。”对于一个从乡间的真实劳作中走出来的人来说,他所看见的,肯定也不是表面的风景,而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苦难场”。《俯仰流年》中的故乡书写撕开了“美丽乡村”表面的风光,让人们去真实地品味尘埋其间的苦涩。因此,其中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自然还是对故乡人物沉重命运的描绘。作者在《跟着父亲闯关东》一文中说“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能忍”,而读者在阅读《俯仰流年》中的人物故事时,感受到的却是心中的难忍。
含辛茹苦的父母、因“缺心眼”而饱受欺凌的“四头”、插在“牛粪”上的表妹、一生坎坷不平的“二特务”、“从不训人”却被批斗的丁印校长,这些工笔绘制的人物肖像无一不令人唏嘘感叹。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被接生的“大嫂”害死的“二姨”,不由得让人想起萧红笔下那个被开水烫死的小团圆媳妇,害死她们的,是同样粗鄙的人心。直面这些凄惨的现实,会让人感到痛苦,但若回避这些真实的苦难,则是一个作者的冷漠。正是因为心中爱之深,才不会冷漠地看风景。
心中的爱是热的,作者手中的笔却是冷的。他在描画这些人物时,并不刻意溢美或升华,而是在冷峻的笔触间让人真实地品味这苦涩。最典型的莫过于《班主任》一文,走出了毕恭毕敬地为长者讳的写作套路,逼真地写出了陈老师上课时爱“嘬牙”“摸鼻子”的习惯,也真实地写出了“我”与陈老师间的“恩怨”。令人印象极深的还有《表妹》一文,文中对素素这个“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女孩”也并不一味美化,而是在人物的动摇与徘徊中,写出了一个农村女孩令人惋惜的婚姻和命运。鲁迅时代那种“哀其不幸”的“毫无新意”的故事,被续写出了新意。
作者还擅长通过乡村景物的变化来书写人心的云谲波诡。如《关帝庙》一文,娓娓诉说了村南一座大庙在不同年代的用途:由焚香许愿之地改作仓库,再改作学堂,又改作为死去的人“领魂”之所,终于变成了90年代的“牲口圈”。一座庙宇,被成功刻写为了世风变异的折影。《青龙河》一文,则用相似视角,记叙了青龙河这条作者心目中的“父母河”由“温馨的河”到“伤心之河”的变迁,景语中的情语亦牵动着读者一起感叹不已。
《俯仰流年》第一辑最后一篇,题为《疏淡了回家的念头》,作者在复述了父亲、母亲、哥哥相继离世的哀痛后,面对着变得陌生的村庄,十分伤感地写道:“过去回家,感受的是失去亲人的伤感,如今又叠加了农村败落而来的失落与失望,回家真没什么大意思了。”在一个人们嚷嚷着要“常回家看看”的时代,即便有人不想回家,恐怕也是“羞于启齿”的。詹先生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率真地讲出“回家真没什么大意思了”的话,除了亲人不在的淡漠感,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是也。
在今天的流行语中,人们熟悉的,是“美丽乡村”“新农村”的传奇,而詹福瑞则用他异常冷静节制的笔墨,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幅不一样的肖像。如作者在《村里的同伴》一文中所言:“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我会不由自主地升腾起对家乡温暖的记忆。但是这种温暖,是苦涩的温暖,不是幸福的温暖。”詹先生在这本散文集中的乡村书写,不是温情脉脉的神话,而是冷峻的肖像。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眼中的真实,但只有能够典型概括时代特征、呈现时代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真实,才是最为可贵的真实,《俯仰流年》无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冷峻的笔触、落寞的情绪、破败的乡村,令人合卷后仍久久难以平复心中的惆怅。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述了鲁迅对故乡的复杂情感:“鲁迅不但对于杭州,并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对故乡的这种“既爱又疏离”的情绪,在詹福瑞的笔下同样弥漫着。《俯仰流年》中的乡村书写接续了由鲁迅、萧红开创的文学传统,敢于逼真地直视“老天爷不睁眼”的种种现实,用一颗赤子之心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肖像,是一种真正能将读者“卷进我们的实际境遇”之中的“介入式”写作,是掏心掏肺、呕心沥血的灵魂之吐沫。
二、大解笔下的荒诞景观
曾凭诗集《个人史》于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大解以诗歌闻名,近年也以余力写就了《傻子说》《傻子寓言》《别笑,我是认真的》等散文集,其中涉及故乡题材的篇目虽然不多,却令人过目难忘。典型的如《解救大山计划》《乡村小路》《老木偶》等篇目,以超现实主义的虚写为主,完全超越了或“神话”或“肖像”的格局,而将乡村风物作为重新摆放的布景和道具,组合成了荒诞化的新景观。大解的这些散文,“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实现了“绕到生活背后”的艺术追求,在风格学的维度上为现代散文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傻子寓言”体。其特色在下面这篇题为《解救大山计划》的短文中展露无余:
我的家乡有一座山,被密集的羊肠小道紧紧缠住,已经多年无法动弹。这些小路像是一条条绳索,从山脚缠绕到山腰,盘旋而上,一直到山顶,没有一点松开的意思。村里人也曾有过解救的想法,但人们每次上山都使小路更加结实,反而加剧了对于大山的缠绕。
类似的情况在别处也曾有发生,人们大多采取默认的态度,不去计较。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些山竟然被小路缠绕窒息而死,幸亏医生救治及时,经过抢救又活了过来。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最近有环保组织提出“救救大山”的倡议,我表示支持。我建议使用特制剪刀,从根部剪断一些小路;也可采取生物治理办法,给一些小路注射反生长素,让他们逐渐萎缩。但所有这些建议必须经过环保组织的讨论和评估,然后经全民表决通过后方可实施。
看到这些进展,我家乡那座被缠绕的大山,流下了感激的泪水,渐渐地,这些泪水成了一条河流的源头。
山是故乡的山,密集的羊肠小道也是乡村生活的实景,但作者的视角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生活的逻辑,而用一种全新的艺术眼光来加以重新组织。其中的情节或许还会给人以荒唐可笑之感,却与西方荒诞派戏剧有着明显不同:荒诞派的“荒诞”一词意指的是“丧失了目标,被割断了宗教、抽象的和超自然的根基;人垮了,人的所有行为都变得没有了意义,毫无用处,不协调”;大解的“荒诞”则是一种积极的艺术处理手法,最终并不指向意义的消解,而是通过貌似荒唐的乡村景观塑造,促使读者重新反思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用新的视角去重建这些关系,背后大多有着严肃认真的主题。原本单一的、平面化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荒诞化重组中开始变得立体,多维时空被并排交错在一起,大解也通过此类貌似荒谬的虚构,拓展了被日常生活经验所遮蔽着的人类心灵。
大解将乡村书写荒诞化的内核,不是表面的滑稽,而是深刻的幽默。他的用意绝非哗众取宠的浅薄逗乐,而是在智慧的闪光中启人心智、反思生活。雄伟的大山本是令人畏惧的崇高形象,在他的散文中却成了被缠住、被窒息、被抢救的弱者形象。人类本是破坏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在他的散文中却成为“拯救者”,而将“羊肠小道”当作了替罪羊。通过这样的反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都被置于反思的位置,而这正是作者的幽默所要达到的艺术目标,它增添了我们对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敏锐感知,让我们获取了审视世界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绝非消解意义的解构。
卡尔维诺曾说:“幽默把自我、世界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各种关系,都放在被怀疑的位置上。”大解散文中的这种佯作痴狂的幽默也如此这般地拆解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各种关系都被赋予了新的理解和可能。这种幽默化、夸张化、变形化的处理,是窘迫的人生必然将会遭遇的种种困境的反弹作用,是追求着超越这种窘境的象征。通过这些貌似荒谬的傻子言说,作者缓解了人类面对未知的宇宙和不确定的未来的永恒恐惧,用表面的揶揄释放了内心深处沉重的窒息,让很多平日里为人们所忽视的思维死角突然在沉默中闪闪发光,也让我们在会心一笑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增添了心中的热量,对于我们的乡村、对于我们的生活更增添了一分热爱。一个大智若愚、从容超脱的作者形象也随之跃然纸上。
三、王海津笔下的村庄史志
上述两位作者,虽然成就不俗,却皆以散文创作为“余事”,相形之下,近年来专心致力于散文写作的王海津就显得更为“专业”了。他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乡村碎片》,并非随意为之的游击战,而是有计划成系统的阵地战。动笔之初,他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其实乡村已经很难再写了,许多人依然不甘罢休。我也是。”因而,当他把“写得不重复”当作一种自我要求,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正如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在《文学的解剖》一书中所言:“诗歌只能从其他诗歌中产生;小说也只能由其他小说产生:文学塑造着自己,不是由外力能形成的。文学的各种形式同样也不存在于文学之外,就像奏鸣曲、赋格曲及回旋曲不能存在于音乐之外一样。”既要在散文的谱系中创造出新的散文,又要与以往的散文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散文家极为难能可贵的自我要求。而王海津这本以故乡为母题的散文集可以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乡村碎片》,虽然题为“碎片”,却改变了人们对散文只是书写零星感悟的片面印象,因为它有着鸿篇巨制般的大结构。动笔之前,作者就已经在腹稿中列出了准备着笔的各个角度,意图全方位地立体呈现“鹊雀窝沟”村的方方面面。在具体行文时,作者由“黑夜的星空”开始写起,想象着就像“上帝在天堂向人间抛撒的一捧沙子之中的任何一粒”那般偶然,“我”落在鹊雀窝沟村,展开了与周围环境逐渐融合的生命历程。从“地名”“人物”“读书”到“家畜”“庄稼”“器物”,事无巨细,可谓面面俱到,全方位、全视角地刻画,简直是一部乡村百科全书。全书终篇时,作者又以乡间流传着的鬼神故事作结,与开篇的星空遥相呼应。起于遥远的星空,归于虚幻的神灵,全篇完成了一个由“空”到“空”的循环,便更突出了“空”与“空”之间的“实有”的真实可贵,“鹊雀窝沟”的一草一木、每人每事也都因之而显现出了神性的光辉。这样的结构安排与《红楼梦》那种缘于幽冥、归于苍茫的宏大气魄十分相似,都是人类心理世界千年积淀的原型。
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作者有效地节制了自己燃烧着的情感,克服了旁征博引的宣泄冲动,既不刻意造神,也回避了过于外露的反思,而用儿童般客观、纯净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纯粹的村庄雕像,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在历史的烟尘中留下了一份极珍贵的文字资料。《乡村碎片》完成了时下最为流行的“纪录片”的工作,却又比浮光掠影的影像记录更有深度,更经得起读者的反复品咂。因为它总是能用虚实相间的比喻手法扩展书写对象的意义空间,把一部百科全书般中规中矩的村庄书写变得充满了诗意。当它展开写实时,总是能令人感受到宛如目前的真实;当它辅以由比喻引申生发开的虚写时,又每每能挖掘出事物背后的诗意,启人由浮想走向深思,由感知乡村的实在世界进入理解乡村与我们的关系的意义世界。
实写与虚写相衔接的部分,是这本散文集最为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诗意最为激荡的部分。如下面这一段关于太阳的描写:
我觉得太阳跟我们一样,也是怕冷的。夏天天暖和,它就起得很早,睡得也很晚;冬天天冷,太阳也不爱起来,早上迟迟不肯露面,晚上又早早就落山了,就像我们早早钻进了热被窝。
此处,作者将冬天的太阳比作“怕冷的我们”便是典型的虚写,它赋予了实写的冬日乡村不一样的光彩,平常的自然现象也由此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建立起了更亲密的关联,并在我们的眼中开始变得妙趣横生。类似的比喻手法在这本散文集中随处可见,每一处乡村景观也借由这般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而联通了无限的审美世界,使得熟悉的事物也能给人带来惊异,进而更新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并因此加倍照亮了乡村世界的存在本身。再比如《门前流过的溪》里的描写:
溪在门前小桥下穿过,瘦得像根弯曲的高粱秆。
鹊雀窝沟里的这条溪没有名字,它瘦弱,普通。瘦弱得孩子踩一脚就把它踩断了,普通得山里到处都有,随便在哪里迈一步,都会踩着。所以,这样的溪,连起个名字的必要都没有。它在门前流了很多年,也确实一直没有一个名字。
通过将瘦弱的小溪比作“高粱秆”这样一个贴切又新颖的比喻,作者既把乡村的风景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也更新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将写实的乡村素描连接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冥想空间。乡村世界的可见之物与那些不可见的意义相联结的时刻,是其产生了真正的艺术魅力的时刻。可以想象,若是没有了这些充满诗意的比喻所赋予的灵魂,它们必然会显得枯燥乏味。借助于实写,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乡村生活的实景,而嵌接在实写中的虚写,又为我们理解他笔下的描写对象提供了更多维度,并进一步建立了乡村生活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的关联,给全书质朴写实的风格增添了灵动的气韵。
可以说,王海津的这本散文集,从总体上看,恰似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为我们如实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乡村生活;从细节处看,又能时刻用它隐喻化的镜头语言本身的艺术魅力,牢牢地吸引住读者的眼睛。书写乡村,是作者回归精神本源的过程,而将乡村隐喻化,则是一个精神升华的过程。在这些精妙比喻背后,无疑深藏着作者的故乡情怀和文人趣味,但作者却冷静地把它们一一克制在被描写对象的陪衬地位上,反而能将实写的乡村场景愈加令人过目难忘地突出出来。
现代散文自独立以来,常以书写情怀或表现趣味为能事,而王海津的《村庄碎片》则打开了一个新的向度,为现代散文增添了有意识地保存人类生活场景资料,而将情怀或趣味推至远景乃至背景的一种尝试。这样的情怀和趣味,因其藏得深远而更耐人品咂。从根本上说,正如耿占春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语言就是一个庞大的未知的隐喻系统。语言使它所谈及的一切都化为隐喻。因此语言的功能并不在于再现现实世界。或者说语言符号由于它是再现着,因而也就是它替代着,也就是让某种东西成为现‘在’的。‘替代’也就是让某种缺如的不存在的东西成为‘现’时的”。王海津笔下的乡村世界,既可以看作对应着现实世界的村志村史,又不能简单地与现实生活相混同,因为它们经过了心灵的浸润与加工,古老的乡村在他的笔端被重新赋予了历史的厚重和诗性的光辉,是名副其实的乡村“史诗”。哪怕是未来的任何一个时空中的人,捧读起这册“史诗”,都能将一个完整的乡村世界呈现为宛如目前的“现在”。由此,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王海津的这本散文集,深入挖掘了散文文体在表达上的可能,是对探索散文本体潜能这一根本问题的有效深入,在推进“何为散文”“如何散文”“散文何为”等本体性问题的思索方面都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推进,每一步都将因其艰难而意义重大。
三位从青龙的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文人”,面对着故乡这一相同的书写对象,以其各异的个性和方向,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神采,为丰富现代散文的乡村题材各自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乡村题材散文,值得我们生长于这“乡土中国”的每一个读者品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