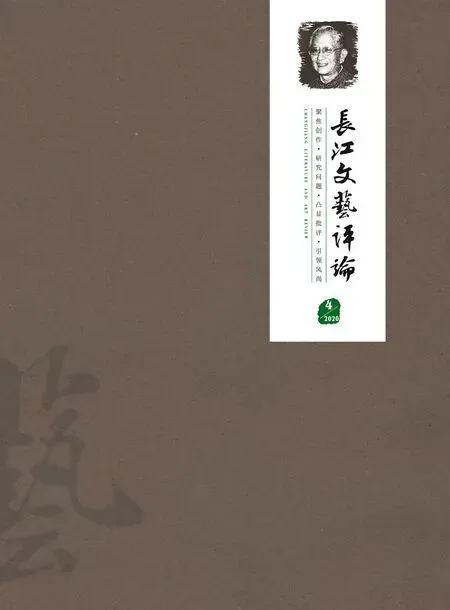重审《作者之死》
◆徐兆正
一、作者
“一件事一经叙述,……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1]这句话里显然存在着双重运动:第一种运动是叙述,第二种运动是脱离。两种运动伴随着发生了:一旦某件事情开始被讲述,它也就开始同叙述者本身的意图相脱离,而“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2]这份来自巴特的判决,毋宁说是在提醒我们两件事:首先,“作者之死”是对文学研究领域“意图”的驱逐;其次,“作者之死”总是一个恒定发生却未经查明的事件,巴特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点揭开给我们看。某种意义上,这篇刊于1968年杂志《占卜术》的文章介于巴特的两部作品(《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与《文之悦》)之间,并且在此间划上斜杠。倾斜标志着作者本人研究重心的偏移。开场白的最后一句:“写作也就开始了”。[3]此刻我们尚且难以确定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但能够察觉这种写作不再是“一件事一经叙述”之前的写作:作者死后开始的写作也不再是作者的写作。这种开始了的写作以作者的死亡为起点。
位于这段开场白下面的一段,有一处不起眼的讯息:“尽管作者的王国仍十分强大(新批评仅仅通常是加强这种王国),不言而喻,某些作家长期以来已试图动摇这个王国。”[4]括号里增添的话并非赘笔。至于何为“作者的王国”,是巴特在上一段中解释的事情:“在人种志社会里,叙事从来都不是由哪个人来承担的,而是由一位中介者——萨满或讲述人来承担,因此,必要时,人们可以欣赏‘成就’(即对叙述规则的掌握能力),而从来都不能欣赏‘天才’。”[5]通过区分过去的作者与近现代作者的差异,巴特指出近现代作者身上闪耀的天才光环——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现代作者则“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6]
实证主义落实在文学批评,[7]即是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与之针锋相对的“传记式批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复又强化了这种关注,将萨满身上的通灵气息转喻为写作的天才迷狂,如此一来:“文学批评(就)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8]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不会认同这种批评模式,这一时期他的批评思想可以参见《米什莱》《论拉辛》等书的二元对立式的主题论写法,即通过对全部拉辛剧作的囊括、分类,再现拉辛本人的深层思想结构。两年之后,雷蒙·皮卡尔针对这部论著提出批评,在《新批评还是新骗局》里,他指出“新批评”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新批评学派主张向作品回归,可它回归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作家的全部生活经历。新批评学派自命为‘结构主义’,可它追求的不是文学结构,而是心理结构、社会逻辑结构、形而上的结构,等等。”[9]在皮卡尔眼中,“新批评”之新,是它用作家内心的思想结构(无意识)取代了作家创作的意图(意识)或作者的生平记录。可是,思想结构仍然是一种意图模式,“新批评”未能如其所说的那样向着作品本身回归——无意识中仍然保留了作者的位置。
1966年,巴特以《批评与真理》回应了皮卡尔的诘难,这一年也是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著名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年份,后者一般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时间节点。《批评与真理》是《作者之死》的先声,其中巴特没有简单地维护《论拉辛》的主题批评色彩,反倒是以更激越的转向——用语言置换作者——超越了他与皮卡尔论战的基础,即何为意图的问题。《作者之死》一文括号里的那句话“新批评仅仅通常是加强这种王国”[10],即显示了处在向后结构主义转型时期的巴特对作者/意图问题的超越。尽管如此,1968年的文章还是透露了巴特的矛盾所在(他的激越与谨慎始终混杂在一起),[11]例如:将语言放在作者曾在的那一位置,此前并非无人言及,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带领我们回顾了摆脱作者历史的五个阶段,这五个历史阶段分别是:一、马拉美(“是马拉美首先充分地看到和预见到,有必要用言语活动本身取代直到当时一直被认为是言语活动主人的人”[12]);二、瓦莱里;三、普鲁斯特(他有意混淆了叙述者与作家的关系[13]);四、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取消了作者形象的神圣性);五、语言学(“言语活动认识‘主语’,而不认识‘个人’”[14])。
二、文本与读者
至此,巴特才顾虑重重地提出了用语言置换作者(用言语活动的主语代替作为言说者个人)这一番几经被历史湮没的构想。我们注意到,重提这一构想不单纯是复古,即肇始于福楼拜的对作者声音严格把控(客观显示而非主观讲叙)的现代写作潮流,也不完全是对现代理论中语言学转向的呼应,诚如格非所说:“早在巴特发表《作者之死》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作者作为写作的主体,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打击。巴特只不过是一个迟到的牧师,他匆匆赶来严肃地宣布这一消息。”[15]如果说这是一次策略性行动,巴特的目的之一也许就在于证实他的同代人如格里耶等作家所开拓的那种缺乏起因的写作的合法性:“疏远作者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实或一种写作行为:它还彻底地改变现代文本”,[16]这一点也十分类似于他在《写作的零度》中对古典写作与现代写作的界定。[17]如是,塑造的不再是整全独立的作品而是由各种能指的引线、文化的符码编织出来的文本:“一个文本不是由从神学角度上讲可以抽出单一意思的一行字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18]
目的之二是为了打造一种与“新小说”相匹配的“新批评”。既往的新批评之所以受到皮卡尔指责,归根结底还是它所强调的深层思想结构里有作者影子的低徊:“赋予文本一位作者,便是强加给文本一种卡槽,这是上一个所指的能力,这是在关闭写作。这种概念很适合于文学批评,批评以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或其替代用语:社会,历史,心理,自由)为己重任:作者一被发现,文本一被‘说明’,批评家就成功了。”[19]巴特在此试图重建“新批评”的合法性,就在于用“作者之死”去成全多义性的“文本”概念,凭借着这一概念,“新批评”得以完成回到作品本身的未竟之功(只有当作品被指认为多义性/互文性的文本时,向着作品回归的批评才是可能的)。但这个时候批评也就不再执著于对“潜藏”于作品中的永恒真理进行诠释,而是开始对构成文本的多种引线加以描述,对文本建构这一变动不居的过程加以观察。[20]诠释是建构性的,描述则是与之相对的解构行为,它不再等同于《论拉辛》中深度模式的透析。在此有必要特别强调一点,解构理论的真正实操,还要等到两年之后的《S/Z》一书,而写作《作者之死》时期的巴特并没有完全放弃结构主义的“科学梦想”。
《S/Z》一书是巴特关于小说《萨拉辛》所做的研讨课记录。书中他进一步地用单义性的可读与多义性的可写强化了作品与文本的差异。[21]让我们回想《作者之死》中那个稍显突兀的三段论:“一件事一经叙述……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22]也许现在我们就能了解:以作者死亡为起始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可写文本的自我生产(重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其将《S/Z》视作一份关于《萨拉辛》的“研讨课记录”,还不如将它看作是对这个中篇小说的重新仿写:当巴特试图以文本中的蛛丝马迹为线索展开描述时,描述已经是一种写作活动。此外,还要避免可读/可写,作品/文本这两对概念的泛滥,如凯瑟琳·贝尔西那样从这种区分出发提出的文类范畴,[23]很可能也得不到巴特本人的赞同。在我看来,巴特的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视角的差异,惟其如此,他的理论才既适用于格里耶、索莱尔斯这些“未来的文本”,也才能够囊括他所喜爱的那些法国古典文学[24],并且在转换的视角以内,将之转化为“过去的文本”研究[25]。两种文本不存在质的差异,它们都属于一个互文性的开放文本空间。
作品总是作者的作品,文本则注定是读者的文本。人们以阅读为中介,从作品过渡到文本,[26]从再现意义过渡到生成意义。这就是“写作的初始”[27],或者说巴特所言,是“写作的未来”。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28]——同样不宜从字面释读。当巴特将“作者之死”描述为书籍之父向“现代抄写员”(“他仅仅是其书籍作其谓语的一个主语”[29])交权的嬗变时,“读者的诞生”在他那里意指一种功能性的隐喻(“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30]),“读者在这种过程中发挥了和文本本身的语言同样的作用。”[31]这里又存在着让人生疑的地方,即究竟是替换掉作者的言语活动,还是读者——在文本中不断生成了新的意义。当巴特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时,他还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尽管文本所指的稳定性已然岌岌可危,而在文章的最后一句里显示的从关注文本的起因转向关注文本的目的的偏离(起因是真理/一的可知,目的就是意义/多的不可知),进一步说,向制造结构的读者与互文性的偏离,则使人隐隐不安地感到他正在放弃结构主义批评的科学梦想,以及一种巴特式的后结构主义正在来临。
三、秩序
《作者之死》之于巴特本人的复杂性,主要是这篇文章暧昧地处在巴特本人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过渡时期。《作者之死》起源于巴特对皮卡尔的回应《批评与真理》,其本义既在于澄清“新批评”与“作者”之间的纠缠联系(通过用主语取代作者,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何为意图的问题),也在于修复“新批评”中“结构主义”倾向的不彻底之处。结构主义诞生于索绪尔对社会性的“语言结构”与私人性的“言语活动”做出的革命性划分。在索绪尔看来,一切言语活动都受制于语言结构的规约。法国的结构主义始于列维-斯特劳斯在1962年发表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所谓结构主义,指的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文学者将语言学视为一种分析的典范,进而将它推广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从而在这些领域尝试着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结构主义考察的是在现象背后、整全的结构内部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总和产生出了结构的功能,而结构的功能则是结构主义者试图发现的深层内容(在文学研究领域,深层内容即是文本的深层思想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结构主义者的工作就是要将不可理解或难以理解的现象全体,复原/重建为一个可以理解的且以语言学为模型建立的抽象结构。
所以,巴特对实证主义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强烈的抨击,可谓其来有自。因为这将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彻底脱离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他在《作者之死》中也确认了这种内在结构不再是一种通过主题论得出的深层思想结构(“新批评仅仅通常是加强这种王国”)。那么,究竟是哪一种结构呢?也许是一种生产所指的形式结构。因此之故,重建的也就不是作品的具体所指,而是这一结构本身。然而,《作者之死》又是一篇“写得太迟”的文章。当巴特在文章最后将“读者的诞生”与“作者的死亡”以因果的关系衔接起来时,当他指认读者是“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32]时,结构主义的理论也就会因为一种对生产所指的形式结构的描述难以为继,从而在内部崩溃。事实上,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一年之前,德里达已经出版了《书写与差异》《言说与现象》和《文字学》三部著作,它们一般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中最激进的解构主义一脉正式被确立的标志;这篇文章发表同年,法国也爆发了“五月风暴”。这一运动虽然没有取得任何现实成果,却在理论界引发了对“结构”本身(作为社会秩序的结构)的怀疑与反省,这就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历史节点。
最后,让我们重新审视《作者之死》这篇文章的复杂性。在我看来,它的复杂主要印证于以下两点:一方面,巴特用作者的主语化正式驱逐了作品中的作者问题,这为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补全了最后一块缺口;另一方面,对作者的驱逐不可避免地成全了文本的互文性,而读者也将成为文本结构的新的制造者,这样就消解了文本内部的“中心”与“等级”,因此像是打开了意义的潘多拉魔盒;封闭的文本变成开放的文本,等于是宣告一种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不再是可能的。1977年,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讲中,巴特指出:“作为语言结构之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是法西斯的。”[33]这是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典型言说,持这一看法的理论家们大多在语言结构、政权秩序与真理[34]之间划上了等号,而对世界的违犯成为了始终在刺激他们更新理论的内心顽念——更新理论,正是为了抵制理论被秩序同化。回顾巴特晚年的这番言辞,很像是他对《作者之死》一文结尾的回顾。“读者”在此后还将是“片断”,[35]是“审美”,[36]是一种“中性”。[37]因此,这篇文章预示着一个时期的结束,也标示着一个新的起点正在形成。
注释:
[1][2][3][4][5][6][8][10][12][14][16][18][19][22][28][29][30][32]【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此文在《罗兰·巴特随笔选》中译作《作者的死亡》),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301页。
[7][17][33]参见【法】罗兰·巴尔特:《两种批评》,《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297-298页,28-29页,183页。
[9]转引自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11]一位朋友曾经记下了巴特对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隐秘看法:“他尝试阅读刚刚出版的小说,但这就‘像是做作业’。于是,他便回到了‘真正的书籍’:《墓中回忆录》。时间长了,他只看重古典作家。‘总是有这种想法:如果现代人搞错了呢?如果现代人里没有天才呢?’如果这种想法是正确的,那么,他自己就‘错大了’:因为他全力支持新小说。”【法】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13]“他不使叙述者变成曾见过、曾感觉过的人,也不使之变成正在写作的人,而是使之成为即将写作的人(小说中的年青人,他到底多大年纪?而且他到底是谁呢?他想写作,但又不能写,可是在写作最后成为可能的时候,小说也结束了),普鲁斯特赋予了现代写作以辉煌的业绩:他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之中,而是彻底颠倒,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了一种创作,而他的书则成了这种创作的样板。”【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7页。
[15]格非:《文学的邀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166页。
[20]参见【法】罗兰·巴尔特:《何谓批评》,《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308页。
[21][26][27][35][36]参见【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自述》,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192-193页,118页,126-128页,144页。
[23]参见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
[24]在《恋人絮语》的前言里,译者也发有类似见解:“有趣的是,巴特在文学主张上厚今薄古,但他批评实践的重心显然又是厚古薄今,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新小说,而他的评论激情却都是宣泄在法国的经典作家身上:拉辛和巴尔扎克。他最喜爱的是‘从夏多步里昂到普鲁斯特期间的法国文学’。”汪耀进:《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恋人絮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页。
[25]“最新的一项研究(如J-P.维尔纳的研究)已经阐明了古希腊悲剧在构成方面的模棱两可的本性;文本是由具有双重意思的词构成的。每个人物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去理解(这种经常的误解恰恰正是“悲剧性”);然而,却有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词,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去理解在其面前说话的所有人物的哑语:这个人便正好是读者(在此也可以说是听众)。”【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301页。
[31]【英】格雷厄姆·艾伦:《导读巴特》,杨晓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34]参见【法】阿兰·罗伯-格里耶:《罗兰·巴特之党》,《旅行者》,余中先等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1页。
[37]参见钱翰:《“中性”作为罗兰·巴尔特的风格》,《文艺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