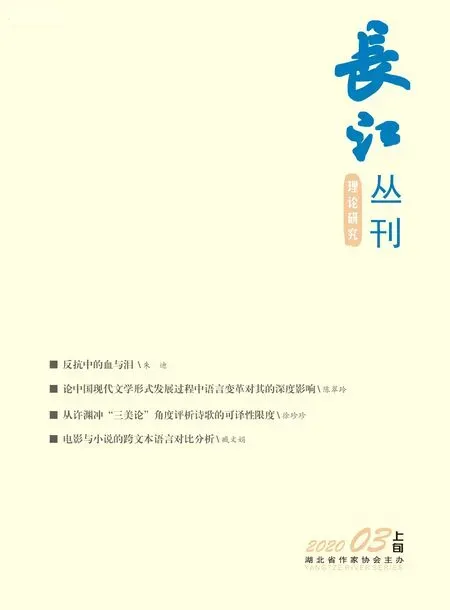永远的叮嘱
■游 平
母亲进重症监护室时,从昏迷中坐了起来,朝我们挥了一下手,扭过头来对着我们似乎想要说什么话。可医生硬是没有让她说出这句话,随手关上重症监护室的门。这门,也就成了生死之门。三个小时再打开时,母亲已经和我们阴阳两隔。我们,也就再也见不到能说一句话的母亲了。
我们为什么不拦下那能移动的病床,让母亲说出她想说的那句话呢?当然,我们知道她已不能说话了。但是谁又能保证神的最后的恩赐不能降临到母亲身上,让她老人家好好地给我们说上一句临别赠言呢?母亲,我们无能!
进重病监护室,我们寄希望于医生,企盼他们能让母亲度过难关,从生死线上拽她回来。但医生说,只能试试,难保晚上撑得过。他们执行的规定很坚决,我们这帮亲人一概不能进重症监护室。母亲最后与死神的抗争,我们不能亲见,不能陪着她一起发力,只能寄希望于渺茫的神,寄希望于母亲生命力的强大。可是一切都是冰冷的,还不到三个小时,医生就通知我们,母亲走了。
我无法相信。转身间,我与母亲阴阳两隔。
泪已是无法流出,唯有震惊和疑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反复询问医生,问得医生不再回话,可怜地看着我们。
当灵堂里所有的人都去吃饭了,我独守着母亲的灵柩,嚎啕的哭声在老家的山野之间孤独地回荡。棺材平放在我的眼前,而母亲已平卧其中,她老人家终于停止了一生的操劳。无声无息,如四野一样静谧。仿佛总算静下心来,看着后人,看着她一生所熟悉的生活,在时光流逝中继续前行。我知道她是放不下的,不然怎么会在昏迷多日后,当临进重症病房时,她竟然翻转身坐了起来,她是想和我们道别呢,还是进行一辈子最后一次的叮嘱?母亲的叮嘱永远不会有个完,永远!
82 岁的母亲,就这样与世长辞,任大班的人抬着,入于黄土之中。
也许,此时的她和早已步入阴间的父亲相会了,还有黄三爷、七爷和八爷,还有早已夭折的妹妹。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只是留下我们这些后代,守着无以排遣的苦痛。
母亲一生强势,不屈人后。她吃尽了人间苦难,却咬着牙从未向人诉说。她11 岁就开始跟外祖父学缝纫,跟父母一起承担了一大家人的艰难生计。她在家里是老大,下面有6 个弟弟,3 个妹妹。这一大家人的担子她在11 岁时就开始分担了,一直到20 岁与父亲结成夫妻有了自己的家也没有完全放弃。
母亲比父亲小9 岁,组成家庭后,与父亲聚少离多。父亲结婚后念大学三年,外出“四清”一年,住西河干校和在这大队那大队蹲点达十三年。家里的一切基本上都由母亲承担了。母亲除了抚养我们兄妹四人,还要在缝纫社做工。别人每天缝制6 件衣服,她要缝制10 件。她成了缝纫社有名的快手,模范职工,收入也是缝纫社最多的。
她的快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家里,她做饭让我眼花缭乱,还没看明白她就做完了。洗衣服也是,你才说上两句话她衣服就洗完了。她的能干、忙碌和嗓门都是县城里有名的。她的快人快语,被人送以绰号“郑大说(方言,念pia)”。
在她下放回老家那些艰苦的年代,更把她的的坚韧发挥到极致,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不会使用簸箕将刚轧的谷跟米分离出来,就蛮着劲飞快地学;不会插秧,就整天在田里泡;可以做缝纫了,就让人挑着缝纫机,而她自己驮着不到两岁的小弟弟走村串户地上门服务,常常一连几天才能回来……
在我惟一的妹妹不幸淹死的惨痛日子里,母亲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悲痛,没有被残酷的命运所击倒。带着面部极度痉挛的痛苦,一天天地挺了过来。她的心中还有我们几个没有长大、没有成人、没有立业的三兄弟。她就像一只外表看似懦弱而心性坚强的母鸡,警觉而拼命地卫护着它的三只小鸡,意志坚定地照料、培养着我们,直到看到我们一个个成为能够自立有用的人,她也没有完全放下心来。
父亲一生怯弱。因档案上标有“控制使用”这样的结论,使他1947 年就进了刘邓大军创办的大别山干部学校的优势化为乌有。其间因由,一言难尽,世态炎凉,窥见一斑。父亲一生夹着尾巴做人,如不是母亲根正苗红,百分之百的工人阶级,父亲一生哪能伸得直腰!
1982 年调工资,父亲是县财政惟一的大学生,第一榜上排名第一,可到第三榜时,已不见了父亲的名字。一问,方知人家说父亲工资本来就高,调资最好让让。父亲大学本科毕业,工资每月51 元。县财政的其他干部职工,大都从每月24 元开始起步,每月增加2 元,逐年增到每月34 元后基本就不增了。相较父亲,工资差距较大,父亲榜上无名似也说得过去。但母亲觉得这是欺负人,她跑到县财政局长办公室,指着局长的脸说:“游仕英的工资为什么不能调?有本事你们就去读大学?你们这样做,好像老游读大学读错了似的。”母亲大声说:“你们这回要不调老游的工资,我天天到你们办公室来骂!看你们怎么说?”局长脸煞白煞白的,好言相劝地对母亲说:“郑大奶,你回去吧,老游的工资我们答应调。”就这样,父亲的工资调了一级。一家人开怀地笑得不亦乐乎,都说郑大奶厉害,可以去跟美国人较劲。
而正因了她的强势,说话直言快语,也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舅爷姨娘。母亲依她做大姐的资历,对待弟弟和妹妹,说话口无遮拦,不管轻重,随说随丢。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她是一概不论,图一时痛快。舅爷姨娘一个个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母亲一概不管,今天批评这个,明天又批评那个,到头来个个对她有意见。而到了送礼,她又不将我们兄弟三人集中起来一起送,做到又好看,又照顾了各人的面子。而是要我们分开送,这个1000,那个800,另一个又600,数目不同。兄弟三人出手不一,舅爷姨娘心里怎么想?结果往往礼送了不少,而舅爷姨娘们心里还有想法。母亲却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弄得我们心里怪怪的,又说不清楚。
但如有人说我们兄弟三个哪一个的坏话,她倒是不改一生护犊的特性,立马就数落来了,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想想,她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母亲年老了,我总劝她少说为佳,积积口德。她总是笑笑,不置可否。当然,这是也有了一把年岁的我说她,要是年轻我气都不敢吭一声,说了她不跳起脚来骂我,还要打我。
去年开始,母亲神志就有些颠三倒四了,一句话重复了说,要说好几遍。我说,这话你都说了四遍了,她张张地望着我,叹了口气,说:刚说的就忘了。这咸菜你要不要?腊肉你要不要?青菜你要不要?我说,我不是刚跟你说的不要。她定定地望着我,又说:咸菜伴粥好吃。你一个人,咸菜拌点,挺好的。又说:儿子的事,你莫管,莫瞎操心,有老婆就行了。你当持好你自己的身体。你要少说,儿子大了,他们有他们的主见。你说多了,他们不爱听。一代人只管得了一代人,莫想太多。家家都一样,都是恩往下流。
我故意说;恩往上流不行吗?她定定地看着我,声音就大了起来,说:只有父母的恩往下流,满世界都一样,哪来的往上流?说不通!父慈子孝。父慈了才子孝。
我说:老人住院,病房里大多冷冷清清,初生的婴儿产房里门庭若市,几代人都来了。若是报恩,哪能这样!母亲看我如此知情达理,称赞我说:是呀!有了懂事的儿就有了一切……
去年腊月,她生日。我们兄弟三人请健在的舅爷、姨娘,还有舅娘,在一家不错的餐馆好好地聚了一下。母亲好高兴。她尽管神志有些呆滞,不如往年谈笑风生快人快语,但高兴的神态还是让人感怀。冲着她的兴致,那天中午我分别和三舅、四舅、五舅、六舅,喝了不少酒,还敬了二姨和大舅娘。
就在这一年稍早的时候,三姨还在,大舅还在,没想到他们竟在之前不久都因病而去了。我不仅自己悲,也替母亲悲。要知道,她小时候可是和自己的父母一起把这些弟妹照料大的。像个母亲一样,对他们千叮咛万嘱咐,深怕他们受到哪怕一点点的委屈。而现在,三姨和大舅又先她而去。她的情感自然又多了一份难以抚平的悲痛。想到这些,我一时泪水奔涌,竟喝醉了。醒来已是黄昏,三舅和母亲陪在宾馆的房间里。我的头也不知在哪里撞了一个大包,喉咙痛得难受。母亲看我醒来,给我倒来一杯水。她的神情中有心痛,还有赞赏,似乎赞赏我不惜把自己喝成一滩烂泥,也要让她的弟妹诸亲多一份喜庆和快乐。这才是她的性格。我记得她独自坐在床边,还长叹了一口气,叹得十分悠长。我还是第一次看她这样……
没想到,这竟成了母亲最后一个生日。3 月31 日晚上她走了。进了重症监护室,就成了永诀。从此阴阳两隔,再也见不到我慈爱的母亲了!
有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冷不丁地觉得她还真真切切地就在我的身边。
直到今天,我经常想,当时一直昏迷的她怎么就在进了重症室的时候,竟然翻转着坐了起来,并用尽羸弱之力伸出那只颤抖的手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会是什么事呢?再一想,对于她老人家来说,她已经习惯了叮咛她的子女们这这那那了,叮嘱了一辈子。没有一个母亲,能对子女完全放下心的。也许她要表达的仍然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叮嘱,但这是最后的叮嘱。她明白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再有了……
有时候我还在想,她扬了扬手,该不是在和我们,和这个世界告别呢?这就更加让人叹息了,她应该知道,我们一个个的从小就沐浴在她的恩荫下,这一生一世是不可能离开她的,她已经长到了我们的身体里。这应该是真的!许多年来,许多从小熟悉的朋友说到我的性格,和我的直言快语,甚至我的大嗓门就说像我妈。
每次回到妈妈的老宅,总感到她还在,随时就会出现在我的跟前。是啊,她能到哪去呢?我们几个做子女的都有这样的感觉,还有我们的后代,包括她老人家整天挂在嘴边的重孙,都觉得她没有离去。有天晚上,她老人家的重孙、我的孙子小锦棠说他看见了她,说她老人家正在向他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