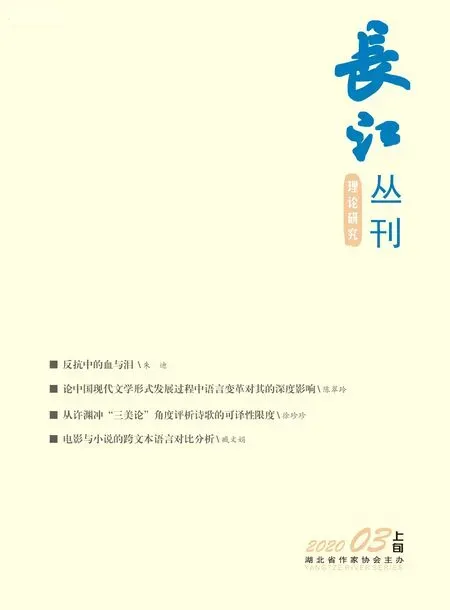我的东头街
■成向阳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我总是觉得,我身体里那种挥之不去的饥饿感是一场乡村的大雨带来的。大雨浇淋在1980 年代的东头街上,雨中一同来到东头街的似乎还有一垛一垛高耸的黄豆荚、几条被啃光的鸡骨和半根纸烟。
这种感觉,如今在午夜想来已既模糊又遥远,有种不同的物质在时间里相互倾轧后已经很难准确切分与重新检视的混沌感。但唯一能肯定的是,饥饿第一次像块石头被搬进我体内的那天,连绵多日的雨应该已经停了。那应该是我六岁那年的秋天吧,那个秋天里,故乡晋东南村子里的雨水很旺,村里沿街的老房子都湿淋淋的,房檐上的屋瓦像伤心的眼睛,滴滴嗒嗒不停地在往下滴水。东头街被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刨开,平地冲刷出纵横交错的深沟浅壑,暴露出土街底下年月悠久的苍黄内里。一个无事的闲人,如果站定在沟壑边细看,能看到一颗一颗黄褐色的沙砾以及在沙砾间盘曲延伸的乳白色树根。东头街,原来真是先人在一片沙地上踩踏出来的啊!
地里的黄豆荚刚刚收割回来,豆秧子都一垛一垛遮盖着牛毛毡,或者戴着谷草扎的锥形帽子,堆积在街道上等待天晴后捶打。我小小的一个人,真是小小的,穿着歪歪扭扭的黄绿布衫和歪歪扭扭的黄绿裤子,从屋子深处走出来,踩着青石廊阶边缘以一个九十度折角穿过苔藓丛生的老院子,迈出二门,下四个青石台阶,又走出两扇黑漆条条斑驳的大门,就来到了东头街上。我抬起小而青黄的脸朝上看看天,确信自己是走在一场雨与另一场雨黑云翻滚的间隙里。街道被一堆一堆戴毡帽的豆秧子分割成一块一块,我就弓着背从一堆豆秧子走向另一堆豆秧子。我总是感觉肚饥,我总是感觉自己腹腔里的胃和衣裤上的四只小口袋一样又空又瘪,又藏着一朵一朵看不见的小火苗。那个秋天下午的东头街上好像一个人都没有,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好像都围在厨房的火炉边烤土豆,烤红薯,烤脱下湿鞋的两只脚,只有我一个小小的人暴露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围着一堆一堆泛潮的灰黑色豆秧子发呆。
东头街其实很短,短得像村子多出来的一个指节,没什么用,却也砍不掉,就那么赘余在我故乡大箕村的村边上,慢慢繁衍出了几十户人家。这里离穿村而过的一条大箕河很远,离山却是很近。一座五指山绵延铺展,轻扣在一片起起伏伏的黄色沙土地上,远看还真像一只人手轻轻按着一只肥硕的灰鼠。年深日久,生满褶皱的指背隆成和缓的苍黄色山丘,指缝则凹成低低的绿色谷地,水流风穿,五谷生长,人和庄稼都踏踏实实的,就这样一茬一茬从古时过来。
村外有座奶奶庙,就修在五指山之无名指的指甲盖上。奶奶也就是送子娘娘,在诸神之列虽可能位份不高,但这庙却修得威武齐整,大殿高高在上,下面还引出了一个向东的阁楼,登楼就可望见村东南巍巍的群山和隐隐约约的河谷。阁楼下,是一道青砖垒成的半圆形拱门。年月悠长,包铁的木头门扇早就朽烂不见了,砖头箍成的门洞却是还在,从村外进了拱门,就是东头街,踩着光镜镜的石板一步步走过来,下一个陡陡的土坡,短短的东头街就算走到头了。
东头街的街面虽说不长,但街上老房子的年头却很长,沿着窄窄坡街而下的一溜老房子都有看得见的古色和来自年岁深处的一股味道。这股味道从各家堂屋的雕花木床底下漫出来,翻过门槛,跳下廊阶,穿过院子,再迈出二门和大门,就萦绕在几乎家家大门前都有的青石雕花上马台前。那些方柱体的上马台能有六七岁的小孩那么高,硬硬地站在大门外青石条砌筑成的门阶石两侧。门阶石上的大门槛也高高的,经过这么些个流水样日子,做门槛的木头上一条一条横斜的纹路都从里向外开裂了,像看多了伤心事,忍也忍不住要开口诉说,但体面还在,因而外形仍然齐齐整整,光滑圆润的上缘总是乌黑油亮亮的,不知有多少辈人从它上面一跨而过,出出进进,去办一些牵扯命运的大事小事。
村街窄,临街的院墙就总森森然的,一个人坐在街的这一面抬头看天,视线抬得再高,也高不过对面房檐上的一排灰瓦。能起这么高房屋的人,内心大概都是有一些尺寸和高度的吧。但,我并没有看见过当年那些起屋架梁的人,在我出生之前好多年,他们就都已经死了。
那个秋天,当我像从一团乌云中偶然降下的一个精怪,在一场雨和另一场雨的间隙里摸索在东头街上,就模模糊糊地闻到了死人的凄凉气味。那种气味,常常能够在隔段时间就出现在街道上的灵棚里面闻到。灵棚,是乡村里一个常见的终止符,它面孔死白,一亮相,作为乡村一个组成部分的某人,就已被连根拔起,就将被发送出村街,安居到五指山下的某一小片黄土里。
东头街上的灵棚,气味格外浓烈而复杂,它混合了松柏木棺材上新鲜的树液味、刚刚刷上不久的油漆味、大把大把燃烧后弥散开来的土香味、烧纸味、暖烘烘用来铺垫泥地的谷草味,花圈和纸人纸马上未干浆糊的酸臭味,以及穿越以上这些气味一路而来真正让人鼻翼翕动的各式供品味。那些花花绿绿的供品,油炸的,面蒸的,水煮的,甜的,咸的,不甜不咸的,都装在各式的白瓷碗碟里,庄严肃穆、威风凛凛地占满了一整张桌子。它们总是丰丰盛盛、巍巍峨峨地高据着灵棚的前台,与灵棚后面那具垫放在两条板床之上的新鲜棺木隔一张草帘对峙。这些诱人的供品,往往颜色鲜艳,它们金黄,它们洁白,它们苍翠,它们粉红,一律散发着毛绒绒的香甜气味。稍微有些突兀的是,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装在木头相框里斜立在碗碟中间,照片里的男人,苍白的脸上发散着暴露在遥远前世里的笑容,努力而暧昧地注视着这些阳间早与他无关的美食。但对于一个站在灵棚边上守候着那些供品的孩子来说,照片里男人的面容是可以视而不见的,一整个守灵待发的夜晚,八音会锣鼓、唢呐和二胡卖力的呱噪以及孝子贤孙们干燥的哭嚎也是可以忍受的,你只需要忍着瞌睡守候,只需要吞咽着满嘴的口水等待,只需要熬过一整个翻来覆去的夜晚,并在第二天上午重新来到这里,早早占据一个最为靠前的位置,就有可能在白衫披麻的孝子摔破满是纸灰的砂锅,阴阳先生拉长腔调大声唱出起灵的那关键一刻,一哄而上,扑向庞大而突然间歪歪扭扭的供桌,将那些香甜的供品据为己有。不,是据有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也不知道为什么,东头街上的男人总是活不过他们的女人。所以你在离开很久之后努力返回东头街,见到的总是那些活死了她们男人的老年妇人。好多年了,她们好像一直都在,好像和那些老房子一样,已经在街上生下根脚,好像岁月风霜已经很难再将她们撼动个一分半寸。这些老妇人们啊,高低胖瘦当然不同,穿鞋的脚也是有的大,有的小,灰发和白发掩映下的脸上的颜色和表情更是各式各样,但都一律睡得很晚,起得很早,她们的白天,也因而显得比手表上的时间要长出许多,有很长的一截多余出来的时间可供她们坐在村街上,或自家小小的门洞里,像一个陈旧而弯曲的影子在流连残存的光景,低头沉默,或者张嘴喋喋不休。偶尔,她们中的某一个,会朝着一面砖墙猛然咳嗽上几声,仿佛要把胸腔里一些灼热的意思,咳进那些厚厚实实的老砖头里凉上一凉。
当六岁的我揣着淋过雨的饥饿游走在东头街上的那些天,街上四奶奶家的一只老公鸡莫名其妙地死了。东头街上就是这样,一切母的东西都耐活,连打鸣的公鸡都活不过他们下蛋的母鸡。但一只公鸡死了,并没有几只母鸡和一群小鸡们替它搭灵棚、为它唱哀歌。那些母鸡和小鸡们依旧聒聒噪噪地迈着碎步兴高采烈,在沙土地的枯枝败叶里啄来啄去,寻找雨后出土的蚯蚓,或几只雨后不甘寂寞的小虫。而死掉的老公鸡早已被褪光了满身红毛,煮在了四奶奶家灶台上的一只黑铁锅里。
四奶奶是东头街上老妇人中很特殊的一个,她个子大、脸盘大,弯弯的脚却小得让人可怜。大白天,她经常坐在东头街坡下第一座房子门外的青石条上,两只深陷在皱纹里的细眼眊着坡街上头,两只手却在麻利地一甩一缠,摆弄自己的一条裹脚布。要不,就是举着半截发黑的木头梳子,贴着头皮一下一下地梳她的半把白发,感觉梳理齐整了,就用手朝后一抓,在脑后挽成一小团圆圆的发髻。她很喜欢把腔调拉得长长的说话,和坡上坡下来来往往的人说,和扛锄头出东阁外上地的人说,和挑着担子下坡担水的人说,和上学放学的小孩子们说。没人的时候,她就嘟嘟囔囔和自己说,嘴角唇边不时飞溅的,是诸如“哎呀,不好过呀”“哎呀,老天爷呀”“哎呀,不当活呀”之类奇怪的感叹。
四奶奶的老头,也就是四爷爷,据说是灾荒年间被山上下来的老狼吃掉的。老人们说,老头是在午后腋下夹着小锄哈腰出了东阁外,去五里外迎旭桥底的田里间快要旱死的谷苗。他蹲在地上,一锄一锄间呀间呀,就感觉天旋地转,就感觉自己也要旱死在小锄上了。朦朦胧胧间扭身一看,就看见一只流口水的狼嘴,狼嘴一张,就咬住了老头的瘦脸,又咬住了脖子,拖下了田塄,拖着走了。老头死后几年,灾荒过去了,四奶奶在东头街上临街养了几只猪娃,每天用米糠、麦麸和野菜煮一桶猪食,提上去猪圈里嗷唠唠地给猪们喂食。到了晚上,她也久久不睡,就一个人坐在门口的上马台上,听猪们在月亮照耀着的猪圈里心满意足地哼哼。有人说,她夜里不睡觉是怕狼从山上下来把猪拖走,也有人说,她是等夜里老狼从山上下来,好看一看自己被狼吃掉的老头是不是也变成了老狼。至于四奶奶在不眠的深夜里究竟等来没等来她的老头和狼,谁也不知道,只是后来四奶奶的鼻梁一夜之间就飞走了,嘴巴和眼睛之间,除了一个朝上翻起的肉鼻头之外,原来权充过渡的一只高鼻梁像风吹般荡然无存。又有人说,四奶奶是半夜去喂猪,被扑起来的公猪一嘴把鼻子拱掉了,也有人说,她是提着猪食桶在雨天里滑倒,鼻子磕在了青石凿成的猪食槽上。总之,四奶奶没了鼻梁,嘴巴之上就是两只细眼,成了东头街上一个特殊而怪异的老妇。
那天午后,四奶奶家窄小的门洞里放射出袅袅的香气。在雨后粘湿的空气中,这香味是如此刺激而陌生。我从豆荚堆后露出半边脑袋,看着那木门半闭的门洞,犹疑着是否应该钻进去一探究竟。但那香味在我的鼻翼里却像一只斑斓的老虎半伏着身子耸动,让我闻而却步。我不确定,那发出奇异香味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究竟能吃到嘴里还是不能吃到嘴里,以及吃到嘴里以后又会怎样。但这一疑问在黄昏的时候被四奶奶打消了。在一团淡淡的暮色中,高大的四奶奶喜气洋洋地站在门洞外,用一个银光闪闪的小白铁盆端出几个长条状的卷白馍。她高声招呼街上闻香而出又远远躲闪着不敢近前的几个孩子:“来呀来呀,奶奶做的卷白馍,馍里卷的可是鸡肉呀!你们谁吃过鸡肉呀!来来来,奶奶给肉吃。”五六个小孩于是动开身子,涌进了四奶奶的门洞。四奶奶笑骂着,用手把一个卷白馍从中间揪开,揪出丝丝拉拉的绿豆芽,这个给半个,那个给半个,还一人给一根锅里捞出来的鸡骨头,说,吃吧吃吧!
终于轮到了我,我伸长脖子,看了看铝盆里卷满绿豆芽和鸡肉丝的白馍,又看看黑铁锅里油腻腻的汤水里浸泡的鸡骨头,狠狠地吞着口水说:“奶奶,也给我一根骨头吃吃吧!”
我高高地向着四奶奶的脸前伸出了一只右手,然后抬起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奶奶圆圆大脸上细成一条缝的眼睛,等待施舍。但四奶奶却好像刚刚看见我一样,用稀奇古怪的声音说:“哎呀,你怎么也进来了?不给你,不给你吃!”然后,她在黑布围裙上擦擦手,像撵鸡犬一样朝我头顶挥舞了几下,说“回哇,回哇”。但我就是不走,嘴里喊着“我要吃,我要吃”,脚就向灶台跟前的黑铁锅走去。可四奶奶终究还是把我推出了门外,又一把关上门,隔着门缝喊:“回去找你妈,想吃回去找你妈!”
第二天午后,天又开始下雨,我戴着一顶草帽出了门,继续在一垛一垛的豆秧子之间空虚地游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总觉得是要给自己空荡荡的胃寻到一个着落。忽然,我在一垛豆秧脚下看见了一小堆鸡骨。那些鸡骨昨天还倨傲地坐在四奶奶家灶台上的黑铁锅里滋滋润润,如今却可怜巴巴地扔在豆荚堆下淋着雨。我蹲下来,认认真真地看那些雨中的鸡骨。它们很细,有的乌黑,有的青白,但一律被不同的牙齿啃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连骨头都咬裂了。此刻,它们浸泡在秋天午后的雨中,滴滴嗒嗒的雨水,更让它们看上去清清白白,楚楚可怜。我伸手从水洼里捡起一根鸡腿骨,想象自己是从四奶奶的黑铁锅里捞出了它,认真看了看,又放到了自己嘴巴前。但心里想的,却是母亲昨夜和我说的那句话:“她家的公鸡,是吃药毒死的,毒死的鸡谁敢吃呀!”
手里冰凉的鸡腿骨却显得无辜而纯良,好像它从来不曾附着过皮肉,不曾沾惹过羽毛,不曾属于过一只活生生打鸣的公鸡,更不曾生病或者中毒而死,可供我放心地举在嘴巴前,想象一场酣畅淋漓的吃鸡盛宴,并虚拟丝丝缕缕的鸡肉在充分的咀嚼之后顺着食管吞咽进肠胃的感觉操演。啊,鸡肉!
我忽然看见了两只鸡爪子。那两只鸡爪子,被一些散乱的豆荚半遮半掩,但爪子上黑黄的肉皮和鳞片仍然清晰可见。雨水清洗着它们,也使它们开始发肿发胀。它们被刀斧截断之处,斑斑的血迹开始变淡,但刀口处已经发黑,仍隐隐约约渗着淡淡的血一样的东西。一刹那间,我感到两只鸡爪在动,感觉它们好像要重新站立起来,好像要重新找到那只早被吃光的公鸡,重新帮助它雀跃奔跑。一刹那间,我空空胃里一车石头般的饥饿像突然翻车一样被倾倒过来,它们山呼海啸,朝着我的喉咙和嘴巴翻涌。我赶紧闭嘴起身,捂着脸向着家门奔逃而去。
仿佛赊出来的太阳又抵押进满满的雨积云,云里又开始拧出了旺盛的雨水。坐月子的母亲,依然躺在东屋的土炕上奶养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我依然在午后感到肚皮里饥饿,依旧会跑出家门,在那些因为无休无止的雨水已经开始泛潮发胀的豆荚堆之间游游荡荡。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偷窃。
我开始偷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向着别人家未经捶打的豆荚下手,为什么会把那些毛茸茸的黑豆荚从豆秧子上摘下来,掰开,一粒一粒取出里面已经开始变得白胖的黄豆,为什么又要把那些黄豆一颗一颗装进自己空空的口袋里,并且上下四只口袋都装得满满当当。我只知道,自己最初是无意识地向着一堆豆荚伸出了茫然的手,只知道是想掰出一颗黄豆放进嘴里尝尝味道,只知道生黄豆在后牙的咀嚼中自有一股既生且涩的香味。但事实是,一天两天三天,我竟从东头街上装回了小半布袋的黄豆,我把它们悄悄积攒起来,藏起来,藏在阁楼上的一堆旧铁器深处。有时,我会坐在那堆铁锈斑斑的锄头、镢头和炉工钳子之间,看着那一小袋黄豆,想象如果把它们加一些红糖炒熟吃进肚子里会怎样。但我竟终于没有机会去炒,我只能再次跑出去,到东头街上的豆荚堆里,一次一次地伸手,一颗一颗地偷窃。终于,我撞见了九奶奶。
九奶奶在雨中抽着一根纸烟,亮晶晶的眼神从大而黑的两只眼里放射出来,定定地罩住了我。她就那么看了一会儿,从鼻孔里缓缓喷出两股烟雾,用软软上扬的方言问我:“小阳儿,你这是干啥呢呀?”
这个九奶奶,在东头街的老妇群中也是极个别的一个人。不用开口,只用她人堆里靠前一站,你就会眼睛一亮,觉得她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本不属于东头街的,只是半路上被一阵风雨移栽到了这里,像她院子里种的一株桑椹,或一丛丛月季花那样。作为女人,她身材高大,但并不像东头街本地女人那般有庄户田间磨砺出的健壮与悍勇。她是软而光鲜的,像一段被面绸子,她的手、胳膊和腿脚都软得轻巧,尤其是腰肢,有着一眼可见的无骨风韵。她走动起来的时候,腰和腰下的臀会收敛不住地摆荡,在周遭带出响动和风声。她的头显大,骨相也有些刚硬,但一双有声有色的大眼,小而尖的鼻子,又让这脸显得灵活而不叫人紧张。她那时候已六十开外,但似乎驻颜有术,满头乌发绝不显白。而一旦她开口讲话,柔和丰厚的唇舌间就像有花枝摇曳出来,话语中,陌生而遥远的滋味与腔调,和短促强直的大箕方言有着天壤之别。更讶异的是,她像男人一样常年吸烟,而且是吸白生生的纸烟。天气好的时候,她就素素净净地坐在大门前一块青石上,娴熟地翘起一条长腿吸纸烟,不时喷吐一团烟雾,然后用夹烟的一根食指轻弹烟灰,再用另一只手拂一拂裤脚。
当九奶奶在秋雨中的豆荚堆边把我堵住的时候,我的手里正捏着一枝豆荚,我的衣服口袋里满满的都是掰出来的黄豆。九奶奶朝我吐出一团悠悠烟雾,然后在烟雾那面对我笑了一笑。她说:“小阳儿呀,你跟我来。”
九奶奶家在东头街上的院子叫后花园。园子已经荒废,几颗硕大的梧桐之间,点有一棵桑椹树,树下种着一丛一丛的月季花。九奶奶的厨间也收拾得整齐,隔着竹帘子,能看见雨水一滴一滴打在凋残的桑叶上,打在月季花枝间。九奶奶让我坐到炉子边烤火,自己走到屋角,弯腰从一只坛子里捞出两把红薯干,又走过来把硬硬的红薯干烤在炉子口上,等烤热烤软了,她说:“吃吧,甜甜的。”我就热热地拿起一个吃,九奶奶看我慢慢咀嚼着红薯干,又说:“你可再不敢去街上捞摸别人家的豆呀!”我说“嗯”。
九奶奶是山西太谷人,又曾流落南方。1940 年代末,跟随当国民党上尉的九爷从太原回到东头街。据说,她回来的那天,在东头街上的男人女人眼里像一个怪物,烫卷发,戴戒指,穿旗袍丝袜,双脚蹬着尖尖的高跟鞋,嘴里吸纸烟。但她人机灵,胆大,门户看得很紧,心又善,很快就在东头街上扎下根来,养育三女一子。
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老人们闲说,九奶奶的早年是在花街柳巷的红灯下讨生活的。而在东头街雨季的厨间炉子边上,九奶奶烤软的红薯干真甜啊,甜得丝丝冒出白气,甜得润我胃肠,荡我肺腑。九奶奶还架起一只锅子,把我口袋里的黄豆加了一点红糖,慢慢炒熟了。就那样,在屋外滴滴嗒嗒的秋雨里,一个小孩,一个老妇,守着火炉,看着雨中的桑树和凋谢的月季,一颗一颗,吃完那些焦甜的炒豆。
即使在吃豆子的时候,九奶奶的唇边依旧噙着半根袅袅的纸烟,烟灰积了老长,却浑然不觉。她偶尔抬起头来,眼神飘渺,朝上穿过了东头街暗色屋顶尽头层层的雨幕。只是我当时太小,不知道她究竟看向了哪里,又看见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