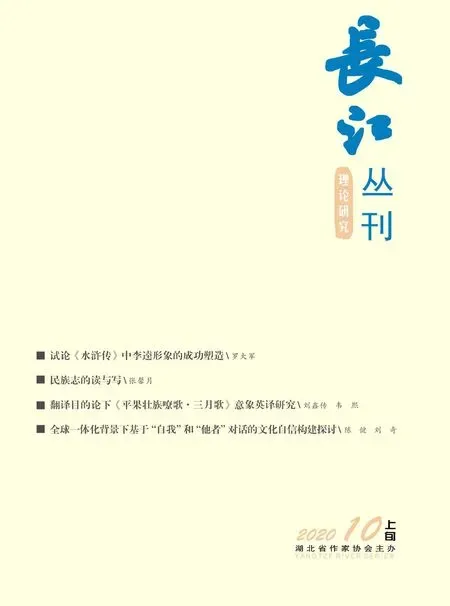民族志的读与写
——评《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
■张馨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论著与生活》一书以格尔兹1983年在斯坦福大学做的四场讲座为底本增补而成。他以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四位人类学家为例,探讨民族志者的写作策略这一问题。“他对民族志文本的生产性质、生产过程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探讨,为我们确立了民族志文本研究的经典范例。”[1]
一、本书特色
直面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格尔茨重读经典民族志,阐释另类的“人类学史”。他认为研究对象的本质是难以抵达的,其同时浸润着需要理解它的、大量的背景知识。[2]此外,研究者也并非白纸似的进入田野状态,他带着自己的“世界”。在此,格尔茨从四位人类学家的写作风格入手,将其与他们所受的知识传统、学术氛围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相联系。因此,对民族志文本的剖析,便是对人类学家给出的有关他者的解释之解释。[3]
格尔茨使用“在那里”和“在这里”两个空间意象作为全书的结构框架,联系起人类学家“在那里”做田野调查和“在这里”写作民族志的两地生活。并在首尾的两处空间中,展开一个非线性的时间序列,格尔茨进入“过去”人类学家写作的文本,思考今天民族志写作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在那里”同时意指着格尔茨对经典民族志文本的阅读之旅,而尾章“在这里”则是他在旅行结束之后,对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模式——实验民族志的批评。[4]
此外,格尔茨的写作旁征博引,文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融会贯通。他在讨论四位人类学家的写作风格时也在展现自己的风格——散文式的语言,幽默还略带调侃和讽刺。此外他擅长用比喻、双关的手法进行阐释,文中穿插着大量文学典故,文本显得意义丰富。如标题中的“lives”既指人类学家的生活,也指被研究者的生活。
二、全书内容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为什么要讨论民族志写作问题;第二部分即按章论述四位人类学家的写作风格;最后探讨当“在这里”和“在那里”的界限逐渐消融,写作民族志的意义何在。
首先,他驳斥了反对讨论民族志的两个意见:一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建构方式是非人类学的做法,二读者认为人类学文本不是文学文本并不值得如此的关注。他认为作者写作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文本的可靠性。接着格尔茨采用福柯和巴特的理论,辨析了“作者”和“写作者”的差异——“作者”是一套话语实践体系的创作者,“写作者”仅是文本生产者,并精心选择了四位人类学家作为他论述的重点。这四位人类学家都分别影响了法、英、美现代人类学特征的形成,他们集中体现了人类学者如何看待和处理从“在那里”到“在这里”的张力。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文本自我指涉性、多义性最强,也最能证明格尔茨所论说的“民族志的写作性质”;埃文斯-普里查德建构文本的方式既富有独特性,在人类学内部又极为有力;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参与式观察;本尼迪克特对“在那里”的生活“化生为熟”,以此来观照、批评自己的社会。这种方式是人类学写作自我反思的另一条路径。
第二部分即进入文本分析。格尔茨挑选列维·斯特劳斯开启论述,因他自觉地重视文本写作方式和文学表达本身,行文中不断暴露文本的生产过程:作者的立场、姿态、反思都清楚地呈现给读者。格尔茨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作品都是围绕《忧郁的热带》的多层次展开。《忧郁的热带》由五种文本互文而成,这五种文本组合转喻而成一个“探索故事”:“在这里”是无聊、熟悉的,“在那里”是一个神秘、黑暗、充满幻想的世界。而列维-斯特劳斯最终颠倒了“在那里的生活”与民族志的关系,即民族志是将“在那里”奇异的生活编织进抽象普遍的文化分析模式中得到的。亲身分享他者的生活是理解他们的基础材料。
普里查德以独特、统一的语言风格入选。选文《阿科博和和吉拉河的故事》展现了他话语方式的所有特征——伪装的即兴讲述、隐含的“想当然”语气。在普里查德看来人类学的使命便是传授关于原始人的知识,进入“在那里”的生活需要克服重重障碍,而经过至少一年的田野工作,人类学家写成的民族志其真实性无需质疑。普里查德大量使用照片、插图等形式,组织起一幅幅明确的形象。也就是说,“在那里”的世界固然是“原始的”,充斥着难以理解的现实图景,但只要人类学家足够耐心,最终的答案就是可辨的。实际上,普里查德有始终关注的问题,他的研究都以一个发现作结。他为表面上难以企及的他者提供有关他们特定生活观的证据。他们是怪异的,但那不算什么。
然而人类学家如今面临的田野环境相较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的准则:搜集资料和理论研究主体的合一。[5]格尔茨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就意识到了人类学工作方法的问题——如何将人类学家“在那里”的个体经验“在这里”写成一个客观科学的田野报告。而人类学家将“在那里”的经历在“在这里”讲述出来,首先就要面对可信性的怀疑。马林诺夫斯基塑造两个互相对立的形象——绝对的世界公民、彻底的调查者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公民可以融入进任何情境,调查者具有客观冷静地剖析精神。其矛盾性体现在文本中便是“一会儿是深不可测的神秘,一会儿又是明确肯定的定律”。有两类人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一类是在文本中自我暴露,把马林诺夫斯基用以自我隐匿的日记形塑成一种有秩序的、公共的风格类型;另一类是将主观的“我”转化为叙述者“我”,即实验民族志中强调以主位和客位视点表述的文本构建模式。通过对三个有关摩洛哥的田野报告的考察,他指出作者都试图创作高度“作者——饱和”的文本,但他们在字里行间表达出的并非令人信服的他者生活,而是自己的不安。由于意识到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联、写作者拥有的文本解释权必然会对他者声音造成遮蔽,“在那里”本身就变成了一件无以为继的事情。而格尔茨认为还原当地文化的想法只会把事情搞混,人类学者不应追求成为本地人,而是和他们“交谈”。[6]
本尼迪克特的文风了展现了人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维度,即借助其他文化的现实来嘲讽与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她的《菊与刀》便是以“像我们看待他者那样看待我们自身”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本尼迪克特的写作风格非常强烈:明确的观点、鲜明的形象、反复的断言、讽刺性的言语风格。她从未真正去过日本,始终是想象性的“在那里”。但她并非去缓和我们关于一个古怪民族的感知,而是通过不断地强化它的怪异来解密它。她在文中并置日本与美国,日本人与美国人形象的针锋相对,使得日本的神秘性渐渐褪去,美国的明晰性却逐渐模糊。
在最后一部分,格尔茨指出“在那里”和“在这里”的鸿沟原先仅是技术上的难题,现今还受到田野工作中的学术伦理、描述分析方法的繁多等诸多因素影响。他认为讲述他人生活道德和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只是现在不再被隐藏起来。而人类学家的任务并没有改变:首先承认民族志是一种想象的写作,而它的写作目的仍旧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人说明在此说明关于他者是如何生活的。
12年之后,格尔茨再次解释了民族志和民族志写作的问题。[7]他指出人类学家应该摆脱“像土著一样思考”的迷思,必须承认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可能共享同样的立场与观点。民族志写作的关键就是在将文化视为文本的前提下,并置当地人和人类学家的描述,对他者的文化解释进行解释。
——兼议彭兆荣的“体性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