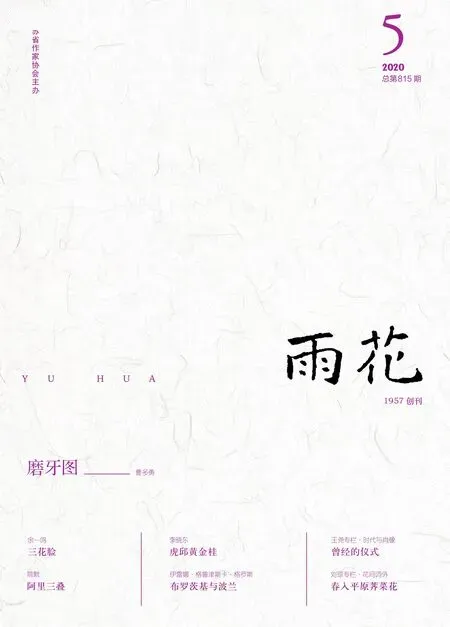洋楼(外一篇)
汪夕禄(江苏)
赵家小姐看到那个病人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那天是末伏,刚刚立秋,早晚天气已经有些凉了。赵家小姐还穿着薄衣轻衫,她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把病人带到内室。
赵家小姐生得圆润,肤色也白,美中不足的是胳膊腰脚都偏长,不敢大步走路,显得拘束而内敛,倒隐没了她原本的圆润和温柔。她是来送西瓜给父亲的。西瓜是垛上农夫送到厨房的,父亲曾救过农夫的命,从此,赵家再没缺过瓜果蔬菜。赵家小姐叫佩环。这名字虽然普通,她却极喜欢,听上去叮叮咚咚。西瓜是佩环小姐亲自切开的,选了最好的一块送给父亲。
佩环没有看到那个病人。病人身体单薄(正是病人该有的样子),却有一张完全不像病人的脸,红润而苍白。“红润”“苍白”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是佩环看到他的脸想到的第一对词语。以后,她将会知道,有一种病,内热而外寒,就会呈现出这种病态的面色。
虽然没有准备,但佩环不愧是佩环,她没有慌张,而是冲着坐在父亲对面的病人点了点头,放下西瓜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可是,佩环也只是佩环,坐到房间里,她的心开始跳个不停,整张脸烧了起来。他可是个英俊的病人呢!
佩环的家被当地人称之为洋楼。三层,西式的框架,中式的里子,外面看上去是洋楼,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是中式的。佩环的卧房,也可称为闺房,在三楼东侧,不太大,堆满了书,大都是古书,也有几本《新月》杂志,封面上简单的“新月”二字,显得非常富有生命力。大多时间,佩环都在房间里读书。借着南窗射进来的光线,一字一句地读,只有一个听众,那只毛黑如缎的波斯猫。
自从那个病人来过一次,佩环没事就喜欢往父亲房间跑。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好像孩子第一眼没有看清某个魔术,于是心里一直惦记,哪一天还要好好看看。她心里其实是想再碰到那个病人。果然,她又碰见了。却是无意,也不是在父亲的房间内。这次是在洋楼院中的凉亭之上。父亲和那个病人,正在手谈。黑白分明的棋子,没有杀气,倒漫着药香,衬得亭子外面的荷花也失色不少。
佩环没有裹脚,走起路来平平稳稳,身材又长,站到院子里让人很难忽视。父亲叫住了她。她终于知道了那个病人就是城里新民小学校的年轻校长,姓孔。佩环向孔校长见礼。孔校长慌忙起来回礼。孔校长也是长身之人,比佩环还高出一个头,只是单薄,眉毛很浓,不是病人应该有的样子。后来,经过父亲的证实,孔校长的病其实早就好了。只是两人在诊治之间,因为谈得投机,竟成了好朋友。所以,三两天就会过来坐坐。
佩环也就和孔校长熟悉了。后来,时局越发乱了。孔校长不太过来。几天看不见孔校长,佩环就觉得心里乱得很,书也看不下去。一天找父亲好多趟,其实是想向父亲打听孔校长的消息。父亲知道她的心思,却偏不说。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赵医生相人是一绝,更何况是自己的女儿。孔校长是好青年,可是太激进,早晚会吃亏。不过,作为父亲他也不好过多干涉女儿的情感。他是个开明人士。
佩环的猫忽然失踪了。那只黑色的波斯猫本最通人性,一夕之间,竟然踪影全无。佩环找遍了洋楼的每一个角落。那天久不露面的孔校长忽然拜访赵医生。因为都熟识了,佩环也就不回避了。佩环认真地打量孔校长,几日不见,他憔悴了不少。佩环的心里,浅浅地疼了一下。如果由她来照顾孔校长,他肯定不会如此。不知道,他这些天吃了什么苦,莫非病又犯了?佩环胡思乱想。
父亲和他谈论时局。“不能再乱了。”孔校长说。“北平真是如报上所说吗?”父亲问道。“只有更糟,已经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了。死了不少学生。学生、工人都不敢上街了!”孔校长激动地说。接着他又讲了北平之行的惊险遭遇。前几日,他到北平采购学校的课本,刚刚办完事情,走在大街上,想好好看看北平。街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举着标语,呼着口号。开始还好,后来来了大批军警,说是有学生放火烧楼。开始大乱起来。他也没敢多待,连夜就回来了。
听孔校长讲外面的事情,佩环睁大了眼睛。她想象不出外面的情景。好在孔校长安全回来了。她多想跟孔校长说,你以后就不要出去了,多危险啊。父亲像知道她的想法,对孔校长说:俊卿啊,你以后就不要四处乱跑了,免得有人担心。说着,故意看了看站立一旁的佩环小姐。佩环又羞又恼,瞪着父亲,扭身就走。
父亲和孔俊卿又恢复了几日一谈的习惯,有时也不只是他俩。他会带几个青年过来。佩环每次都旁听,并不多言。几个人慷慨激昂,纵论天下的样子。
孔校长向赵医生提亲了。同来的还有一个男青年,几乎和孔校长长得一样,疏眉俊目,细瘦长身。那是他的弟弟,孔飞卿。兄弟俩长得像,但如果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不同。俊卿沉稳,像一潭深水。飞卿浅浪,两只眼睛顾盼有神,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眼神,总令人难以放心。孔校长却是替飞卿提亲。赵医生愣了很久,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送走孔氏兄弟,佩环从楼上下来,问父亲:“他是来提亲的?”父亲点点头。佩环掩饰不住心里的高兴,显露在脸上,满室春光。赵医生看女儿情态,忙说道:“不是。”佩环诧异:“不是?”“他是替他兄弟提亲,兄弟叫飞卿,长得和他很像。”“您怎么说?”“没怎么说,你怎么看?”医生问女儿。“不行。”佩环答得很干脆,不是她心里的人,她不答应。
事情就有些曲折了。起初孔校长还登赵家的门,后来见赵家迟迟没有回复,知道事无可成,也就不再登门。赵医生知道此事可能伤了孔校长的自尊,想等有机会再向他解释,相信并不会造成大的嫌隙。可是,佩环却病了。
佩环的病来得突然。没有征兆,先是说头疼,后来又说胸口疼,最后竟至于哪里都疼,躺在床上不愿动。父亲亲自诊脉,除脉息沉些,并无不妥。可是,佩环还是一天天瘦下去了。本来长身丰腴的姑娘,竟像被什么抽去了一部分,留在这世上的既像是她又不像她。赵医生束手无策。
赵医生去找孔俊卿,那天他恰不在。弟弟飞卿在家,赵医生让他带口信,请孔校长得空时去家里一聚。飞卿在院子里,甩水袖,咿呀着唱戏,答应了赵医生的请求。赵医生想该留下点什么,苦于手边无纸笔,又不想麻烦沉浸在戏中的飞卿,只好作罢,叹一口气,离开了孔家。
赵医生在洋楼没能等到孔校长。佩环的病不见好转。院子里一棵好好的石榴树却一夜间绿叶尽落,剩了枯枝败叶。赵医生暗叫不好。这棵石榴是佩环母亲生前所栽,已近十年,成熟后每年挂果,石榴多子,汁液甘甜,现在一夜间,枯败下去,不是好兆头。眼见中秋将至,月已半圆,佩环仍是卧床不起。父亲知道女儿因何而病。女儿钟情于俊卿,可是因为俊卿替弟弟向她提亲,而断了爱他的路。如果佩环母亲在,也许她可以向母亲诉说,也不至气郁于心,邪毒攻入经脉。
赵医生去看女儿。佩环小姐斜依在榻上,见父亲进来,挣扎想起来,终是力竭,没能起身。佩环满脸羞愧,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不言。赵医生看女儿如此,暗恨自己当年不该一味沉迷医术,冷落妻子,而让妻子有了癔症,并死于此病。
“这几天,我老看到母亲。”佩环终于发声,“她就站在北窗下,不看我,却朝外看,似是要破窗而走的样子。我想,母亲是来带我走的。”
父亲心如刀绞:“儿啊,不要胡思乱想,你肯定做梦了,梦醒了就好了。你这么年轻,母亲怎么忍心带你走呢?”
“可是,母亲也是年纪轻轻地就走了呀!”女儿的话再次戳痛了父亲的心。
十年前,洋楼刚刚建成。一切都是新的。这座洋楼是整个城市最时髦的建筑,请了宁波的工匠,参照西洋造房术建成。赵医生并没有花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是一位巨富所出,只是为了感恩,因为赵医生救了他一命。所谓知恩图报,即是此。赵医生名声大噪,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传遍了附近的城市。他又在洋楼东边建了几座平房,用来坐诊。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妻子的不正常。
那时候,他的心中只有病人和医术。妻子本是个爱热闹、有情怀的女人,不仅识字还写得一手好字,并且会做诗,说才女是一点不过分的。可惜,他不懂得珍惜,冷落了妻子。“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与断瓦残垣……”在写给表哥的信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表哥与她青梅竹马,也是才子,书信往来,先是纸上有了烟霞,写信如做诗,那些汉字在他们的笔下活了起来。可是,活着活着,那些汉字的手脚就不规矩了,手脚不规矩的汉字,如果让外人看到了,就有了相思的味道,有了追述旧情的味道。偏其中的几封信落到了赵医生的手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医生,看到那些娟秀的汉字,在他眼中,那些美丽的汉字一点也不柔弱,相反,它们是一把把小刀,直插他心。
他狠狠地打了她,将那些信送给了她的父母。再以后,他不想再回忆了。现在想来,错的其实都是自己。如今报应来了。
赵医生还是去找了孔校长。果然不出所料,孔飞卿并没有告诉哥哥医生请他的事。他就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赵医生到孔家的时候,孔飞卿正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打水,弄得水花飞溅,打湿了从旁边走过的赵医生。孔俊卿正在书房,临着米元章。赵医生不知如何开口。直接说请孔校长看看佩环,她因为您而生病了,这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的。赵医生嗫嚅着:“令弟的事情……”孔校长不等医生说完,摇摇头,说道:“无妨,缘分天定。”医生又说:“孔兄长久不到寒舍,家里人都惦念着呢。”话再说就明了。孔校长点点头:“最近学校事务多,等闲下来,一定拜访,你我还要分出胜负的!”他讲的是围棋。赵医生不好再说什么,怏怏地告辞,院子里孔飞卿还在打水。医生远远地对飞卿说:“飞卿,先告辞了。”孔飞卿直了直身,没有言语。医生也不见怪,匆匆而过,这回井水没有溅到身上。
俊卿仍不登门,医生也就死心了。每天上午诊病,下午陪女儿。日光有脚,踢踢踏踏,恍然月余,中秋是早过了,索然无味。入了深秋,佩环竟一天好似一天,本来皮包着骨头,渐渐地竟然又有了肉色。虽仍是病态,生命肯定是不打紧了,只是眼眸间少了过去的灵气。真正奇特的是那只波斯猫竟然又回来了。皮毛打结,浑身肮脏,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折磨。那天,佩环到院子里散心,见假山上似乎有一个黑色的点,走近了才发现是那只波斯猫。猫有九命,它才丢了一条。她佩环也有九条命,也才丢了一条。如此一想,心里顿时安定,过去的几个月,好像过了百年,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别人根本没有参与进去。回头看看,倒是可以一笑的。
赵家和孔家不再来往。没有仇隙,却不相往来。佩环的病好了,但也留下了后遗症,听不得孔氏兄弟的名字。时间又过了好些年,赵家洋楼好像已经忘却了那个人。没有人主动提出,也没有人主动回避,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佩环慢慢也有了笑容,都浅浅淡淡地,浮在脸皮上,似乎与面皮以下的部分脱节,令人不舒服。总之,和谐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在以后像棉絮一样漫长的时间当中,佩环小姐再难有爱的心。曾经的爱在她的心中,就像蛛网暗生一般,吐出一根根纵横着带着黏液的细丝,那都是恨啊。在高达三层的洋楼里面,长身的佩环,像幽灵一样地上下巡视。她总能想起初见孔校长的那一天,阳光那么好,父亲的神态,两个人的话语,和一老一少两种不同荷尔蒙占据空间后形成的奇妙感觉,压迫着,令她窒息。她被这种感觉折磨着,同时又渴望这种感觉的突然降临。起先,那是时光还在眼里一点点流逝的时间里,她总有办法让自己抵达那种感觉。后来,时光死了,像一只僵硬的巨鸟停卧在了洋楼伸出的廊檐上。她的心不痛了,全身虚空,她觉得灵魂已经飞远了,而留下的躯壳是可以乘风而去的——凭虚御风,她这样理解。如此,洋楼里的赵家小姐总是幻想自己可以飞起来,像一只被淋湿翅膀的鸟,或一张被做了法术的纸人。
关于洋楼和佩环的故事,以后都是重复,就像她房间里的那只蜘蛛,每天修补着被穿堂风吹破的网,用尽了余下的全部生命。
问
项剑在八字桥上等到了一双鞋。这是一双木底草鞋,正是三哥平时所穿。时在下午,阳光猛烈,流水不动。三哥的鞋倒覆于桥面,鞋底由于长久使用,已经磨平。两只鞋子呈八字放置,并无异样。项剑细看,一群蚂蚁,正踌躇满志地冲向鞋底的一块黄色糖渍。项剑折下桥头的一根细柳,扫向蚁群,飞来横祸,蚂蚁四散。片刻,蚁群安定下来,在一只褐色蚂蚁的带领下,又重整旗鼓向草鞋冲去。项剑不敢动鞋子,左右观看,蚁群再次逼近。项剑下定决心,将两只鞋提到手上。鞋子底下压了一张黄元纸。项剑不识字,捡起黄元纸,放到口袋里,扫视一眼失去目标的蚂蚁,小心地将鞋底糖渍挑出,扔向蚁群。
项剑回到城隍庙。三姐正在等他。他将鞋子递过去,三姐接过鞋,脸上现出惊惶神色。
是三哥的鞋,三姐仔细嗅嗅说道。
在哪里找到的?她问道。
八字桥上,项剑回答。
八字桥?三姐将鞋子抱到胸前。
项剑说,我在桥上还看到一群蚂蚁。
蚂蚁怎样?三姐茫然。
没有什么,项剑自觉荒唐。从口袋中掏出黄元纸。
黄元纸的正面用炭笔印画着财神像,上书“招财进宝”,下书“敬神如在”,四边由铜钱串绕着,背面有一行黑字,字小如蚁,并不工整。三姐看完,长叹一声,你三哥是被人绑架了。
三哥并非行三。只因名字中有一“山”字,人都称为“山”哥,时间一久,便成三哥。三姐不一样,三姐行三。
三姐问项剑,你跟三哥时间最长,三哥最近是否得罪了不该得罪之人。
项剑沉思,翻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他有记日记的习惯。项剑不识字,记事全是图画,共三幅。
其一,画面人物有三。一虬髯汉子,一妙龄女子,项剑自己,画面中心有一只土狗。这是讲三哥当街杖毙疯狗的事。
那日,项剑与三哥巡行街上。见一妙龄少女,独自行走,街巷之上,春风荡漾。正在此时,一恶狗从暗处窜出,妙龄少女花容失色,几欲惊倒。危急时刻,三哥一手扶住少女腰肢,另一手执棒扫向恶狗。恶狗顿时毙命。事后,并没有狗主出来。死狗被街上无赖牛二剥皮烹食。
三姐接过日记本。虬髯汉子正是三哥,项剑站在一边。妙龄少女面目模糊,唯胸部画得逼真,呼之欲出。三姐赞道,你倒是好本事。
第二页,全用墨汁涂黑,并无一人一物。
三姐奇怪。
项剑解释,这是我与三哥巡夜。当时天色如墨,我们摸黑而行,不知哪个家伙,打了我一闷棍就跑了,我当时眼前一黑,是三哥将我送回家的。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个下的毒手。
三姐点头。第三件事呢?
却是一座酒楼,楼名“望天叹”,三哥与人豪饮。三哥对面是一白面书生。项剑画图时并未用心,一张白脸草草勾就,然后顺脖子的方向狠狠往下撇了一笔,即是身体。项剑自己也坐着,英姿勃勃,完全不是本来模样。白面书生脚下还蹲着一条黑狗。也可能是其他颜色的狗,项剑没有交代。
就这些?三姐问道。
我知道的就这些。项剑答道。
谁还会比你知道得更多?三姐说。
项剑刚想答话,三姐以手势止住,说道,不要说了,我们去问问她吧!
她住在幽深小巷中。木门未漆,墙头探出半树紫薇,火红,衬得青色院墙隐约跳动。敲门。片刻,女子应门,引二人进去,三姐并不进屋,而是长身立在院中银杏树下不动。树已百年,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女子不强求,倚立树侧,静待三姐发问。三姐不问,用眼睛示意项剑。
项剑与女子原是熟识,未问话先讪笑,这个月的房租交了吗?此话一出,自觉无聊。
女子玉手扯下一片银杏叶,答道,交了,三哥将一年的都交上了。
三姐转身,盯视墙角紫薇,那花开得正艳,蜂蝶戏蕊,喜气洋洋。
项剑又问,三哥最近到过你这边吗?
女子闻听,不知何故忽然轻佻起来,答道,当然来过,都是晚上来,早上走。
昨天晚上呢?三姐忽然问道。
来了,不过半夜就走了,女子说。
为什么?
不知道。
那你是否发现三哥最近有不对劲的地方?
腰没以前好了。女子说完像只母鸡一样“咯咯”笑起来。
嗯?
以前是公狗腰,现在有点塌了,还喊累。女子笑得更厉害了,仿佛看到三哥的腰真塌了下来。
还不是因为你!三姐厌恶地说道。
女子不语。三姐转身离开。项剑没走。项剑站在女子面前,说道,三哥失踪了,你今晚不要等他了,晚上我过来。
女子说,我身上不方便,昨晚就是因为这个,三哥才半夜走掉的。
项剑叹息一声。这倒是一个线索。
三姐和项剑来到八字桥。此桥呈八字,撇捺各半。项剑指着桥面上的一块糖渍,上面的蚁群蠕动似蛆虫。三哥的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倒覆着,项剑说。三姐站上桥头,看两边来往的行人,又探下身看桥下的情形。此刻正是早市,农民们将地里的菜蔬用小木船运到城里卖。两三条渔船棹着双桨,一眼可见船舱里的鲜鱼。再往远处,河流渐渐开阔,船只也更多了。除此之外,别无线索。
我们去西荡看看,三姐转身对一边呆看着蚁群的项剑说道。
项剑一惊,去西荡?
西荡是本地凶险之地。小城多水,几十个湖荡遍布城市周围,那些湖荡都有名字,或因形状,或因物产,或因位置,或因历史。大多数湖荡都与城市保持着善意,有些不仅是善意,简直是休戚与共,有着母亲和婴孩的关系。湖荡将自己生产出的鱼虾蟹鳖像乳汁一样喂给城市,把城市养得白白胖胖,吸引五湖四海的人来此定居,城市便繁华起来了。西荡不一样,龙生九子,西荡是“睚眦”,龙身豺首,性刚烈,最是好杀嗜杀好斗。西荡是荒地,茫茫大泽不通陆,隐身其中,外界难以进入,是杀人越货、藏污纳垢的好所在。三哥跟西荡的兄弟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
您真的要去西荡?项剑迟疑着问三姐。
三姐不答。项剑不敢再问,只好到河码头雇船。舟人很多,围拢过来,听说是去西荡,就无人敢应承了。项剑恼怒,最后只有用强,才和一顾姓老者说好,雇船不雇人。
二人当即出发。项剑划桨,三姐坐在船头,一声不吭,只是看水。项剑怕她。三姐本是西荡儿女,随着三哥出了草荡,再没回头。父兄那边鲜有往来。三姐性烈,又有草荡儿女的桀骜不驯,时间一长,三哥渐渐与她疏远。开始还应付,热闹的节日,一起逛逛,买几件女人喜欢的物件,哄哄。后来,干脆连哄也懒了,只是不理,想怎样就怎样。三姐没有办法,也着实闹了几回,弄得大家都无趣。最可恨的是街面上的人,都以为这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在街上传播散布,添油加醋。传回三姐耳中,事情就不是那个事情,事情里面的人物也不是那个人物了。三姐猛然醒悟,不该如此,江湖儿女,是最闹不得的,静水深流,最深的草荡往往有最美的风景,波平浪静,才能尽赏风景。于是,三姐不再管三哥。两人的感情反倒好了。现在三哥忽然失踪,只留下一双鞋,还有黄元上歪歪扭扭的几行小字。起初,她一看这字,就想到西荡的父兄。许是自己与三哥的纠葛传到了草荡之中,草荡和城里消息的传递本就滞慢,传到父兄耳中的消息,估计都是她与三哥如何不好,三哥如何冷落于她。而在她这里,这些都是过去。她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和生活负责,可她也知道,父兄虽然怪她,却也最爱她。
项剑哪知道三姐心思,用力划桨,因为也是水上人家,两片桨在他的手中倒很妥帖,就像鸟儿的两只翅膀,低空飞行。眼见得出了西水关,身后的城市越来越远,渺小得如一座小岛。水面上银波微闪,堆叠起一层层的细浪。后来,风浪渐大,小船开始晃荡。三姐皱眉,起身,迎着风,看向远处的草荡。那里是她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地方。
十年前,此地无风三尺浪。三哥,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他是谁。那日,三姐站在父兄的大船上,头上扎了一根红头绳。他们正在草荡间巡视。大哥哼唱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韵白。她听了只觉滑稽。他们靠草荡吃饭,大部分时间捕鱼,如果有富商或地主的船经过,他们也会顺便发点小财,并不全部劫走,抢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把事情做绝。那天,当时的英俊小伙,后来的三哥一头闯进了草荡的八卦阵,躲在一边的三姐眼看着他的船在草荡间来来回回走不出去。船上的人都说是鬼打墙了。其中的一个细瘦老头,将一张黄元纸燃着,嘴里念念有词,将纸灰撒入水中。并没有作用。父兄等到这条商船上的人转得筋疲力尽,才从隐藏着的芦苇丛中将船驶出,拦在了商船的前头。
商船上的人大惊。父亲抱拳说道,朋友莫慌,知道你们被困,特来营救,带你们走出这百里草荡。
三哥答话,既然如此,谢谢了。请带路。
对面船不动,几个人同时笑出声音。三姐没笑,三姐的眼睛盯着三哥。三哥那时还没有长出虬髯,嘴唇上的青茬胡子规规矩矩。三哥的眼睛也亮,躲在眉毛下面,就像两粒尚未熟透的黑葡萄。三姐的眼睛探到了黑葡萄的边缘,她还想再向里面走一走。她小心翼翼,就像黄昏的阳光爬行在草荡的苇尖。这是个危险的事情,在三哥的眼睛边缘,三姐没有站稳,一个趔趄,整个人就淹到了黑葡萄中。三姐在三哥星子般的眼睛里挣扎了许久。她想不明白。她见过无数的眼睛,没有哪一双眼睛有这样的魔力。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湿润了,她想叹气,她更想哭泣。她羞愧难当。然而,现实中的三姐还是三姐的模样,风不动树不摇的样子。只有一抹很难让人察觉的红晕飞上了两腮。
三哥的眼睛顾不了许多。他认出了领头的老者。认出了也就明白了。他不知道老者的名字,但他知道老者的故事。在小城方圆几百里能留下故事的人并不多,能留下名字就很不错了。老者没有名字,却有故事。老者慈祥。
您想要多少?三哥等对方笑完了问道。
十袋大米。老者说。
三哥商船里有一百袋大米,从常熟运过来。商船的主人在常熟做桐油生意,这些大米是给城里亲戚吃的。
三哥笑了,三哥的笑听起来就像要吟诵什么。笑完了的三哥,一手挟着一袋米,走到船头,准确地将米袋扔到了对面大船的艎板上。如此五个回合,对面船上就有了一座小小的米袋山。再看三哥,仍是面不改色,似乎刚才扔的是几条白鱼。湖荡上的空气就有些凝固,对面船上的人都敛了笑。三姐大哥面沉如水。这是一种挑战,看上去像是示弱,其实却是挑战。他明白,对方软绵绵地挥来了一记硬拳,下面就看他如何回应。但父亲在,他不敢造次。
老者仍是笑,从活水舱里捞出两条铜头鱼。这是回礼。边说边将鱼扔到了商船的船舱中,那里因为少了十袋米而空了一大块。三哥并不看鱼,甚至动都没动,盯视着对面的船,两颗黑葡萄呈现紫色,射出精光,简直可以吃人。
老者并不恼怒,说道,感谢兄弟的米,我舱中的鱼随你挑选,也算交个朋友!
三哥不语。空气凝固,老者略显尴尬。三哥看到呆立着的三姐,目光忽然温柔下来。他轻声说道,我要她。所有人都看了过来。三姐粉面如霞。这明明是欺负人了。大哥暴怒,操起尖头竹篙,就要刺过去,被老者一把拉住。我们走。老者说完,一声长啸。木船扭转头,驶向苇丛深处。三哥正愣神间,一只小划子,不知从何处驶来,船上插着一杆小旗,中间红色,四周黑边,并无文字和图案。跟我走,船上汉子喊起来。小船如水面上的长肢小虫一样,迅速划向远处。
三哥商船跟随小划子驶出了西荡,停到码头,众人动手将剩余的九十袋大米运上岸。老者甩进来的两尾铜头,鱼头均刺入米袋寸许。三哥咋舌,真正动起手,胜负也是难料。
后来的故事,既俗又不俗。动了春心的三姐出荡寻找三哥,终于相见,两情相悦。荡中自然不肯,也挡不住三姐以死相逼,终于认可,却不相往来。
项剑和三姐划至西荡,早有人将她们带入西荡深处的垛上。此垛无名,是他们的大本营。父亲已年逾古稀,头发落尽,留下一捧银白胡须。我来要人,三姐并不客气。父亲不解。三姐又说,三哥不见了,是不是在你们这?父亲摇头。三姐再问,真不在你这?父亲点头,白胡子跟着不停颤抖。三姐不语,转身在人丛中寻大哥。并不见影子。父亲知道她在寻大哥,说道,你大哥到上海办事还没回来。这次来,你多住几天。三姐说,不住了,这就走。说完,并不和众人打招呼。上了船,就要走。父亲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女儿啊,父亲老了,你能不能多住几天?三姐愣了一下,说道,等我找到他,我们一起来。我一个人,不住。父亲无奈,只好目送着二人的小船消失在西荡茫茫的草荡之间。
二人回城,船停在八字桥下。二人弃船上岸,登上桥头。此刻正是黄昏时分,残阳如血,八字桥头的小庙正燃着香,烟雾和夕阳映照得八字桥的一撇一捺越发生动,有了起转腾挪之势。三姐叹一口气,低头跨上石阶,项剑紧跟。三人忽见桥面之上,不知何时卧着一只黑狗。项剑细看大惊,正是先前白面书生脚下的黑狗。三姐不知。却见黑狗所卧之处,倒覆双履,与三姐怀中三哥的旧鞋一模一样。三姐不解,项剑亦不解。沉思良久,三姐吼道,不找了,不找了。话音未落,已将手中的草鞋扔向桥下。鞋子落水的声音并不大,却惊起一对在桥下觅食的黑鸟。这对黑鸟受到惊吓,张开翅膀,黑压压地向三姐飞来。两只鸟飞到桥上并未停留,而是径直飞向天空,就像两只被人操纵着的黑色风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