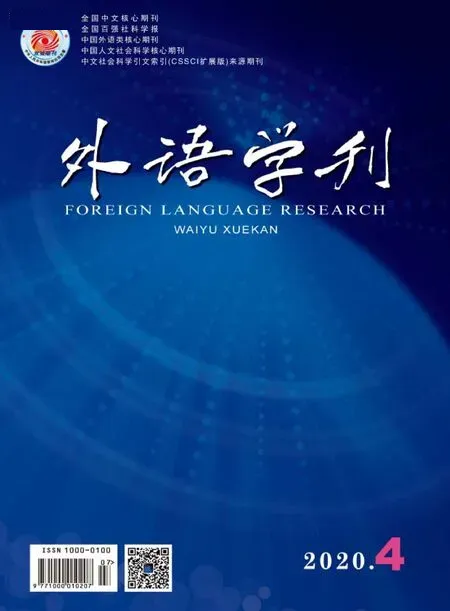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创构 *
——以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胡作友 张丁慧
(合肥工业大学,合肥 230601)
提 要: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研究成果迭出,但翻译对意识形态反作用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翻译可以传播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译者的意识形态及建构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既传播中国古典文论,又向西方世界输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改变目标读者对中国文论形象的认识,推动西方世界研究《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热潮,增进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神秘形象的了解,并在影响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1 引言
早期的翻译研究侧重于翻译质量研究,而忽略文本外的因素,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点由文本内转向文本外的文化因素,其中,意识形态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从20 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意识形态研究冲破原有文本转换的狭窄束缚,让翻译研究从文本外出发,探索翻译活动所进行的文化阐释与意义建构,以拓宽翻译研究的视角。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研究却非常少。王晓元指出,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是互动的关系(王晓元 1999:10);蒋骁华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蒋骁华 2003:24-29);陈浪认为,勒弗菲尔并未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具体运作等提供充分的解释(陈浪 2014:66)。已有研究都提出翻译对意识形态有反作用,但并没有解释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到底是什么。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文心雕龙》英译为例,拟就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展开探讨,希望有助于“龙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 翻译对源语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
翻译可以视为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它以传播为目的,是对以源语文本意识形态(文本生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源语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杨建刚 2010:20)。源语文本的产生过程是原著作者的思维过程,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源语文本的素材选择、人物、句式、语言等都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意识形态隐藏在源语文本中,即使经过翻译的多重过滤,仍然会得到强有力的传播,其中包括原著作者的意识形态、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翻译传播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与风格特征,让目标读者欣赏原著的文化精神风貌。翻译在为目的语输入新思想、新内容、新文体、新语汇的同时,也传播以源语文本为代表的原著作者的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心雕龙》的英译也是如此。
洪堡特曾经说过,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洪堡特 1997:51)。所以,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精髓,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语言是对社会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因此,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语言不仅只是声音和字,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语言对人的影响,也可以视为这种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单纯”或“无辜”的语言,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跟其民族思想、文化、精神息息相关(于坚 谢有顺 2003:38-44)。翻译在向异域传播语言的同时即在传播意识形态,《文心雕龙》的英译充分证明这一点。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章节名称以及人名的翻译,宇文所安基本采用音译的方式,以再现中国文论的原生态风貌。他把《文心雕龙》直接音译为WenxinDiaolong,把“伯牙”译为Bo-ya,把“钟子期”译为Zhong Zi-qi. 对原著中的中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是如此,如把“气”译为Qi,把“阴”译为Yin,把“阳”译为Yang,把“离骚”译为Li Sao等。用汉语拼音直接音译以保留原著的神秘感,让读者体验中国古代文论关键词的别样特色。音译可以最大化地展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传播来自东方异域的魅力。
语言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之一,其结构形式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意识形态是在长期的地理、经济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从句式上来看,《文心雕龙》深受魏晋时期文体——骈体文形式的影响,刘勰在其书中也讨论骈偶产生的原因,指出骈偶产生于造化,是大自然的产物;同时又从哲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偶是由客观事物的二元对应关系转化为人的艺术思维活动,即二元对应思维样式。二元对应思维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不断地总结、内化实践后凝炼出来的一种思维模式,是中国最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是魏晋南北朝以对偶句式为主的骈体文产生的外在与内在的哲学依据(包通法 2014:185)。《文心雕龙》的句式与刘勰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精神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如果与源语文本的句式结构差异较大,这就相当于改变原著严谨的精神格局。宇文所安在翻译的过程中尊重源语文本的句式结构,他担心由于语言结构的改变,可能会无法传达源语文本语言形式中所蕴涵的精神。因此,他宁愿牺牲译文的流畅度,也要与原著保持句式上的一致(宇文所安2003:14)。
①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In setting forth the affections there are lodgings; in setting down language, there are positions. (Owen 1992:261)
②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Juan Chi [210-263] was unrestrained; thus the resonance of his work was aloof and the tone far away. Hsi K’ang [223-262] was bold and heroic; thus his being stirred (hsing) was lofty and the colors (ts’ai) blazing. P’an Yüeh [247-300] was airy and clever, thus the pointedness of his works was in the open, and his rhymes were diffuse.(同上)
宇文所安的翻译保留原著的句式结构,英语中虽然也有parallelism,但像这样工整的对仗句式非常罕见,目标读者读过不免会感到怪异。他的翻译保留异域文化特征,译出中国古典文论的原汁原味,取得陌生化的效果,使目标读者对阅读对象的感觉发生偏移,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使目标读者充分领略来自异域的文化,感受新鲜的思维模式和精神格调。
翻译是一种文化上的双赢活动,而非零和博弈,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互融互惠,互助互利。译作从各个方面对译入语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是能丰富译入语社会的语言,而语言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镇源 2019:91)从翻译中得来的有关中国汉字和句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目标读者获得类似于阅读原著的享受,使其体验中国文化的高深与复杂、博大与包容,同时也可以丰富英语词汇,增强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交流。
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文心雕龙》博采众家之长,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不仅富含文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专业知识,而且富有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文化知识。著名学者黄维樑对《文心雕龙》推崇备至,称之为“情采通变体系”的文论经典,深信它有弘扬中国文化的意义,可为国人参考,甚至可为各国文论界参考(黄维樑 2016:21-33)。翻译这样的经典,传播的不仅是中国文论,还有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宇文所安除了对专业的中国文学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外,还翻译介绍原著中比比皆是的文化典故、历史典故等,向目标读者和译入语社会传播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这可以视为向异域传播中国古典文学意识形态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宇文所安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源语文本进行分析和翻译。每当涉及章节名称等中国文学问题时,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对章节名称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例如,对《体性》篇的翻译,他首先对“体性”一词做出介绍,认为“体性”集中概括中国文学思想的两个关注点:一是作家的内在特性与写作的关系,二是规范类型的地位(Owen 1992:210)。再如,对于《通变》篇的翻译,他也是先介绍“通”和“变”这两个词与文学的关系,说明“通”和“变”的来源,认为它们是《易经》用来描述卦象运作的技术词汇。他提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和“变”已经成为《易经》“哲学”的关键术语。他还指出,“通”和“变”也可以指文学的其他方面,如一个作品的展开、或一个作家的作品集、或一个时期的不同作家之间的差异(同上:264)。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这份热爱也迁移到他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上。翻译《文心雕龙》其实也是翻译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及意识形态。在翻译《隐秀》篇时,为说明“隐”和“秀”的关系,宇文所安不惜笔墨介绍中国的卦象文化,还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做相关介绍。例如,在翻译《知音》篇时,为让目标读者了解“知音”这个典故,他就介绍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这样,读者可以明白“知音”的文化内涵,加深对源文的理解。
源语文本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原著作者的实践性思维过程。原著作者身处特定的社会背景,其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写作方法等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在写作中表现出来。《文心雕龙》是刘勰对世界、对社会、对文化、对写作的认知体验,同时也是其所处时代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反映,体现华夏民族的形象、整体的思维模式和兼容、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隐藏在源语文本中,经过语言的迁移及文化的洗涤,散发在译文的字里行间,在新的异域空间得到传播,从而遂行翻译的使命。宇文所安的翻译不仅传播中国的古典文论,而且向西方世界输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因此会丰富译入语的文学和文化。
3 翻译对译者和读者意识形态的改造
翻译不仅传播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检验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引进既在翻译过程中完成,又在翻译实践中得到检验。读者是最终的消化者和检验者,决定意识形态最终的命运。译入语社会总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和需要对引进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取舍和塑造,对适合自己需要的加以吸收,对不适合自己需要的加以抛弃。翻译首先是译者理解源语文本的过程,然后是形成译作的过程,最后是读者解读译作的过程。由于思维的流动性和跳跃性,在每一个过程中都会伴随着对前过程意识形态的改造,这种改造或是显性的或是隐性的。译者阅读原著的过程伴随着对原著意识形态的改造,而译者创造译本的过程同样伴随着对源语文本和自身意识形态的改造,读者对译作的理解亦是对源文和译文的改造。无论是源文还是译文都是作者和译者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
译者不仅是源文的读者,也是译文在异域生存延续的决定者,即译文的作者。译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对源文进行再创造,在解读过程中会受到源文意识形态的影响,源文本身是作者在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翻译的最初阶段是作者与译者意识形态的交流阶段,译者在阅读源文时,无法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理解源文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会发生一些改变,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由作者意识形态和译者意识形态合而为一的新意识形态,并贯穿于整个翻译活动的始终,最后作用于目标读者。译者作为源文的“读者”、译文的“作者”,在其“创作”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想象和需要对引进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加工和塑造,求同去异,因此其“作品”必然包含一些新的意识形态。
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宇文所安的学者身份决定他的翻译目的,他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前言中写道,他翻译的目的是将源语文本作为西方高校的教学内容,带有明显的学术目的性。他选择翻译《文心雕龙》也正是为了用东方文学的养分去滋养西方文化,从中国优秀文化中吸取精华,以便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加以改造。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采用总述→源文→译文→解说和评述的模式在每一篇译文之前加上总述,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一段源文一段译文,译文后再解说,对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乐黛云 2003:44)。这种翻译阐述模式是西方文学思想长期以来形成的术语定义模式,但这种模式在中国文学思想传统中不存在。宇文所安用西方视角来阐述东方文化理念和文学思想,由此形成一条新的路径,即用中西混杂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这种做法使文本中长期被忽视、被遮蔽的思想,甚至作者试图弥合的某些缝隙,都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其副产品就是杂合作者意识形态与译者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考虑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考虑目标读者的阅读喜好、阅读兴趣以及译入语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调适译者的翻译策略,有的译者不得不迎合译入语读者的意识形态(胡作友 张丁慧 2018:126)。同时,译者作为实践的个体,难以摆脱其所处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译者将源语文本所含有的科学、文化、人文、宗教等引入译语文化,承担跨文化交际的使命,调整源语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成为必然,以适合目标读者的需要。宇文所安作为专家译者,对意识形态内容的调整展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
③ 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Thus theHsi-tz’uchuanclaims that precepts[of theBookofChanges] are far-reaching and its phrases(tz’u)are refined (wen), that its words hit the mark and the events (shih)[implied in it] are hidden.[When Confucius studied theBookofChangeslate in his life,] the leather straps[binding the bamboo slips on which theBookofChangeswas written] broke three times[from the intensity of his study of the work]: truly for our wise Sage this [theBookofChanges] was the abyss in which the black dragon[held the precious pearl beneath its chin].(Owen 1992:196)
从这段译文中明显可以看出,宇文所安采用增译的手法,增加源文所没有的When Confucius studied theBookofChangeslate in his life和bin-ding the bamboo slips on which theBookofChangeswas written的文化背景来解释“韦编三绝”。“韦编三绝”对于目标读者难以理解,它的典故来源于孔子。孔子晚年读《周易》折断了编串竹简的牛皮3次,后来用以表示勤奋学习。为了便于目标读者理解,宇文所安把这段文化背景增加到译文中,这样目标读者就易于明白其中的缘由。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在译文中阐释典故的做法,印证翻译对意识形态的改造。
读者是翻译的消化者和检验者,读者阅读译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获取新信息的过程,也是改造其原有认知的过程,读者的解读过程会直接受到译作意识形态的影响。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英译本主要针对两类目标读者:一是希望理解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学者;一是初学传统中国文学的学生(宇文所安 2003:11),还有一些游离在宇文所安预期读者之外的人,即《文心雕龙》的研究者。
宇文所安预设的目标读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且对中国文论感兴趣的研究者或学习者。目标读者阅读译作后会有自己的收获,这种收获可以视为译作对其意识形态的改造。首先,宇文所安的译作改造目标读者关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以前,也有西方译者翻译过中国文论,但他们往往打着“读者”的旗号,对中国文化典籍随意翻译,导致中国文论的形象在国际文坛上被妖魔化。那时候,西方文化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有些西方国家的译者因心理优势而蔑视落后国家的文化,这就容易导致落后国家的优秀文化在国际文坛遭遇被埋没的命运。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阅读,也值得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宇文所安并没有像一些有偏见的译者那样做,而是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努力贴近源文的内容与结构,保持“异质性”,这体现出他尊重中国文化的立场。北美学者林理彰(R.J. Lynn) 通过仔细分析宇文所安的翻译及译文末尾的独特见解后指出:“宇文所安的英译本符合西方汉学研究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理解的需要,填补中西文论史上的空缺”(Lynn 1994:51)。宇文所安的译作使目标读者不得不花费时间重新审视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文论,改变他们对被传统西方文论妖魔化的中国文论形象的认识。
对那些游离在宇文所安预期读者之外的人,即国内《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宇文所安的翻译实践会改变他们的研究路径。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内容的细致分析,尤其是他的西方视角,给“龙学”研究者以极大的启示。阅读宇文所安的译作,他们可以在西方文论的语境中找到新的方法和角度,可以借他山之石来重新观察和阐释久已熟知的中国古典文论,使他们感悟、反思、阐发,从而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国内“龙学”研究者来说,他们可以跳出习以为常的“龙学”研究模式,找到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中西文论互动中通过“双向阐释”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途径(乐黛云 2003:44)。
4 翻译对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
译者不是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翻译丰富译入语文化。Barnstone指出,翻译是改变文学观的工具(Barnstone 1993:123)。既然翻译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各种因素交错作用,共同影响翻译的过程,因此最终形成的译本必然携带文化的因子和社会的印迹。翻译在受到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又反作用于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强化或者改造其已有的意识形态,或者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如严复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译介,有助于开启中国的民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和实践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使译作变成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对目标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译作流入译入语社会后,目标读者对译本进行阅读解构,经过译入语社会的文化改造,最终会影响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蕴含中国文化的精髓。这部作品阐述中国古代文人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学精神。《文心雕龙》日益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于它蕴含的美学道德能够慰藉现代人日益干枯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比当代艺术更能感发人的心灵。宇文所安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很大的原因就是其蕴含的美感和丰富的启示意义,他的翻译在某些方面可以影响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
首先,宇文所安的翻译能推动国内外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文论研究从属于文学系统,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文论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吸取他国精华改造本国文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宇文所安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翻译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文论。那时,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著作很少,他所任教的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还没有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但到了21世纪初,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已有不少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欣欣向荣,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宇文所安。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文心雕龙》,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研究它的英语论文也逐渐增多。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心雕龙》著作书目提要只需一页的篇幅,但现在,关于《文心雕龙》的著作一份最基本的书目提要都会占用不少的篇幅(宇文所安 2003:1)。
其次,宇文所安的翻译构建一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国内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从“五四”时期开始逐步成型,当时,作为研究视角的“观念史”成为该领域的明确特征。“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指从文本中抽取观念,考察一种观念被哪位批评家所支持,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以及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观念怎样发生变化(同上)。至今为止,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成熟,吸引众多知名批评家进行专门研究,出现大批学术成果。作为固定研究视角的“观念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范本,但这种方法忽视观念在具体文本中的运作,使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体系僵化。宇文所安主张以文本为中心阐释中国的文学思想,即他不仅希望知道“中国古人的思想是什么”,而且希望展现文本的最初面目(同上)。这种方法就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侧重于文本的生成环境、构成因素的考察,并在仔细研读原文的基础上,从词、词组、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回到具体的语境中去阐释原文的意义,力求回到文本最初的模样,而不愿借用前人的相关理论去研究中国文论。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更是小心谨慎,除去译文部分,他花费大量笔墨对文本进行分析探究,力求还原文本生成的面目,使读者能通过他的研究方法体验到中国文论的最初面貌。他的解说形式会根据不同文本的需要而有所变化,根据每个文本不同的特性采用适当的解说论证形式,而不是以统一的论述模式去阐述。这样,读者可以了解刘勰与西方所使用的文学范畴的不同,改变对中国文论固有的研究视角,为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做出示范。宇文所安的翻译扩充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系统产生影响。
再次,宇文所安的翻译为西方世界读者构建中国思想文化的神秘形象。《文心雕龙》作为充满哲理的优秀文化典籍,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髓,它内涵的中国文学思想是我们民族文化思想的源泉。在西方读者眼中,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神秘的东方异域风情。为满足目标读者学习他国文学和文化的心理,宇文所安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构建出神秘的东方哲思文化。他认为,一种民族的文学思想传统由一套“术语”组成,这些术语随历史的不断变革而改变,含义也随之扩大,它们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影响力。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执着于术语的定义问题,学者们希望把词意固定下来以便掌控,而中国文学对于定义的追寻没有那么严谨认真(同上:3)。中国文论术语在具体的文本中含义不尽相同,可谓博大精深,不像英文术语有确切的概念、定义,中国文论术语大多具有诗性的内在特质和感性的外在式样。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论对于不谙中文的国外读者就像是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宇文所安尊重这样神秘的中国文化,对《文心雕龙》重要术语的翻译,他采取直译加音译的方法。例如,“气”是《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为了不破坏这个词的丰富内涵,宇文所安将它音译为Qi,以维护其内在的统一性,他还在全文最后的术语集释中专门解释说明“气”。文学中的“气”是指吟诵发声时所排出的气体,指的是“气”的生理学功能。在中国古典哲学里,“气”指物质中那种纯而又纯的、活动的元素,它出现在由“理”构成的世界里。在批评作品中,“气”有时被说成一个整体性范畴(同上:654)。在西方文学的术语中,不可能找到与“气”完全对等的术语。英文读者根本弄不清楚“气”在文本中的具体含义,只有靠与特定文本特定层面的重复性联系才能建构其意义,所以重要术语的直译加音译能保存源语文本的神秘性。
最后,宇文所安的翻译有助于构建中国文论的话语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有越来越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但仍有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认识不全面或者不正确,因此,中国需要构建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话语”的本意是指交谈、谈话等,最初是属于语言学层面的术语。后经西方学者的阐释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关系。现在“话语”演变为与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相交织的术语,根据意识形态的定义,仍从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中国文论的外译日益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而中国文化古籍是华夏文明的积淀,蕴含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思想,承载深厚的中国文化特色。为了使西方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这个正在苏醒的文明古国,宇文所安选择他认为的《文心雕龙》的精华内容进行翻译,同时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地保存文化差异,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这样,在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中构建中国文化话语,使西方世界读者对自身文化和中国文化能有更清醒的认知。
5 结束语
意识形态与翻译是互为影响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并制约翻译实践,翻译实践对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有些学者夸大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控制力,却忽略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制力。意识形态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并非单向的、绝对的,而是双向的、相对的。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集儒、释、道于一身的中国古典文论专著,既探讨专业的文论知识,又富含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文化,它的翻译与意识形态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英译是中西两种意识形态的剧烈碰撞和交锋。中国文论所蕴含的文学养分和中国独特的思维认知在译入语社会证明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悄悄地改变译入语社会。
翻译传播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译者的意识形态,影响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的翻译能传播中国古典文论,向西方世界输入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改变目标读者对中国文论形象的认识,推动西方世界研究《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热潮,提高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神秘形象的认识,并在影响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