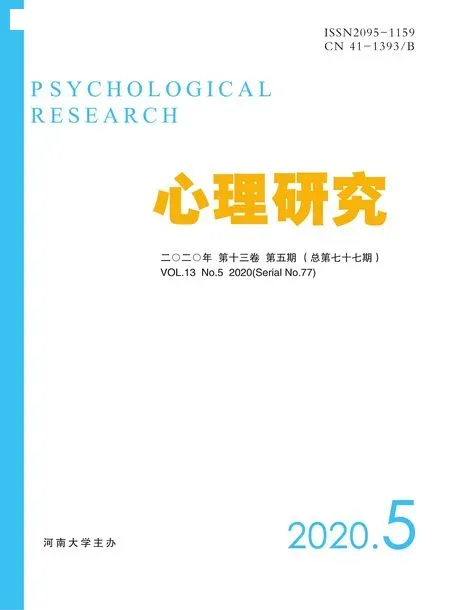善意即是有益?善意性别偏见之析辩
朱文婷 曹佃省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扬州225002)
性别偏见(sexism)是基于性别差异的先入为主的不公正态度,是对特定性别及其成员的消极态度和言行,是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言行举止以及个性特征无视客观事实及个体差异的笼统归纳(Swim,Aikin,Hall,&Hunter,1995)。研究指出,针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可能包含敌意性别偏见(hostile sexism,HS)和善意性别偏见(benevolent sexism,BS)两类。前者往往通过贬损异性来证明自身的优势,后者则往往将异性设想成为需要保护或照顾的对象来显示自身的优越(Glick,Lameiras,Fiske,et al.,2004)。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两性平等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传统的敌意性别偏见通常表现为对女性公然的负面态度,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认为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否认女性的价值,基于社会刻板印象将女性置于不利的地位,使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Glick&Fiske,2002),通常表现为对女性无能的蔑视以及对女性“离经叛道”言行举止的打击和怨恨(Kuchynka,Salomon,Bosson,et al.,2018),致使女性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压力(Salomon,Burgess,&Bosson,2015)。而善意性别偏见则认为女性虽不像男性那样能干,但她们有亲和力、仁慈善良并且温柔可爱,需要男性的保护和珍视,如此“善意”的态度往往受到部分女性的拥护(Connelly&Heesacker,2012)。如今,赤裸露骨的敌意偏见言行渐趋减少,而以温和、间接等“善意”形式的性别偏见仍在继续。但就其本质而言,与传统的敌意偏见一样,善意性别偏见仍在维系着两性间的不平等,仍在影响着女性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1 善意性别偏见之本质
敌意性别偏见是“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主要指向违背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例如女权主义者和职业女性等),对其给予否定的评价,通过贬低女性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体系,是一种消极的概念。
善意性别偏见往往指向那些遵循传统性别角色(如母亲和妻子等)的女性,并对其给予某种“肯定”“积极”的评价。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以男性的主导地位(男性主导、女性依附)及传统的刻板印象(男强女弱、男尊女卑)为基础,仍与敌意性别偏见拥有同样的观点,即女性应该被限制、被紧缩在偏见所设定的“柔弱”角色中(Glick&Fiske,1996)。
善意性别偏见作为一种家长制偏见,由内群偏见与群体间依赖结合发展而来。刻板印象的观点认为“组内成员必须各就其位”(Gill,2004),女性因其生育繁衍的能力而被禁锢在家庭内,男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占有大部分的财力与资源。由此,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不断被巩固和强化,女性渐渐陷入“贤妻良母”形象中,成为男性的从属。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不太可能拱手让出自己的优势地位,亦不太可能主动修正 歧 视 与 偏 见 (Wakslak,Jost,Tyler,&Chen,2007)。由此,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性别角色更加被固化,男女地位愈加分化,男性更在此分化中获益。
2 善意性别偏见之危害
与敌意性别偏见直接外显的消极影响不同,善意性别偏见的影响更为复杂。尽管善意性别偏见表面上可能为人所接受,但其“善意”是有条件的,是对女性的差别对待,本质上仍在延续着社会结构的不平等,若不揭开其伪善面纱,善意性别偏见之危害必将会更为久远(Connelly&Heesacker,2012)。
2.1 影响身心健康
善意性别偏见与女性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善意性别偏见看似是对女性的照顾与体贴,但实质是在暗示女性能力不如男性,需要仰赖男性保护。善意性别偏见似乎给女性带来温暖和慰藉,但这种愉悦和满足是粗浅和短暂的。遭受善意性别偏见的女性更易受到能力不足的暗示,致使自我能力贬低,自我效能下降,自尊水平受损,负性情绪体验更为频繁(Jost&Hunyady,2005)。女性可能在遭受善意偏见后,依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规范行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貌上,以获取男性的认可,由此,自我客体化状况明显(Calogero,2011)。过强的客体内化压力甚至导致女性产生身体羞耻感、滥用药物(Carr&Szymanski,2011)、损害道德认知及人际交往中的表达欲和行动力(郑楠,2017)。长时间遭受偏见影响者,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能够获得男性赞许的领域,迫使女性按照世俗标准塑造身形,失去自我认同,危害身心健康。
2.2 影响职业生涯
善意性别偏见强调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作用。职场中,人们对符合或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持有善意或敌意性别偏见,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女性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Jones,Stewart,King,et al.,2014)。女性在求职阶段,性别就成了迈向职场的壁垒。研究显示,在求职过程中,男性大学生得到的面试机会多于女性,即使女性拥有优秀的成绩和出色的表现也不能打破这种偏见和歧视(葛玉好,邓佳盟,张帅,2018)。机构借由性别偏见合法化的方式,将女性排斥在“男性职位”之外,仅允许低权力阶层“女性职位”对女性的雇佣,将女性限制在特定岗位之中(乔志宏,郑静璐,宋慧婷,蒋盈,2014),使原本缺乏就业职位的女性的就业途径更受局限(Hideg&Ferris,2016)。职场中,持善意性别偏见者认为女性是善于合作但同时又是需要帮助的,面对类似偏见时,女性往往会怀疑自身的业务能力,而无法专注于业务素养的提高(Dardenne,Dumont,&Bollier,2007)。即便女性身居高位,善意性别偏见仍然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影响。例如,若女性领导表现出“严厉严肃、雷厉风行”等反传统形象,则易引起高敌意性别偏见者的反感,致使其内隐追随力下降,由此,女性的领导风格又被禁锢在单一模式之中(蔡汶珈,2019)。国内工程、技术和数学等学科领域内的女性,三分之二者认为在工作评估中受到了性别偏见,很多女性亦将“女性难以在科学领域成功”“学术属于男性”等观点内化,由此,难以接触到核心层次的工作,其潜能的发挥受到压制,职场中的巅峰成长遇到障碍,多样化发展的路径受阻。
2.3 影响个人生活
亲密关系中,受善意性别偏见影响的女性,觉得持善意偏见的男性更具魅力,对其持有更多的信任,更认同依靠男性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观点,更认为自己的成功会对丈夫造成威胁(Exposito,Herrera,Moya,&Glick,2010),在与伴侣的日常互动中,更多地付出精力和情感,充当传统的照顾者角色(Hammond&Overall,2015)。高善意性别偏见内化者,由于倾向于低估男性婚后不忠和出轨可能性,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婚后反而更容易受到伤害(李玟,黄喜珊,滕飞,2019)。
生活中,人们会把一些称谓、职务等默认为是男性所有,当涉及女性时,则会加以贬义标签。如,人们对男性婚前性行为较为宽容,倘若婚前性行为发生在女性身上,则被认为其婚后更易出轨,被加注放荡不贞等负面标签(Sakalli-Ugurlu&Glick,2003);人们对不做家务的男性较为宽容,而对少做家务的女性加注懒散、不负责任等标签(Silvan-ferrero&Antonio,2007);遇到交通事故尤其有女性卷入的交通事故时,人们通常不问是非曲直,直接给女性司机加注马路杀手的标签,使女性承受额外的压力(李莲莲,2016)。此外,在诸多案件中,对女性当事人的性别偏见,影响着法官的审判认知,致使女性该有的公正审判权在性侵犯、离婚财产分割、监护权争夺及家庭暴力等诸多案件中受到侵犯,阻碍了性别平等权的司法实现(杨云霞,许岚,2012)。由此,善意性别偏见将女性禁锢在“温良恭俭让”的传统角色之中,跳脱出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易受到恶意对待。
3 善意性别偏见之成因
3.1 教育教学领域角色选摘的比例失衡
教科书中性别偏见备受关注,主要体现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角色品质刻板等方面。首先,教科书中男性角色的出现频次和配图比例高于女性,男性担当主角的人物数量远大于女性(高兵,红梅,李雪瑶,2015)。在文科类教材中,男女性别角色比例为3∶1(陈应心,2009),男性在课本插图中的角色形象远远多于女性(邱明月,2018)。其次,教科书中男性的角色品质往往优于女性,男性伟大、坚毅、勇敢等性格品质被突出强调,而女性往往被划入愚昧、小气、贪婪等负面的性格范畴,且多为男性的烘托(苏勇,2014)。另外,教科书中男女职业分工刻板印象突出,男性普遍活跃于社会公共领域中,而女性却多以家庭生活的形象出现(葛逻夷,2018);男性拥有科学家、英雄人物、工程师、清洁工等多样化的职业形象,女性多为教师或护士等固定角色(乔晖,2008)。男女形象塑造的两极化及呈现比例的严重失衡,束缚着学生对女性角色的多元认知,影响着性别身份的塑造,致使其角色印象狭隘刻板,影响自身特别是女性将来的多元发展。
3.2 新闻媒体领域性别关注的狭隘固化
大众媒体中的性别偏见也十分突出。大众传媒依旧遵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将女性纳入家庭等私人领域,多与时尚、美妆和生育有关,而男性则更多地出现在公共领域(林沐,2018),即使男性在家庭中,也较少从事与家务相关的活动(刘伯红,卜卫,陈新欣,1997)。传媒中更多强调男性气质是走向成功的核心特质,而女性气质则只适于家庭琐事中(李海燕,2017)。在报道家庭暴力时,媒体将焦点偏重于女性“软弱无能”与“纵容忍让”,而不去探讨男性的过失问题(王晓彤,2018);在性骚扰、性犯罪报道时,反复探讨女性特征而不去关注事件本身(刘壹昭,2017),且报道中女性的生理特征被反复强调(董天策,罗小玲,2011),女性身材容貌被放大观赏(汪振军,2007)。如此的渲染和传播,如此偏颇的宣传和报道,潜移默化地深化着大众传统的性别观念与角色印象,致使女性不断被框定在特定的负面形象之中,亦使性别偏见的壁垒更难被打破。
3.3 善意性别偏见跨文化的一致性
善意性别偏见虽然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但其本质并未改变。跨文化研究显示,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善意性别偏见都影响着个体的择偶行为。中国的男性与女性都倾向于寻找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伴侣,但侧重点不同——女性想要找一个供养者、保护者,男性则想要寻找一个支持其事业发展的贤妻良母(Chen,Fiske,Susan,&Lee,2009);美国的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寻找一个体贴的伴侣,在此基础上,男性更关注伴侣的魅力与容貌(Lee,Fiske,Glick,&Chen,2010)。社会工作中的女性常因备受家庭的束缚而分身乏力,使其难以调和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而身心疲惫。无论哪个领域,无论哪种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宣传始终难以摆脱刻板化,强调其外貌而忽视其能力,强调其在家庭中的角色而轻视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以隐性的方式鼓励女性固守家庭。在此潜移默化的观念影响下,女性不得不按照社会主流规范的预期,保持单一的角色形象,放弃其在公共领域的发展。
4 善意性别偏见研究之展望
目前的研究大都以女性的视角为切入口,探讨了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造成的各种影响,显示善意性别偏见存在于教育、新闻媒体等各个领域,对女性的身心健康、职业生涯、自我评价、个人生活、学术发展以及合法权益等方面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今后研究中,要注意以下方面。
要拓展善意性别偏见对男性危害的研究视角。学界普遍认为,善意与敌意性别偏见的本质并无不同,对女性而言弊大于利。性别偏见并非只危害女性,男性同样也会在此偏见中反受其害。若将女性限制在家庭中,让男性活跃于职场上,这种角色分工在阻碍女性发展的同时,是否也会为男性带来困扰和压力,类似从男性角度的很多问题值得深化研究。
要加强防范性别偏见形成的教育。少年儿童身心处于发展巨变之中,若缺乏正确的引导,加之网络传媒的影响,错误的性别观念很容易内化于思想深处,将两性不平等的观念延续下去,阻碍他们尤其是女性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及成长的方向。目前国内教育系统中尚没有规范的性别教育的课程体系(姜蒙蒙,2015),性别教育内容如何设置,教育如何实施,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要重视教师及家长性别观念的教育。学校中,教师的性别观念直接影响其教学行为,对学生性别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家庭内,母亲的善意性别偏见水平正向预测青春期女儿的善意性别偏见水平。因此,要注意对教师及家长科学性别意识的培养,注意在教师职业培训、家校互动沟通中增加性别意识的相关内容。
要注重女性对性别偏见的主动应对。女性身份与女性角色处于学校、家庭、社会的塑造中,各影响因素与女性个性特征、认知水平、社会支持等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协同影响着社会规范的内化程度。由此,需要增强对女性多元发展的示范与教育,丰富女性对多元发展的认知,增强女性对自身潜能的认识与挖掘,教会女性对善意或歧视性别偏见的辨别与应对,发挥女性身处外在影响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发现自我潜能,做到自我实现。
要重视善意性别偏见内涵的科学界定与本土化研究。有研究以“男主内,女主外”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考察了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变化,结果表现出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许琪,2016),预示着善意性别偏见所固化的女性传统形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更好的接受度。当下,如何对善意性别偏见的内涵做出科学界定,如何研发高信效度的测评工具等问题,都需要本土化纵向研究,以深化人们对善意性别偏见本质的认识。
性别刻板与性别偏见是对女性潜能与角色的固化,是女性向上生长的天花板,前进的绊脚石。善意性别偏见以其温和的方式维持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是一种父权意识的延续。善意性别偏见是“天鹅绒下的铁手”,是“裹着蜜糖的砒霜”,诱使女性成为温水里的青蛙,阻碍其发展,影响其生涯(张珊珊,谢晋宇,吴敏,2019)。增强对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是对“男主外,女主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妻子支持男性事业是天职”等性别刻板印象的回击。女性不应该被定义,帮助女性正确认识自我价值,唤醒女性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保障女性享受合法权益,促进两性潜能的最大发挥与实现,仍需要各界的关注和努力。
- 心理研究的其它文章
- 郝耀东:生平与学术贡献
- 人格心理学教材的中国化及教学反思